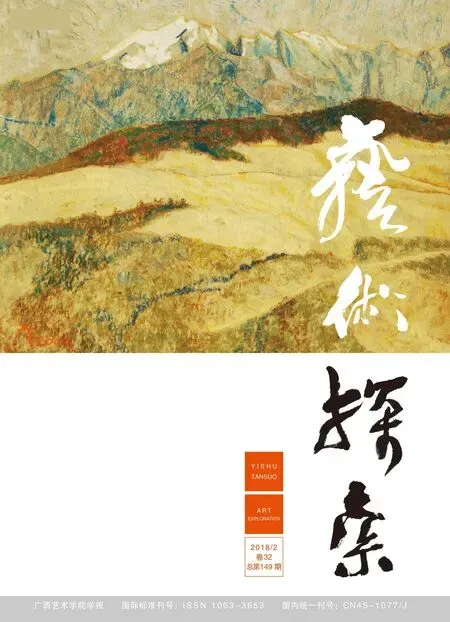論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與情節劇的旁觀者
羅成雁
(云南行政學院 文化與科技教研部,云南 昆明 650111)
當今的電影、電視、游戲充滿了披著寫實主義外衣的情節劇因素,如單一的情感、模式化的情節編制、“完美”的道德幻象、轟動的效果等,影響著觀眾的觀看方式,讓觀眾認同情節劇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實,這一問題早在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與情節劇的相互作用中就已經形成。因此,探究其成因,對反思當代文藝和傳播媒介中存在的情節劇問題,是很有必要的。
19世紀的寫實主義戲劇吸收了情節劇情節編制的手法,從而也和情節劇一樣,塑造了被編制在激烈的沖突、懸念、情感之中,追問著“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并認同“完美”道德主角的旁觀者——觀眾。觀眾在計算好的鼓掌點中,喪失了參與、介入、批判戲劇事件的能力。因此,本文從分析有機體情節的編制入手,梳理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與情節劇的相互影響,并探討有機體情節是如何編制旁觀者,旁觀者如何喪失參與和批判能力等問題。
一、19世紀寫實主義戲劇對情節劇的吸收
情節劇的英文單詞為Melodrama,原為“樂劇”之意。到了19世紀,其融入了浪漫主義的激情和感傷,吸納了傳統戲劇情節編制的成果,臺詞常充斥大量的道德說教,成為當時歐洲最為流行的戲劇形式。情節劇是20世紀頭十年中劇院流行的戲劇形式,后來也成為頗受歡迎的一種影視形式。然而,正是由于具有面向大眾、情節模式化、追求轟動效果、人物性格單一等特性,情節劇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成為了一個貶義詞,“松散地用來表示任何機械地制作的娛樂,這種娛樂靠的是庸俗華麗的布景、不可信的動機、虛夸的聳人聽聞和虛假的悲愴來取悅觀眾”[1]9。事實上,情節劇作為一種“靠情節和情境取勝”的戲劇,既與傳統戲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深深地影響著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的寫實主義戲劇。
首先,對于19世紀末的寫實主義戲劇思潮來說,情節劇既是其發展的基礎,也是其批評的對象。左拉對薩爾都、斯克里布、奧吉埃和小仲馬戲劇的批評和溯源,表明了19世紀情節劇與寫實主義戲劇之間復雜的關系。他指出,“一經以劇情代替了敘述,一經讓驚險經歷在人物身上取得重要地位,他們就滑向錯綜復雜的情節,滑向以一線來牽動的木偶戲,滑向一系列連續的突變以及出人意料的結局花招上去”,“夸大了劇情這個新原則”,使人物成為一個“裝配得很好的物件”,將觀眾“推向極端虛假的情感”。[2]426但是,他認為,這些戲劇對自然主義戲劇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倘若說他頻頻地從真實旁邊走過,他依然是在以其獨特的方式為自然主義事業服務的。”[2]427它們的貢獻就在于“將日常生活盡可能準確地作物質的再現,將它精確地搬上舞臺”[2]427。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主張以“細節的真實”再現現實生活,如追求劇場布景的真實,突出環境的重要性,再現處于社會環境中的人物,這同樣受到了情節劇的影響,
第二,在將日常生活搬上舞臺的同時,19世紀的情節劇實際上已經拓展了戲劇的題材,使戲劇開始談論一些原本不可談論的社會問題。它力圖使那些被社會劃定為不可見的人、事物和問題,在戲劇、劇場中可見,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抗議性。左拉說,小仲馬是第一個敢于談論那些虛偽的社會道德禁止談論的問題(如少女的性欲和男人的獸性)的戲劇家。情節劇題材廣泛,有關于戰爭的,有關于現實犯罪的,“對大都市的貧困也作了寫實主義的全景式的描寫”[1]62。它甚至取材于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反映了各階層生活、下層民眾的態度、技術發明的沖擊等問題。只是,小仲馬又把自己“弄成了上帝在塵世的代理人”[2]428,制定法則、對觀眾進行說教、怪誕的想象妨礙了他對現實的觀察,戲劇中的“環境也是虛假而艱難的”[2]428,顯得做作而不真實。奧吉埃的戲劇陷入了情節劇的陳詞濫調之中,但他能對生活進行“準確的觀察”,將真實生活搬到舞臺上,“用樸實的確切的詞語描繪我們的社會”,使戲劇的人物和環境更富有人情味。[2]431以上都是19世紀中后期的情節劇對寫實主義戲劇的潛在影響。
易卜生曾描述過19世紀末的戲劇界對情節劇的矛盾態度。他指出:“斯克里布的劇仍然像從前那樣引人入勝。……可是,最后一場的帷幕一落下來,斯克里布立時便遭到嚴厲的譴責。”[3]202人們在譴責中,已將抽象的、富有詩意的因素置于戲劇性之上了。而實際上,沖突激烈的情節仍有存在的理由。正如易卜生有13年的情節劇劇場實踐經驗一樣,對情節劇因素以及舊有舞臺慣例的運用已然成為寫實主義戲劇家創作中的一種“無意識”。
第三,這種創作的主觀“無意識”和客觀的戲劇傳承,使得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創作需要借用情節劇的技巧。盧卡契指出,易卜生一生將斯克里布的技巧現代化了,雖然他的戲劇在題材、世界觀、對人的觀察等方面都與情節劇不同,但“他只是使老的技巧(即情節劇技巧,筆者注)更為精煉細膩,他一再努力使它變為不透明的,給它罩上自然主義的外衣,掩蓋起來,但從本質上他沒有對這種技巧有什么改變”[3]263。他對情節劇技巧的運用,表現在編排偶然事件、大場面、糾葛的線索及強力推動情節發展的人物等方面。這給易卜生的戲劇帶來了損害,比如主題與情節的不和諧、象征變成了寓言、對白的機械性等等。但是,情節劇的編排技巧也是易卜生在處理資產階級淺薄無聊的生活時所必需的。威廉斯也指出,情節劇因素是易卜生戲劇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其《青年同盟》《社會支柱》等作品從反映現實生活和編排情節兩方面來說,“都是情節劇,并且整體上是諷刺劇”[4]44。
在某種程度上,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將情節劇的技巧、結構掩蓋并自然化,或者說通過寫實主義來完善,且往往通過嵌入情節劇因素而獲得成功。蕭伯納不遺余力地批評情節劇的劇場慣例,卻又推崇法國情節劇作家百里歐的劇作。誤會、聳人聽聞的犯罪事件、糾葛的人物關系、機智巧妙的轉折、推動情節發展的偶然事件,以足夠逗趣或激動感人的方式說話和行動的人物,都是情節劇的常見因素。威廉斯分析蕭伯納的劇本發現,這位在英國扛起寫實主義大旗的戲劇家,其實是個情節劇作家。他的戲劇人物是抽象觀念的化身,沖突是兩個空洞的觀念的沖突,角色的情感表達方式是浪漫主義的,慷慨激昂的,但卻是模式化的,觀眾應如何去感知和反應也已經在評論式的舞臺提示中精確的告知。“蕭伯納的戲劇淪陷為情節劇了。”[4]290
綜上所述,寫實主義戲劇從產生到發展,都與情節劇密切相關。一方面,寫實主義戲劇受到了情節劇舊有慣例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借用了情節劇的編排技巧。寫實主義戲劇“細節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追求,就需要借助高度凝練而充滿沖突的情節來實現。要體現環境對人的決定作用,人和環境之間的沖突,要突出場景“細節真實”的重要性,就要通過情節編排來呈現往昔糾葛和復雜的人物關系,以及塑造推動情節發展的模式化人物,更何況,戲劇還要吸引在場觀眾。
二、“有機體情節”對寫實主義戲劇旁觀者的編制
這些情節劇因素在寫實主義戲劇觀演關系的建構過程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對其觀演關系的建構模式有何影響,只有厘清這些問題,才能抓住那些披著寫實主義外衣將情節劇技巧自然化的戲劇,在建構觀演關系上所存在的問題,才能看清其對觀眾觀看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影響。
19世紀末情節劇通過編制精巧的情節,編排有機事件,設置懸念,來吸引并保持觀眾的注意力和興趣,引導著觀眾的情感反應。其優劣勢均在于情節編制及對觀演關系的建構。情節劇的有機體情節編制存在很多問題,如具有封閉性,喜歡制造突轉,區分了觀看和行動的等級,排斥異質因素等等,在客觀上把觀眾編制成了“旁觀者”。這種對旁觀者的編制在情節劇與寫實主義戲劇的相互影響中尤為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有機體情節對旁觀者的編制
19世紀的情節劇在編排有機體情節過程中,非常注重對觀演關系的建構。成書于20世紀初的《劇作法》(阿契爾,1912年)、《戲劇技巧》(貝克,1919年),對寫實主義之后的情節劇編制技巧進行了總結。如同寫實主義戲劇既批評情節劇又借用情節劇的技巧一樣,這兩本著作同樣既批評庸俗的情節劇,又以優秀的情節劇為例。在此,本文通過梳理二者的情節編制理念,來探討19世紀末20世紀初情節劇的性質及其對觀演關系的組織。
阿契爾和貝克都強調了情節編制對組織觀演關系的重要意義。動作和情節是戲劇的核心,關鍵就在于其對觀演關系的組織。這兩本著作在開篇都極力說明,戲劇因劇場觀眾這一因素而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戲劇情節編制的目標就在于對劇場觀眾的組織。貝克說他所探討的是“經過觀眾考驗或者是為了經受這種考驗而寫出的戲劇”[5]5,而不是案頭劇,對動作—情節的重視,目的在于贏得觀眾的注意,維持觀眾的觀看興趣。阿契爾覺得案頭劇就是笨拙而莫名其妙的東西,“學習如何用好的戲劇形式去敘述一個故事,如何把它發展和安排得最抓住并保持劇場觀眾的興趣”[6]9。
在情節編制上,他們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情節編制—行動哲學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表面上看,亞里士多德《詩學》似乎是一本關于研究悲劇創制技藝的著作,實際上他探討的卻是行動哲學。在他看來,情節編制并非是對觀演關系的組織。亞里士多德將悲劇定義為對“一個嚴肅的、完整的、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依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對事件進行組合的情節就是悲劇的核心,這源于情節就是對行動的摹仿。而對于人來說,行動又是至關重要的,人生活的幸與不幸、成功與失敗均取決于人的行動。[7]64因此,《詩學》探討的是人的行動,是對行動所做的實驗和反思,就如編制情節的“詩學”(Poiesis)也正是行動一樣。“亞里士多德轉向戲劇,源于戲劇在比敘事詩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做和看待做——也即行動和反思——之間的區別”[8]8,他探討行動就像在探討詩。
情節編制的靈魂是突轉與發現,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是指反思和重新認識。“突轉讓觀眾反思一個最初看起來不可能之行動的必然性。”[8]11發現是從不知到知的轉變,是一種自知之明,是認識的開始,而不是情感的緊張。于是,由此引發的情節編制的效果——觀眾的憐憫與恐懼,并非道德上的升華或者優越感的出現,而是由此對自己或親近之人的一種反思,反思情節中的行動,反思道德上的義憤。“詩使我們在行動整全之前就能將其作為整體來體驗。”[8]6因此,亞里士多德才會說,悲劇即使不上演,也不會失去它的潛力,即情節的編排,并不是結構觀演關系。
阿契爾和貝克卻認為,情節的關鍵是對觀演關系的組織,即吸引觀眾的注意力,維持并加強興趣和情感。“動作的重要性正在于,動作是激起觀眾感情的最迅速的手段。”[5]25在情節劇中,情節成了一種控制觀眾情感的手段。貝克說:“從戲劇方面來講,情節是劇作者把故事編排起來以使他在演出時能獲得他所期望的情感反應。為了創造和維持興趣,劇作者給故事以他認為是巧妙的、簡單的或復雜的結構,并且從中分辨出懸念、吃驚和高潮諸要素。”[5]64如此一來,他們將那種對人類行動進行思考的情節編制,轉化成了演出中對觀眾的組織;將突轉和發現所帶來的觀眾的重新認識和反思,轉化成了對觀眾情緒的調控。
情節編制成了一種影響觀眾觀看方式和情感反應的手段。阿契爾依據首、身、尾而認為戲劇最好的形式是三幕劇,這樣才符合人的體力和注意力變化規律,滿足觀眾的情感。貝克也相信,作家在首、身、尾一個接一個的場面序列中“使其持續不斷地增加興趣,就是說,使其具有曲折變化的運動”[5]95。
整個戲劇的情節編制也是對觀眾情感的預估,是對“緊張”的均衡分配和計算。斯特林堡說,1860年代到1870年代,能為皇家劇場所接受的“戲劇必須有完美的五幕,每一幕大概有24頁的長度,總共是5乘以24等于120頁”,要分為開端、中段和結尾,而每一幕必須包含一個掌聲點,“一個長時間的情感爆發、一個懲罰或者揭露幾乎是必須的”。[9]126這指出情節劇創作的一個重要傾向,即編排“被計算過的效果、鼓掌的點”。這既是對劇作家的限制,也是對觀眾反應的調控。威廉斯也說,在蕭伯納的情節劇中,“我們已經被精確地告知如何去感受和反應”[4]281,這不僅僅是通過舞臺提示,也通過他的情節編制模式。
(二)懸念對旁觀者的編制
情節劇對旁觀者的編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通過對情節的編制設置懸念,制造緊張感。阿契爾說,戲劇最大的秘密就在于“緊張”,“而劇作家的技巧的主要內容就是在于產生、維持、懸置、加劇和解除緊張”,通過演員呈現的緊張場面,“最終不過是一種促使觀眾精神緊張的一種方法”。[6]164無獨有偶,貝克認為情節設置,懸念是關鍵,目的是使觀眾迫切地追求“緊張”的解決。易卜生《玩偶之家》最后一幕在娜拉和海爾茂爭吵之前插入阮克醫生的上場,《羅斯莫莊》中布倫德爾的兩次出現也正屬于此。因此,多條情節線索的交織也是保持懸念的重要手段。
這種情節緊張感的設計,使觀眾在懸念之中,獲得一種“前進”的感覺和向前追問的興趣,從而被裹挾到人物的行動之中,專注于“結”與“解”的線性發展,放棄了對行動的反思。“不要打斷觀眾的興趣,或者使它彷徨無著,而是要在下一幕里給它安排一個可以清楚預見的東西作為它趨向的鵠,或者設下一個謎,使觀眾迫不及待地想求得它的解答。”[6]151因此,平內羅的戲劇“永遠有某種‘事變’正在醞釀著,使我們急切地期待著它的發展”的情節編制,是一種良好的模式。處在懸念之中,觀眾的興趣便令迫切奔向終點。[5]215因此,不管他們多么強調人物性格的刻畫和人物對情境的制造,首要的問題都是“接下來會發生什么”。而這也將觀眾從對行動本身的關注引向對結果、結局的關注上。對這樣的觀眾而言,像《到大馬士革去》這樣追尋自我意識、最終“什么也沒有發生”的環形戲劇結構是難以被接受的。情節劇對懸念的設置,使觀眾既不影響行動,也不用對行動負責,更不用被迫做出決定,在這種緊張—放松的節奏中,他們獲得的是情感滿足,而不是智性反思。
(三)認同情節劇意識的旁觀者
這種懸念模式是在情感的高度激發中使觀眾形成對情節編排的認同,對人物的認同,對情節劇意識的認同。貝克說:“作為懸念之根本的是觀眾對于劇中某一個或若干個人物的同情,其同情在某種程度上恰與作者所預期的同情相一致的。”[5]222形體動作
(行動)或性格描寫會讓觀眾產生同情或者反感。情節編排就是最好的獲得觀眾認同的手段,因此為寫實主義戲劇所借鑒。
情節劇的人物是“完整的”,完全的善或完全的惡,因此“超然于在矛盾的責任和欲望之間做出痛苦的選擇,并以飽含其整個個性的那種毫不動搖的獨一無二的沖動來迎接一切情境的到來”[1]11。與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悲劇人物遭受不幸是因為犯了“某種偉大的錯誤”不同,情節劇的行動和人物的不幸都完全取決于外部性的敵人,不管是善勝惡敗,還是惡勝善敗,情感和結局都很極端。由懸念激發觀眾形成或同情或憎恨的單一極端情感,來實現所謂的“凈化”。作為情節劇的觀眾,“我們欣賞勝利而不考慮別人因此而付出的代價,欣賞絕望而不去尋找可替代的出路,欣賞抗議而不去就我們自己那居高臨下的道德完整性的基礎提出質疑”[1]14。因此,被編制的情節劇觀眾,獲得的是極端的快意、道德的義憤、夢幻的滿足。在這夢幻的滿足之中,觀眾被“凈化”掉的是那種對社會環境的不滿、反思和抵抗。當我們認同斯托克曼醫生(《人民公敵》)那毫不讓步的憤怒時,“便覺得自己成了反對市政府腐敗和貪污舞弊的富于戰斗性的戰士了”[1]14。就是那種以插曲的方式對主角進行懷疑和批評的內容也往往只是虛假的批判,反而增強了我們對主角受到外部邪惡力量迫害,對主角所代表的正義、勇敢等道德的認同。
這就是一種對情節劇意識的認同,對資產階級道德神話的認同。“這些人物戲劇行為的動力是要他們符合資產階級道德的神話。這些不幸的人們在道德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束縛下經受苦難生活的煎熬,道德和宗教的華麗辭藻掩蓋著他們的艱苦處境。”[10]130在觀看那些表現資產階級道德神話的戲劇時,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意識形態化的“主角”及其經歷身上,并從中看到了自己。這種外在于真實生活環境的、異己的、強加的情節劇意識,往往建立并強化了本身就處于意識形態之中的民眾與真實生活環境的想象性關系,從而使觀眾喪失了對自己與真實生活環境的認識。
因此,現實生活與情節劇就會出現同構的可能。阿契爾說,戲劇情節那種突然的突轉和發現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比如在法庭審判事件中,在報紙的報道之中。[6]225事實上,并非我們的真實生活如情節劇這般充滿戲劇性和賞善罰惡,而是我們以情節劇的意識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情節劇在觸及生活問題時,也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情節劇式的解決模式,這些模式同樣出現在寫實主義戲劇中。《社會支柱》中博尼克的反思,《群鬼》中阿爾文太太勇敢的獻身,《人民公敵》中的斯托克曼醫生“渾身閃耀著代表真理的炫目光芒”[1]108,這些都激起了觀眾的義憤。
三、經寫實主義改造后的情節劇旁觀者
寫實主義戲劇借用了情節劇的因素和劇場慣例,但也改良了情節劇,并使情節劇能夠在寫實主義的外表下,繼續它的“說服”藝術,繼續為觀眾“造夢”,繼續以有機體情節和懸念編制旁觀者。琳達·威廉斯分析,情節劇依托于寫實主義戲劇,以寫實主義的因果邏輯和情節劇展示激情、動作的手法,來達成情節劇的效果。總之,“情節劇因借用了寫實主義手法而具有現代氣息,而寫實主義則具有了情節劇的激情和動作”[11]9。
第一,寫實主義戲劇“細節的真實”使情節劇手法自然化。在布景、動作、敘事和表演上,寫實主義戲劇“細節的真實”往往服務于情節劇所要達到的效果。“細節的真實”作為對現實生活的忠實再現,使情節劇中那不自然的、功能性的、機械性的人物顯得自然。《玩偶之家》中林丹太太和娜拉之間那場推心置腹的談話,《社會支柱》中婦女們做針線活的閑談,都是情節劇技巧中“知心人”的變身。那些天意、人為的機巧,也在對現實生活的細節真實再現中,被視為是生活的片斷。這些生活細節往往還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因素。《玩偶之家》中的信件、扇子、悄悄藏起的零錢,或者那些潛臺詞,都是貝克等非常重視編排次序的細節。“細節真實”的安排不但使劇情明了,重點突出,而且“通過造成越來越多的懸念而使興趣不斷增加”[5]185,日常生活場景成為調節緊張和情感的手段。
“細節的真實”力圖再現社會生活中各階層的人物,因此往往將視角轉向那些下層人物,以弱者激發觀眾的同情。情節劇往往“都激發我們對被強勢者欺凌的不幸人物即受害者的強烈同情”[12]4。于是,情節劇在寫實主義揭示真實的可見性機制的掩蓋之下,反而以這些純潔無辜的人物作為主角,作為道德神話的代表,激起觀眾的同情和認同。寫實主義的批判情懷被轉化成了激發觀眾道德義憤的情緒。情節劇表面上是再現日常生活,實際上并非如此。
第二,在“第四堵墻”理論影響下,二分的觀演關系建立。觀眾與演員的區隔、旁觀者位置的固定、由“第四堵墻”所造成的鏡式反映,使情節劇更好地激發觀眾的深度移情和對角色的認同,完成情節劇對夢幻的營造。在觀眾與演員固定的位置結構和行為規則的設定之中,觀眾并不能介入舞臺上的行動,舞臺上演員的行動也并不迫使觀眾做出決定。戲劇盡善盡美地創造出真實的幻覺。觀眾則是通過對角色的同情來感受人物行動。因此,觀眾或者是一個無能為力的觀看者,僅在全心全意移情于主角與邪惡斗爭中獲得令人振奮的快感;或者是在位置和道德上高高在上的觀看者,所產生的不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對行動的反思,而是一種道德的優越感。因此,作為劇場中的享樂主義者,“我們可以看到一切人類命運的錯綜復雜的反應,而自己卻無需參與其事,也不必對此負責。這種優越感是永不會使我們生厭的”[1]145。
情節劇于1918年后在劇場中衰落了,而情節劇的因素卻出現在傳播能力更為強大的電影、電視之中,繼續影響著我們的觀看方式和感受方式。史密斯說,情節劇在舞臺上逐漸衰退的原因之一,便是電影這一新藝術和娛樂方式的崛起,實現了劇場中難以實現的現實場面和轟動性場面。“普通的觀眾在銀幕上再次發現,已成俗套的舞臺情節劇又重新制造出奇跡”[11]71,那些具有固定的情節劇成分的電影,紛紛取得了成功。“美國情節劇電影的淵源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舞臺的著名戲劇和演出。……那些據稱是寫實主義的電影效果——不管是布景、動作、表演或敘事鋪墊——往往正是用來服務于情節劇性的效應的。”[11]4情節劇通過對觀眾情感的計算和控制,使觀眾因情感被激發而形成鏡像認同,成為旁觀者,喪失了行動和反思能力,這也成為當下電影、電視主導的一種觀看方式。
總之,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與情節劇相互作用,通過編制有機情節和預設的懸念,通過激烈單一的情感、人物,傳播情節劇意識,并將這樣的編劇意識自然化,塑造出喪失參與、介入、反思和批判能力的旁觀者。于是,在對情節劇的借鑒之中,寫實主義戲劇往往也違背了反映社會現實、進行社會批判的創作初衷,甚至以情節劇意識掩蓋了對現實問題的揭露。寫實主義戲劇和情節劇相互作用中遺留下來的旁觀者問題,繼續存在于后來出現的電影、電視等媒介中。如今,我們被電影、電視中披著寫實主義外衣的情節劇圍繞,成為情節劇意識的理想主體,以此來認識我們與真實生活的關系。因此,反思19世紀末寫實主義戲劇和情節劇的關系,反思二者共同編制旁觀者的問題,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詹姆斯·L.史密斯.情節劇[M].武文,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2]周靖波,編.西方劇論選:變革中的劇場藝術[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3]易卜生.易卜生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4]Raymond Williams.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M].London:Penguin Books,1998.
[5]喬治·貝克.戲劇技巧[M].余上沅,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
[6]W.阿契爾.劇作法[M].吳鈞燮,聶文杞,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4.
[7]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8]劉小楓,主編.詩學解詁[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9]August Strindberg,Strindberg on drama and the a tre[M].Egil Tornqvist,BirgittaSteene,ed..Amsterdam:Amsterdan University Press,2007.
[10]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1]琳達·威廉斯.改頭換面的情節劇(下)[J].章杉,譯.世界電影,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