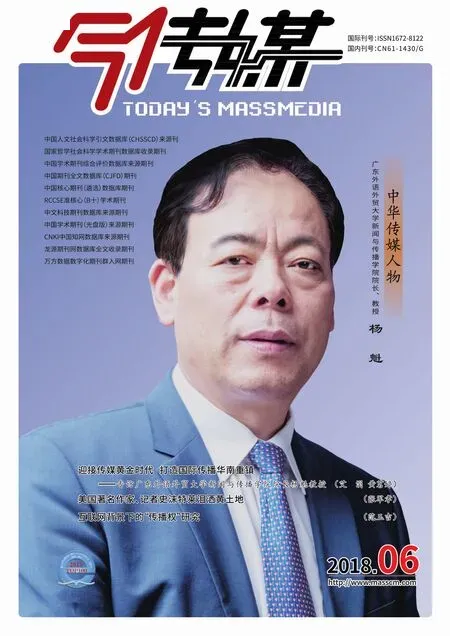文化詩學視閾下香草美人文化符號初探
司家瑜
?
文化詩學視閾下香草美人文化符號初探
司家瑜
(山西大學 文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作為楚地文化環境產物的《離騷》通過香草美人意象彰顯了其審美情趣、文化心理,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影響力的擴大反過來又成了民族文化的底色,香草美人意象成為一個民族情感的寄托物、一個民族文化的價值符號,如同一個召喚結構,詢喚出民族對于香草美人符號的一切記憶和潛意識寄托,又在道、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實踐理性的思想影響下,香草美人這一文化符號就有了溝通天與人、集體與個體的功能,美人就不單單是客觀意義上的女性,它是大道在人間的化身,知識分子通過這個符號完成近乎無限的表達。
香草美人;《楚辭》;神話原型;符號
《楚辭》是中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而其中的《離騷》更是最為優秀的篇章,其神奇瑰麗的想象、引類譬喻的創作手法、香草美人的詩歌意象在文學史上早已有定論,然而其背后的文化內涵以及對民族性格的塑造則需要深入探究。著名學者葛兆光認為精英思想文化的誕生都有其時代或顯或隱的一般知識、思想、信仰世界的作為背景,任何思想觀念的提出總有一個終極依據在支撐,盡管這一終極依據隱藏在最深處,但沒有這一終極依據任何思想文化都無立足之地。因此《離騷》中香草美人意象的運用絕不是作者憑空地想象,它與作者的生存環境、創作心理、民族觀念有深切的聯系。作為一部影響民族千年之久的文學作品,其價值成就早已超越了文學的范疇,香草美人的詩歌意象已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手法,更成為一種民族的文化底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作為楚地文化環境產物的《離騷》通過香草美人意象彰顯了其審美情趣、文化心理,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影響力的擴大反過來又成了民族文化的底色,香草美人意象成為一個民族情感的寄托物、一個民族文化的價值符號。
一、 香草美人的源起
香草美人最初是指一種引類譬喻的創作手法,最早出現在《楚辭》中,以屈原的《離騷》為代表。作者用香草來比喻人物的高潔品格,如在《離騷》中有這樣的詩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1]。木蘭、秋菊、薜荔皆是自然花草,自在之物,詩人將它們與個人品行聯系起來,實是抓住他們之間的某種相似之處建立了一種人為的聯系。首先楚地地處南方雨露滋潤,花鳥百草在所多有,是詩人觸手可及的事物,再者秋菊木蘭因其自然特性,或能于深秋萬物肅殺之時開放或能于幽谷悄然綻放,被詩人用來當作孤標傲世的代表就自然而然了,移情于物,以物喻人。作者用美人來代指詩人自身,如《楚辭》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1]用美人遲暮的遺憾比喻自身抱負不能實現的愁悶。又如在《山鬼》中屈原用迷離之筆觸、瑰麗之想象、比喻之手法塑造了一個善良而又深情綿邈的巫山女神形象。全詩開頭即以香草比喻這位女神: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為了突出這位女神的神秘獨處作者言道:表獨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女神徘徊良久、深情悵惘卻不得君子而來: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閑。最后以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結束全詩[1]。無論后人如何解讀,或認為這是詩人求遇知己而不得,或認為抒發詩人被君王誤解的憤懣,或言乃楚地娛神之詩,都無可否認的是詩人以女子形象塑造這些來抒發自己的某種感情。用女性來指代詩人自身,于文學作品來講這是一種取得詩歌美感的技巧但這里面涉及到性別轉換的心理機制,詩人之所以用女性這一身體來寄托某種感情是因為他認為可以獲得審美意義的美感。至少在以后的民族藝術作品中女性形象被賦予了各種含義或贊美或批判,它們共同的心理基礎是女性這一性別符號可以承載無限多的內涵,呈現出開放的姿態。上文的三種對女神的解讀就是很好的證明。在《楚辭》以后的文學作品中這種手法已經屢見不鮮,但對于第一個使用香草美人來引類譬喻的詩人來說這種偉大的創造必然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法國著名藝術理論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種族、時代、環境是考察藝術創作的三個基本要素[2]。宋代學者黃伯思曾言道: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由此可以推斷《楚辭》的創作顯然深受楚地人情風物的影響,香草美人的誕生也是楚文化的凝結與產物。首先從《楚辭》的詩歌語言形式上可以明顯看出楚地方言的影響,《離騷》全篇2400多字,兮字占了相當的篇幅,各種楚地方言詞更是不勝枚舉。再者《楚辭》描寫的多是南方楚地的人情風貌,最重要的篇章《離騷》更是楚人屈原抒發生平遭遇的凝結之作,而《少司命》《九歌》《湘夫人》等也是楚地巫頌娛神之風的體現。如《湘夫人》講述了湘君思戀湘夫人卻不得的情景,由飾湘君的覡和飾湘夫人的巫演唱。這里的湘君就是湘水男神,湘夫人就是傳說中帝堯的女兒,湘夫人因溺水湘江而成湘水之神。《湘夫人》就是獻祭給湘水之水的祭歌。學者劉懷榮在《香草美人與雙性同體比較研究》中指出“香草美人是遠古神話思維的體現”(劉懷榮《香草美人與雙性同體比較研究》),因此香草美人的神話思維必然和楚地巫頌娛神觀念有密切的聯系。屈原正是在當地巫頌風俗的基礎上創制了包括《離騷》在內的騷體詩歌,如在《離騷》中用大量篇幅描述詩人“上下求索”周游神界的奇情軼事,這是將楚地娛神之歌曲轉嫁發揮成文學作品抒發個體感情的表現。如詩歌描述道“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紲馬”卻筆鋒一轉“哀高丘之無女”[1]。屈原借助大量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游遍六界卻“求女”不得而歸,手法浪漫、筆法奇麗,實乃楚地巫頌之遺風,只不過屈原賦予了這些奇幻文字以現實世界的情感和內容,使楚地娛神之辭擺脫了民間粗糙成分和迷信色彩成為了浪漫的詩歌載體,進而影響了歷代的文學創作。因此詩人自比神女是有現實依據的,只是把娛神表演中的表演者換成了詩人自己而已。表演者在進行表演時是作為神的替代者出現的,他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神話因素都被詩人移植并填充了新的內容,香草美人原本是娛神之舉現在具有了娛人的功能,而轉化就在《楚辭》中完成,香草美人由神話到文學的轉變也由此完成。
二、 香草美人的神話內涵
前文指出香草美人是遠古神話思維的產物,在《楚辭》中成為具體的詩歌意象和創作手法,并被后人用“香草美人”四字代指。香草美人的實質就是男性的女性化,并用女性這一載體來表達某種觀點或抒發某種感情。這種轉換背后的思維方式來自神話思維,那香草美人的神話原型和內涵又是什么,它是如何演變成文學意象的,則是接下來需要分析的問題。聞一多先生曾指出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伏羲女媧,雖然名字不一樣但實際是指代一個原型,“二人本皆謂葫蘆的化身,所不同者僅性別而已”[3]。也就是說伏羲女媧本為一體同出一源,即使性別不同那也不影響二者的相互溝通。這就如同西方神話中上帝造人一樣,夏娃是亞當的一根肋骨。而香草美人的源起——楚辭本就是楚地巫頌娛神的產物。楚辭中的《九歌》就是屈原依據楚國南部民間長期流傳的祭祀樂歌加工編寫而成的一組祭祀詩歌,最為著名的《山鬼》就是其中一篇,祭祀的正是巫山神女,而這屬于一種女神崇拜。西方學者認為在宗教史上男神只是后來才出現的,而且它們的神圣地位來自它們的母親,即女神[4]。女神崇拜的淵源顯然來自于母系社會的生殖崇拜,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地區百家爭鳴,理性的曙光開始照耀這片大地,而南方楚國仍未脫離原始文化的籠罩,因此巫頌娛神的原始宗教性質活動依然盛行,《山鬼》、《湘夫人》等巫頌性質的詩歌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這也可以看出《楚辭》正處于巫頌娛神的宗教祭歌到充滿人性光輝的過渡時期,而《離騷》是完成文學轉身的代表。香草美人在《楚辭》中兼備女神崇拜和人性寄托的雙重性質,似乎更偏頗于人性寄托。女神崇拜是香草美人的神話原型,遠古人崇拜女性神祗在于生存與繁衍的本能愿望,更在于女性身體在原始人意識中代表著開始之初、也代表著某種回歸式的留戀,因此必然會在女性身體、女性符號以及由此衍化出的女神身上寄托情感、傳遞信仰。《湘夫人》中的湘夫人在神話中(或曰歷史傳說中)本是帝堯之女、大禹之妻,因思念的淚水而成就了淚竹,又因溺水于湘江而成為湘水之靈,起初人們懷念她,久而久之成為湘水之神,被人們寄托了更多的其他心理訴求,這才會有屈原的《湘夫人》。無可置疑的是《湘夫人》詩歌中必然會有作者的情感寄托,但寄托何物則歷來眾說紛紜,本文不做深究。本文只是指出香草美人意象源出于女神崇拜的神話原型。它從神話中走來,又在詩歌中成為一種創作手法,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又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承載著世間人們的眾多情感,即通過男性女性化抒情寫志或通過塑造女性形象來闡釋家國之思。而這一切的合理化或曰民族無意識正在于女神崇拜或曰女性崇拜的神話原型。
三、 香草美人作為文化符號
前文已經指出香草美人源出于女神崇拜原型,隨著時代變遷又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它表現在藝術作品中是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要想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則必須要在思想文化領域予以理性的確認或者必須找出它的理性表達方式。二者誰前誰后限于本文的體量不做探討,但二者必然有密切的聯系,因為它們具有共同生長的土壤—古中國農業文明。李澤厚和葛兆光都認為先秦思想同處于巫史傳統。《易經系辭上》言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德經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5]。不管這兩者的道有何含義的差別,但都指向某種混沌體。它們最早都來自原始歌舞巫術禮儀過程中出現的神明,多元、恍惚、朦朧而又確然存在。由此追溯,道和母性崇拜有莫大的關系,只是時代久遠聯系已經被賦予了其他的含義。至于陰陽的概念,葛兆光指出其最早與地理有關,而在殷商西周時期與天象發生了關系,白晝或曰太陽屬陽,夜晚或曰月亮屬陰。由此可以看出在很早的時代人們已經有了二元對立的觀念,這是人們觀察生存環境和自身的結果,因此陰陽并不特指某兩種屬性,而可以代指任何構成二元對立的概念,男女性別的陰陽關系也就自然而然的確立了。然而不容忽視的是盡管世間有陰陽對立,但它們同歸于道。道德經有言:反者道之動,世間萬事萬物無不回環往復生生不息,因此陰陽是可以轉換的。這樣的思想觀念盡管看起來玄之又玄,但仍然可以找到它在人間的根源,因為實踐理性始終是中國文化的主流脈絡,它既不超脫飛揚,也不庸俗茍且,不偏不倚。香草美人的性別轉換也就有了它的理性依據,再者儒道思想和道家思想對中國藝術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柔弱處上、上善若水、心齋、坐忘、神秀、“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物”、天人合一等思想無不在彰顯一種內向型的情感體驗模式,因此中國古典藝術整體傾向于一種陰柔含蓄之美,這和香草美人形成了天然的契合關系,這也是《楚辭》對后世最重要的貢獻所在。
因此香草美人作為一種性別互換的創作手法及表現方式有了它的思想的歸一之處,從而成為了一種民族的文化符號。首先它擁有穩定的文化生存環境,中國擁有兩千年封建史,不管朝代如何變遷、統治者是漢族還是異族,儒道始終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其次中國是一個從遠古以采集業為主,狩漁業為輔發展而來的農業文明,與之相關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構成了民族文化的底色,香草美人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上成型和凝聚,進化為一個文化符號或者被用來表述君臣關系如歷代對《離騷》的解讀,以美人比喻臣子以丈夫比喻君王;或者被知識分子用來抒發自己的志趣情感如李商隱的《嫦娥》、流行于五代的花間詞;或者被民間文學作品用來表達一種美好的愿望如《穆桂英掛帥》《木蘭辭》。由此可見香草美人這一文化符號是一個短路符號即沒有所指的能指。它既可以寄托文人的高潔志趣,又可以表達某種糟粕觀念將亡國之責推卸于女性。可以看到香草美人中“美人”始終是由男性把控話語權的,包含著男性的審美意趣在里面。屈原的《離騷》是遭遇離憂、家國破碎的詩人滿腹憤懣借助香草美人來抒發,時代的動蕩、男性的無力迫使詩人退行到女性的軀殼中暫時逃避以獲得安慰,其中的微妙心境需要結合作品的時代環境來把握。
香草美人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其所指總是處在變化之中,不同的時代環境、不一樣的民族境況使其含有不一樣的內涵意義,不變的是性別轉換的心理機制,變得只是時代背景下性別轉換的微妙心境和暗含的意識形態策略,它們混雜于藝術作品中構成一個時代的香草美人形象。電影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形式,其生命力、影響力至今昌而不絕,考察中國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可以有助于把握香草美人這一文化符號的流轉與變遷,更能從中窺探到時代的風云激蕩、意識形態的復雜糾纏、審美的變與不變、民族心理的矛盾糾結。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許多以女性為題材的電影,它們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家國情懷,對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創作者對女性的不同態度,其中包含著創作者期望通過女性形象委婉闡發自己對時事政治的看法與觀點。香草美人這一文化符號再一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符合民眾的審美觀念,人們對于女性形象出現在電影熒幕上并不排斥,其次電影作為一種視與聽的藝術,女性形象具有天然的上鏡頭性,可以滿足人們視覺欲求、心理訴求,文人通過女性闡發政治觀點古已有之,電影人可以毫不費力的繼承之。因此香草美人成為了絕佳的載體,如同一個召喚結構,詢喚出民族對于香草美人符號的一切記憶和潛意識寄托,既然美人可以一笑傾人國,那么美人也是可以拯救國破家亡者的心里失落、彌合民族的心理創傷、重振民族自信心、寄托家國幽思,這對于二十世紀上半葉面臨國破家破的人們來說無疑具有重大的激勵作用。
四、 結語
兩千年中華文明史,也是兩千年中國藝術史,香草美人源出于遠古時期以采集農耕為主要生存手段的華夏祖先的女神崇拜中,被屈原以藝術作品的形式確定于民族的審美心理中,而中國人的審美心理是建立在實踐理性的基礎之上并與其互滲交融。可以這樣認為,中國人的審美超越是一種建立在現實之中的超越,始終不離這生存的世界的土壤,其思維方式的重直覺性、聯想性、經驗性都使中國藝術呈現出迥異于西方的審美情趣。中國哲學思想中的體用不二、物我不分、天人感應、陰陽五行,把天、人、地聯系在一起,它們互相糾纏互相影響,這也使中國的思想、文化、藝術、現實常常糾纏在一起界限模糊,如《莊子》既是一本哲學思想著作又是一本優秀的先秦散文集,既有較為嚴謹的邏輯又有奇譎瑰麗的想象、縱橫捭闔的行文,香草美人也在這樣的物我不分的土壤上從文學的修辭方式衍變成文化符號,凝聚著民族的微妙心境、復雜情思并積極的參與到了中國廣泛的社會實踐當中。香草美人如同一個召喚結構,詢喚出民族對于香草美人符號的一切記憶和潛意識寄托。又在道、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實踐理性的思想影響下,香草美人這一文化符號就有了溝通天與人、集體與個體的功能,美人就不單單是客觀意義上的女性,它是大道在人間的化身,知識分子通過這個符號完成近乎無限的表達。
[1] 汪璦.楚辭集解[M].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1994.
[2] 法)丹納.藝術哲學[M].傅雷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
[3] 聞一多.神話與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4] (德)埃里希·諾依曼.大母神—原型分析[M].李以洪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5] 周振甫.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
[責任編輯:艾涓]
2018-04-13
司家瑜,女,山西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詩歌美學研究。
G210
A
1672-8122(2018)06-018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