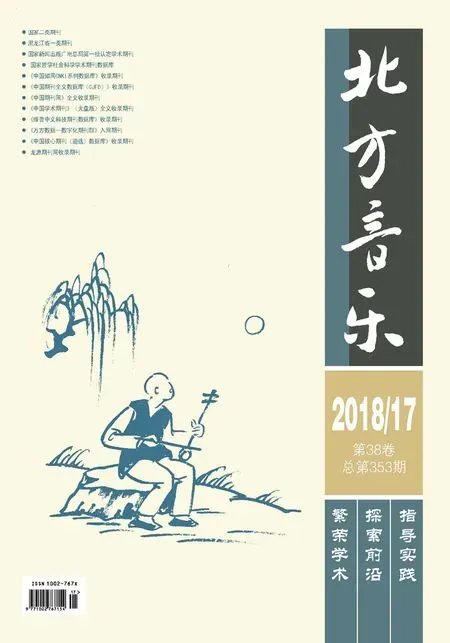淺談近代西方音樂在中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傳播及其影響
吳婧瑀
(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1120)
一、20世紀三四十年代近代西方音樂在中國的傳播方式
(一)非主動接受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音樂對中國的傳播方式更多的是一種強制性的植入。如為了緩解我國當時緊張的國內局勢需要在外交活動中爭取到西方各國的支持,西方音樂就成為一項有利的工具,他們希望借用西方音樂與西方國家達成藝術審美上的共識,而接受統治的民眾盲目跟從統治者的選擇,也加入了欣賞、傳播西方音樂的隊伍中,將其作為追求時尚、身份高貴的一種象征,西方音樂一時間在中國炙手可熱,受此浪潮驅使,國內不少學者開始研究西方音樂,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方音樂的傳播。
(二)主動學習
鴉片戰爭后,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往來增多,不少傳教士留在中國進行傳教,他們帶來了當時西方的教會音樂,利用音樂對教會信仰進行傳播,西方音樂也因此得到和平擴散,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民眾主動學習西方音樂奠定了基礎。民眾對西方音樂的認識了解逐漸深入,自身的審美取向發生變化,對西方音樂的態度也逐漸從被迫接觸轉變為主動學習。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的文化發展雖然稍有停滯,但與外國的文化交流仍舊存在,在交流的過程中,受眾開始主動選擇學習西方音樂。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中國學生外出留學,接觸并學習了西方音樂文化,受到西方音樂熏陶的同時,對其了解與認識更加深入,回國后也為中國民眾主動學習西方音樂產生一定的吸引力,并為西方音樂的學術研究和形式創新提供了契機。
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音樂在中國傳播產生的影響
(一)加深了對中西音樂關系的認識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音樂的社會功能愈加受到重視,圍繞“是否要汲取西方民族樂派的經驗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樂派”這一問題,各派音樂家展開了持久的論戰,持肯定態度的派別認為中西方音樂文化并非是不可調和的,希望能借此改變當前傳統音樂陷入的瓶頸局面。而在西方音樂在中國傳播范圍逐漸擴大、程度逐漸加深后,新的音樂觀念逐漸成型,主張“新音樂”的派別隊伍日漸壯大,他們開始靈活、創新地應用西方專業的音樂手段,創作出了許多備受歡迎的新型民族音樂,如《義勇軍進行曲》《延安頌》等,其中《義勇軍進行曲》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礎上,糅合了西歐進行曲的音樂風格,充分彰顯了這首樂曲的戰斗激勵作用。這表明,音樂家們在接觸、學習西方音樂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了中西方音樂文化的協調性,西方音樂自有其精髓之處,批判性地借鑒、吸收西方音樂理論與技法,能夠更好地促進民族音樂的發展。
(二)促使大批優秀音樂家涌現
西方音樂在中國的傳播,客觀上促使了大批音樂家的涌現,這批音樂家在西方音樂理論層面具有較高的造詣,他們將西方音樂形式引進國內,并在民眾中普遍推廣開來,為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在音樂創作層面,將西方的作曲技法和理論知識應用其中,開辟了對新時代中國音樂的探索之路,諸如冼星海、譚小鱗等;在音樂表演層面,將西方演唱技巧、樂器演奏技巧等應用到表演中,為中國音樂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馬思聰、周小燕等。除此以外,還有部分音樂家從西方國家留學回來后,在創作樂曲之余,還編纂了數量可觀的音樂類著作,系統全面地對西方音樂加以介紹,著作中涉及西方音樂作曲技法和理論知識的論述,為中國音樂實踐創造了新局面,如陳仲子編寫的《近代中西音樂比較觀》、蕭友梅編寫的《樂學概論》等。在中西方音樂文化碰撞交融的過程中,中國音樂家的音樂文化素質得到普遍提升,為中國近代音樂創作提供了人才力量。
三、結束語
近代西方音樂的傳播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推動了音樂教育的普及、加深了對中西音樂關系的認識、促使大批優秀音樂家涌現,加快了中國傳統音樂近代化的進程,對我國音樂的長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