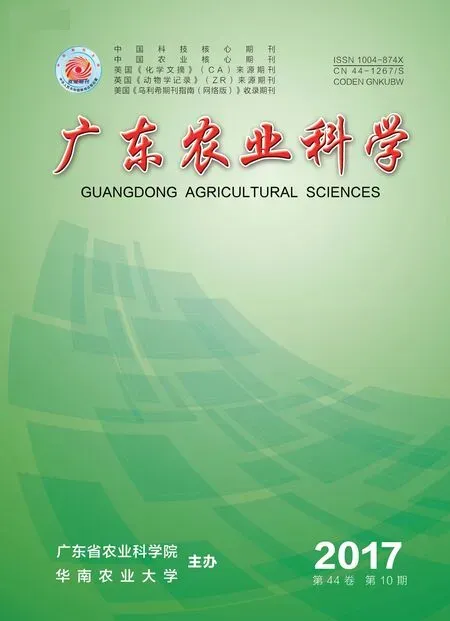黃鱔和泥鰍感染顎口線蟲的分類鑒定研究
黃燕瓊,鄧 艷,張 森,何淑華,戴 金,柏建山
(1.廣州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國家水產品檢測重點實驗室,廣東 廣州 510470;2.華南理工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0)
顎口線蟲病是一種食源性疾病,由旋尾目(spirurid)的顎口線蟲引起。當人體食入生的或未熟的感染顎口線蟲的食物后可能感染顎口線蟲,引起移行性皮下包塊和匐行疹,蟲體也可侵入人體重要器官,如肝臟、腎臟、肺臟、眼睛甚至中樞神經系,引起嚴重后果甚至死亡[1]。目前,顎口線蟲有13個有效種、5個致病種(4種分布在亞洲,1種分布在拉丁美洲)。棘顎口線蟲是亞洲地區的主要致病種,首次被發現是在倫敦動物園的老虎胃內。剛刺顎口線蟲、日本顎口線蟲和杜氏顎口線蟲病例主要發生在日本[2],雙核顎口線蟲是拉美地區流行的唯一蟲種[3]。在墨西哥和泰國,已報道的病例均超過9 000例,日本病例4 000例[4]。
感染人體患病的主要是顎口線蟲第三期幼蟲,其宿主廣泛,其中淡水魚是顎口線蟲的重要宿主,也是感染人體的重要來源。在淡水魚中,泥鰍和黃鱔的感染率非常高,這兩種魚類在亞洲地區廣泛存在,在很多調查中,黃鱔的感染率很高[5],在東南亞有些地區黃鱔的感染率可達100%,泥鰍中也經常發現顎口線蟲。本調查對從廣州機場口岸入境的黃鱔以及國內的黃鱔、泥鰍感染情況進行調查和分類鑒定,以期為顎口線蟲的防控提供重要的參考數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1.1.1 樣品來源 國外蟲體來源于廣州機場口岸入境的黃鱔,進口自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國內蟲體來源于不同地區市場所售泥鰍和黃鱔,包括廣東廣州、福建漳州、吉林長春、重慶、四川內江、湖北荊州。
1.1.2 主要儀器 生物顯微鏡(Lecia DM5000B)、體視顯微鏡(Lecia S8APO)、恒溫振蕩器(THZ-D)、冷凍離心機(Siama 3K15)、梯度PCR儀(BIOMETRA TRRADIENT) 、電泳儀(BIA-RAD、PowerPac Basic)、凝膠成像系統(VILBER)、手術刀、小鑷子、昆蟲針、載玻片、蓋玻片。
1.1.3 主要試劑 8.5 g/L生理鹽水、胃蛋白酶-濃鹽酸消化液、酒精、乳酸-酚-甘油混合透明液,試劑配制方法參照《淡水魚中寄生蟲檢疫技術規范》和《水產品中顎口線蟲檢疫技術規范》。TaKaRa Universal Genomic DNA Extraction Kit試劑盒、Agarose Gel DNA Extraction Kit Ver.4.0試劑盒、Plasmid Purification Kit Ver.4.0試劑盒、10×PCR buffer、dNTP、Taq酶、pMD18-T載體、DH5α感受態細胞,購自寶生物工程(大連)有限公司。
1.2 試驗方法
1.2.1 顎口線蟲蟲體的分離 逐條剖開黃鱔,檢查腹腔內蟲體感染情況,再分離頭部,剪碎肌肉和肝臟后,用消化液對其進行消化,過夜消化至消化液內無明顯組織,將消化液濾過孔徑2.0 mm的篩,吸去上清液,加水攪拌后沉淀20~30 min,再吸去上清液,用清水反復清洗幾次,直至上清液透明為止,分離出蟲體,置于有生理鹽水的培養皿中。泥鰍的消化方法與黃鱔類似,但由于泥鰍個體偏小,沒有逐條進行消化,而是直接稱重,數條泥鰍一起消化。
1.2.2 蟲體的形態學鑒定 用體視顯微鏡觀察,疑似顎口線蟲的蟲體發黃,頭部有棘突,卷曲,體長一般2~5 mm,在生理鹽水中卷曲或有包囊包住,將蟲體放入乳酚透明液中,至透明后,置于載玻片上,在生物顯微鏡下觀察。觀察鑒定后將蟲體放入裝有75%酒精的離心管中-20℃保存。
1.2.3 蟲體DNA提取 將單條蟲體從75%酒精的離心管中取出,置于經滅菌的1.5 mL離心管中,用純水洗凈后用研磨棒研磨,后根據TaKaRa Universal Genomic DNA Extraction Kit試劑盒的步驟提取蟲體基因組DNA。將基因組DNA置于-20℃冰箱保存備用。
1.2.4 PCR擴增ITS2序列 對顎口線蟲ITS2序列進行PCR擴增,引物信息見表1,擴增體系如下:2.5μL 10×PCR buffer,2.5μL Mg2+,1μL dNTP,1μL PE-5.8S引物,1μL PE-28S引物,0.5μLTaq酶,1μL DNA模板,用超純水補足至25μL。反應程序為:94℃預變性4 min;94℃變性 30 s、55℃退火 30 s、72℃延伸 30 s,30個循環;最后72℃延伸10 min。取反應產物5μL在1%瓊脂糖凝膠中進行電泳20 min,在凝膠成像系統中觀察并拍照記錄結果。

表1 對顎口線蟲ITS2序列擴增引物[6]
1.2.5 擴增片段回收克隆 使用Takara公司的Agarose Gel DNA Extraction Kit Ver.4.0試劑盒,按照說明書步驟進行PCR擴增片段的純化回收,將純化產物連接到pMD 18-T載體上,然后轉化至感受態細胞DH5α中培養,將DH5α感受態細胞培養液涂布到含有氨芐青霉素、IPTG、X-gal的LB瓊脂平板上,37℃恒溫培養12 h,再進行藍白斑篩選(方法參照《分子克隆實驗指南》第3版),挑取單個白色菌落,按照Takara公司的Plasmid Purification Kit Ver.4.0試劑盒說明書步驟進行質粒提取。將質粒置于-20℃冰箱保存。
1.2.6 測序、構建系統進化樹 將陽性克隆質粒送Invitrogen公司進行測序,校正處理獲得的序列,使用NCBI的BLAST在線工具進行序列比對。在GenBank中獲取不同種顎口線蟲的ITS序列,包括棘顎口線蟲(G. spinigerumn,登錄號為KP784343)、杜氏顎口線蟲(G.doloresi,登錄號為AB181156)、雙核顎口線蟲(G. binucleatum,登錄號為EU334741)日本顎口線蟲(G. nipponicum,登錄號為JQ824051)、剛刺顎口線蟲(G. hispidum,登錄號為JQ824057)、膨脹顎口線蟲(G.turgidum,登錄號為KF648548)、宮崎顎口線蟲(G. miyazakii,登錄號為FJ497055)、G. lamothei(登錄號為EU334738)、美麗筒線蟲(G. pulchrum,登錄號為AB646106)。將測序結果與下載的ITS2序列用ClustalX軟件進行差異性分析,并進行必要調整,然后用MEGA5.0(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 Analysis 5.0 version)軟件,使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構建系統發生樹,自展值(Bootstrap values)重復1000次。
2 結果與分析
2.1 廣州機場口岸入境黃鱔中顎口線蟲的檢查情況
廣州機場口岸入境的黃鱔主要來自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這是入境水產品中唯一的一種淡水魚,對每一批次黃鱔進行抽樣調查(共19批次,其中12批次來自印度尼西亞、7批次來自菲律賓)。從表2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亞的黃鱔感染率較高,批次陽性率達到91.7%,感染強度1~9條不等;菲律賓黃鱔中沒有發現顎口線蟲。
術后兩組患者均常規使用替硝唑片(廠家:湖南迪諾制藥有限公司,批準文號:國藥準字H43020659,規格:0.5 g)抗感染治療,劑量為1 g/次,1次/d;同時采用補佳樂(廠家: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批準文號:國藥準字J20171038,規格:1 mg)加黃體酮膠囊(廠家: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批準文號:國藥準字H20041902,規格:50 mg)治療,劑量分別為2 mg/次、100 mg/次,1日2次。以21 d為1個治療周期,停藥7 d后再進行下1周期治療,兩組患者均治療3個人工周期。3個月后,取出人羊膜包裹球囊和節育器,并記錄兩組患者療效。
2.2 國內部分省市市售黃鱔和泥鰍中顎口線蟲的檢查情況
2015年9~12月,對國內廣東廣州、重慶、四川內江、湖北荊州、福建漳州和吉林長春的部分市售黃鱔和泥鰍進行了檢查,只在漳州的泥鰍中發現了18條蟲體,在黃鱔中發現了1條蟲體,其他地區均無發現蟲體(表3)。因為本次檢查的時間較短、樣本有限,數據只能作為參考,需要進一步的調查。
2.3 形態學鑒定結果
在體視顯微鏡下,活體稍透明,呈黃色,頭部和尾部都向內卷曲,呈盤旋狀;死亡蟲體呈半透明,頭部伸直,尾部向頭部卷曲呈半環(圖1 A、B,彩插四)。透明后在生物顯微鏡下觀察,蟲體表面可見到體棘,約2~5 mm,向后延伸逐漸變細;蟲體可明顯分為唇部、頭球和體部3個部分,唇部向前突出,位于頭球前端;頭球表面有棘突,內部向下連接4個頸囊;食道與口唇相連,食道顏色較淺,從前端向后逐漸膨脹,在最膨大處于腸道相連,界限明顯,腸道較細,有彎曲,顏色深,長度大約是食道的1.5倍(圖1 C、D,彩插四)。
在高倍生物顯微鏡下進一步觀察,初步鑒定為3種顎口線蟲,福建漳州黃鱔中蟲體為棘
顎口線蟲,泥鰍中蟲體1條為棘顎口線蟲,17條為日本顎口線蟲,印度尼西亞黃鱔中檢出9條剛刺顎口線蟲,其余全部為棘顎口線蟲。

表2 廣州機場口岸入境黃鱔中顎口線蟲的檢查情況
(1)棘顎口線蟲:蟲體較大,體長4~5 mm,各個器官清晰可見,唇部位于頭球中央頂端,有兩對突起,共兩對頸囊,每側分布1對,食道與腸道交界如漏斗狀,尾端可見肛門和尾感器,頭球表面有棘突,呈不規則長方形,共4環棘突:第一環棘突數為40~47,第二環為37~49,第三環為42~57,第四環為42~48;頸乳突位于11~16體環處。根據這些特征初步判斷為棘顎口線蟲(圖2,彩插四)。
(2)剛刺顎口線蟲:在高倍生物顯微鏡下觀察,蟲體各部分結構符合顎口線蟲形態,頭球棘突呈不規則啞鈴型,共4環:第一環棘突數約為40,棘突數向后逐漸增加,第四環約為48;頸乳突位于9~14環體棘之間。根據以上特征初步鑒定為剛刺顎口線蟲(圖3,彩插四)。
2.4 ITS2序列PCR擴增結果
以編號為Gn-FJ1~Gn-FJ6和Gn-In1~Gn-In13的線蟲基因組DNA為模板,使用顎口線蟲ITS2通用引物PE-5.8S和PE-28S進行PCR擴增,片段約640 bp,與預期片段大小相符(圖5)。

圖5 部分顎口線蟲ITS2序列PCR產物電泳結果
2.5 序列分析
樣品測序結果經Blast分析比對,Gn-FJ5、Gn-FJ6、Gn-In1~Gn-In9、Gn-In12和 Gn-In13的ITS2序列與GenBank中已知的棘顎口線蟲(G. spinigerumn)相應基因序列(登錄號為KP784343)同源性達99%~100%;樣品Gn-FJ1~Gn-FJ4與日本顎口線蟲(G. nipponicum)同源性達99%~100%(登錄號為JQ824051);樣品Gn-In10和Gn-In11的序列比對結果與剛刺顎口線蟲(G. hispidum)同源性達100%(登錄號為JQ824057)。
2.6 構建系統進化樹

圖 6 基于ITS2序列以最大似然法構建的系統進化樹
對19個樣品的ITS序列進行多重比對后進行必要調整,采用M-L法構建系統發生樹。從系統進化樹拓撲圖(圖6)可以看出,顎口線蟲屬對應美麗筒線蟲構成一個大分支,Gn-FJ5、Gn-FJ6、Gn-In1~Gn-In9、Gn-In12和 Gn-In13與棘顎口線蟲構成自展值為99%的獨立分支,這個分支又與雙核顎口線蟲組成一個自展值為87%分支;Gn-FJ1~Gn-FJ4與日本顎口線蟲構成自展值為90%的獨立分支;Gn-In10和Gn-In11與剛刺顎口線蟲構成自展值為98%的獨立分支,又與杜氏顎口線蟲構成一個自展值為98%的拓撲結構分支。一些可信度比較高的分支與這些蟲體的某些特性吻合,如膨脹顎口線蟲的形體是顎口線蟲中最大的,與其他蟲體形態差異明顯,在進化樹中獨立自成一支,說明其可能與其他蟲體的遺傳距離較遠;剛刺顎口線蟲和杜氏顎口線蟲的終末宿主均為豬和野豬,它們的生活史比較接近,在進化樹中,這兩個蟲種組成一個自展值為98%的分支,表明它們的遺傳距離較近;而棘顎口線蟲是亞洲地區的主要致病種,雙核顎口線蟲是美洲地區的主要致病種,兩者組成一個自展值87%的分支,說明兩者遺傳距離較近,是否與其致病性有一定關系還不得知,需要進一步研究;其他蟲種分支的自展值比較低,存在很大不確定因素,需要結合其他基因作進一步研究。
3 討論
本次從國內的黃鱔和泥鰍中發現了少量顎口線蟲,集中在福建漳州地區,187條泥鰍中發現了18條顎口線蟲,其中17條為日本顎口線蟲、1條為棘顎口線蟲,10條黃鱔中發現了1條棘顎口線蟲。雖然蟲體不多,但也說明了福建漳州地區存在顎口線蟲。購買的黃鱔和泥鰍有些是通過野生捕撈獲得,有些來自人工養殖,這對調查的結果造成一定影響。
棘顎口線蟲是世界范圍內廣泛的顎口線蟲,在歐亞、大洋洲、非洲、美洲都有發現,在我國北京、上海、江蘇、福建、廣東等10余省市均有報道,亞洲地區包括我國的絕大部分顎口線蟲病是由棘顎口線蟲引起,此次國內的檢查中在福建漳州的黃鱔和泥鰍體內各發現1條棘顎口線蟲,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本研究在福建首次發現日本顎口線蟲,2012年李雯雯等[7]在廣州和黑龍江泥鰍中分離到日本顎口線蟲,為首次在我國本土發現日本顎口線蟲。在此之前中國出口到韓國和日本的泥鰍中有發現日本顎口線蟲[8]。本研究再一次證明我國本土存在日本顎口線蟲,在國內可能廣泛分布[9-13],需要作進一步調查研究。
對廣州機場口岸入境的黃鱔進行檢查,印度尼西亞的黃鱔顎口線蟲感染率較高、為27.9%,而菲律賓黃鱔中沒有分離到顎口線蟲。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黃鱔在入境時均申報為野外捕撈,在檢查中發現印度尼西亞的黃鱔大小參差不齊,體內有大量其他寄生蟲,如棘頭蟲、吸蟲、胃瘤線蟲等蟲體,說明其生長環境復雜;而菲律賓的黃鱔體型較大且均一,體內的寄生蟲很少,說明其生長環境單一。僅2016年,從廣州白云機場口岸入境的印度尼西亞黃鱔為1379.049 t,菲律賓黃鱔為802.659 t,而且黃鱔的入境數量逐年增長,尤其是現在冰鎮黃鱔等食用方法比較流行,但該方法并不能徹底殺死寄生在肌肉內的顎口線蟲,因此需要特別重視入境黃鱔的寄生蟲檢疫工作[14]。
[1] Katchanov J,Sawanyawisuth K,Chotmongkol V,et al. Neurognathostomiasis,a neglected parasitosi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J].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11,17(7):1174-1180.
[2] Nawa Y. Historical review and current status of gnathostomiasis in Asia.[J].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 Public Health,1991,22 (S1):217-219.
[3] Murrell K D,Murrell K D. Food-Borne Parasitic Zoonoses[M]. New York:World Class Parasites,2007.
[4] Ando K. Gnathostomiasis in Japan[M]. Foodborne helminthiasis in Asia,AAA Committee :the Federation of Asian Parasitologists,2005:1,231-239.
[5] Rojekittikhun W,Waikagul J,Chaiyasith T.Fish as the natural second intermediate host ofGnathostoma spinigerum[J].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 Public Health,2002,33(Sl3):63-69.
[6] Ando K,Tsunemori M,Akahane H,et al.Comparative study on DNA sequences of ribosomal DNA and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1 of mitochondrial DNA among five species of gnathostomes[J]. Journal of Helminthology,2006,80(1):7-13.
[7] 李雯雯,李樹清,張子群,等. 黑龍江與廣州顎口線蟲幼蟲分離株的形態學觀察及其分子鑒定[J]. 中國預防獸醫學報,2012(2):104-107.
[8] Sohn W M,Kho W G,Lee S H. LarvalGnathostoma nipponicumfound in the imported Chinese loaches[J]. Korean Journal of Parasitology,1993,31(4):347.
[9] 陳清泉,林秀敏. 剛刺顎口線蟲病流行區的發現及其生物學研究[J]. 廈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0(2):214-217.
[10] 林秀敏,陳清泉,彭文峰. 江西省九江地區剛刺顎口線蟲病流行學調查[J]. 武夷科學,1992(9):245-248.
[11] 黃錦源,林金祥,張良應,等. 福建省將樂縣豬體感染顎口線蟲調查研究[J]. 中國人獸共患病學報,2008(1):89-90.
[12] 林開鉛,陳月香,張榕燕,等. 將樂縣野豬陶氏顎口線蟲病流行現狀調查及蟲卵發育至早期第三期幼蟲的試驗觀察[J]. 福建畜牧獸醫,2011(4):1-3.
[13] 張鴻滿,吳慧芳,江河,等. 廣西市售部分水產品中顎口線蟲感染情況調查研究[J]. 應用預防醫學,2012(4):193-196.
[14] 李樹清,李雯雯,陳志飛,等. 入境黃鱔顎口線蟲檢疫及蟲種鑒定[J]. 中國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雜志,2011(5):358-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