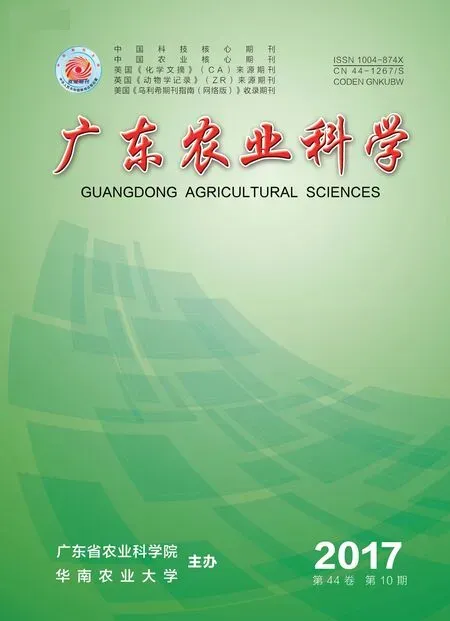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現狀與對策研究
彭思喜,姜百臣,胡秀麗
(1. 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2;(2.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資產管理處,廣東 廣州 511483)
“協同創新”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是落實黨十八大“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現實選擇[1]。2012 和2015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協同創新是克服農業科技體制弊端、促進農業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因此,關于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和理論意義,是當前科研人員的研究熱點。本研究以廣東為例,探討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現狀,并針對廣東農業科技協同創新中的“閉路循環”與“供求失配”問題,從“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聯動發展視角,提出了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機制與對策。
1 農業科技協同創新內涵
目前國內外多數學者一致認為協同創新是“不同創新主體(高校、科研機構、企業)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以資源共享或優勢互補為前提,合理分工,通過創新要素(如技術、市場、戰略、文化、制度、組織、管理等)有機配合,經過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實現1+1>2 的整體協同效應的過程”[2]。
與一般“協同創新”內涵不同,農業科技協同創新具有中國特色內涵,是在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特定歷史情境下提出來的,在政府的引導和協調下,通過協同創新的方式,有效整合農業高校、科研院所、農業企業等創新主體資源,促進創新主體間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研究,從而建立起“國家需求導向、項目任務帶動、平臺資源共享、機制創新推動”的高效協同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管理模式,實現協同創新的增值效應。
2 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現狀
2.1 廣東省農業科技創新資源狀況
2.1.1 農業科研機構數量擴大 “十二五”期間,廣東省農業科研機構數量擴大明顯,截止2016年,數量達到147個,其中國家級7個、省級22個、市級41個。從學科門類看,種植業72個,畜牧業16個,農墾與農機化類19個,此外漁業、農產品加工與檢測等其他類別有40個[3]。由此可見,廣東農業科研機構涉及的門類比較全面,研究方向涵括產中、產前、產后全過程。
2.1.2 農業科研經費投入加大 從2010年以來,廣東省對農業科技協同創新日益重視,持續加大科研經費的投入。表1顯示,2010—2015年廣東省農業科研機構的經費收入總額是逐年增加的,到2015年農業科研機構的經費收入總額已達2010年經費收入總額的2.12倍。從經費來源看,絕對金額逐年增加的政府財政基金所占的比例最大,占60%以上;從農業科研機構經費收入與支出相比,收支保持平衡,沒有出現嚴重透支情況,表明農業科研機構的科研活動有比較足夠的經費保障;從農業科研經費支出看,經費支出從2010年來,也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表明科研機構對農業科研創新與投入也越發重視。
2.1.3 農業科技人才實力持續增長 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1)農業科技人才數量增加。2015年廣東省從事農業科技活動的人員達到5638人,是2010年的1.56倍;(2)農業科技人員結構優化。從學歷看,層次大幅提高,2015年農業科技人才具有博士和碩士學歷的比例達到42.38%,比2010年提高了32.45%;(3)農業高層次人才引進和培養成效顯著。“十二五”期間,廣東省大力引進和培養高層次農業領域科研人才,截至2015年,引進和培養農業領域院士6人、長江學者12人、珠江學者9人、國家突出貢獻人才23人、農業部杰出人才10人。

表1 廣東省農業科研機構經費情況
2.2 廣東省農業科技成果產出狀況
“十二五”期間,廣東省農業科研機構在農業科學領域發表科技論文共8 739篇,出版農業科學類專著169篇,在農業領域制定新的國家或行業標準243項。表2數據顯示,廣東省在農業科學領域發表論文數量是每年增加的,其中2015年發表國外四大索引論文342篇,是2010年的2.87倍;制定新標準61項,是2010年的1.97倍。從獲得獎勵看,“十二五”成果中,獲得廣東省和國家科技進步獎有210項,廣東省農業技術推廣獎有962項,農業部科研成果獎有82項。

表2 廣東省農業科學領域論文、著作及其他科技產出
2.3 廣東省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狀況
2.3.1 加大實施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項目 為了進一步與國家財政資金實現聯動,2012年廣東省科技廳設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2012—2015年期間,一共資助了113項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項目,金額達6 060萬元,累計獲得經濟效益30億元,申請通過123項國家專利,培育出54個動植物新品種。同時,廣東省還設立了142項農業產業化關鍵技術應用與推廣示范項目,吸引了眾多社會金融資本的投入,有效促進了相關農業龍頭企業對關鍵技術成果的應用與轉化。
2.3.2 構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和載體 農業園區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平臺和載體。“十二五”期間,廣東省科技廳通過專項基金大力資助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截止2015年底,廣東省已建立了4個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表3)和10個省級農業科技園區,地點遍布廣州、湛江、珠海、河源、梅州、韶關、汕頭、汕尾等地市,是廣東省農業協同創新與成果轉化的重要載體和平臺。

表3 廣東省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
另外,為了響應國家建設現代農業示范區政策號召,廣東省從2010年開始逐步構建以現代都市農業示范區(順德、佛岡、從化)、生態型現代農業示范區(梅縣、河源、仁化)、外向型現代農業示范區(開平、惠城)和亞熱帶現代農業示范區(廉江、澄海、陽東)為核心的現代農業示范區戰略格局。截止2015年,廣東省已建立220多個現代農業示范區,其中國家級11個(表4)、省級3個。

表4 廣東省國家級現代農業示范區
2.3.3 建立信息服務平臺,創新農業技術推廣方式 信息化服務平臺能夠更方便快捷地為農村和農民提供科技信息服務,及時解答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碰到的技術難點,促進農業新技術的宣傳與推廣,從而提高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從2003年開始,廣東省就著力實施廣東農村信息直通車工程,通過聯合農業、教育、信息、企業等農業產業化眾多部門,整合各類有價值農業信息,采取“統一品牌、統一標準、統一服務、統一管理”的“四統一”策略和“政府引導、共建共享、企業運營”的模式,構建集“多渠道、多終端、多元化、多層次”于一身的現代農村信息綜合服務平臺[4],極大地促進農業技術推廣的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
3 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存在的問題
3.1 農業科技創新“孤島現象”仍然突出
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主要是指在科技創新體系中,某一環節、要素與其他環節、要素出現“隔離”,在創新體系內部中形成“閉路循環”的現象,導致完整創新鏈的斷裂,致使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效率低下[3]。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也存在類似 “孤島現象”。
3.1.1 科研選題與農業產業需求脫節 政府財政基金是課題經費的主要來源,因此項目指南便成了科研人員進行選題的重要依據,這導致科研人員只注重選題的先進性和前沿性,而忽視選題的產業需求和成果轉化的市場前景。即使在科研課題進行申報時,有預測選題的產業需求與成果轉化情況,但其實這些預測往往是憑主觀想法或以往經驗得來的,大多數是“紙上談兵”,很少有基于深入市場調研和數據分析得來的。
3.1.2 科研人員與農業生產脫節 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對科研人員的考核更注重論文、專利、課題、獎勵等主要指標,指標是否完成直接影響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經濟收入和工作績效等。因此科研人員都將精力放在發表論文、申報課題、申請專利等基礎研究上面,而對成果轉化、農業生產、技術服務等工作視而不見,導致科研人員空有“理論成果”而與農業生產實際脫節。
3.1.3 創新成果與農業市場脫節 科技成果轉化可以看作是技術創新最為重要的環節,是新技術、新發明最終實現市場價值的“驚險一跳”,是科技進步支撐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是科研成果在高校科研院所研究出來后經過一系列的中試、大試、推廣、示范等階段,實現商業化應用的復雜過程[5]。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面臨更加復雜的過程,除了要經過一系列的中試、大田試驗、推廣等過程外,還受到許多嚴格的外部環境限制。例如,植物新品種會受到土壤、氣候等外部條件限制,這就要求該品種在成果轉化過程中,需要建立相關的配套技術。因此,更加苛刻的限制條件導致廣東農業科技成果更多只停留在實驗室,缺乏需求性、成熟性與適用性,離農業產業化市場距離較大。
3.2 農業科技成果供給結構不合理,轉化率低
“十二五”期間,廣東省農業科技成果產出眾多,但在成果轉化過程中卻面臨農業科技成果供給結構失衡,成果轉化率低的窘境:一方面有大批農業科技成果被鑒定,并獲得國家或省級科技成果獎;另一方面,大批科技成果卻只停留在實驗室,未能有效提供和解決農業產業化生產中需要的技術。廣東農業科技協同創新仍然面臨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困境,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業科研活動結構缺陷,科研人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中農業技術的研發與創新,而忽視產后的農產品貯藏與深加工技術,使得成果轉化的鏈條斷裂;二是多數農業科技成果的適用性和適用性不高,不能滿足農業企業或農民的需要。例如,廣東特色優勢產業——蠶桑業,經濟效益高,但卻存在“家蠶發病率高,勞動強度大”的問題,而科研人員卻未能針對農民對養蠶“省力化、輕簡化”的需求,仍將研究重心放在“產繭量高、單繭絲長、絲質好”的育種目標上,導致農民逐漸放棄“勞力重、風險高”養蠶業而轉移到“省力化、風險小”的種植業,昔日特色優勢的養蠶產業而今逐漸萎縮。
3.3 農民接受能力低下,對農業科技成果有效需求不足
在中國,農民是最主要的農業生產者,亦是最主要的農業科技成果的最終用戶。然而,眾多的數據表明,農民對新技術、新品種的接受能力低下,對農業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不足。在廣東,這個問題尤為明顯。由于地處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廣東農民面臨更多的到珠三角地區打工的條件和機會,從而造成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力外流,老人婦孺滯留在家種田,其對農業科技成果的接受能力更低,直接制約廣東農業新成果的推廣和轉化。另外,當前的農業科技成果主要針對規模化、機械化、專業化、集約化農業生產,而廣東大部分地區屬于山谷盆地,農業生產以家庭承包為主的經營模式,規模較小,土地條塊劃分,零散分布,分割嚴重,極不利于當前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和轉化,也造成廣東農民對需要大規模土地使用的農業機械化、生產專業化、生物防治等農業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
3.4 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不完善
農業技術推廣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綜合性系統工程,需要農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農業推廣機構、農業合作社、農業生產者等眾多主體進行有效銜接,協同完成[6]。廣東省農業推廣體系主要采用采用自上而下的“單向式”推廣模式,與基層機構缺乏互動,造成基層機構管理渙散,“上面推廣”的技術與基層需求脫節,造成農業技術推廣成效低微。具體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3.4.1 上下科研機構缺乏聯動 省級科研機構擁有先進的農業科技成果,然而缺少成果轉化的服務人員,很少參與到成果轉化的中試和推廣過程。地市級科研機構科研實力較弱,科研投入較少,因此本地化適用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上比較滯后。兩者之間聯系橋梁的斷裂,造成了廣東省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難以達到產業化成果轉化的要求和標準。
3.4.2 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不受重視,甚至有些地方下放鄉鎮管理 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待遇低、晉升少”,導致“積極性不高、人心浮亂、隊伍不穩”,農業技術推廣效率低下。
3.4.3 農業技術推廣內容以單項實用性為主 目前廣東省基層農業推廣人員科研素質較低,在推廣內容上多以單項實用技術為主,缺乏對本地化適用的現代農業綜合配套新技術進行研究、試驗和推廣。
3.4.4 推廣服務不能滿足生產需求 當前廣東省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在方式上大多仍停留在“走村串戶、以會代訓,口傳面授”的傳統方式上,而本地化適用的農業新技術實地試驗、示范和推廣卻很少,造成技術推廣服務難以滿足實際農業生產需求。
4 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發展對策
4.1 建立農業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市場導向機制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當前我國農業科技協同創新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我國科研人員將主要精力放在完成論文、專利、課題等考核指標上,而對成果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于轉化視而不見,導致“科研”與“市場”脫節,新技術成果不能有效滿足農業生產的實際需求。在歐洲發達國家,由于建立了健全的市場導向機制,市場需求從一開始就是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目標,在選題階段就非常注重市場調研和產業分析,從而創新成果具有極高的針對性和適用性,大大提高了成果產業化應用的轉化率[7]。
4.1.1 構建市場導向的農業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機制 首先,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完善資金鏈。這就要求項目指南的編制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編制前要廣泛征集專家學者、公司企業、基層農業生產組織、農業科技人員和農業生產者的意見,對農業產業進行實地全面調研,從而明確農業生產的實際需求,著力突破農業產業的關鍵共性技術。其次,在財政上加大對農業龍頭企業和科技型農業企業的資助,推動農業企業逐漸成為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主體。再次,實行科研項目的分類管理。不同類別的項目,政府資助的方式和要求要分類管理,確保財政基金使用高效安全。例如,公益性農業科研項目采用“無償資助”方式,強化產業化應用的需求導向,提高項目成果的產業化應用與轉化,而非公益性農業科研項目,則需注重建立市場導向機制,采用“后補助、合同補貼、以獎代補”的方式,加強監管審計和績效評價。
4.1.2 改變傳統的農業科技成果評價機制 好的創新成果必然經歷中試、大試、推廣和示范階段,并最終經過不斷地成熟和完善從而適應農業生產實際需求,產生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然而傳統的以“論文、專利和課題”為主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必然導致對成果轉化“小試、中試、示范和推廣”階段的忽視,導致科技成果缺乏成熟性和適用性。因此,要改變傳統的以“論文和專利”為主要指標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把農業科技成果的評價標準落實到成果的適用性和實用性上,以成果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作為重要的鑒定依據。
4.1.3 建立與完善科研人員激勵機制 要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與農業產業的融合,解決農業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矛盾,就要引導科研人員以農業產業發展需求為導向,在農業產業中找課題,才能更好地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推廣。一是完善廣東省高層次農業科研人才引進和培養機制,全面提升廣東省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形成一批高層次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在農業生產的產業化關鍵共性技術實現重大突破;二是完善農業科技人員職稱評審機制,將成果轉化、技術轉讓與“論文、專利、課題”作為一樣重要的考核指標;三是制定合理規范的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農業成果轉化的激勵與保障機制。
4.2 構建企業為主體的農業科技協同創新體系
隨著創新發展戰略的實施,很多企業都非常注重技術創新,對企業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但在農業領域,科技創新還主要靠政府財政資助,科技創新主體依然單一,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農業成果的推廣與轉化也主要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單向式農業技術推廣模式,對市場需求非常敏感的農業企業卻難以參與其中,這也是“上面推廣”的技術難以與基層農業生產需求匹配的關鍵原因。歐美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農業企業主體作用已非常突出,在完善的市場機制作用下,企業根據自身需要和市場需求,主動地尋求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合作創新,使得創新成果具有極大的針對性和適用性,提高了農業成果轉化率。廣東省也應根據自身條件和需求,積極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農業科技協同創新體系。
4.2.1 構建“源頭創新、成果轉化、示范推廣”為一體的協同創新支撐平臺 2015年成立的廣東省農業科技創新聯盟由華南農業大學等農業院校、各級農業科研機構、農業企業、農業示范園區、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眾多主體構成,涵括了廣東農業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主要力量。通過該聯盟,廣東省采用 “政府引導、科企聯合”模式,整合優化創新資源,強化產業需求導向,打造一個集“源頭創新、成果轉化、示范帶動”為一體的農業科技協同創新支撐平臺。
4.2.2 促進農業龍頭企業構建研發機構 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實現“科技”和“經濟”相結合,必須注重科技創新的產業需求,構建以企業為主的協同創新體系,提高創新成果的轉化效率。目前,廣東農業企業技術創新水平和能力比較低下,政府應積極引導,鼓勵農業企業構建自己的研發機構,才能真正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的主體作用。實踐證明,企業越重視研發,企業發展越有動力[3]。比如,廣東大華農生物藥品公司不但成立自己的研發機構,每年還將公司銷售收入的7%作為研發經費,重獎做出杰出貢獻的技術人員。同時,在“成果”有效轉化成“商品”后的3~5年內,每年將該商品30%的銷售金額投入研發。企業也在研發成果的支持下得到了跨越式發展。
4.2.3 構建“風險共擔、成果共有”的利益捆綁機制 當前,廣東農業科技協同創新方式比較單一,主要以項目合作為主,處于淺層次階段,難以達成長期性的深層次協同與合作。廣東溫氏集團和華南農業大學的合作為我們提供了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業院校進行校企協同創新的合作典范,其成功之處可歸納為“五個捆綁”:(1)利益捆綁。1992年華南農業大學以“技術入股”方式入股溫氏集團,技術作價1 200萬,占10%股份,緊緊把雙方利益捆綁一起。2015年華南農業大學溫氏集團的股份分紅已達1億多遠。(2)責任捆綁。華南農業大學與溫氏共同承擔風險,如果溫氏集團效益不好,則少拿或不拿股份分紅。(3)權利捆綁。對企業的管理,溫氏與華南農業大學形成了“校企共管”機制,華南農業大學派老師到企業兼職工作,擔任企業的技術中心經理、總經理助理、種雞場場長等重要的經營管理工作,提高了產學研創新成果在企業的轉化率。(4)人才捆綁。一方面華農派遣優秀專家和技術人員全面參與優質肉雞育種、飼料營養研究、雞病疫情監測、經營管理、技術培訓等工作,另一方面華農專家、技術人員與企業合作一起申報成立研究機構,共同開展科研工作。(5)聲譽捆綁。華農與溫氏的合作,已在社會廣泛傳播,在聲譽上,雙方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實現聲譽捆綁。
4.3 健全農業科技服務體系
4.3.1 構建和完善農業科技創新中介服務機構 中介服務機構是技術創新和促進創新成果商業化的重要媒介,它與高校、科研院所和技術需求者聯系比較緊密,是溝通各種創新主體間的粘合劑,是促進創新活動的催化劑。然而農業科技創新的中介機構卻非常欠缺,嚴重影響和制約農業科技成果合作創新與成果轉化,因此必須構建和完善農業科技創新中介服務機構。一是構建農業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和協調機構。目前廣東農業院校和科研機構都沒有專門的農業成果轉化機構,科研成果無法通過合適的渠道去尋找買家,造成許多成果不能及時轉化。農業高校和科研院所通過構建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和協調機構,能夠有效幫助本單位農業科技成果尋找需求信息和合適的買家,并提供成果轉化過程中的相關服務,促進本單位成果轉化進程。二是構建農業科技成果孵化基地。擁有“人才、技術”等資源優勢的農業高校或科研院所應積極籌建本單位農業科技成果孵化基地,與眾多農業企業以基地為載體形成良好合作,在解決企業技術問題的同時,積極引入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逐漸形成“孵化+創投”的成果孵化模式,促進農業科研與成果轉化的聯動發展。
4.3.2 健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 截止2016年,廣東省農業技術推廣已形成比較完善的網絡,全省共有2 737個各級農業推廣機構,行業上包括綜合站、種植業站、畜牧業站、農機化站等,地域上遍布全省306個縣和2 205個鄉鎮,農業技術推廣機構已成為促進廣東省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載體,但依然存在例如基礎設施建設差、推廣方式單一、推廣服務不到位等各種弊端。因此,政府應加大建設力度,健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改善基層基礎設施建設,轉變運行機制,促進推廣服務市場化,激發基層推廣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5 結語
以“農業科技協同創新”驅動廣東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是廣東全面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經過“十二五”發展,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在農業科研機構、科研經費投入、高層次人才培養、農業科技成果產出、成果轉化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依然存在著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的“閉路循環”、農業科技成果供給與需求結構性失衡、農業成果有效需求不足、農業推廣設施與服務不足等重要的瓶頸問題。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通過實地訪問調查和二手數據收集,分析了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的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并通過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聯動發展理論,提出了廣東省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的發展對策,為廣東省在農業領域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經驗總結和理論啟示。
[1] 周緒紅. 科技協同創新的模式與路徑[J]. 中國高校科技,2012(12):59-65.
[2] 蔣志勇,李君. 我國基于產業協同創新的旅游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研究[J]. 改革與戰略,2017(9):132-138.
[3] 張潔華. 廣東省農業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聯動發展研究[D]. 廣州:華南農業大學,2016.
[4] 杞人. 駛向未來的“中國農村信息直通車”[N]. 科技日報,2011-09-02(5).
[5] 蔡躍洲. 科技成果轉化的內涵邊界與統計測度[J]. 科學學研究,2015(1):37-45.
[6] 林偉君,駱浩文,孫明華,等. 新形勢下創新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的思考[J]. 廣東農業科學,2005(6):102-104.
[7] 張曉靜. 國外農業科技創新經驗對中國的借鑒與啟示[J]. 南方農業,2016(36):69-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