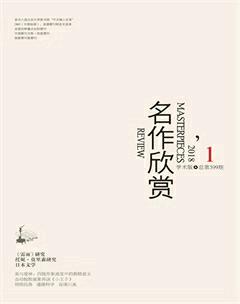對照與差異:從中外藝術創作的共鳴到意義世界的探尋
張赟
摘 要:盡管存在年代、民族、地域的差異,古今中外藝術家們的創作仍然可能存在高度相似性,這可以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和而不同”思想來解釋,即在參差錯落的差異中謀求一種思想認識的一致性。本文通過契訶夫戲劇與錦云的戲劇、皮蘭德婁戲劇與余華小說、中西方戲劇家筆下的《灰闌記》三對組合的對照,從特定視角反映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精神歷程的同步性與差異性,以及在同步性與差異性背后蘊藏的豐富性與多義性,實現了超越歷史時空的藝術精神的對話與交流。
關鍵詞:相似性 歷史車輪 “二母爭子” 瘋癲者 相對性
當我們漫步在煙波浩渺的世界藝術長廊里,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面對一部特定的世界藝術精品時,其具體的題材、主題、人物、框架,或者一個片段、一個細節、一個結尾,會使人產生似曾相識之感,從而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它的精神兄弟——在另一個迥異的歷史時空里的另一部作品。因為人類共通的精神世界,各異的生活體驗也能造就相似的精神感悟。我們不難發現,在不同年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前提下,存在著藝術家們的創作出現高度相似性的情況,但只是相似,而不是相同,即一部作品相對于另一部作品,盡管存在相似題材、情節、主題或人物等因素,卻呈現一種全新的設置或鋪排,并蘊含迥異的思想意蘊。①
事實上,這種現象可以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和而不同”思想來解釋。“和而不同”,這一成語原意是指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茍同于對方。“和”是指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相似或統一,有別于“同”。這一傳統文化精神也是一種美學精神,即肯定多樣化的統一。在藝術世界里,“同”是雷同,是遭到鄙棄和否定的,而“和”則是作品追求的理想化境界。任何事件、人物形象或命運的“和”不能掩蓋作品內部或作品之間更豐富的差異性。即便故事框架相似,但其中具體的人物、情境、事件、細節、環境等等,都各具時代、民族、文化背景或細節的獨特性,我們看到的是同中有異的絕妙境界,讀者絲毫不會有雷同之感。本文將關注這種創作的相似性,通過比較和對照,實現對不同作品更豐富的意義的探尋。
一、《櫻桃園》與《狗兒爺涅槃》中歷史的車輪聲
俄國作家契訶夫的戲劇《櫻桃園》(1903),描寫了女地主安德列夫娜只知享樂,面對櫻桃園將被拍賣的現實,無所作為。作品的結尾,在拍賣莊園之日,安德列夫娜還在家里舉行舞會,拍賣消息傳來她才痛哭流涕,最后再次遠赴他鄉追逐情人。作品結尾寫道:“傳來一個遙遠的、像是來自天邊外的聲音,像是琴弦繃斷的聲音,這憂傷的聲音慢慢地消失了。出現片刻寧靜,然后聽到砍伐樹木的聲音從遠處的花園里傳來。”這聲音像是突然發出、來自歷史深處,或來自神秘的宿命,它對安德列夫娜來說似乎是措手不及的,卻是必然的。然而歷史的車輪不會為任何人暫駐、停留,在“砍伐樹木的聲音”中,它們隆隆駛來。“砍伐樹木的聲音”,既是實指櫻桃園的毀滅,更是象征歷史車輪的無情逼近。
應該說,契訶夫對于櫻桃園的未來是充滿憂慮的。被拍賣的櫻桃園被新興資本家羅伯興收購,他將毀掉櫻桃園建起別墅。櫻桃園不僅代表著地主階級的沒落,它還代表著一種浪漫、詩意、溫情的舊時代的田園生活,摧毀它的是追求金錢、利潤的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地主階級的沒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資本社會的前景卻也充滿了陷阱和危機,這代表著作家的矛盾心態。
櫻桃園里的歷史聲響同樣出現在錦云的話劇《狗兒爺涅槃》(1986)中。劇本塑造了一個有著沉重精神負擔的老中國兒女“狗兒爺”形象。狗兒爺的父親當年“跟人家打賭,活吃一條小狗兒,贏人家二畝地,搭上自個兒一條命”,“狗兒爺”名字的來歷暗含著中國農民對土地的強烈渴求和歷史命運的悲劇性。“狗兒爺”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搶收了地主的芝麻地,又在解放區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下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和房產,然而隨著“大躍進”和“合作化”的到來,“狗兒爺”的土地、家畜又被收歸集體所有,“狗兒爺”被逼瘋。新時期到來后,農民等來了好政策,“狗兒爺”的兒子大虎開始開礦辦廠,并準備把妨礙通車的大門樓推倒,這遭到“狗兒爺”的反對。對“狗兒爺”來說,當年地主家的大門樓是自己悲慘的發家史,是人生夢想實現的標志,但當新舊兩代人為此產生沖突時,最終妥協的是“狗兒爺”,他放了一把火燒掉了門樓。劇本的結尾是這樣的:
滿臺大火。巍巍門樓被火焰吞沒。
人聲、馬達轟鳴聲,雄渾地交織在一起,直響到終了。
有人喊:“推土機來啦!”“快救火呀!”
……
馬達聲大作。推土機隆隆開入。
大火燒掉舊門樓,也埋葬了中國農民的舊時代,同時照亮未來的美好新生活。新的歷史時期,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農民過上新生活,劇作家對此充滿樂觀的期待。最后一句“推土機隆隆開入”,是不可阻擋的時代車輪,它開啟了新的時代,代表著光明、希望!在這背后,“狗兒爺”與兒子大虎形成對比。而事實上這體現出劇作家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作為時代“新人”的大虎們會在未來的生活中自由馳騁,但“狗兒爺”卻并不會實現向新人的過渡,只能作為新舊過渡的橋梁存在,他更多存在于過去。
契訶夫和錦云都在作品中用象征的手法預示了時代的車輪迅疾向前,不可逆轉。但兩相比較的話,會發現他們對此迥然不同的態度:契訶夫滿腹憂慮,櫻桃園里“砍伐樹木的聲音”帶動起讀者哀怨的情感,幾乎促使人想要去阻止;而錦云筆下“推土機的隆隆聲”,則充滿樂觀積極的態度,使人恨不得再去助推。不難理解這差異背后的原因。契訶夫生活在19世紀后期沙皇俄國的反動統治時期,劇作家更多的是批判現實;錦云活躍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繁榮時期,劇作家更多的是肯定現實。契訶夫筆下的主人公安德列夫娜代表著沒落的地主階級,哀其不幸中更多的是嘲諷;錦云的“狗兒爺”則是中國農民的代表,他有保守的一面,但更多地承載著中國農民在舊時代的血淚,對農民主人公的基調,不是嘲諷,而是熱愛,因為“狗兒爺”就是我們民族的父輩。endprint
二、《亨利四世》與《河邊的錯誤》中瘋癲者的現代隱喻
皮蘭德婁的戲劇《亨利四世》與余華的小說《河邊的錯誤》中都出現了瘋癲者的形象,兩位作家最終都以非理性的瘋癲來應對理性的現代社會,在思想內涵上存在高度相似性。
皮蘭德婁是意大利戲劇家,他的《亨利四世》(1922)描寫二十年前主人公在一次慶典中裝扮成皇帝亨利四世,當他騎馬接近自己所熱愛的女子時,馬被情敵刺傷,他落馬昏迷。蘇醒后他發了瘋,并以亨利四世自居。親友把周圍環境布置成皇宮的樣子,雇傭“樞密顧問”陪伴他。劇本開端,他已恢復神志,他痛苦地發現情人已被情敵奪去,自己虛度了年華,“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完了”,“好像一頭餓狼赴了已散的宴席”。兩鬢斑白的他,深感生命虛度,用劍將情敵刺傷。為避免刑罰,他不得不繼續扮演一個瘋子的角色——做他的“亨利四世”。
皮蘭德婁制造了相反的兩個世界,一個是主人公瘋癲非理性的世界,另一個是周圍貌似文明理性的世界。可這兩個世界又是顛倒的:貌似理性的文明世界由賣淫的娼婦、下流的嫖客和騙子老手組成,他們帶著假面具去干著丑惡勾當;主人公的瘋癲世界里充滿胡言亂語,卻代表著經受現代文明禁錮的人,在無窮痛苦之中渴望自由。由此,皮蘭德婁通過瘋癲者的世界的真實性,隱喻了現實世界的荒誕本質。
主人公“亨利四世”假裝瘋癲的精神歷程,與余華小說《河邊的錯誤》中警察馬哲高度相似。《河邊的錯誤》(1987)是先鋒小說家余華的實驗系列作品之一,小說虛擬了一個偵探故事:在神秘的河邊,么四婆婆慘死。警官馬哲經過重重波折,發現殺人犯就是那個瘋子。因為在法律上無法將瘋子繩之以法,瘋子逍遙法外且又犯下多起殺人慘案,忍無可忍的馬哲開槍打死瘋子,為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在妻子和局長的哀求下承認自己是瘋子,進了精神病院。瘋子連環殺人卻總是能夠免于刑罰,瘋子被警察槍斃,警察最終成為清醒的“精神病人”。這是現實理性社會的非理性呈現,所謂的社會文明秩序只是表象,并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小說最終所體現的是對世界“荒誕”本質的揭露。
作為剛剛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皮蘭德婁,與剛剛經歷過“文革”的余華,有著相似的對理性的懷疑,不同國別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有著對現實的悲觀感悟:兩個主人公最終都為了躲避懲罰,而假裝瘋癲,說明人類的理性在非理性的瘋癲面前束手無策,即便是作為人類理性產物的法律,也對一個非理性的行為失去了懲惡揚善的作用。由此可見,我們素來堅信和依賴的客觀世界,其實是多么脆弱,支撐這個世界的道德規范、價值判斷和理性思維,竟在突如其來的由瘋子造成的意外災難面前變得不堪一擊。
所不同的是,《亨利四世》中的主人公將瘋狂和清醒集于一身,他經歷了從清醒到瘋癲,再到清醒,最終假裝瘋癲的過程,也就是主人公最終同時具備了瘋癲和清醒,并用瘋癲戰勝外部理性最終獲得了勝利;《河邊的錯誤》中瘋癲者的形象則由兩個人分飾,開始時瘋子代表瘋癲,警察代表理性,他們各自獨立,后來警察槍殺瘋子,瘋子死去,但瘋狂的因子并未消除,反而轉移到警察身上。槍殺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瘋癲,所以馬哲就不再是一個理性的警察,而是瘋癲和理性合而為一的警察,瘋癲并不能被消除,它仍然繼續,并實現了對所謂理性社會的勝利。
在皮蘭德婁和余華的筆下,亨利四世和警察馬哲都陷入瘋癲給理性設置的陷阱,理性在其中迷失并最終陷入瘋狂。真瘋子和假瘋子的隱喻內涵,直指世界本質的荒誕,預見了人類的生存現實,并對理性自身進行消解與追問。
三、《包待制智賺灰闌記》與《高加索灰闌記》中的“二母爭子”
中國元代戲劇家李潛夫的雜劇《包待制智賺灰闌記》,講述了一個“二母爭子”的故事,妓女張海棠嫁給土財主生下一個兒子,財主大妻不能容忍,與奸夫合謀毒死財主,又為爭奪遺產謊稱兒子是自己生的。這宗爭兒案由包拯審理,他叫人用石灰畫成一個闌,把孩子放中間,令張海棠和大妻拽拉,誰把孩子拽出來,誰就是孩子的親生母親。大老婆狠命拉扯,張海棠卻怕扭斷孩子的手臂,不敢用力,結果大老婆拽出了孩子,但包公也看出了誰是孩子的親媽,做出公正判決。
李潛夫戲劇中“畫闌拉子”的安排更富于動作性和觀賞性,適合戲劇舞臺演出。同時他著重傳達的是以家庭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價值觀念,強調血緣親情的無可取代,這直到現在也仍然是東方民族非常重視的一個因素。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受到李潛夫《包待制智賺灰闌記》的啟發,但又生發出完全不同的內涵。一場暴亂中,總督夫人逃跑時把兒子扔給女仆。為了保護孩子,女仆多次死里逃生,與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感情。天下太平后,總督夫人為了遺產想從格魯雪那里奪回孩子,法官也采用了包拯的辦法,這時孩子的生母卻不顧孩子死活使勁拉扯,女仆以一顆慈母的心放手。法官最后判定真正疼愛這個孩子的女人才是孩子的母親。布萊希特在這里表達的價值觀是,母愛不是天然的,世間的一切權利也都不是天賦的,正如山川土地不應屬于地主,而應該歸于能夠耕種糧食、熱愛土地的人,孩子也理應屬于具有慈母心腸,能夠保護他呵護他的母親。所以,這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布萊希特在孩子與母親、土地與農民之間做了置換和隱喻,順便表達了他的政治觀點和立場。
兩個“二母爭子”的故事,在共同的情節核心下生發出不同的環境、人物、事件以及思想觀念,這必然是由時代、民族、文化的差異,以及階級、政治的差異造成的,而顯然,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將這個故事原型提升到更高遠、更深刻的藝術等級。超越了血緣關系的母子之愛更恢宏,體現出更廣闊的社會價值觀念,同時它的政治隱喻又增加了它的厚重。
筆者舉出三組例子來說明古今中外的藝術創作中相似性現象的存在,通過分析,我們在原本看似毫無聯系的作品與作品之間、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建立了某種聯系,實現了超越歷史時空的靈魂對話與交流,反映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精神歷程的同步性與差異性,以及在同步性與差異性背后蘊藏的豐富性與多義性。正如后現代主義哲學家福柯所說:“世界的意義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不可計數的意義。人們解釋世界的方式是無限的,我們面對現象,應當尋求多種多樣的解釋。”②藝術家們的創作都是對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發現、解釋,或質疑,創作相似性的存在,使我們在比較和對照的視角下,在聯系中洞悉藝術作品各自豐富的意義世界,從而得到更豐富、更深刻的解釋和知識。
{1} 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來源于英國古老傳說,一般認為莎士比亞根據已有無名氏的劇作改編而成;王實甫創作《西廂記》之前有元稹的《鶯鶯傳》和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約圣經》,在達·芬奇之前,這個基督教圣經中最重要的故事幾乎被所有宗教畫家描繪過。
② 轉引自馮俊:《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哲學轉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