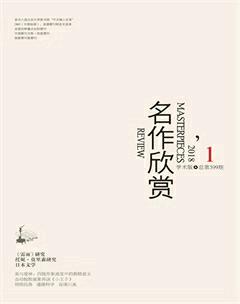民族文學的建構
栗子然
摘 要:王安憶的《小鮑莊》與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都是富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學,前者明顯受到了后者的影響。《百年孤獨》在虛構族群聚居空間、書寫民族傳統信仰、引入民俗文化意象三個方面影響了《小鮑莊》,這種影響源于兩位作家具有相似的創作語境和文化反思立場。
關鍵詞:《百年孤獨》 《小鮑莊》 影響研究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拉美文學迅速崛起,一大批拉美作家作品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流行,這一文學現象被稱為“拉美文學大爆炸”。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正是拉美文學運動的主將之一。他是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領軍人物,出版于1967年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獲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孤獨》講述了馬孔多小鎮上的布恩迪亞家族七代人由遷移、生存、繁榮至覆滅的興衰歷程,反映了拉美土著文化的日漸衰微。
20世紀80年代,《百年孤獨》在中國文壇上引發強烈反響。尋根文學的興起正是受到了《百年孤獨》傳入中國的直接影響,莫言、賈平凹、韓少功、閻連科及阿城等本土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帶有《百年孤獨》的影子。
當代作家王安憶也毫不諱言《百年孤獨》對她的影響。她曾多次在文章中表示對《百年孤獨》的稱贊,更在《小說家的十三堂課》里列單章分析《百年孤獨》的敘事結構與主題思想。她于1984年問世的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小鮑莊》,更被視為“得之于《百年孤獨》的啟迪”①。《小鮑莊》以小鮑莊為背景,勾勒了鮑家人的世態眾生圖,描述了仁義觀這一傳統道德價值逐漸走向衰亡的歷程。
本文擬從民族文學建構的視域入手,論述《百年孤獨》在虛構族群聚居空間、書寫民族傳統信仰、引入民俗文化意象三個方面對《小鮑莊》的影響,并探究這一影響產生的條件。
一、《百年孤獨》對《小鮑莊》的影響
(一)虛構族群聚居空間
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里構筑了一個虛擬的族群聚居空間——馬孔多小鎮。馬孔多小鎮由布恩迪亞家族的第一代族長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所建立。他為了逃避因近親結婚而殺人的良心譴責,帶領著一干族人離開了原本居住的印第安人村莊,翻山越嶺,在一片荒原中開辟了新的家園,慢慢繁衍生存。在馬孔多這個虛擬的村鎮里,布恩迪亞家族的七代人歷經移民開發、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內戰、美國香蕉公司的經濟掠奪、軍警鎮壓工人等歷史事件,映射了拉丁美洲近百年的興衰歷史。
王安憶借鑒了馬爾克斯的這一技法,如她所言,“我還得承認《百年孤獨》對我們的影響,就像約好了似的,都以虛擬一個空間展開故事為形式”②。《小鮑莊》里的小鮑莊也是一個作家虛構的族群聚居空間。王安憶同樣虛擬了小鮑莊的歷史由來,小鮑莊原是由因治水獲罪的先人所建,出于贖罪心理,他挑選了地勢最低洼的地點安家落戶,逐漸繁衍發展為一個幾百人口的村莊。
這兩個族群聚居空間的共同點在于,它們同樣是封閉落后、與世隔絕,和外部世界迥異的原始村鎮,村民們擁有著群體性的文化心理。但是,一旦有外界的介入,打破這種封閉自守的狀態后,它們就失去了平衡,脫離了常規。馬孔多和小鮑莊是民族文化高度濃縮的象征,分別代表印第安原始文明和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文化。
在《百年孤獨》里,馬孔多一直以來都處于孤獨、落后和愚昧的狀態;在另一個層面來說,卻也是一方自給自足的“世外桃源”。然而,隨著外來力量的步步入侵,馬孔多代表的印第安原始文明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喪失了獨立自主,不斷走向沒落。當馬孔多的鐵路開通后,外國人受香蕉的吸引,如潮水般紛紛涌進馬孔多。香蕉公司掀起的“香蕉熱”為馬孔多帶來了現代化,卻也為馬孔多帶來了混亂和屠殺,使馬孔多淪為經濟上的殖民地,人們更是在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失去了對本民族文化的歸屬感。
小鮑莊也是一個自成體系的原始村鎮,不與外部世界同步發展。村民們一直固守根深蒂固的“仁義觀”,“仁義”是他們最高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他們在為人處世中處處講求仁義。鮑彥山的妻子即將生產,村民送來了小麥苗;鮑五爺的孫子社會子不幸早夭,他成了老絕戶,村民紛紛答應照顧;鮑毅德不忍心與瘋了的妻子離婚,也是因為“不能不仁不義”③;撈渣更是仁義精神的典型代表,集聚了一切美德。他尊敬老人,禮讓兄長,善待朋友。然而,隨著撈渣因救鮑五爺而死,經過媒體的大肆宣傳和政府的物資嘉獎,“仁義”被納入官方意識形態,村民們也紛紛從撈渣之死這一仁義之舉中獲益,“仁義”逐步走向失落乃至崩潰。
(二)書寫民族傳統信仰
相比現代人善用抽象理性的邏輯思考,先民們更習慣用直覺和想象,形象化地闡釋他們對生死、宇宙萬物的一系列看法,從而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民族信仰。民族傳統信仰是一個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因素,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拉美民族的土著——印第安人普遍信奉萬物有靈論,認為死人可以與活人對話,人與鬼的界限可以互相混淆。《百年孤獨》里一再出現死人還陽的情節。被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殺死的普魯鄧希奧·阿斯拉爾的鬼魂因害怕孤獨,一直追隨著前者,甚至與其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密友。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死后,他的鬼魂也一直在樹下游蕩。在萬物有靈論的基礎上,馬爾克斯筆下的印第安人還相信神秘的占卜、巫術和預言。梅爾加德斯用羊皮卷為布恩迪亞家族“第一個人被捆在樹上,最后一個人正被螞蟻吃掉”④的命運做出了預言。奧雷里亞諾上校對事物的發展有預知作用,早在三歲時,他就能預知桌上湯鍋的掉落,從軍后,他更是憑借自己的預感,多次死里逃生。阿瑪蘭坦更是因為在臨死前見到了死神,開始為自己縫制壽衣。
同樣,《小鮑莊》里也描寫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傳統信仰。王安憶所表現的是漢族人普遍信仰的佛教輪回觀,佛教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都要經歷輪回。鮑五爺剛開始不喜歡撈渣,源于他認定他早夭的社會子被撈渣抓了替身。他后來被撈渣的仁義打動,認為撈渣正是社會子的轉世,才會與自己如此投緣。鮑毅德的妻子在水災中離奇失蹤后,他一度認為撈渣是出于“仁義”,才化作鬼魂拉走了瘋妻這一負累。endprint
馬爾克斯與王安憶,憑借書寫各自民族的傳統信仰,再現了各自民族的原始思維方式,描摹出各自民族最本真的性格心理。
(三)引入民俗文化意象
在印第安人古老的民間風俗中,黃色象征著兇兆、災難和死亡,這與他們的圖騰崇拜有關。印第安人崇拜虎神,視虎神為勇敢的象征和死亡的預兆。黃色正是老虎的顏色。⑤在《百年孤獨》里,馬爾克斯借用了這一民俗意象,用黃色隱喻悲劇和苦難。小說中神秘的黃色事物總是伴隨著布恩迪亞家族的不幸事件出現,如小黃花、黃色火車和黃蝴蝶。梅爾基亞德斯逝世前,水杯里的假牙生出了小黃花;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去世時,馬孔多紛紛揚揚地落了一夜黃花雨;烏爾蘇拉死后,水泥地的裂縫里長出了小黃花。馬爾克斯在三位老人與世長辭時,都安排了小黃花的出現,渲染了神秘的死亡色彩。黃色火車為馬孔多帶來了蜂擁而至的外國殖民者和慘痛的香蕉工人大屠殺,馬孔多也從此走向衰敗。蝴蝶在印第安人的文化中被視為不祥之物。⑥梅梅與巴比洛尼亞相戀,巴比洛尼亞的每次出現,都有飛舞的黃蝴蝶環繞其身,當最后一只黃蝴蝶隕落時,二人的愛情也以巴比洛尼亞的癱瘓而悲劇告終。
王安憶在《小鮑莊》里,雖然沒有著眼于民俗文化中的顏色寓意,但也采用了古老而傳統的民俗文化意象作為貫穿始終的隱喻,用以增強作品的民族特色。貨郎鼓又稱撥浪鼓,是一種用手搖動的雙面皮鼓,誕生于戰國時期。貨郎常常用肩膀挑著擔子,手上拿著貨郎鼓走街串巷,招攬顧客。在《小鮑莊》里,它是一種為儒家傳統文化所不容的禁忌情感的隱喻。它的每次出現,都與拾來的情感有關。拾來是小馮莊老姑娘大姑的私生子,大姑迫于傳統文化的壓力,謊稱他是撿來的孩子而取名為“拾來”。對此毫不知情的拾來,竟對大姑產生了超乎母子情誼的性沖動。從結局可以看出,當年與大姑私通的人正是一位老貨郎鼓。大姑對拾來的情感覺察后,把珍藏的貨郎鼓交給了拾來,迫使拾來自力更生。拾來挑著擔子來到小鮑莊,與寡婦二嬸組建了家庭,大姑的夢中也不再如往昔般響起“叮咚叮咚”的貨郎鼓聲。結尾處,拾來正是因為聽到了貨郎鼓聲,辨認出了自己的父親。大姑與拾來之父的私通,拾來對大姑的禁忌情感,都伴隨著貨郎鼓的出現。貨郎鼓可謂是與“仁義觀”相對抗的不潔象征。
鮑秉義唱的花鼓戲也是一個重要的民俗文化意象。花鼓戲是一種口頭傳唱藝術,源自民歌。它貫穿小說全文,象征著濃縮了五千年歷史的仁義觀。鮑秉義唱古唱出了自己作為孤老頭子的孤獨與凄涼,道盡了古往今來民間傳說故事匯聚而成的仁義史,拓寬了小說的時間和空間維度。尾聲,鮑秉義的唱古一曲終了,也隱喻著仁義觀的歷史到此結束,仁義自此走向沒落。
馬爾克斯和王安憶從各自的民俗文化中汲取豐富營養,將復雜紛紜的民俗意象作為隱喻象征。這些民俗意象一方面呈現出一種鮮明而獨特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當這些特定的民俗意象一旦融入民族心理的特定內涵,就能暗示出更深廣和普遍的社會意義。⑦
二、影響產生的條件
從作家個人和文本的比較出發,《百年孤獨》對《小鮑莊》的影響的產生條件是什么?為什么王安憶會自覺地選取《百年孤獨》作為自身創作藍本?
(一)相似的創作語境
《百年孤獨》與《小鮑莊》有著極為相似的創作語境。哥倫比亞所在的拉丁美洲與中國同屬第三世界,二者同樣經歷了深重的政治劫難,也同樣擁有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
19世紀到20世紀初,拉美相繼興起了克里奧約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社會現實主義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但它們并未在世界產生廣泛影響。原因主要是受歐洲文學影響過深,缺乏文學獨特性。面對拉美文學日漸式微的現狀,馬爾克斯清醒地意識到應走出歐洲文學的束縛,充分利用拉美本土文化資源來構建富有拉美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他在《百年孤獨》中正是不斷地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資源,以激活民族記憶,強化民族意識,尋求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
20世紀80年代,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開始邁向現代化進程。面對西方文學思潮的紛紛涌入,中國作家同樣感受到了如何處理自身民族文化和西方現代派文學觀念的關系的困惑,以及對本民族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缺乏話語權的憂慮。而拉美文學大爆炸包括馬爾克斯獲諾貝爾文學獎,使中國作家看到了第三世界文學走向世界的希望,得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啟示,民族自信心得以增強。有鑒于此,韓少功在1985年提出了“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⑧的宣言,正式開啟了尋根運動的文學思潮。借鑒了《百年孤獨》的王安憶,早在《小鮑莊》的創作實踐里就踐行了這一主張,將民族文化作為文學創作的源泉,《小鮑莊》也被視為尋根文學中的佼佼者。
(二)相似的文化反思立場
拉美文化是一種由古印第安文化、非洲黑人文化和西歐移民所帶來的基督教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如馬爾克斯所言:“我們的文化是一種混合文化,是博采眾長而豐富發展起來的。”⑨ 隨著歐洲殖民文化的入侵,拉美土著文化——印第安文化降為從屬地位。對此深感憂慮的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里,立足于印第安文化,以虛構族群聚居空間、書寫民族傳統信仰、引入民俗文化意象等技法建構了富有民族性的拉美文學。
從《百年孤獨》可以看出,馬爾克斯對待拉美傳統文化尤其是印第安文化的態度非常復雜。一方面,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入侵,他對本民族的土著文化懷有深沉的眷戀;另一方面,他也尖銳地揭露了拉美傳統文化的弊病,呈現具有現實指向的批判。他在諾貝爾獎致辭中曾說,《百年孤獨》的主題在于寫出拉丁美洲孤立封閉的現實。面對拉丁美洲動蕩不安的現實,馬爾克斯正是從更廣闊的背景——文化出發,以尋求當前政治的答案。
王安憶坦承馬爾克斯的民族文化反思立場對《小鮑莊》的創作有莫大影響,如她所言:“讀到《百年孤獨》你會很吃驚,在政治原因底下其實有著文化的原因,于是就進一步追問,為什么這樣的政治發生在我們的國度,發生在我們的民族身上,其中實際包含有地域、氣候、生存方式、文明教化種種原因。”⑩ 她從《百年孤獨》中獲得啟發,植根于漢民族的信仰、民間傳說故事和民俗文化,對以仁義觀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反思。與馬爾克斯相似,她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同樣曖昧。在她的筆下,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集中濃縮在撈渣的身上,她對撈渣代表的仁義精神充滿認同。然而,傳統的民族文化也有其落后愚昧的一面。《小鮑莊》里的村民固守封建禮教貞潔觀和長幼有序、等級分明的宗族觀。大姑因為害怕村民的非議,不敢與自己的私生子相認。拾來與寡婦二嬸的相戀被村民們視為丑事。小翠唯有等作為哥哥的建設子成親后,方能與弟弟文化子成親。從這一層面來說,村民們的身心不自覺地受到傳統文化的束縛與壓制。一方面,王安憶對積淀于人們集體無意識中的僵化落后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她又為充滿仁愛精神的儒家文化的失落唱出了一曲不舍的挽歌。endprint
從民族文學建構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在技法上還是在觀念上,《百年孤獨》對《小鮑莊》的影響都不可回避。然而,《小鮑莊》并非對《百年孤獨》的本土化復制,王安憶在師承馬爾克斯的基礎上,透視了本民族的精神狀態、思維方式和文化心理,建構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學。
{1} 王安憶、陳村:《關于小鮑莊的對話》,《上海文學》1985年第9期,第93頁。
② 王安憶:《小說家的第十四堂課》,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134頁。
③ 王安憶:《大劉莊》,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37頁。
④ 〔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范曄譯,南海出版公司,第360頁。
⑤ 葉繼宗:《尋找本民族的群體意識——〈百年孤獨〉與〈小鮑莊〉的比較》,《外國文學研究》1989年第1期,第108頁。
⑥ 陳光孚:《魔幻現實主義》,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頁。
⑦ 鮑煥然:《民俗與小說的遇合》,《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4期,第127頁。
⑧ 韓少功:《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5頁。
⑨ 〔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門多薩:《番石榴飄香》,林一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73頁。
參考文獻:
[1] 王安憶.大劉莊[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
[2] 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M].范曄譯.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1.
[3] 加西亞·馬爾克斯,門多薩.番石榴飄香[M].林一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4] 王安憶.小說家的第十四堂課[M].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
[5] 陳光孚.魔幻現實主義[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
[6] 王安憶,陳村.關于小鮑莊的對話[J].上海文學1985(9).
[7] 韓少功.文學的根[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
[8] 葉繼宗.尋找本民族的群體意識——《百年孤獨》與《小鮑莊》的比較[J].外國文學研究,1989(1).
[9] 鮑煥然.民俗與小說的遇合[J].探索與爭鳴,2005(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