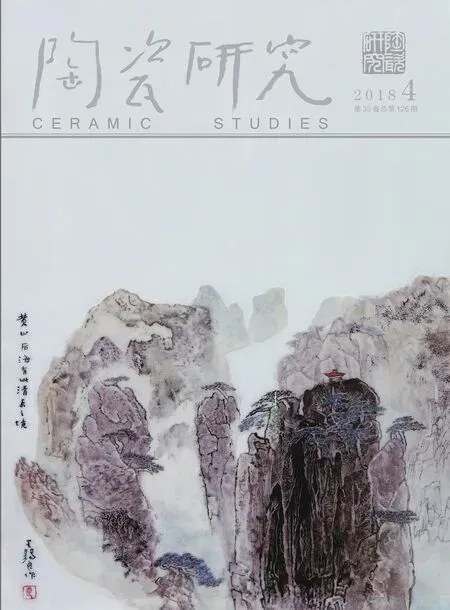佛教文化對(duì)中國(guó)陶瓷的影響探究
羅娜
(羅娜陶藝工作室,景德鎮(zhèn)市,333000)
1 佛教?hào)|傳和中國(guó)陶瓷的時(shí)間暗合
在中華文明的紀(jì)年斷代上,有一件特別值得玩味的事,即考古意義上的瓷器出現(xiàn)的時(shí)間和佛教傳入中國(guó)的時(shí)間有所暗合。
“新平冶陶,始于漢世”,但是瓷器的出現(xiàn)大約在東漢年間,以青瓷居多。“白馬馱經(jīng),佛教?hào)|傳”,是在東漢永平十年,中土的第一座寺廟在洛陽(yáng)誕生。之后,佛教步入本土化進(jìn)程,又被稱作“像教”的佛教,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開(kāi)啟了“表法”的新時(shí)代,也就是傳存至今的魏晉南北朝的佛教石窟石刻。在今天看來(lái),中國(guó)陶瓷雕塑的發(fā)展,植入了玉雕、泥塑、石刻等藝術(shù)形態(tài),其在造型上的優(yōu)美程度、技藝上的嫻熟程度及藝術(shù)語(yǔ)言上的豐富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佛教石窟。
這點(diǎn),從當(dāng)前出土的諸多文物,可以管窺一二。大抵從此,佛教——當(dāng)然是特指漢傳佛教和陶瓷文化的相互影響,直接或間接地從教義觀念、造型藝術(shù)等方面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2 佛教文化和中國(guó)陶瓷文化的器物關(guān)聯(lián)
如上所言,這種相互作用,首先是使用功能層面的,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器物的功能邊界,豐富了功能內(nèi)容,比如圍繞教義儀軌而產(chǎn)生的法器,比如佛菩薩的人物塑像。因特定的使用方向,器物不再僅僅是器物,而是具備了某種神性,成為了人與外部溝通的媒介。其次,是審美層面的,毋庸置疑是豐富了器物的造型和裝飾內(nèi)容,比如圍繞體現(xiàn)佛教精神而出現(xiàn)的紋飾符號(hào),被廣泛運(yùn)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亦有交集的元素種類,比如“蓮花”,成為被反復(fù)使用和表現(xiàn)的對(duì)象,是佛教之宗教特色,也是民族之性格特色。
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形式,在傳播途徑上,與其他宗教大同小異,譬如運(yùn)用禮制儀軌、圖像符號(hào)。禮制儀軌主要在物質(zhì)層面上展開(kāi),是關(guān)于“使用什么”和“怎么使用”的問(wèn)題;圖像符號(hào)主要在精神層面上展開(kāi),是關(guān)于“為什么使用”的問(wèn)題。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陶瓷在器物屬性層面上,因?yàn)槟撤N人為干預(yù)的神秘性,比如“人—手”、“泥—火”等變幻效果,以及囿于生產(chǎn)條件的不可控或偶發(fā)性,抑或說(shuō)是日常狀態(tài)下的某種不可言說(shuō),而具備了宗教表達(dá)的可能性。
3 佛教文化影響中國(guó)陶瓷的兩種路徑
在禮制儀軌方面,如前所言,器物的使用功能被拓寬,不再限于器物本身,而是作為親近佛陀、表達(dá)佛陀思想的“供器”。器物還是那個(gè)器物,但是功能被約定到了特定的范疇。粗看以為是被局限了,其實(shí)是被放大了。比如,幾乎與菩薩同在的一種瓷瓶,名叫“凈瓶”,或盛水,或插柳枝,在塑像面前,其尺度大小、位置方向,均有講究。其實(shí),它最初用于佛門(mén)剃度的場(chǎng)合,是一種盛水的器皿,因?yàn)橄笳魇嵉奶甓葍x式中需要事先凈手。之所以用于此種情景,是因?yàn)槠湓煨徒朴谒诜鸾痰闹卮笠饬x無(wú)須贅述。比如,幾乎被視為佛法傳承象征的一種器物,名叫“缽”,本為瓦器,后為陶或紫砂等,譬如禪宗六祖慧能流傳至今的遺物中有紫砂缽。原是僧人盛裝食物的物什,在諸多教義經(jīng)典中已被規(guī)制化,然而,在常人手中,不過(guò)碗爾。
在圖像符號(hào)方面,嚴(yán)格意義上可以視作器物的一個(gè)抽象化或隱喻化的生產(chǎn)過(guò)程,是基于陶瓷作為物質(zhì)載體的前提,是可以被修飾和雕塑的。最典型的,莫過(guò)于以紋飾的形式出現(xiàn)。當(dāng)然,廣義上的紋飾,包括了人物形態(tài)、植物形態(tài)和器物形態(tài),它們共同作用于某一件器物,使之成為佛陀的化身,或佛陀精神的具象,如前所言,它不再是單純的樣式,而是神性的,是可以和“佛—心”對(duì)話的一件法器,是被寄予了超越功能的。這一點(diǎn),在陶瓷制作商,往往以紋飾裝飾的形式出現(xiàn),包括繪畫(huà)、雕刻等。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蓮花”、“海草”等“八寶”。蓮花堪稱佛教“教花”,是佛教描述的凈土世界的象征,傳說(shuō)佛陀足有蓮紋,而且出世時(shí)步步生蓮。反觀中國(guó)陶瓷史,從唐三彩至當(dāng)下,屢見(jiàn)蓮花紋的應(yīng)用,而且對(duì)照云門(mén)、敦煌等石窟壁畫(huà)上的蓮花紋,相似度很高,而且從斷代上看,嬗變的時(shí)間也幾乎保持一致。總的來(lái)說(shuō),“八寶”作為佛教的經(jīng)典符號(hào),以極其繁茂的生命力存在于中國(guó)陶瓷的各個(gè)裝飾種類中,從單色釉的刻瓷,到清代的“裝飾大熔爐”,無(wú)一遺漏。“人物”作為佛教的法脈傳承符號(hào)如禪宗的祖師禪,以“一葦渡江”的達(dá)摩祖師形象為多,當(dāng)然,在明代,亦出現(xiàn)了佛教本土人物如“布袋和尚”的造型,它一度與“彌勒”在民間信仰中混淆不清。準(zhǔn)確說(shuō),從宋代開(kāi)始,尤其在清康乾,佛教作為宗教形態(tài),是朝廷政權(quán)縱橫的一種手段,因“禮”而制的陶瓷如宋官窯瓷、元青花瓷、清粉彩瓷等,隨著廟宇的廣建而以“八寶”、“人物”紋飾大量出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大量出現(xiàn)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很大程度上,與佛教本土化的興衰更替基本一致。梳理中國(guó)佛教史,佛教本土化大抵完成在晚唐,尤以中國(guó)禪宗為典型,叢林清規(guī)的建立在這個(gè)時(shí)期。禪宗“一花五葉”,至宋時(shí)蔚然成風(fēng),浸透到了文學(xué)藝術(shù)的骨子里;元時(shí)社會(huì)潦草,始終有“異域”氣質(zhì)的元青花深諳圖案符號(hào)的精髓;明代重禮制,在佛教和回回之間徘徊;清時(shí)擅技藝手段,工藝亦成熟,佛教的社會(huì)功能居重,佛教文化和陶瓷文化的融合是一劑安穩(wěn)廣袤疆域的好藥。
4 結(jié)語(yǔ)
如此種種,兩廂交融,無(wú)不生動(dòng)鮮活地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生活的面貌:佛教文化因其蘊(yùn)含的人之于美好生活的樸素情感,而有了吉祥意義;中國(guó)陶瓷因其物質(zhì)之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載體功能,而有了表達(dá)價(jià)值,共同成就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