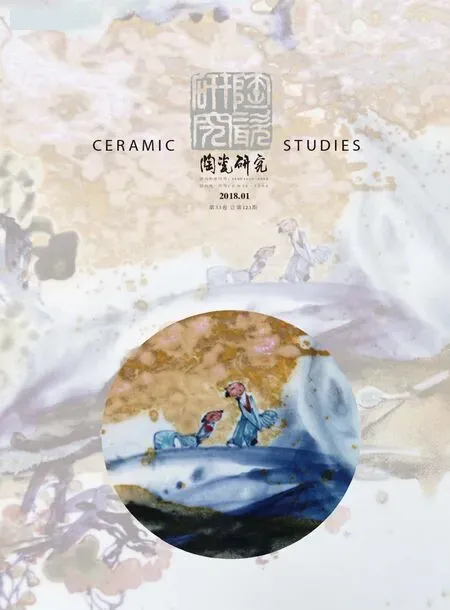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當代陶藝和影像技術(shù)的結(jié)合
李思安
(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景德鎮(zhèn)市,333000)
當代藝術(shù)從誕生之初似乎就一直伴隨著爭議,因此,有不少人為了避免爭端把當代藝術(shù)定義為時間上今天的藝術(shù),以此來區(qū)分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而事實上這樣的定義完全逃避了當代藝術(shù)的精神內(nèi)涵。在如今的藝術(shù)史上,我們可以明確地找到“當代藝術(shù)”這一專有名詞。當代藝術(shù),即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盡管是從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中孕育而生,但又對現(xiàn)代主義充滿質(zhì)疑,充滿反叛。在藝術(shù)史上,按照眾多國際上的專家和學者達成的共識,將當代藝術(shù)的誕生時間定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此之后,那些在當代藝術(shù)環(huán)境中繁榮生長的,同時又具有當代藝術(shù)風格的陶藝作品被陶藝學者定義為“當代陶藝”。
我們不可否認的是,當代陶藝是時代的產(chǎn)物,承載了當代的文化,是在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和資源共享的信息化時代這一大社會環(huán)境的母體中誕生。藝術(shù)與科技早已不是全然獨立存在于世,每一次科技的變革都會給藝術(shù)的意識和形態(tài)帶來改變,如1878年,美國人艾德沃德·麥布里奇第一次成功地使用攝影技術(shù)記錄了馬兒在奔跑時的動作記錄,從此人們看清了用肉眼無法抓住的瞬時,改變了以往的主觀臆斷。又如,波普藝術(shù)的繁榮正是因為它依賴于大眾的傳播媒體而被人們迅速認識并喜歡,在1970至1980年代,安迪·沃霍爾在各種領(lǐng)域無孔不入,有《安迪·沃霍爾電視秀》、《安迪·沃霍爾的十五分鐘》等電視節(jié)目,還有各種時裝秀和平面廣告。他一改以往藝術(shù)家特有的清高和冷傲,以特立獨行的姿態(tài)闖入大眾的視野,更是將藝術(shù)品拉入“復制”、“量產(chǎn)”的瘋狂時代,摒棄了藝術(shù)的原創(chuàng)性和技巧性,用算不上精巧的,流水生產(chǎn)的工業(yè)化產(chǎn)品將藝術(shù)品拉下原本崇高的地位。因此,當代陶藝也表現(xiàn)出了更多尚未開化的實驗性,我們也更加容易理解當代陶藝多元共生的樣貌。
當代陶藝的發(fā)展已經(jīng)有幾十年有余,我們不難看出陶藝的幾次蛻變。從一開始摒棄日用陶瓷,將陶藝獨立為藝術(shù),探索和征服土與火的變化到逐步重視創(chuàng)作者的個人情感,再到不以追求陶瓷的物性為目的,更加自由的將陶藝作品作為創(chuàng)作者思想傳達的媒介。一個完整的陶藝作品不應(yīng)該是從窯爐出來那一刻就完成了的,相反,在當代陶藝中我們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和實驗性,陶瓷也能和各種不同的材料發(fā)生碰撞,如玻璃、金屬、木材等等。另一些陶藝作品更加注重“場”的構(gòu)建,結(jié)合燈光效果、聲音效果、和影視動畫效果等等。這些陶藝作品無不豐富了我們的認知,有的甚至顛覆了我們已有的觀念。
這樣看來,當代陶藝似乎變得不再“專一”,它不僅僅是純粹的陶瓷,而是更多媒介,更多藝術(shù)種類的綜合。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更容易理解當代陶藝的這種不“專一”的現(xiàn)象。在社會心理學中有兩個重要的觀點如下:其一,我們構(gòu)建起社會現(xiàn)實;其二,社會影響又反過來塑造我們的行為。誠然,人類通過各種社會行為構(gòu)建起社會關(guān)系,而每個人的社會行為和社會觀念的總和又反作用于人們的社會活動。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面對如此豐富瑰麗的現(xiàn)實社會,各種藝術(shù)種類和藝術(shù)流派的碰撞,人們似乎難以專情于某一種藝術(shù)門類或者藝術(shù)流派,所以我們不難看到許多藝術(shù)家同時在多個方面都有成就。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有許多藝術(shù)家不僅在雕塑方面有杰出的造詣,同時也是偉大的繪畫家、建筑家或是詩人,意大利的米開朗基羅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再如,中國歷史上提倡的“書畫同源”,“書”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境,同樣也體現(xiàn)了我國文人對書法繪畫和詩歌的追求。人類對各種藝術(shù)的博愛促使了各種藝術(shù)的欣欣向榮,同時也催化了這種不“專一”的產(chǎn)生。
從1839年,法國的路易-弗朗索瓦·阿拉貢宣告了攝影術(shù)的誕生,到攝影技術(shù)的成熟,逐步成為獨立的攝影藝術(shù),再到錄像藝術(shù)的出現(xiàn),電視的普及、電影的黃金時代。在今天,影像技術(shù)早已不是遙不可及,而我們也每天生活在影像技術(shù)的包圍之中。這樣看來,當代陶藝創(chuàng)作者們運用影像技術(shù)介入自己的陶藝創(chuàng)作也顯得理所應(yīng)當并自然而然了。韓國弘益大學教授,陶藝家禹寬壕的作品《一萬個禮物》,就是由數(shù)千個大大小小的貍貓人偶組成,吸引人眼球的是旁邊來自不同人發(fā)來的人偶照片組成的照片墻。在每一次展覽,觀者都可以自行免費挑選一個陶瓷人偶,拍一張有趣的照片,然后將人偶的照片反饋給作者。這樣開放、互動的方式不斷地完善作品本身,使得陶藝作品不再孤零零地擺在展臺之上,而是和觀者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發(fā)生跨越時空的對話。在這里,照片不是完全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存在,而是與陶藝作品本身產(chǎn)生密切關(guān)聯(lián),并且與陶瓷共同組成完整作品來傳達作者思想的媒介。
另一方面,無論是威尼斯雙年展還是國內(nèi)的當代藝術(shù)展,在大部分的當代藝術(shù)展覽中,我們都無法忽視影像藝術(shù)的分量,它似乎是最符合當代藝術(shù)的代名詞。當代陶藝在尋新尋突破和回歸本真之間不斷迷離游走,當影像技術(shù)繁榮生長,當代陶藝搭上這根“橄欖枝”也許會顯得更加符合“當代”的身份。在社會心理學中,可以用“從眾”一詞來理解這種心理。這里要提出的是“從眾”一詞并非含有消極的含義。從眾,不是簡單地與他人保持一樣的行動,而是個體受到大眾的影響,并且從內(nèi)心真誠地接納認同,從而保持行為上的一致性。它不同于順從和服從,它是經(jīng)過個體的判斷之后構(gòu)建到已有的價值觀念體系之中,是具有思想性的。當代陶藝創(chuàng)作者的這種“從眾”行為正是基于本人對影像藝術(shù)的欣賞和認同,從而運用到自己的陶藝創(chuàng)作中來。如澳大利亞的陶藝家皮普·麥曼納斯的作品《夜船》,記錄了泥土塑造的人在水中逐漸分化、消融,最后只剩懷中抱著的小船在水面上獨自漂浮,用一種悲壯的形式訴說種種有關(guān)人性的話題。又如,我國青年藝術(shù)家耿雪的《海公子》,是一個以陶瓷人偶為原型,用陶瓷布置故事場景,拍成動畫小短片形式展示了一個山海經(jīng)中的故事。這些作品我們很難用傳統(tǒng)的定義來界定這是不是陶藝作品,但不可否認,影像技術(shù)的確給當代陶藝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當代陶藝和影像藝術(shù)的跨界組合,極大地豐富了陶藝創(chuàng)作的領(lǐng)域,也為陶藝創(chuàng)作者們提供了新的契機和新的語言。在這種藝術(shù)與藝術(shù)的結(jié)合碰撞中,陶藝的邊界似乎也變得模糊,這種模糊也提醒著我們不得不重新探討當代陶藝種種新生的問題。
盡管當代陶藝和影像技術(shù)的跨界組合顯得并不是那么的主流,但是我們依然有理由相信它具有生命力。它為我們構(gòu)建了新的視覺效果和審美方式,也為陶藝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理念表達和更具開放的公共性。當代陶藝方興未艾,它快速而又多元的變化是我們所始料未及,因此也讓我們更加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