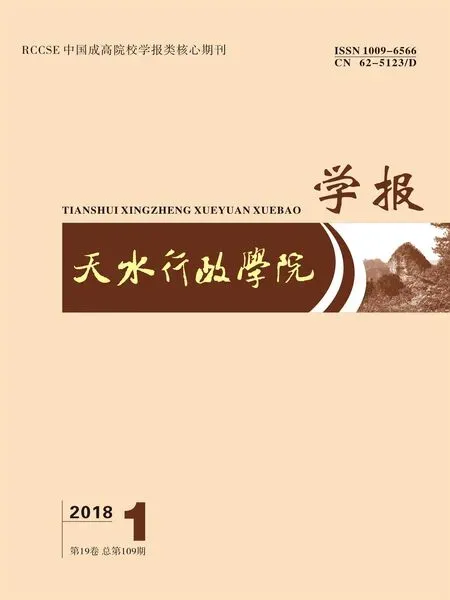“大資管”的性質回歸與監管路徑
辛雨靈
一、問題的提出:“大資管”戰場的“亂象”與“險生”
資產管理是我國近年來金融市場上發展勢頭最猛的金融創新工具。雖然對其概念至今未能形成統一,但一般認為,現代資產管理業務起源于美國,最初是投資銀行管理人及其相關人士的資產,后逐步演變為機構或個人委托專業金融機構管理資產的一種金融業務[1]。在我國雖然起步較晚,但2012年我國重啟資產證券化以及各類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創新后,資產管理行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點到面的發展過程。從一開始狹窄的公募基金到如今以公募基金、陽光私募基金和券商資管三足鼎立的“大資管”格局,行業內更是不斷以各種創新方式加速打破原有資產管理者之間的產品界限和分業壁壘,深刻改變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產品結構[2]。與此同時,毫無顧忌的“大資管”創新潮流中也隱藏著眾多風險。
一方面,市場上打著各類“資產管理”名號的業務風起云涌,實際中資產管理的模式千姿百態。由于“資產管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國內資管行業對其外延和內涵均未能形成統一,甚至在定性上就已經產生諸多爭議,或為信托或為委托并不一致,各種類型的資管產品亂象橫生。這就直接導致在不同概念理解下,資產管理的實際操作難免會有爭議,例如以資管計劃購入股票中的表決權行使、實際控制人和一致行動人的判斷、信息披露義務人的判斷、信義義務的存廢與程度等等就會因信托或委托的不同定性而產生不同結果,對此問題業內也是眾說紛壇、莫衷一是。
另一方面,為了應對伴隨著復雜而大規模的資管產品而來的監管困境、控制其給市場穩定帶來的隱患,在傳統“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思維模式的指引下,不同行業對資產管理業務頒布了不同的管理辦法。具體包括《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證券公司集合資產管理業務實施細則》、《證券公司定向資產管理業務實施細則》、《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暫行規定》、《期貨公司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關于保險資產管理公司有關事項的通知》、《關于保險資產管理公司開展資產管理產品業務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信托公司集合信托管理辦法》等等,將不同金融理財產品歸屬不同的監管部門,大致分為信托理財計劃與商業銀行個人理財產品由銀監會監管、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與基金公司的證券投資基金由證監會監管、保監會則監管保險公司開發的具有投資理財功能的險種,且不同機構監管下的資產管理又對各自的金融理財產品的準入條件、發行條件、募集對象、審批條件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投資風險分擔、資金使用要求、監管措施及法律責任方面的內容“各自表述”[3],因此也造成了金融理財監管“政出多門”、標準不一、監管重疊、體系紊亂的格局[4],原本資產管理機構的“專業性”都外化為“持牌”沖動。規避監管而產生的各種銀信合作、銀基合作等通道業務應運而生,復雜的資產管理之間更是互相嵌套,投資者往往對此無所適從,資產管理實際上成為金融市場“牌照玩家”斂財套利的工具,無疑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雪上加霜”,更使投資環境險象環生。
“大資管”格局的形成和深化實質是鉆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之漏,并以“四兩撥千斤”之勢顛覆了我國傳統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在分業監管難以應對這種混業經營的趨勢、“大資管”的監管卻刻不容緩的情況下,對資產管理的性質定位必然是首要任務,但到底是將市場中所有名為“資產管理”的產品納入麾下,還是明確區分定義“資產管理”的本質屬性?又是否有一個性質定位可以囊括所有所謂的“資管產品”?同時,怎樣的監管路徑才能在維護金融創新靈活和市場活力的同時,恢復市場的穩定有序呢?
二、資產管理的性質回歸
資產管理的性質定論是解決資管運作與治理問題的首要基礎。目前,對各類資產管理所涉法律關系定性爭論仍然存在,主要有“信托說”、“委托代理說”,其他還有少數人持有“行紀合同說”、“合同關系說”、“物權二元結構說”、“綜合法律關系說”等觀點[5]。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劉燕教授富有創造性地提出,因為資產管理項下的交易結構往往是一系列復雜的“合同包”,難以為一種有名合同所能涵蓋全部內涵,而越加成熟的資產管理成長為一種獨立的商事活動,往往涉及到組織和行為雙重層面的規范,不是信托或委托關系項下的任一法律可以全面規范的。因此,為了解決資產管理信托和委托性質爭議的困境和定性不足,類比合伙、公司這樣的商事組織體,以SPV框架來認識資產管理,反而有利于從宏觀上對具體問題的解決[6]。但事實上,SPV作為“特殊目的實體”,本身就不是一個法律概念,而是用來描述金融市場參與者為投融資目的而構造的一個與發起人破產隔離的金融實務術語[7]。或許在相關理論成熟之后可以超脫于公司、合伙等組織形式成為與他們并列的商主體概念,其合法性也的確已經在證券、銀行、基金等行業規范中得到確認,但在理論和實務對SPV框架的具體內部治理、外部法律關系的研究都處于初級階段的現在,這種“特殊目的載體”毫無疑問是比資產管理概念更廣的上位概念,這種提倡也只能作為推動SPV相關理論發展的助力,并不能有助于目前資管行業統一監管規范的形成,更無法有助于解決目前關于資產管理的性質爭論。
因此,回歸到資產管理的性質之爭,其實是源于目前金融實踐中以信托型和契約型這兩類資管產品的種類最多。要治理資管產品橫生且不一的亂象、統一監管,就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做出清晰、統一的選擇。
(一)信托性質的再定位
現代信托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被理解為“受托人基于委托人的信任,以名義所有人身份,就委托人授予的財產為受益人的利益進行管理和處分的行為”[8]。其特點包括信托財產的完全獨立、受托人全權管理處分的權利、信托財產管理的虧盈都為受益人承擔、受托人只收取傭金。因此,如果暫時不論實務中特意被設計成的契約型資管產品,立足于資產管理“代客理財,自負盈虧”的宗旨,本身作為一種投融資工具,資管計劃與信托計劃處于同等地位。那么,有關其信托性質的猶豫又來自何處呢?只是因為實務中的契約型資管產品恐怕也不足以成為維護資產管理委托性質的全部理由。其實,真正的根源還是在于我國對“信托”概念理解的偏差,和由此引發的法律缺陷。
首先,由于對物權概念的理解不一,大陸法系國家在引入信托制度時均有不同程度地偏離英美傳統信托的典型特征,但我國尤為明顯。最典型的就是我國的《信托法》第二條為規避物權之爭,對委托人財產交付給受托人過程的描述措辭為“委托”,以委托人為中心,而規避了傳統信托關系中的“受托人中心主義”,使得在受托人和受益人財產權利的紛爭之外還多出了委托人原始所有權的爭議。同時,信托登記的缺失也導致信托的法律地位混沌不清,遑論如何表彰信托財產的獨立性[9]。加上《信托法》給委托人保留的權利之多也在事實上改變了傳統信托性質的要求,這種極易與委托代理模式相混淆的制度設計無疑成為資產管理性質定位的絆腳石。
其次,由于我國在信托理念移植過程中的缺失,立法中也產生了偏差。《信托法》第四條規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機構形式從事信托活動,其組織和管理由國務院制定具體辦法”,明確了我國《信托法》和《信托業法》兩分的立法取向。然而迄今為止,國務院并未就信托機構的組織和管理出臺行政法規,作為民法性質的《信托法》只是對信托當事人、信托行為、信托法律關系做出了規定,難以作為對信托業整體運行監督的行政法律加以規制。實踐中,由銀監會頒布的《信托公司管理辦法》替代了國務院的立法職能,使得本應作為一種通用于資產管理工具的信托及信托關系,卻成為銀監會管轄下信托公司的專屬業務和工具。同時,在傳統分業監管的“牌照”思維模式之下,市場排除其他未經監管部門核準的公司經營信托業務[10],那些其他金融機構展開的事實上的“信托關系”只在各監管部門的規章及規范性文件中來規制。在《信托業法》的缺位下,作為新生物種的資產管理,無法對其性質定位找到統一的法律依據,造成法律關系混亂的局面。例如證監會在《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等法律規范中將立法依據定位為《基金法》,才得以信托財產獨立的法律效果來宣傳自己的資管計劃,但在之后的《基金管理公司單一客戶資產管理合同內容與格式準則(2012年修訂)》中,又在法律關系層面開始尋求《合同法》作為上位法,允許委托關系的存在,似乎是信托卻又實在引入了委托關系,模棱兩可。而這樣在上位法上的混亂絕非一例,根源在于市場對法律漏洞的投機性,使得原本就適用《合同法》的委托代理關系成為性質判斷的桎梏。
最后,回到金融市場中資產管理的亂象。除了證券投資基金和私募基金明顯地體現了信托的特征外,其他很多打著“資產管理”旗號的產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背離了受托人獨立的“代客理財”的管理權,和受益人“自負盈虧”的要求,從而引發在提煉資產管理特征、總結資產管理性質的過程中產生困惑。例如通道類業務在實質上架空了受托方獨立管理人的地位,往往由一些強勢委托人直接決定資金投向和銷售客戶,從而在根本上顛覆了“代客理財”的資管本質而具有更濃厚的委托代理特性;再如資金池業務中混合了各個受托的獨立財產,且具有自營性質的可能(尤其在資金池投資收益超過發行預期收益,剩余收益歸受托人享有),也是一些金融機構規避監管的手段,尤其是作為“影子銀行”的一部分,已經受到規制;另外一些剛性兌付下的保本保息業務,更是完全背離了信托關系下受益人自負盈虧的風險模式,而在實際上變為一種實際上的借貸關系。
以上種種原因最終導致了委托代理法律關系干擾了資產管理信托性質的統一。而事實上,如果擺脫我國對信托概念的理解陷阱,回歸到資產管理本身,作為財產管理的重要方式,“大資管”與信托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也只有信托能夠為其發展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
1.未能逃避信托結構本質的資產管理。
大部分的資產管理中,委托人為了財產的保值增值才將自己的財產交付受托人,其不僅是被管理財產的原始所有人,也是財產管理的利益和風險最終承擔者。雖然信托的典型結構是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結構,但在信托分類中根據委托人和受益人是否重合也分為自益信托和他益信托。資產管理中委托人、受益人身份的重合就是典型的自益信托。雖然市場上充斥著類型復雜的資管產品,但拋開那些明顯用來逃避監管、充滿存廢爭議的通道、剛性兌付等業務而言,大部分的資管產品都是在信托概念下進行操作的,典型就是一對多的集合類資管產品。即便是被認為最具“委托”特性的一對一資管產品,趨于實際商業運作的必然規律,在現實中難以真正實現信托性質上完全的“受托人獨立管理”的要求,也依舊不足以顛覆其“信托關系”的基礎。只要在監管規范允許的范圍內,定向資管產品只是與集合資管產品受托人自主管理上有著程度的區別[11]。而一些資產證券化產品均在法律上得到了實質信托性質的承認,多為典型的他益信托。因此,雖然三方結構的程度不同,但這種名義上的區分是與委托代理法律關系代理人、被代理人兩方結構相區別的首要特征。
2.受托財產的獨立性價值。
信托概念下的資管,由受托的資管機構取得受托財產的名義所有權,這種所有權不僅與投資人的財產獨立、與受托機構管理的其他投資者財產獨立,也與投資管理人自身的財產獨立,資管機構由此取得以自己的名義處分和經營該筆財產的絕對權利,直至資產管理目的的實現。區別于委托代理中財產因從不歸屬于代理人,管理、事務的決策都必須依賴于被代理人指揮,在信托模式下,信托財產的所有權歸屬就算在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間有爭議,也絕不再歸屬于委托人。資管機構不再淪為被委托人“操縱”的傀儡和逃避監管的通道工具,更能實現資管產品作為金融創新的設計初衷,發揮其實際應用價值。
3.信義義務有助發揮受托人管理主動性。
基于信托性質下的財產獨立性,受托人享有對受托財產獨立支配、管理權利,但同時也必須負有較高的勤勉、忠實的信義義務,不能濫用自己支配地位和權力損害委托人或受益人地位,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定責任。但即便這種信義義務對管理人有所約束,也是信托關系中的本有之義,是對受托人權力的合理限制,并沒有破壞受托人的自主管理能力。相反,委托代理本質上是一種消極、被動的管理方式,且僅在過錯的情況下承擔責任,依據委托代理詮釋金融理財將極大限制資產管理公司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12]。
概言之,雖然我國在移植英美信托概念和制度的過程中產生了偏差,但其實,擺脫行政資質的束縛,僅從產品本身的法律結構和理論分析,大多數資管產品依舊是實質上的“信托產品”。那些背離了信托性質的資產管理如通道業務、剛性兌付等,本身存廢的合理性尚有爭議,更不應成為破壞資產管理信托性質屬性的例外。
(二)委托代理性質陷阱的剝離
委托代理是我國民法代理類型中的一種。《民法總則》第七章第二節中對于“委托代理”做了專節規定,雖然理論上認為這種稱謂其實是立法者未能區分代理的基礎關系與授權關系,而誤將理論上的“意定代理”理解為“委托代理”[13],但本文所討論的資管計劃中是典型的“委托基礎關系”,由“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權”,受托人根據委托人的指令管理財產,而委托人仍然保有對受托財產的所有權。
我國現有所謂資管計劃中確有許多以委托人的名義而非受托人的名義管理受托財產。例如雖然在證監會出臺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中,對資產委托人做出了“不得要求資產管理人在證券承銷、證券投資等業務活動中為其提供配合”,“不得違反資產管理合同干涉資產管理人的投資行為”的要求,但在對所謂的定向資管計劃即“一對一”資管計劃中,《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第三十一條明確規定了“證券公司辦理定向資產管理業務,由客戶自行行使其所持有證券的權利,履行相應的義務”,從而確立了定向資管計劃的委托代理法律關系。而就算是在“一對多”的集合資管計劃中,尤其是結構化模式之下出現兩種不同類型的委托人和受益人,優先級有固定回報的承諾,劣后級獲得剩余回報、率先承擔風險,往往因此以獲得決策權為對價,最終還是很容易陷入了委托代理的關系中。而這種模式下的受托管理人只是消極的財產托管、清算與記賬等信托事務管理服務的提供者[14]。
對此,有學者犀利指出,那種在規范文件中做出委托代理關系確認的規定,是因為在分業監管體制下,不同監管機構的監管原則發生沖突。在監管權力的“爭奪”中,這種法律關系成為中國證監會的一種刻意安排[15],是人為扭曲了所謂委托理財的信托屬性,有意規避我國金融法律監管制度[16]。而那些在上文所述的資產管理泛濫亂象中的通道、剛性兌付等產品更是規避監管的產物。
的確,在委托代理關系下,托管賬戶中的財產屬于委托人,只是以代理人的名義持有。代理人如果完全依據委托人的指令進行證券投資活動并據此收費,在證券類的資管計劃中已經構成《證券法》下的證券經紀業務,也涉嫌違反賬戶實名的強制性規定、場外配資等諸多問題,更為本質的還是涉嫌規避“本業”監管。
(三)小結
概言之,由于對物權概念的理解不一,我國在移植英美信托制度的同時也在法律層面對傳統信托概念的理解和治理產生了偏差,導致資產管理行業興起之時沒有合理的上位法作為信托性質定位的依據。加上分業監管模式的影響,進一步引發了市場各類資管產品泛濫的亂象,從而使資管產品陷入與委托性質的紛爭。若資產管理行業規范一直陷此泥潭,則不僅可能影響資產管理行業的自身運作,還會進一步干擾到企業并購、公司治理、證券監管等層面的判斷。
但其實,回到資產管理“代客理財,自負盈虧”的宗旨,目前市場上大多資管產品并未能逃脫信托屬性。信托屬性下受托財產的獨立性、信義義務的約束也更能激勵受托管理人勤勉、忠實、合規地投入到財產管理之中,有助于在“大資管”趨勢之下,資管公司對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至于其他通道、資金池、剛性兌付的理財模式是否具有存續的必要,是限制還是禁止則是另外的課題,決不能陷入他們給資產管理性質判斷帶來的“委托性質”陷阱,而必須堅定地回歸到資產管理信托性質的本源。這也預示著信托業整體正迎來蓬勃發展的春天。
三、性質回歸后的監管路徑探析
金融風險有系統性風險和金融風險本身兩部分。雖然系統性風險對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存在巨大的危害,但金融風險本身是金融市場創新和充滿活力的源泉,且正因為金融風險的存在,才能對市場主體的行為起到約束作用。可以說,金融的本質是經營風險。在這風險經營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做好財產管理公司內部的風控,外部監管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大資管”背景下,從事資產管理的機構往往橫跨銀行、證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等,牽扯金融市場內部多個子市場,其應用也涉及了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證券法、基金法、銀行法等眾多法律門類,操作愈加復雜、混業趨勢加強,更隱藏著巨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對此,我國監管層祭出了“穿透”的法器。例如在銀行業監管中以層層穿透的監管方法引導影子銀行的消減,防止風險錯配和系統性風險的失控;再如對證券市場中資管計劃層層穿透式監管,防止出現規避法律的公司、股東和投資者,使得監管信息透明化,從而防止非法集資等風險的出現。
但是,由于現有分業監管模式下往往標準不一、顧此失彼,使得“金融創新”逐步背離了資產管理的本質,引發“偽大資管”現象。重大市場風波事件中對風險控制的失控,打擊了市場參與者們的信心,對市場活力起到抑制的消極作用,行業法規的設計中更引起不同監管部門之間的齟齬。雖然對監管模式改革的提倡為時已久,但在對“大資管”信托性質回歸的探討后,才能真正把握監管改革的路徑。
(一)從機構型“分業監管”向功能型“混業監管”的升級
1.機構型“分業監管”的困境。
以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不同機構作為劃分監管權限的依據,某類金融機構的所有業務活動均由其所歸屬的監管機構監管的模式便是機構監管[17],也是傳統意義上所稱的分業監管。我國的資管行業一開始就是在分業監管的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從1995年到2003年,從證監會到銀監會,為解決私募、公募等金融創新下的監管真空,我國逐步確立了“一行三會”分業監管的格局,這也是世界各國在金融業發展中必然會采用的初始金融監管模式。例如英國在1997年成立金融服務局(FSA),頒布《金融服務和市場法》(FSMA)以及美國在頒布《金融服務現代化法》(GLBA)之前,均是對混業經營加以限制,分別成立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行駛各自的監管職能[18]。
由此,在資產管理行業體系內,央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分業監管格局下的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等,各自發展資管計劃;在體系外,非屬一行三會監管的第三方機構借助監管真空的寬松環境和對市場真實需求的靈敏反應,在資管業務種類和管理資金規模上取得了巨大發展,逐步成為資管行業的領軍隊伍。這樣一種第三方資管機構監管缺位的問題,直到《證券投資基金法》(2012修訂)和2013年中編辦印發《關于私募股權基金管理職責分工的通知》明確將PE基金的監管權授予證監會之后,才在大體上解決了監管真空的問題。
但是,誠如本文提到,逐步混業經營下各類資管服務提供商的產品盡管在內容特性上并無二致,卻因監管缺乏統一性,尺度張馳不一,埋下了制度套利的隱患[19]。同時,這樣一種分業監管的模式雖然避免了業務重疊和監管重復,但相對的,嚴格監控框架下金融市場可發展的空間也較小,商業發展的趨利性受到限制,突破是必然。
2.功能型“混業監管”的必然趨勢。
以金融機構從事的不同業務或者說履行的不同功能作為監管依據,同類金融業務由相同監管機構監管,不論從事該業務的是何種金融機構的監管模式就是功能監管、混業監管[20]。其基本原則是以金融產品為中心,相似法律關系的產品受到類似的監管,而不再以原先監管機構分屬不同金融領域為中心。
正如上文所述,我國目前資產管理行業的規模已經足以導致系統性金融危險,分業監管已經難以兼顧、不堪重負,但仍然缺乏相應的宏觀審慎監管。從國際趨勢,當資管機構的業務和產品出現交叉而機構監管難以有效防止監管套利等積聚風險的行為之后,功能監管往往應運而生,典型就是美國在1999年GLBA通過后的監管體系[21]。在我國,雖然混業監管還沒實施,但在監管機構內部已經開始進行結構調整。2017年2月,多家媒體披露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透露出了統一監管的趨勢。剛結束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也明確了未來在“一行三會”之上建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統一監管的指引。這樣的混業監管已是“大資管”背景下必然的金融監管改革趨勢。
(二)《信托業法》亟待出臺
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所論述的那樣,各金融機構開展的資管業務的基礎法律關系應當回歸到實質意義上的信托,這也揭示這信托業整體對金融各領域滲透的必然趨勢。然而在法律層面,只有信托公司的信托理財才明確適用《信托法》,其他金融機構均不受此調整。但即便是《信托法》,屬于民商法范疇而不具有行政法屬性,自身缺乏對信托業監督管理的規定。這種《信托業法》的缺失,導致落入實質信托性質的資管產品沒有監管的上位法依據,各監管機構都欲將自己領域的資管產品納入“麾下”,造成監管混戰的局面,形成監管套利的空間。因此,對資產管理信托性質的回歸也將倒逼《信托業法》的建成,以統攝各類金融理財行為,為混業監管的形成提供更為合理的上位法依據。
(三)小結
應該說,在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以機構監管為中心的分業監管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著控制金融市場風險、穩定金融市場秩序的作用。只是在“大資管”的背景下,資產管理機構的業務已然發展到業務交叉互融、產品同質化競爭的階段,以不同名目出現的資管產品卻在基礎法律關系或基本特征上高度一致,囿于目前分業監管模式下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形成不同資管機構提供的同類資管產品或業務受到不同監管部門差異化監管的局面,為市場投機者帶來監管套利的空間。因此,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監管必須在明確資產管理信托法律性質的基礎上進一步向標準化、統一化的功能監管邁進[22],并以此為契機,倒逼《信托業法》的出臺,從而更好地指引“大資管”的混業監管,乃至對我國信托概念的理解偏差撥亂反正。
四、結語
資管計劃本身是價值中性的金融工具,其為適應、推動商事交易的發展而在民商法律關系中靈活設置出的模式在理論上不應受到過分的限制,但其在發展中觸發的風險對金融市場穩定造成的波動亦不可視而不見。這其中隱藏的不僅是一些通道、剛性兌付等投機資管產品、復雜嵌套中的投資風險問題,還有例如結構化資管計劃本身復雜的法律關系在遇到商事組織主體治理的過程中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包括投票權、實際控制人、一致行動人等等,已經對我國現存的監管模式造成挑戰。
對于這其中的矛盾,從脫韁的混業經營回歸到資產管理應當圍繞“代客理財,自負盈虧”為宗旨的信托性質是解決問題的基礎,也幫助我們進一步明確資產管理的內涵并不是用來囊括市場上存在的所有以“資產管理”為名目的理財模式,那些實際是委托代理關系的資管產品更是背離了資產管理設計的初衷,穿著皇帝的新衣成為規避監管的幫兇。更為重要的是,“大資管”的崛起牽涉多個法律部門、金融領域的合作,也催促著傳統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改革升級的必然進程,更倒逼上位法《信托業法》的建設,將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全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姜再勇.關于國內資產管理業務發展問題的思考[J].金融監管研究,2013,(11).
[2][11][18][21]郭強.中國資產管理:法律和監管的路徑[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2,22-23,62.
[3]黃韜.我國金融市場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的法律路徑——以金融理財產品監管規則的改進為中心[J].法學,2011,(7).
[4]胡偉.大資管時代金融理財監管的困境與出路[J].財政金融,2013,(6).
[5]李景欣,李楠.銀行個人理財產品的法律分析[J].法商研究,2007,(5).
[6][22]劉燕,樓建波.企業并購中的資管計劃——以SPV為中心的法律分析框架[J].清華法學,2016,(6).
[7]樓建波.特定目的營業主體在商法上的地位———兼論商主體的規制原則[J].社會科學,2008,(3).
[8]元照英美法詞典[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360.
[9]樓建波.信托財產分別管理與信托財產獨立性的關系——兼論《信托法》第 29 條的理解和適用[J].廣東社會科學,2016,(4).
[10]黃韜.我國金融市場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的法律路徑——以金融理財產品監管規則的改進為中心[J].法學,2011,(7).
[12]胡偉.大資管時代金融理財監管的困境與出路[J].財政金融,2013,(6).
[13]朱慶育.民法總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329-340.
[14]劉燕,樓建波.企業并購中的資管計劃——以SPV為中心的法律分析框架[J].清華法學,2016,(6).
[15]劉正峰.證券賬戶名義持有人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7,(5).
[16]劉少軍.信托業經營的法律定位與公平競爭[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1,(1).
[17][20]巴曙松,陳華良,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發展報告(2013)[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19]郭強.求解私募基金監管體制[J].新世紀周刊,2013,(42).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