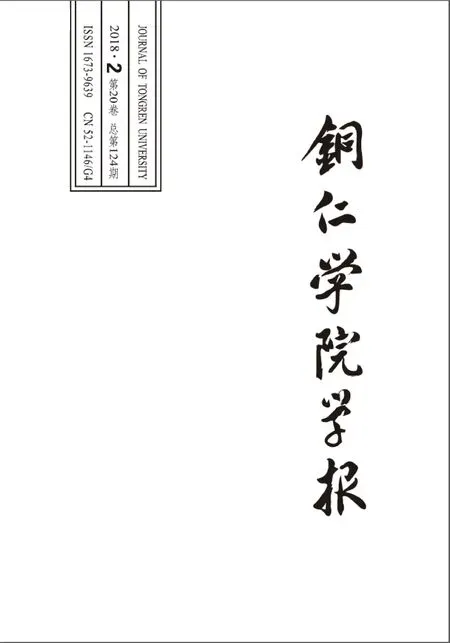霍布斯與洛克自然法思想的比較研究
張 衛
( 鄭州輕工業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
從自然法的思想演化史來看,存在從“合乎自然秩序”到“合乎權利秩序”的轉向。霍布斯與洛克正是這一思想轉向的有力推動者。他們的自然法思想滲透了十七世紀英國社會的各方面,進而塑造了現代英國。
霍布斯與洛克的自然法思想都具有革新色彩,但旨趣相異,立意、觀點與目標也不盡相同。本文從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兩個核心要素“理性”與“自然狀態”切入,對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思想進行比較分析,具體考察他們思想上的這些差別,能使我們對這一時期的自然法思想的發展演變有更為細致準確的理把握。
一、霍布斯自然法思想中的理性要素
古典學者一般將理想人的完善本性作為基本出發點,認為人是天生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動物。人應當努力完成對自身本性的認識和復歸。如果復歸達成,那么人便也自然而然地享有了和諧的社會政治生活。霍布斯摒棄了這種傳統的論述方式,自我保存觀念成為他全部政治學的起點。他逐條列舉的自然法以及它們包涵的規范性內容,雖然對世俗的政治建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這些自然法法條本身卻是從更為基本的一組觀念中析出。自然狀態、自我保存、自然權利、契約、理性訓誡(自然法)和主權者,這些觀念及其關聯也構成了霍布斯自然法思想的基本圖景。
首先,生活在自然狀態中的人的總是處于“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狀態。人們都傾向于自我保存,而在自然狀態中,自我保存的方法和手段則出于激情或情感。霍布斯提出了造成人與人彼此爭斗的三種原因:競爭,猜疑和榮譽——“第一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利益、第二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安全、第三種原因使人為了求名譽而進行侵犯”。[1]94它們存在于人類的天性之中。顯然,直接依照人類天性的生活只能將人類帶入悲慘和毀滅的境地,自然狀態等于戰爭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強調這種戰爭狀態不僅存在于真實發生的攻擊和傷害之中,而且存在于人們普遍的戰爭意圖之中。伴隨普遍戰爭意圖的是普遍的恐懼情緒。正是由于強烈的恐懼感,使人們注意到并認真傾聽理性的聲音;與此同時,霍布斯指出,人的理性能力不只依附于激情,而且巧妙地利用恐懼這一特別突出的激情樣式——“理性的任務就成了尋找到一種辦法以引導和加劇對死亡的恐懼和對舒適的渴求,從而超越并進而消除追逐榮譽所帶來的破壞性效果”。[2]471
其次,霍布斯堅持認為無論人類的天性表現如何都是無可指責的,因為道德哲學正是基于對人類天性的考察才建構起來,一般的道德評判標準只是這種考察的結果。人要自我保存,人的天性又割舍不掉競爭、猜疑和榮譽,那么每個人為此做出的行為和采取的手段也只是人的天性使然。霍布斯的推論在他的敘述邏輯中合情合理:“人類的欲望和其他激情并沒有罪,在人們不知道法律禁止以前,從這些激情中產生的行為也同樣是無辜的”。[1]95據此,霍布斯提出了極富現代性色彩的自然權利觀念。自然狀態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狀態,也是每一個人對一切事物都享有權利的狀態。這種權利在自然狀態下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擁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當戰爭意圖普遍地浸透在人們心中的時候,每個人隨時有可能亦有權利去掠奪和毀滅他人,與此相應,每個人也隨時有可能被他人掠奪和毀滅。“正因為這種權利的效用總是相同的,就如這種權利不存在一樣”。[3]29“每個人對一切事物享有權利”只是一種修辭,這與“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并無實質區別。自然狀態下的自然權利顯示出無可救藥的悖謬意義,愈是享有完全的自然權利,愈是深陷自然狀態難以自拔。那么自然權利如何才能夠發揮積極作用?這便要訴諸于自然法。自然法以權利的相互放棄或轉讓,即契約,來規避自然權利的悖論。但被放棄或轉讓的權利并未消失,它們集合成“共同權利”,也即“主權”或“主權者”——這是簽訂契約的直接后果。
最后,主權者的出現是使先前的自我保存到契約簽訂理論的論證得到實現的保障。人類必須從自然狀態走向和平狀態,而這必須依靠主權者所能發揮的力量。國家的誕生和世俗政權的建立,以及主權者所享有的絕對權利最后保證了自然法,也保證了人類的和平。顯然,在霍布斯的自然法思想體系中,主權國家(利維坦)才是人類思想和行為真正的守護神。與根據主權者意志擬定的實證法有別,自然法作為實現和平的引導條件,將善惡的尺度從個人的欲望與意志中轉移出來。
盡管霍布斯是近代理性主義自然法思想的重要代表,但理性在其思想體系中的位置頗為尷尬。自然法雖是理性的訓誡,但理性并未被復刻到人性之本,即便占有一席之地,也湮沒在強大的激情與情感力量之中。理性顯示出的力量不過是一份薄弱的理解力量。純粹的理性力量在霍布斯的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中顯得無能為力,它必須通過與激情的合作并依靠激情的力量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進而標明自己的身份。在霍布斯的整個政治學推論中,理性既沒有充當推論的原因,也沒有成為推論的結果。強烈的情感才是這一切推論的根源,并一直不斷地為推論提供動力。理性的任務則僅屬“認識論”范疇,以它的修辭力量更正或祛除情感力量的盲目性。理性要求人們簽訂契約,而“契約本身只是空洞的言辭”[1]135。這一任務的完成完全依賴主權者提供的強力,不然單憑文字的力量根本不足獲取任何有意義的成果。雖然人類的理性能力教導給人類永恒的自然法,且唯有研究自然法的科學才是真正的道德哲學,但道德哲學所致力追求的“和平”被自然法認清面目之后,卻得不到自然法的保障。
霍布斯對待理性曖昧不明的態度使其自然法思想顯得并不徹底。他拒絕承認人類具備某種完善本性,更不曾設想人類能夠通過理性之光的照耀而安享品德高尚的生活。霍布斯的敘述中不斷出現的是“每一個人”的激情、理性和權利。他一一確證了這些個體能力,卻對這些能力不抱充分的信心。盡管人類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自然狀態,可以不再依靠天命的自然和上帝的自然,但最終拯救人類的只能是“另一個上帝”利維坦。在那個啟蒙開啟和認識論轉向的時代,霍布斯于時相宜地回復到個體,個體權利被一再提及。然而,自然狀態下的自然權利雖是權利,卻也根本談不上權利,對權利進行規訓的自然法也缺乏基本的制約力量。這些從個體本身開顯而來的論證要素和環節最終被歸結到主權者身上,服務于主權者的身份確認。個體的獨立性在統治權力的籠罩下消失殆盡,個體自主與自治成為奢望。霍布斯堅決拒斥了傳統,然而他的現代性精神卻猶疑不決。從強烈的情感到絕對的利維坦,理性和自然法只不過扮演了一個擺渡人的角色,它們與作為主體的個人仍處于分離狀態。
二、洛克自然法思想中的理性要素
洛克同霍布斯一樣,將論證政治權力的基礎追溯到自然狀態,但他對自然狀態的預想與霍布斯不同。當他一開始論及自然狀態時,也一并提出了自然法這一概念。在霍布斯看來,自然狀態里的人首先憑借各自激情開始生活,欲望和恐懼使人們陷入到悲慘境地。霍布斯詳盡描述了這一境地的種種慘狀之后才轉而探討自然法,因此,無論從論證邏輯還是時間順序來看,自然法都位于自然狀態之后。而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并沒有列出單獨章節論證自然法,自然法已然被預置于自然狀態,并且指導著自然狀態下人們的個人生活及相互交往。由此看來,洛克的自然法學說似乎更多地追隨了傳統的教條,將自然法視作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自然秩序或者上帝頒布給人類的命運法則。但事實是,作為推動政治變革的政治理論,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比之霍布斯是更為激進的。我們來看洛克對自然法的定義:
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4]4
理性不再單純地承擔與智慧相應的認識與辨識任務,理性等于自然法,它直接向人們提出了權利和義務的要求。個人只有兩個選擇,要么遵從理性,要么違忤理性,而違忤理性相當于與他人為敵。理性自然法直接昭示了人所應享有的自然權利——生命,自由和財產;同時,它也昭示了人所應盡的義務,“每一個人都有義務保存自己,每一個人都有義務保存全人類”。[2]571
正如霍布斯的自然法思想,洛克也將其自然法思想直接歸結到人類并進而歸結到個體。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沒有過多提及人類怎樣享有品德高尚的生活,也沒有論述任何一種品德高尚的生活樣式。他注重的是每個人如何實現自身的利益,以及如何能夠保證利益所帶來的舒適。為此,他著重論述了財產權。因為在自然狀態中已經能夠和平實現自身利益,而與自然狀態并存的自然法就具有不證自明的權威性,理性便也成為個體求取生存的前提性要素,“上帝是把世界給予勤勞和有理性的人們利用的,不是給予好事吵鬧和紛爭的人們來從事巧取豪奪的”。[4]21較之霍布斯,洛克自然法思想中的理性要素占據更為關鍵的位置。在霍布斯那里,理性教人認清了自我激情以及激情的盲目性;而在洛克這里,理性教人在更深層次上意識到自我作為一種理性存在及其獨立性。
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所明確的權利要素使其頗具解放性色彩,但由于人的理性能力是通過上帝啟示直接給出的,自然法內蘊的主體能動性和主體自我立法并不存在論證關系。這就顯示出了洛克自然法思想的矛盾所在,一方面“他對自然法的忠實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篤信”[5]272;另一方面,作為主體的個體理性并不參與立法,它所做的不過是篤信而已。
三、不可還原的自然狀態
自然法在霍布斯和洛克這里都與自然狀態密不可分,自然狀態觀念的引入直接擺脫了對“自然”形而上學和神學的理解,而對自然狀態的超脫只是為了人類自身利益,并且只是依靠人類自身的力量。但他們對自然狀態的設想大相徑庭,相應于自然狀態的具體政治設置也迥然有別,甚至截然對立。
關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與自然法,海因里希·羅門的解讀認為“自然法實際上僅有一條基本規范:‘必須遵守協定’”。[6]78契約被包括在自然法的首要法條中,并且由對待契約的態度衍生出真實有效的道德用語。其中重要的德性之一“正義”便直接源于對契約的遵守。因為自然狀態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狀態,所以“從自然狀態中唯一可得到的補償就是我們有可能擺脫自然狀態”。[2]471“自然”不再是人類依附的主體,相反,“自然”成為人類征服的對象。任何導致滑落到自然狀態的舉動都是不赦之惡。霍布斯無疑對正在進行的英國革命持否定和反對的態度,他對“和平”的強烈向往之情最終使“和平”成為一個形式化、絕對化的觀念,而牢固地維持“和平”的絕對集權和專制成為他的選擇。戰爭是人類重又陷入自然狀態最明顯的標志,因為自己撕毀自己簽訂的契約,此后在自然狀態中的所作所為便不再是無辜的,而是罪惡。
霍布斯關于自然法的研究,關于善惡科學的研究,也即唯一真實的道德哲學所要教導給人們的眾多原則,歸根結底只是一個嚴肅告誡:自然狀態不可還原!這與霍布斯的政治生涯密切相關。從 1640年離開英國及至 1642年內戰爆發,“其間霍布斯舉出大量的證據,說明自己為什么不喜歡國會,而支持保皇黨人的事業”。[7]241霍布斯對主權者在學理上的證明也是直截了當,每個人并未與主權者簽訂契約,沒有共同權力的保障,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從霍布斯所處時代的政治狀況來看,他無疑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對維護君主權力的辯論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然而他的不平凡的智識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把人們引入到現代,“我們之所以成了現代的了,僅由于抓住了導致敬畏的權力,并把它轉變為自己手中的權力”。[8]90可以說,霍布斯的自然法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這一權力的說明者,自然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世俗的自然法。
四、可還原的自然狀態
洛克的自然狀態是這樣的:“那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他們在自然法的范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無須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4]3
因為這樣一種自由、友好、和平的自然狀態,作為政治的歷史性前提,自然狀態與政治社會的關系便不再是分裂和敵對的。相反,由于自然狀態的源始意義和溫和特性,倒成為張顯各種天然權利的最佳保留地。自然狀態可以隨時與現行政治狀態相互轉化。只是由于自然狀態對人類實現自身利益時的不便利,以及這種不便利引起的沖突與仲裁問題,人類才需要走出自然狀態,從而尋求更穩定的自身利益和公共福利。在洛克的契約理論中,存在兩個層次的關系,用“同意”一詞來概括便是:一層指向個體彼此之間的同意,另一層指向個體對政治權力的同意。洛克在論政治社會的起源時說,“政治社會的創始是以那些要加入和建立一個社會的個人的同意為依據的”。[4]65因為人的自然權利在自然狀態中已經被自然法所規制,人所享有的自然權利也是有限的權利。這一細節之處的限定在洛克的推論中事關重大——個人所能轉讓的權利和權力范圍便沒有可能給“專斷權力”留下任何余地。理性狀態良好的任何兩個人都可以避免戰爭狀態而和睦相處,彼此之間訂立的契約亦沒有“專斷”的影子。在洛克的自然狀態中,沒有誰享有專斷權力,也沒有誰需要專斷權力,不存在專斷權力的放棄與轉讓。洛克在論立法權時說的再清楚不過,“他所享有的只是自然法所給予他的那種保護自己和其余人類的權力;這就是他所放棄或能放棄給國家的全部權力”。[4]84那么,維護公共福利就成為行使國家政治權力的唯一目標。否則,人們就可以義無反顧退回自然狀態。
此外,洛克的自然狀態還存在兩個細節問題,反映在自然狀態、政治社會、戰爭狀態三者關系之中:其一,只有自然狀態才是戰爭狀態的寓所,戰爭狀態必然發生在自然狀態里;其二,即使政治社會的各職能部門運轉正常,自然狀態依然會在各種危急情勢之下出現。洛克對自然狀態的定義以“共同裁判者”為顯著標志,“不存在具有權力的共同裁判者的情況使人們處于自然狀態”。[4]13但他對戰爭狀態的定義卻又撇清了與“共同裁判者”的關系,“不基于權利以強力加諸別人,不論有無共同裁判者,都造成一種戰爭狀態”。[4]13與此同時,政治社會提供了可以依附其強力的“共同裁判者”。問題在于,求助“共同裁判者”需要一個耗費時間的申述程序,正常情況下我們應當訴諸法律,不能擅自懲罰侵犯者。然而,在一些即時發生的危急情況中,為了保護生命和財產,“我”可以以強力反抗甚至殺死侵犯者,這時我便與侵犯者處于自然狀態,同時也處于戰爭狀態。對洛克而言,自然狀態像是一個閃回的片段,可以在任何有必要的時刻再現。顯然自然狀態與政治社會存在兩個層次的關系:第一層,自然狀態作為論證政治社會的基礎和標準;第二層,自然狀態作為構成要素滲透在政治社會之中。
判斷戰爭狀態存廢的關鍵在于是否“不基于權利而以強力加諸別人”,一個人在自然狀態中違背自然法使自己陷入與他人的戰爭狀態。而一個人在政治社會中陷入與他人的戰爭狀態,則在于“共同裁判者”的即時缺場——當一方侵犯另一方時,如果另一方可以從容訴諸“共同裁判者”,則雙方并非處于戰爭狀態之中,而是處于實證法律關系之中;如果另一方無法訴諸“共同裁判者”,即“共同裁判者”強力暫時失效時,則雙方處于自然狀態亦處于戰爭狀態。盡管自然狀態作為政治社會的參照意義重大,但鑒于戰爭狀態只潛在于自然狀態,所以組成政治社會并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就顯得極為必要。
五、小結
霍布斯的自然法是對自然權利的規避,洛克的自然法是對自然權利的伸張;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是不可還原的,洛克的則可還原。這種區別直接導致對具體政治設置的不同預期,也顯示洛克比之霍布斯對個體自身能力抱有更大信心。
通過對洛克和霍布斯自然法思想的比較分析,顯示了在此階段自然法與“人”的關系進展到何種程度。這可以簡要概括為三點:
第一,從人出發,人成為自然法思想的中心。作為英國經驗論的典型代表,霍布斯和洛克都堅持將“感覺”作為認識的根源,而訴諸感覺的討論直接將神秘自然或神圣上帝給人的“感應”排除在討論范圍之外。在此之前,彼岸世界是人類生存前提,有限的感覺能力把人與彼岸世界隔離開來;現在,并非完善性的人怎樣在此岸世俗世界生存下去,就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理解的是我們自己。當我們將一些行為界定為好或壞時,應注意到這樣做是人為的活動過程,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而不是實現宇宙的自然規律的運動。”[8]94霍布斯和洛克共同關注的是,擺脫傳統至善論和目的論之后,人如何維持穩定和舒適的生活。盡管自然法思想源起于人的思想和行為,但它最終的落實還是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關系上。
第二,人應該且能夠發揮自己的智力與智慧,建構起合適的社會生活以及合理的社會生活規則。盡管霍布斯與洛克最終的政治構想相互對立,但顯而易見的是,霍布斯與洛克都從對人的分析起步,引入契約觀念,最終建構了詳盡的政權組織模式。無論是霍布斯的集權模式還是洛克的分權模式,它們都基于人的智慧對人的缺陷所做的修補,以避免戰爭帶來的災禍。正如登特列夫對近代自然法思想的解讀——社會契約是一個框架,也是一份藍圖,對它的各種不同的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它們的起點都是個體。它們的基礎都是近代的俗世的自然法觀念,以及由之衍生的人之‘地位’。[9]64-65霍布斯與洛克對自然權利的處理不同,相應的契約內容也各異其趣,但就契約本身而言,其實質并無分別。契約關聯的不再是人與神,而是人與人。
第三,自然法思想的演繹最終使人掌握了權力。霍布斯對《圣經》的解讀特別強調的是上帝的絕對權力。“霍布斯認識到,服從的根據就是上帝,因為他‘擁有一種獨享的、不可違抗的權力,有權力統治和懲罰一切違背他的律法的人’”。[8]89霍布斯在此做了一個源于傳統卻又叛離傳統的獨到類比。而事實上,這是一個開創性的發現:既然上帝可以依靠純粹權力看待和指導宇宙之一切,那么在塵世,足夠強大的世俗權力一樣可以大有可為。緊隨于此,洛克細致入微地論述了權力的制衡。政治權力的前提不再是自然和神,它的惟一的前提是“人”。權力觀念成為一個可以單單從“人”身上發掘出來的觀念,它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不因為上帝的缺場而有絲毫減損。
參考文獻:
[1] (英)霍布斯.黎思復,黎廷弼,譯.利維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2](德)列奧·斯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編.李洪潤,等,譯.政治哲學史[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3] (英)霍布斯.論公民[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4] (英)洛克.葉啟芳,瞿菊農,譯.政府論(下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5] (加拿大)詹姆斯·塔利.梅雪芹,等,譯.語境中的洛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6] (德)海因里希·羅門.姚中秋,譯.自然法的觀念史和哲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7] (英)昆汀·斯金納.王加豐,鄭崧,譯.霍布斯哲學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辭[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8] (英)韋恩·莫里森.李桂林,等,譯.法理學:從古希臘到后現代[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9] (英)登特列夫.李日章,等,譯.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