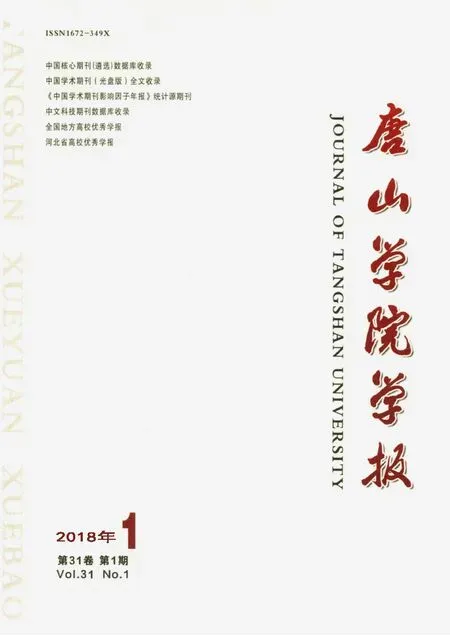李大釗在非基督教運動中的獨特貢獻與歷史價值
談思嘉
(復旦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433)
非基督教運動是20世紀20年代首先在上海爆發進而波及全國的一場規模宏大的反對基督宗教的運動,最初只是起于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一次關于宗教問題的學理討論,后來隨著國內民族主義不斷高漲,逐漸升級演變為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成立甫半載的中國共產黨積極主導,在運動組織上和理論宣傳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的李大釗在運動中始終扮演著領導者的中堅角色。一方面,他積極參與并出席非宗教大同盟各項活動,對非基督教運動的發展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他撰寫大量文章闡發鮮明的宗教觀,為非基督教運動做強輿論宣傳。然而,在以往的李大釗研究中很少學者關注到這段歷史的進程,故有必要對李大釗在非基督教運動中的言行進行深入考察,進而更全面地了解李大釗的思想和生平。
一
關于非基督教運動究竟是一場隨機觸發的愛國運動還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預謀,至今仍存在不少爭議,其中關于政黨組織究竟與非基督教運動的爆發有無關系,政黨是否參與并策動了非基督教運動等問題的探討尚無定論。但只有厘清這一問題,才能進一步定位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者的李大釗在非基督教運動中的重要貢獻。
目前學界主要分成兩派。一派以魯珍烯、楊天宏、顧衛民等學者為代表,認為政黨組織在非基督教運動產生之初與之并無太大關系,“如果一個政黨的思想政治綱領沒有對這場運動產生直接作用,就沒有理由認為這一政黨參與了運動”[1]。雖然有不少國、共兩黨黨員參與到運動中,但這僅屬于無組織的個人行為而不能代表政黨的主張,至多只能代表個別社會精英或某個小團體。而另一派以郭若平、牟德剛等人為代表,他們根據近年陸續披露的史料和檔案,認為非基督教運動的產生與政黨有著直接關聯,如果沒有政黨參與其中并發揮一定作用,非基督教運動不可能以如此的面貌和規模出現。對于上述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可以肯定的是前者“無關說”顯然與現已披露的史料相背離,政黨確實是發生非基督教運動的直接推動力量。但是“無關說”也不失參考價值,它強調五四以降中國社會發展態勢、歷史條件和群眾基礎等背景構成非基督教運動發生的歷史合力。而在承認政黨作用的學者中,有的學者僅將共產黨或者國民黨視作非基督教運動產生的唯一力量*參見田海林、趙秀麗的《早期中國共產黨與“非基督教運動”》,牟德剛的《中國共產黨在非基督教運動中的立場態度及其歷史意義》,陳海軍的《中國國民黨與非基督教運動(1923-1927)》。;有的學者認為非基督教運動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兩個政黨組織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趨同促使了運動的持續發展*參見周興梁的《二十年代初期國共兩黨成員指導進行的“非基督教運動”》,郭若平的《國共合作與非基督教運動的歷史考察》和薛曉建的《論國共兩黨與非基督教運動的關系》。;還有學者通過觀照國際政治格局認為共產國際的介入也是不可忽略的力量,它“除了最初直接策劃了非基運動外,在以后錯綜復雜的革命局勢中,仍一再表現出對非基運動的關注”[2]。對于上述各方觀點,本文更傾向于中國共產黨是非基督教運動發生和發展的主導力量。僅從非基督教運動爆發前夕的情況來看,有以下兩點值得重視。
第一,中國共產黨人對批判基督教有了思想認識。新文化運動中,一批受過新式教育洗禮的知識分子在思想領域進行了一次深刻變革。在以往人們的觀念中,新文化運動只是將矛頭直指封建傳統文化的核心代表——孔教。其實,新文化運動在“反孔”的同時也展開“非耶”的批判。基督教信仰作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主要工具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壓迫和奴役,以及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精神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使其不可規避地遭受批判。特別是到了新文化運動后期,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接受并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剖析宗教問題的相關理論成為了他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的理論前提。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指導下,一股批判宗教尤其是批判基督教的熱潮在思想界涌現。李大釗利用唯物史觀辯證地考察了宗教的產生及影響,在肯定宗教“堅人信仰之力”的同時,更主要的是深刻揭露“其過崇神力,輕蔑本能,并以諱蔽科學之實際”[3]98的弊端,更堅信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宗教也必將消亡。此外,諸如陳獨秀撰寫的《基督教與中國人》、惲代英的《我的宗教觀》等文章也都是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立場上對基督宗教進行了深刻剖析,為非基督教運動實踐提供了思想基礎。
第二,中國共產黨及其后備組織對運動爆發有了組織準備。非基督教運動的發端要追溯到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內部發生的一場矛盾,當時學會的機關刊物《少年中國》第2卷第4期中的《評議部紀事》一文中,在涉及學會會員宗教信仰問題時規定,“凡有宗教信仰者,不得介紹為本會會員”,并且“主張已入本會而有宗教信仰者,自請出會”*《評議部紀事》,見《少年中國》第2卷第4期,第87頁。。規定一經刊登,立即在少年中國學會內部激起波瀾,繼而引發關于宗教問題大討論,成為非基督教運動的前奏。而引發矛盾的少年中國學會是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釗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的進步團體,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后來,當運動正式爆發,第一個非基督教運動的組織就是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發起成立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當時在華工作的利金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報告》中寫道,“運動的總指揮部從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產黨中央局手中,它通過青年團成功地控制了整個運動”[4]91,還稱“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4]92。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為非基督教運動的爆發做了充分準備。
二
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者的李大釗究竟與非基督教運動有著何種聯系,還需通過對非基督教運動的歷史進行深入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李大釗對運動的發展態勢所起的重要指引作用。
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索一般被認為是1922年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第十一次大會。此次會議的召開被認為是基督教組織意識到中國反宗教潮流將限制和挑戰教會事業的發展,故在此時選擇在中國地區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大會加以應對[5]。但是,四川大學楊天宏教授揆諸歷史事實發現這一判斷并不能成立,聯盟大會早在1913年就決定第十一次大會于1916年在中國召開,只因“歐戰”正酣才延期至1922年,而且從譴責戰爭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會議主要議題上也不存在任何政治和文化上控制侵略中國的企圖[6]。
但隨著新文化運動以來理性主義和破除偶像的熱潮在中國興起,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大會的召開在一定程度上觸發了當時知識分子敏感的神經,尤其是聯盟大會中某些不當宣傳最終導致了非基督教運動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下被引爆。于是在聯盟大會召開前夕,社會主義青年團在2月26日就在上海召集起反對基督教的同學成立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同盟成立后便向全國各地發出通電,非基督教運動立即得到各地積極響應,尤以北京反應最為激烈。據范體仁回憶,“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在北京大學第三院開非宗教運動大同盟成立大會,到會者五百余人,由范鴻劼主持”[7]。李大釗出席大會,并與蔡元培、汪精衛、鄧中夏等15人一起被推舉為干事,負責日常事務。期間,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的李大釗投入大量精力,作出重大貢獻,推動了非基督教運動的蓬勃發展。
第一,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推動非宗教大同盟的建立。1918年,在李大釗的倡導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秘密成立,這是中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研究會除了搜集馬克思著作,組織有翻譯能力的會員對其進行編譯和宣傳,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外,還積極探討科學與宗教的關聯問題,強調在思想領域內不應當回避宗教問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多次在研究會內部商討組織非宗教同盟的事宜,這在羅章龍的《椿園載記》中的回憶可以得以印證。羅章龍回憶道,當時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即組織非宗教同盟”[8]90。后來,非宗教大同盟的成立主要就是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為成員基礎的,再廣泛聯絡北京部分高校的師生參與其中[8]91。
第二,執筆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通電堅定非宗教立場。1922年3月20日,李大釗、陳獨秀等77位學界名流以非宗教大同盟的名義聯署發表同盟宣言并通電全國,宣言就為何要發起非宗教大同盟以及為何將矛頭對準基督教的緣由進行了深刻闡釋。宣言和通電一經發布,全國各地應聲四起,紛紛成立非基督教團體。但與此同時,思想界也開始出現反對聲音,周作人、錢玄同等多名教授認為非基督教運動干涉了信仰自由,將會為日后用強力取締思想自由埋下禍根。對此,李大釗于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開幕當天再次主筆起草《非宗教者宣言》,重申了非宗教立場,并對反對派的觀點做出了回應,表示堅決反對“信教自由”,否認宗教和自由并立的可能。
第三,積極參與非宗教大同盟活動,以提升運動宣傳力度。非宗教大同盟的常規活動主要是組織公開的學術演講[8]91,身為同盟主要發起人和常務干事的李大釗積極出席各種集會并發表演說。1922年4月9日下午1時至5時,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學第三院大禮堂召開演講大會,李大釗到會并發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說,就發起非宗教大同盟以及將矛頭對準基督教的緣由再次進行闡釋。1925年12月25日,非基督教大同盟舉行第二次公開名人演講大會,李大釗再次出席并發表了基督教侵害中國的種種情形及補救辦法的演說。李大釗通過發表演說,以自己的社會聲望號召更多社會人士加入同盟,擴大同盟的隊伍和力量,使非基督教運動得以不斷向前發展。
三
除了積極參加非宗教大同盟集會活動外,李大釗還就宗教問題撰寫了《非宗教者宣言》和《宗教與自由平等博愛》等多篇文章,闡明了鮮明的、徹底的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宗教觀。這不僅有力地配合和聲援了非基督教運動的進展,為運動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更深化了人們對宗教本質的認識,為人們探求科學真理和思想自由掃除了宗教迷信的毒害。
第一,宗教有礙思想自由。非基督教運動興起后并未形成一邊倒的情形,在猛烈批判宗教的同時,一些學者教授和信教人士也針鋒相對地發出反對聲音。其中,周作人等北京大學5名教授就于3月31日聯名在《晨報》上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堅決反對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的運動,認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確承認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必須遵守約法規定,保證宗教信仰應當享有絕對的自由而不受任何人干涉。一場關于宗教信仰與思想自由關系的論爭由此引發。次日,李大釗便立即發表通電,批駁周作人等人雖表面上不擁護宗教,但已經有傾向于擁護宗教的嫌疑。在他看來,宗教信仰是對神的絕對體認,信仰神就必然受到神定的束縛,既然受到神定的束縛,那么“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響之下,斷乎不能存在”[3]98。所以,承認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不代表思想自由,反而“宗教實足為思想自由的障蔽”[3]98。按照馬克思宗教觀所認為的,只有當人類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都發展到一定高度,不需要向虛妄的神靈尋求精神寄托,能夠擺脫宗教這一異己力量的支配,那么人類才能實現真正解放,獲得充分自由。同樣,李大釗也主張“與其信孔子、信釋迦、信耶穌,毋寧信真理”[9],只有使人們在思想觀念上“從真實的知識,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為無足輕重”[3]98,那么才有真正實現和維護思想自由的可能。
第二,宗教教義的虛偽性。但凡宗教總是通過宣揚自身教義以俘獲世人之心靈,使之投身該宗教而成為其教徒。表面上各派別宗教教義無比光明正義,如基督教教義頗含對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崇尚之意蘊,但李大釗卻對此表示懷疑,認為宗教只是假借宣揚教義之名,行不義之實。為此,他在《宗教與自由平等博愛》一文中逐一進行批駁,直指宗教與自由、平等和博愛精神的背離。尤其在論及宗教與平等關系時,李大釗剖析了原始宗教產生的條件,認為原始人類面對自然界的強力而存在著物質和精神上雙重缺陷,從而產生敬畏和崇拜,“便對于一般人民成為有不平等關系的優者強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仰”[3]99,不平等的關系也就此表現出來。由此,人們將宗教視為精神寄托來謀求實現平等關系從宗教產生的源頭就已斷然不可能實現。既然宗教的自由、平等是虛偽的說教,缺乏自由、平等作為基礎的博愛自然也是經受不住拷問的。
第三,宗教妨礙人類進步。從李大釗早期的宗教觀來看,對于宗教歷史作用的評判并非是全盤否定的。李大釗對宗教能夠“堅人信仰之力”尤為贊賞,還一度號召“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類有無盡之青春”[10]。對于宗教內部具有合理部分,李大釗一開始也主張應依據真理的標準辨別吸收精華,剔除糟粕。但是,為了配合非基督教運動的輿論宣傳,李大釗在評判宗教的作用時,只考慮宗教的消極因素而忽略其合理積極的一面。他認為“把所有的問題都想依賴宗教去解決,那是一種不承認科學文明的態度。換言之,這是不懂得進化論為何物”,因而違背科學、逆社會發展進程的宗教在傳遞“廉價的幻想”的同時也成為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礙。譬如,李大釗以基督教宣揚的無抵抗主義為例,認為所謂“人批我左頰,我更以右頰承之”“人奪我外衣,我更以內衣與之”等語,嫁接到現實生活后,它某種程度上就暗含了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無需做出任何反抗,只需安分守己甚至容忍并主動讓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自己。而這必然不符合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獲得徹底解放、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所以,李大釗尖銳地指出宗教是妨礙人類進步的東西,依賴宗教幻想是毫無意義的,必須竭力加以反對。
四
李大釗積極參與非基督教運動,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上都對推進非基督教運動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在深化時人對宗教本質的認識、壯大中國革命隊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首先,李大釗的宗教思想深化了人們對宗教的本質認識。五四運動以前,早期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人士對于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內基本持有正面肯定的態度。然而,隨著非基督教運動的開展,他們的宗教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大都轉向痛批基督教的教義,但缺乏一定的理論基礎。李大釗則首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和研究宗教問題的先河”,為掃除宗教迷信毒害、正確認識宗教問題和制定科學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礎。
其次,李大釗參與和領導非基督教運動壯大了中國革命的隊伍和力量。非基督教運動爆發后,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積極投身運動,對自近代以來作為帝國主義侵華工具之一的基督教信仰予以沉重打擊,蕩滌了一切宗教迷信,為中國人民探求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作出了獨特貢獻。反帝反教理論的廣泛宣傳,吸引了一大批先進知識青年投身革命,使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剛剛建立半年、人數不足百人的小政黨團體逐步發展壯大,成為了國內政黨團體中領導民族獨立和反帝斗爭的中流砥柱。并且,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具體的革命實踐,使政黨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都得到了充分歷練,尤其是掌握了如何發動學生、工人等群體參與革命斗爭的策略和機制,為日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最后,李大釗在非基督教運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不僅在于推動了非基督教運動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直接證實了在政黨組織與非基督教運動的關系問題上堅持“無關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他的行為某種程度上同樣代表著全黨的思想和意志。盡管目前尚沒有材料能直接表明李大釗是接受黨組織的決定領導和參與了非基督教運動的,但從實際歷史的進程來看,在李大釗的影響下,一批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前赴后繼地參與到非基督教運動中,直接影響了非基督教運動的發展態勢。由此,早期中國共產黨是非基督教運動發生和發展的主導力量的觀點是毋庸置疑的。
[1] 楊天宏.基督教與近代中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294.
[2] 陶飛亞.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J].近代史研究,2003(5):114-136.
[3]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91.
[5]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444-445.
[6] 楊天宏.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與中國反教運動關系辨析[J].歷史研究,2006(4):173-177.
[7] 范體仁.記“五四”運動前后北京若干團體[M]//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74.
[8] 羅章龍.椿園載記[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9]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7.
[10]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