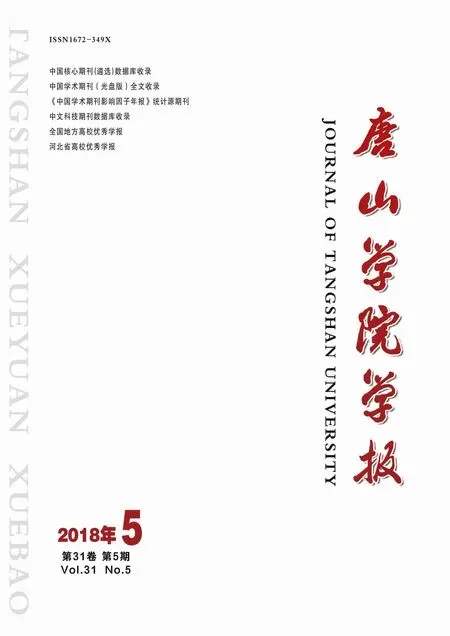論清末廣東的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
——以歐榘甲的《新廣東》為考察對象
魏燕齊
(中央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081)
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學者在論述20世紀的民族主義時都這樣開篇:“20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民族主義是人類世界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是19世紀初在歐洲誕生的一種學說。民族主義認為:“人類被自然地劃分為民族,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證實的特性而能被人認識,政府的唯一的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1]即由一個民族根據某種理念建立民族國家的思想和運動。中國清末的變革和民國的建立亦離不開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的糾葛。我們可以確信,中國在清末民初所面臨的變革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激蕩的變革。在風云際會的清末最后十幾年里,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走向。然而它的產生與發展卻不是平鋪直述的,其中的一條顯性的發展道路,即由漢民族主義的覺醒到“大民族主義”升華,其發展過程已經為人熟知。而另一條略顯隱性的道路,即從地方主義到民族主義的發展經過,尚未被人熟悉。特別是在中國南方,這一條民族主義的發展道路也對中國近代的國家建設造成了一系列的影響。
關于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的研究已經紛紜雜沓,關于清末民初地方主義的研究也層見疊出。如美國著名漢學家杜贊奇,他在他的名著《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中略論了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省自治話語的出現,并著重探討了民國時期湖南和廣東的聯省自治運動[2]。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施恩德(Andre Schmid)主編的《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中的部分文章、鄭大華和鄒小站主編的《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劉青峰主編的《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都從眾多不同的角度對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又如,胡滌非的《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政治變遷》一書通過對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建立與衰敗過程的具體考查,分析了民族主義在其中的歷史作用。也有從其他角度探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與地方主義關系的論文,如江遠山的《近代中國地域政治化與國家建設——以省為考察對象》和《近代中國地域政治化研究——以廣東為考察對象》、方平的《地方自治與清末知識界的民族國家想象》等,這些研究都以“省話語”的出現作為出發點,考察了省級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現代國家建設的關系。他們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拓寬了中國民族主義研究視野的廣度和深度,對我們有很重要的啟發作用。
關于廣東地方主義這方面的研究也已有比較多的著述,比如程美寶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一書從歷史敘述、種族血統、學術傳承、方言寫作、地方民俗等多方面探討了廣東近代“地域文化”話語的建立過程。而對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歐榘甲的研究目前還不多,只見宋德華和劉雪琴的《辛亥前期歐榘甲革命自立主張探析——以〈新廣東〉為中心》,從歐榘甲在辛亥革命前期對革命派產生重要影響的角度探析了《新廣東》一文,這對本文的撰寫有著重要的幫助。
一、廣東地方“民族主義”的胚胎——廣東地方主義
(一)廣東地方主義產生的條件
清末意義上的廣東位于遠離中央政府的東亞大陸的最南端,其北面的南嶺成為阻隔中原文化的一條天然屏障,而南面的南海卻便利地送來了西方的訊息,使之成為自古以來中外交往的要沖。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從秦漢時期就開始海上貿易,當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清朝閉關鎖國之時,廣州也是中國唯一允許進行海外貿易的城市。這樣的一種地理區位,使得廣東無論在政治、文化還是語言上都與北方中央王朝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并能夠與海外進行持續的交流,成為所謂的傳統漢族十八省中最有可能獨立甚至叛離中央王朝的地區。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侵略加劇,自然經濟加速解體,清政府為解決財政危機,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廣東部分地區的地方資產階級精英階層的經濟地位不斷鞏固,新士紳階層開始出現,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近代意義上的社會政治活動正在此時逐漸興起。他們通過局部聯合的形式,成立商會、農會等組織[3]。由于他們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這些局部組織形式便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團體。在這段時期,廣州地方資產階級精英和新士紳對辦報表現出很大的熱情。這些報刊在不同程度上表達了資產階級和新士紳的政治和文化思想,成為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城市居民聯絡發動的重要手段,以及與官府抗衡的工具[4]。報刊傳媒業的發展,無疑為包括地方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思想現代意義上的傳播提供了基本媒介。
政治上,作為新士紳的早期維新思想家們主張仿照西方的地方政制,這導致地方自治的呼聲不斷高漲,特別是在1900年以后,清王朝在外交上的軟弱無能使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府組織形式的合理性遭到了各類知識分子前所未有的質疑,他們便希望通過各省的獨立與自治來逐步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統一。此后,新士紳自發的小地方自治形式和官紳合辦的小地方自治形式在廣東逐漸開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廣東普通民眾的鄉土之情[5]。
(二)廣東地方主義的表現形式
1.鄉土志書與鄉土教科書的編寫
鄉土志書與鄉土教科書都是清末民初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出現的小學鄉土教材,在清政府鼓勵下各地自行編纂出版,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產物。晚清政府推行一系列新政,皆以日本和德國為楷模,由此,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傳統對清末的鄉土教育產生了一定的作用。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從1906年到辛亥革命前夕,編纂和出版的鄉土志書和鄉土教科書至少有十幾種[6]。這些鄉土志書和鄉土教科書的編撰目的,是為了在列強侵略的背景下培養民眾的國民意識和愛國意識,但同時也從多方面把廣東塑造為一個擁有獨特的文化傳統的獨立單位,使地域意識和地方主義進入了正統的國民教育的范疇。在對地域意識的強化中,對族群差異的書寫尤為明顯。如1906年出版的《廣東鄉土史教科書》中所述:“南宋時,中原人避亂,多遷居南雄珠璣巷,故粵人多中國種。”這是把說粵方言的“粵人”追溯到更久遠的中原譜系。同樣的,由客家人主導編撰的《興寧縣鄉土志》也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衣冠南渡”:“邑中人類,本中原衣冠舊族。宋南渡時,播遷轉徙,多由閩贛而來,語言風俗,與土著異,故當時土著稱為客家。厥后由縣轉徙他方者,遂自稱客家,而并無改其語言風俗,示不忘本也。”[7]
2.精英文化的創造
精英文化指的是精英知識分子中的文人知識分子創造、傳播和分享的文化[8]。廣東作為中國南方邊陲,其地方文化傳統雖然與北方中原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但在地方主義思潮的作用下,清末的廣東知識分子也開始試圖創造用其自己的語言書寫的文化。
(1)學術文化傳統的追溯
清末南方系的革命派精英知識分子,在當時知識分子界日漸歐化的背景下,為復興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于1905年創立了名為“國學保存會”的學術社團。作為廣東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國學保存會成員黃節草就了《粵東學術源流史》一文,綜述漢代以來嶺南的經學發展,該文在1908年以《嶺學源流》為題,刊登在該會的機關報刊《國粹學報》上[9]188。
(2)粵劇的“粵”化
有學者認為,“粵劇”一詞可能在光緒年間開始出現并流行,但在光緒末年之前,廣東演出的戲曲或者粵劇,并沒有粵方言大量摻進戲曲以至成為其主體。到了清末民初的時候,粵劇吸納了粵方言區南音、龍舟、粵謳和咸水調的傳統,這時,粵方言才漸漸成為粵劇劇本的主體。此后,粵劇成了革命先鋒們在海內外宣揚革命、愛國與漢民族主義意識的傳播媒介。這種把方言用作地方劇種主體語言的活動,使粵劇成為真正的粵劇,其發生絕對不是偶然的[9]133-138。
(3)粵方言書籍的編寫
在文言文作為官方書面語言的時代,廣東精英知識分子為表達自己國家精英的身份,從來沒有把用粵方言寫作的文章和書籍納入到他們觀念中的“文化”范疇中去。廣東民間的木魚書、南音、咸水歌、粵謳、粵劇等粵方言文體雖種類繁多,但卻不出聲色娛樂之范疇,不能成為正統的“雅”。這種情形一直到19世紀末的最后十年才稍有改變。在清末新政的推動下,各地為普及國民教育,提倡以白話辦報和寫作教科書。
真正應用粵方言撰寫教科書并影響及于婦孺的實踐家是康有為的一位學生陳子褒(1862-1922)。陳子褒雖然并非是第一個用粵方言編寫教科書的人(在陳子褒之前,南海人麥士治用白話譯寫了《書經》和《詩經》,分別在1893年和1894年出版),但他創新之處,不僅僅在于用粵方言白話寫作教科書,更在于他的教科書的內容完全擺脫了傳統封建儒家式啟蒙教育的桎梏。他于1903年編寫的小學教材《婦孺三字四字五字書》,內容淺顯,富于廣東地方特色[9]157-160。
二、廣東地方“民族主義”的胎動和消解——對《新廣東》的分析
清末民初廣東的地方“民族主義”,只是一個假想而非實際存在物。這個詞用以描述在地方上未能成功提升成民族主義的地方主義,是我們為了方便考察其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系而刻意制造的概念。在此,我們必須使用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觀念,來描述清末民初的精英知識分子在無意識中去努力塑造一個民族的可能,雖然這些努力在他們自身看來都只是國家民族主義框限下的地方主義。因此,如果我們把上文所提及的鄉土志書和鄉土教科書的編纂活動和精英文化傳統的創造活動看成是在廣東地方主義意識下所進行的活動,那么我們必須把下面所要論述的歐榘甲在其政論著作《新廣東》所做的表述認為是在地方主義基礎上的地方“民族主義”了。
(一)地方“民族主義”的胎動
歐榘甲(1868-1913),字云樵,號太平洋客,廣東歸善(今惠陽)人,1891年入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是當時有名的新式知識分子和新士紳。1902年,在對中央王朝徹底失望后,歐榘甲以筆名太平洋客在《文興報》上連載長篇政論文《論廣東宜速籌自立之法》27篇,他大聲疾呼“廣東省,廣東人之廣東省也”,并且提出“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為之倡,則其余各省,爭相發奮,不能不圖自立”的廣東獨立的主張。該文1902年8月易名《新廣東》,由橫濱新民叢報社出版單行本。《新廣東》一文出版后,“新廣東”一詞廣為流傳,在當時幾乎可以當作是歐榘甲人人皆知的身份代碼了。此后,類似于《新廣東》性質的模仿性文章也相繼出現,如湖南籍留日學生楊篤生以“湖南之湖南人”署名出版的《新湖南》。1905年,《新廣東》《新湖南》《新民叢報》等二十多種“悖逆”書刊被清政府軍機處嚴行查禁,可見這些著作在當時廣為流傳,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的[10]。
在《新廣東》一文中,作者分別論述了廣東必須獨立的特質、原因、目的、方式等方面。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我們并不分析作者有否構建一個獨立于中國的廣東民族的企圖,我們只是試圖通過地方“民族主義”的視角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分析這部時論著作。
1.中央朝廷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感
作者在論述廣東獨立之必須時,讓人處處感到了來自中央朝廷與帝國主義列強內外雙重的壓迫感。如在表達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時說道:“然而彼揚子江、東三省、云南、廣西、福建、山東諸省,雖云默許諸國,而土地則完全如故,若廣東則四分五裂矣。諸省雖云割棄,然成專歸一國,而廣東則祭仲之妻所云‘人盡夫也’,不知身屬何姓矣。以現勢論之站立:廣地圖中央者,非英、法、葡之三國乎?異日潮州或連福建而為日本所爭,惠嘉或因教會而為德國所據(客人所居德國教會最多),西江諸府縣或因商務鐵路而為美國所要割,又必至勢也,然則廣東地圖,其變為紅色、綠色、白色、藍色者實可預料。”[11]283由此,作者隱隱地表露出一種對廣東命運的擔憂。這種擔憂不單單是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了廣東不同于被專歸于一國占有的其他省份,廣東正在被多個國家分割,若現在不主張廣東獨立,將來的廣東可能難以再團結為一個省了。其后果正如他所說的:“然則廣東不能自立,廣東之地,必全屬于他人,廣東之財,必盡奪于異種,廣東之人,必盡淪于鋒鏑。”[11]285
而對于北方朝廷的無能,作者也表示出極度的憤懣,表示必須與其決裂:“我中國人之甘為順民也,以朝廷能保我也,朝廷不能保我而反棄我,是朝廷先為叛逆也。……斯時,君臣之義既絕,彼非我君,我非彼民,來侵者一例以敵人視之,旦靖內,且括外,鐵血流澌,以換國民之幸福而已。”[11]274這種內外交加的壓迫感,使得作者意識到廣東之孤立無援,而必須謀求獨立。
2.廣東人族群的統一
作者為了謀求一省作為一國的獨立,則必須使省內各族群拋開分歧,去試圖構建一個統一的“民族”。由于廣東省內有著客家、福佬、本地粵人等主要漢族族群和其他部分少數民族族群,作者的任務就是論證這三個主要漢族族群的同源性。
作者認為:“此三者種族,同出一源,不過因聲音而異,抱此劣見,猶之可也。……無論此三者種族,智識心思,腦輪角度,形體精神,不相上下,即以其族譜而言,其祖先莫不由中原喪亂,越嶺南遷。故本地之族多由南雄而至廣肇,客家之族多由雄州而至惠嘉,福佬之族多由江浙而轉福潮,其聲看之異,亦由所居之地而變遷意。常有一姓祖父子孫,不同聲音者,居福潮則言福潮之話矣,居惠嘉則言惠嘉之話矣,居廣肇具言廣肇之話矣,然則因其言而定共為客、為土、為福者謬,因其客言、土言、福言而定其為黃族苗族,尤不可也。……然以大體考之,福佬本地皆有官話,字皆有可通,非若苗族也。然則三者同為種族,無可疑也。”[11]305作者在這里所說的“種族”,即為現在所說的族群,也就是說他認為客家、福佬、本地粵人都為漢族無疑。
由此,作者拋開了方言的分歧,認為方言的差異僅為因居地變遷而產生,直接把三個族群都追溯到中原的黃帝譜系下的正統漢族。廣東省內三個漢族族群的矛盾由來已久,這些矛盾基于方言和文化的分歧。作者把這三個族群追溯到一個血緣之下,其基本動機在于為一個類似民族國家性質的必須由同一民族組成的獨立的廣東省論證其民族的先天同一性。與此同時,作者還把他認為落后的苗族等非黃帝民族從廣東人這一身份中排除出去。這樣,一個不再有族群血緣分歧的漢族廣東才得以在廣東民眾的觀念中被建立起來。這種對廣東省內各族群族源同一性的追認,與顧頡剛等學者在國家淪陷之際為構建一個同一族源的中國時所做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史學論證具有非常類似的性質。
3.獨立的必要措施和準備
在論述完廣東為何需要獨立之后,作者為使這種獨立觀念不成為空談,又提出了將其付諸實際的具體措施。
首先是開廣東省自立報館。作者認為廣東原來雖有省報,但依舊是帝國主義列強和清政府的附庸,沒有表現出一省自理之精神和理念:“非有專言一省如何危亡,如何關系,如何憤發,如何聯合,如何經營,如何改革,始可使全省人民,智識開通,張獨立不羈之精神,不受朝廷之束縛,不受他邦之吞噬者。”[11]288
其次是開自立學堂。作者提及廣東原雖有水陸師學堂,但實際上是清政府教化和斂資的工具。因此,設立民間私立的學堂,是傳播自由獨立思想之必須[11]290。
最后是組建秘密會社。清末民初的秘密會社多由同鄉同地之人組建,其主體成員多為下層民眾。作者對于當時遍布南方的秘密會社有切身的體會,認為秘密會社擁有極強的鄉土意識和地域意識,容易激發一地之人的地方“民族主義”意識[11]293。
由此可見,作者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在一個歷史上具有長時間中央王朝統治的國家的背景框限下,想要讓廣東人產生獨立自治的意識,就必須通過各種可行的手段廣泛傳播廣東的地方“民族主義”思想,讓廣大知識分子和民眾認識到廣東是廣東人的廣東。
(二)地方“民族主義”的消解
之所以認為歐榘甲的思想是地方“民族主義”,是因為他的思想具備了民族主義的諸多要素。與土生土長的地方主義不同,以歐榘甲為代表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地方“民族主義”包含了很多類似國家民族主義的特征。因為他們追求的是一省人的政治獨立,這是一般民眾的地方主義所不能發展到的程度。更重要的是,他們把原來存在分歧的三個漢族族群認可為同一血緣的族群,并把他們認為屬于苗族的非漢族民族從“廣東人”這一族群身份給排除了,由此把廣東構建成為一個純粹是漢族廣東人占有的“國家”,這種思想已經基本屬于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了。
然而,本文所說的廣東“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還未出生便已消失了。因為作者基于各種原因最終把這種地方“民族主義”主動地納入到國家民族主義的目標體系之中了。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上至大之問題,即中國之問題,中國若有自立,則世界之風云必為之變色,萬國之政策必為之推移。”[11]308同時,作者依舊認為整個漢民族的統一才是必要之務,廣東的真正振興,也只能基于中國的獨立。所以,“務合漢族以復漢土,務聯漢才以于漢事,以救中國,則中國可興,以立廣東,則廣東可立”[11]310。
基于此,作者又參考了近代德國和美國的建立過程,認為中國的漢人國家的重建可以基于各個獨立的省的基礎之上。可見,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并沒有把廣東的獨立作為最終目的,而是將其作為一級邁向更高的漢民族的復興和獨立的階梯。就這樣,廣東的地方“民族主義”就發展到了極限,再不能脫離漢民族國家建設和漢民族主義的框限了。
三、廣東地方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的關系
在介紹了廣東的地方主義和分析了歐榘甲所代表的地方“民族主義”之后,我們必須從地方“民族主義”為何沒能在地方主義的基礎上生成這個角度去探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一)精英與鄉土的交錯
在論述廣東精英知識分子的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被他們的話語所掩蓋了的廣大植根于鄉土的農民的地方主義。中國自然經濟特性的影響使廣大農民的地方主義伴隨著中國歷史的始終,“秘密會社”即是農民的地方主義思想的重要承載體之一。清末的“秘密會社”多由受地方觀念和宗族觀念影響的農民和鄉村手工藝人集結而成,是一種缺乏明確的政治原則性和政治目標的組織。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時而也歸順朝廷,幫助鎮壓其他地區的秘密會社。因此,在他們自身的基礎上沒能夠產生明確的國家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思想綱領。而受到了西方思想影響的廣東精英知識分子則超越了農民的地方主義,將狹隘的地方主義提升到國家民族主義的高度。他們把地方主義作為一個階梯,用以間接使民眾理解國家民族主義的思想。正如歐榘甲在他的《新廣東》中所說:“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親戚急,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如何也。……因人心視其生省份之親切,易于鼓舞。”[11]270可見,精英知識分子認為普通民眾面對一個廣大的中國,是難以產生一種切身的國家民族主義的,他們中大多數的生涯和視野可能僅局限于一省甚至一鄉。
因此,精英知識分子們希望普通民眾首先能夠產生一種地方“民族主義”,產生對鄉土的忠誠和熱愛,然后以此為階梯,去理解整個國家和漢民族中不同省份的人們之間的“無名的團結”。然而,他們在到達目的的前一步就改變了目標,在地方“民族主義”還未完全生成前就邁向了國家民族主義。由此可見,精英知識分子雖然打開了通往地方“民族主義”的通道,但又在到達目的地前改變了方向。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提升了普通民眾的地方主義,又因為種種原因,使地方“民族主義”納入到國家民族主義體系內,致使普通民眾的地方主義再無可能提升為地方“民族主義”。
(二)身份與文明的執著
我們需要對上文所提及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兩重性作出一定的解釋,即為何廣東的精英知識分子沒有把當地的地方主義推升到地方“民族主義”的層次,卻選擇了將其向國家民族主義轉化這一道路。
1.基礎要件的缺失
霍布斯鮑姆認為,從西方的歷史經驗觀之,似乎只有三種固定標準可稱得上是構成民族的要件:第一,它的歷史必須與當前的某個國家息息相關,或擁有足夠長久的建國史;第二,擁有悠久的精英文化傳統,并有其獨特的民族文學與官方語言;第三,武力征服,唯有在優勢民族挾其強權進行兼并的威脅下,才會讓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與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對外[12]。這種西方的經驗如用在近代中華民族的構建上也非常吻合。我們也可以用這三個條件去考察清末廣東“民族”的構建活動。
如果要問清末的廣東是否有外力的武力征服的壓迫,那么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尤其對于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來說,這種壓迫感應該比普通民眾更加清晰和強烈。帝國主義列強在廣東開辟市場,瓜分利益,并且以戰爭這一令人“矚目”的顯性形式宣告其侵略意圖,這無疑讓當時已經逐漸產生了國家民族觀念的先進知識分子奔走相告:廣東是“廣東人之廣東”。那么,悠久的精英文化傳統和獨特的民族文學與語言呢?我們只能說有,但還不充足。在清末,雖然廣東的精英知識分子已經開始逐漸確認、創造自己的文化傳統,使用其自身的書面語言形式。但是,這些努力無論如何都只是草創,還不足以稱之為悠久,而且,這些新創造物都還未獲得普遍的認同和廣泛的傳播。最后的一個問題,是否有足夠長的建國史?雖然在古代,廣東曾經出現過南越國、南漢等地方政權,但是存在時間不長、年代又太過久遠,而且最后都被重組到中央王朝內了。所以,這個重要的基礎要件的缺失致使包括歐榘甲在內的廣東精英分子難以去構建一個獨立的廣東,明確的漢族性質也將建構一個新的民族之不可能一錘定音了。
2.“中華文明中心的南移”
作為我國一個在近代史上離西方的“距離”最近的海岸,廣東省不但是最先受西方侵略的地區,也是當時思想最活躍的地區。與當時北方中原思想界的自閉和陳腐相對立的是,廣東的精英知識分子則借助日本的譯作大膽地向西方學習。他們在這種環境中意識到,雖然北方的中原地區是漢文化的發祥地,但是已經日漸式微了,而面朝大海的南方的廣東,則是一片生機勃勃之地。
1905年,梁啟超又撰一文《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論述了自古以來廣東在世界史上的交通地位。他認為,雖然“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價值者也”[13],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海運的重要性逐漸凸顯,“若其對于本國,則我沿海海運發達以后,其位置既一變;再越數年,蘆漢,粵漢鐵路線接續,其位置將又一變。廣東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國中矣”[14]。
由此可見,梁啟超作為一個廣東人,在新時代的面前,在新思想的熏陶下變得格外自信。本文所述的先進知識分子歐榘甲也是如此,他們相信面朝大海的廣東,其政治經濟地位將不斷提高,將逐漸代替北方中原成為中華文明的中心。正是當時精英知識分子的這種自信和優越感,使得他們沒有拋開漢文化為中心的歷史敘述去構建一個獨立的廣東文明,而是把自己作為匯入到中華文明主干中的一股新的血液,把自身作為未來歷史的敘述者和漢民族的新代言人,從而賦予了廣東地方“民族主義”以漢民族主義的任務和內涵,使之成功轉型。
四、結語
在一般的定義上,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扦格,但在清末民初的特殊歷史環境下中,地方主義不僅沒有阻礙民族主義的發展,反而成為向民族主義的過渡工具。以往,多數學者雖然已經注意到清末民初的精英知識分子借助地方主義去推動普通民眾的民族主義,但未說明其推動的具體過程。本文以歐榘甲的政論著作《新廣東》為具體案例,探討了廣東的“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廣東的“民族主義”的發展經歷了由地方主義過渡到地方“民族主義”,再由地方“民族主義”升華到國家民族主義漫長過程。并且在這一探討的過程中,我們也由此發現了省級地方“民族主義”為何沒能形成的原因,即:一方面,精英知識分子身份的兩重性,使他們既希望代表懷有鄉土情結的廣大民眾,又不脫離華夏文化觀和漢民族本位的限囿;另一方面,缺失霍布斯鮑姆所謂的“民族主義原型”中的基礎要件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這些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普遍會遇到的問題,在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要被重新深刻的理解。地方“民族主義”的消解說明在國家形成過程中統一認同才是主流話語導向。晚清廣東知識分子作為地方話語權力的掌控者之一,其做法也為解決當下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民族主義問題提供了借鑒和反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