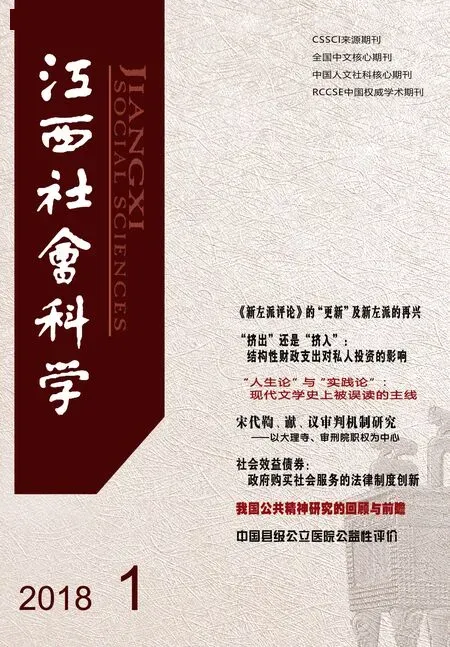差異性:理解霍爾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
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是伯明翰學派的旗幟性人物,被尊為“文化研究之父”。他的研究生涯以政治學為起點,繼而轉向文化研究領域,并在回歸自我身份認同的旅途中將移民身份、政治學和文化多元主義拼合在一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差異性”思想。2003年,介紹霍爾生平與思想的第一本著作《斯圖亞特·霍爾》問世。隨后,學界要求“認識霍爾、思考霍爾”的聲音愈發響亮。2004年,霍爾開始進入國內研究者的視野,在對他的思想闡釋在呈現多元化趨勢的同時,相關研究也逐步向縱深拓展。在此背景下,為求最大限度地接近霍爾思想的本來面目,國內學者編輯的文集《理解斯圖亞特·霍爾》(以下簡稱《理解》)應運而生,其中特別強調霍爾思想的“流散性”和“差異性”,這不僅對我們的文化研究具有深刻的啟迪作用,更為文化研究領域中的翻譯理論引入了全新的思考點。
一、差異性與流散敘事
正如《理解》一書的編排順序體現的那樣,霍爾的一生就以“流散性”為敘事邏輯,他的思想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處于不斷的涌動之中。霍爾走上學術生涯之初時忙于闡述自己的“身份”——牙買加的黑人新移民和英國中產階級的獎學金男孩,接著關注政治問題,進而拓展到各個社會領域尤其文化領域的研究。在這樣的流動場域中,霍爾密切關注著身份、文化、社群和霸權等各個學科領域的問題,對問題中的“差異性”尤其重視,反映出霍爾思想在流散中彰顯差異的特點。
霍爾的文化理論從關于個體與族群的理論開始。由于霍爾的“身份”問題,學界一直對膚色與其研究的關聯性存在著很深的誤解。《理解》一書準確地回應了霍爾的“身份”問題,從而對霍爾的學術定位與學術貢獻進行了撥正。在明確其個體身份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準確地把握霍爾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在霍爾的學術歷程中,“流散群體”[2](P25-37)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源于霍爾自身的“流散性”。作為一名逃離牙買加的知識分子,霍爾一生的理論思考都將對原生家庭的情感指涉、對種族膚色的回應方式和對移民、法治及社會秩序的思考轉化為有機因子,融于對社會的觀察和反思之中。可以說,霍爾“流散性”的童年生活對其學術心理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沉淀為他的文化研究理論的原始底色。尤其是,“黑人”膚色更成為霍爾思想歷程中一件顯著的具有流散性特征的文化事件。“事實上,‘黑人’也從不僅僅出現在那里。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個不穩定的身份。同時,它也是一個敘述、一個故事、一段歷史。它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被講述的、被談論的,而不是簡單地被發現的東西……黑人身份是一個需要被學習,并且只能是在某個特定時刻學習的身份。”[3](P45)這樣的“流散性”特點逐漸內化為霍爾文化研究與學術思想的行為特點,使“流散概念擁有一種存在于和穿透各種身份文化之間的功能”[1](P141)。
當霍爾進入國家與種族、社會公共教育和都市生活問題時,霍爾思想的巨大張力與滲透性進一步呈現出來。圍繞著國家與種族問題,過去的幾十年來,英國不斷有流散群體加入,產生了新的族性。霍爾提出“干預”理論,解讀這一現象。“雖然霍爾不是以對族性與種族的思考作為他工作的起始的。不過,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自我)發現之旅。”[4](P3)霍爾立足于種族形成的歷史特殊性,將種族的形成與多種身份的識別形式進行了多樣化的對接,并將各類文化與受到各界影響的社會機構進行緊密關聯,在極為宏大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下探討英國新族性的形成問題。
關于社會公共教育問題,霍爾的“跨學科公共教育觀”得到系統的體現。他始終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進行跨學科的理論研究,他的公共教育觀無疑也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征。這種公共教育觀是霍爾的文化斗爭意識與文化政治學思想在教育理論上的直接反映。霍爾主張激發批判主體、種族正義以及經濟與政治的民主熱情,提升公眾的社會責任感,將實踐與社會正義“接合”為規劃的文化政治學和教育學方法。關于都市生活問題,霍爾的空間美學、政治想象和道德倫理思想在都市這個集中化場景中得以匯聚。霍爾認為,文化形式的運用使得“統治性的種族政治倫理學”被放置于“都市生活中的主體和建筑的中心”[1](P233)。他對這種統治階級的做法持批評態度,我們也能夠感受到霍爾的這種都市批判思想帶有的“城市抵抗地圖”[1](P233)的意味。
在文化的流散特質、對民族與社會構成進行空間批判的理論基礎上,霍爾也探討霸權問題,并沿著倫理學、哲學以及政治學的方向延伸。在關于霸權問題的探討中,霍爾的理論陳述方式被指認為一種“葛蘭西式”[1](P262)的沖動,其理論形態是將國家觀念、話語觀念和“接合”觀念相互交互在一起。關于霍爾思想的倫理學延伸,“偶然性”特質與“寬容倫理學”是其倫理學的顯著特征。霍爾具備的慈愛之心在他作為倫理思想家的身份中扮演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他的倫理學思想對政治、社會、文化斗爭以及對個人身份的追求等問題的闡釋都具有深刻的意義。有關霍爾思想的哲學內涵,“差異性”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生發點,促發著霍爾對異質性和多元性觀點的思考。在哲學思想的形成歷程中,霍爾重視“差異”的生長性,積極吸收阿爾都塞、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哲學成果,并在與同時代其他哲學流派的批判對話中,不斷磨礪自己的理論鋒芒。關于霍爾思想中的政治學延伸,我們可以看到,霍爾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內容,并在后續思想發展中持續思考馬克思主義,他與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接合經歷了三個階段:英國新左派運動時期、文化研究時期以及撒切爾主義批判時期。在這三個階段,霍爾都與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保持著對話的狀態,尤其是在撒切爾主義批判時期,霍爾實施了撒切爾主義的“批判工程”,建構了一種處于社會危機狀態下的“資本主義國家形式轉型理論”。在突破英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背后的靜態的英國性概念中,霍爾發揮的作用不可低估。
從事文化研究的英國學者克里斯·羅杰克說:“這么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探索霍爾學術興趣轉移的復雜線索,據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正視霍爾在牙買加的成長經歷。”[5](P47)從霍爾的個人身份到流散群體,再到他關于民族、社會和都市問題的剖析,進而到向霸權理論、倫理、哲學和政治學的延伸,霍爾的個體性、社群性和思想性在流散中演進,各類問題和理論通過“差異性”的面貌拼合在一起,體現了霍爾對差異的尊重與重視。此外,霍爾思想與論說堅持著“不作保證”的作風,保持著作為具有差異性個體的獨立判斷,有明顯的批判性,為霍爾進行開放與批判并舉的研究提供了精神力量,展現出了獨特的理論魅力:“這種開放性為后來的文化理論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理論可能空間。正是這種卓爾不群的風格一直吸引著眾多人們走向霍爾的著作。”[6](P28)
二、差異性與多元文化接合
霍爾文化理論的群落十分龐大,難以一言概之。在眾多思想頂蓋下,“差異性”(或“異質性”)作為其文化理論的基點之一,流動在霍爾理論的各個分支渠道中。對“差異性”概念的關注,既是把握霍爾思想的基礎,也是對其思想進行闡發的重要途徑,更是對我們研究現代文化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多種學科理論大有裨益。
從概念意義的形成史來看,自從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符號學中提出“差異性”后,這一概念經歷了一個從差異到延異、從意義延異到文化延異的建構過程。索緒爾將語言塑造的概念(即所指,signifier)視為一種差異,認為概念由“概念與系統當中其他概念之間的否定關系”[7](P651-652)決定。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同一替換集合中的符號“按相似性的不同程度”依次排列,相似性以浮動狀態呈現出來。德里達(Jacque Derrida)認為概念的符號通過“延異(différance)”[1](P311)彼此關聯,突出符號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延遲性。霍爾則完成了延異與差異的對接,將差異視作一種有機的、連貫的存在。概念意義通過具體的說寫行為,被歷史地、暫時性地固定在話語序列上,顯現出各種差異,同時也對話語產生返還作用。
霍爾的差異理論與文化研究關系緊密,伴隨著霍爾文化理論的發展而演進。霍爾對文化的研究最初以“文化主義”的面貌呈現出來,理論內涵帶有一股居高臨下的精英意味。在這一理論中,霍爾自覺地區分文化階層與非文化階層,差異化在這樣的理論氛圍中被遮蔽,服從于階層所決定的從上至下的規制。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為打破這種精英文化意識做出了主要貢獻。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視角下,文化的重新構建具有了結構主義的框架,差異理論在結構主義的語境中得以生發出來。進入后結構主義時代,文化研究逐漸突破了“反映論”的局限,成為“現代世界的構成要素”以及“經濟、政治或社會變遷的要素”[8](P13),差異性的表現日趨明顯,在新型的社會結構中彰顯出其獨特的理論價值。
差異理論是多元文化的動力來源,并為多元文化的“構建”提供了理論啟發。霍爾認為:“差異將民主定義為真正的多元空間。”[9](P236)差異強調自身的異質性,即尊重多元性,對多樣性空間的營造有著理論上的誠意,能夠接納差異化帶來的各類細節問題與要求,并能積極重視問題的彼此協商與轉化。因此,差異促成了多元文化的營造,是其動力的真正來源。不過,霍爾在肯定后結構主義對差異的重視時,也批駁了其理論缺乏“整體性”。因此,霍爾的差異理論不僅僅是一種強調個體與個性存在的理論,同時也是一種對“差異化”整體的構想,其在“差異接合”方面的探索就是一種證明。
霍爾的差異理論突出差異的“接合”。霍爾肯定后結構主義支持的“差異永動性”的觀點,但同時也指出,作為整體的話語“是不同要素之間的結合”,這些構成要素同樣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進行再結合,“能夠將兩個不同要素在同一種情景之下進行結合的連接形式。這永遠不是一種必然的、決定的、絕對的和必要的連接……一種話語的‘整體’確實是不同要素之間的接合,而這些要素也能夠以其他不同方式進行再接合,因為他們并沒有必然的‘歸屬感’。這個‘整體’涉及的是在接合話語和相應社會力量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連接,但是并非是必然的連接”[10](P53)。應該看到的是,霍爾的這番指認并沒有將差異帶向盲目無序的游離狀態,而是肯定了差異會以一定的“方式”實現對接,重組的結果是一定時空中的意義,此番意義既可能成為意識形態,也可能因其意義的不固定性而發生反轉,從而消解掉意識形態。因此,這種結合是一種“引起或者構筑在社會、經濟力量以及政治和意識形態形式之間的接合,這或許能引導大眾在實踐當中以一種進步的方式來干預歷史”[11](P95)。霍爾將差異與接合視為一種文化的存在形態與文化斗爭方式,這是其差異理論對實踐的描述以及指導實踐的價值所在。
霍爾正是在各種理論的“差異性”基礎上將它們結合起來,從而提出博大精深的文化理論。“霍爾領導一批更年輕的新左派學者,從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出發,接合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葛蘭西)、結構主義、符號學等諸多當代理論資源,對當代傳媒、青年亞文化、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現代國家、歷史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以及階級與性別之間的關系等現實問題進行跨學科研究,反復探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抵抗的可能空間,在創立伯明翰學派的同時,也使自己成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1](P12)
三、差異性對翻譯理論的影響
“差異性”理論對文化研究領域影響甚巨,作為文化研究的“伙伴”與文化傳播手段之一的翻譯行為,始終與“差異”理論保持著對話,是差異性在語言文化及相關領域的生動展現。翻譯即是一種文本釋讀,不僅是一個完全被動接受的過程,其中也有對抗性的因素,“在協調的看法內解碼包含著相容因素與對抗因素的混合:它認可旨在形成宏大意義(抽象的)的霸權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個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層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規則—依據背離規則的例外運作”[12](P357)。通過這種背離,原初文本就會解讀出多重意義,與原初的意義不僅有差異性,也有可能是對立的。霍爾的這種差異思想與編碼/解碼的模式給翻譯理論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翻譯與差異的對話由來已久,無論中西翻譯界都將差異作為翻譯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歸化/異化”之辨、“文質之爭”等對翻譯思想的深層思考都突顯了翻譯中差異化因素的地位。不過,將差異作為翻譯研究的視點是在翻譯研究完成文化轉向之后發生的。在20世紀后期,翻譯研究經歷的“文化轉向”,是從以語言學為導向的翻譯研究轉入以文化為導向的翻譯研究。在文化研究中,霍爾明確提出必須要重視差異性原則,尤其是在話語中,話語的意義源于具體的語境。“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似乎被劃分為各個話語領地,等級分明地組合進主導的或選中的意義……這些事件必須首先安排進各自話語的領地才可以說‘具有意義’。”[12](P353)而在翻譯中,要確定話語的意義不能僅僅從原始文本出發,更要根據譯者主體的生活經歷與意義認知,從文本的意義流動中來確定文本意義。因此翻譯不但不能忽略差異性,而且更要重視差異性的存在及其影響。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影響翻譯的多種因素浮出水面,如意識形態、詩學等因素都對翻譯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對翻譯的同一化要求逐步邁向差異化。翻譯研究進入后現代語境以后,差異更是成為后現代翻譯的實踐追求目標。差異在翻譯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更成為翻譯的亮點。這一轉向不僅為譯作投來探照之光,也讓源語熠熠生輝。對翻譯中差異的關注,是對翻譯的宏觀流變與微觀動向的殷切“注視”,對于翻譯實踐的進行、翻譯自身的探索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霍爾認為,話語并不是“對‘現實’的‘透明’呈現,而是通過‘符碼操作’來對知識進行建構”[13](P129)。而翻譯作為一種重要的話語轉譯活動,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意義的轉化與差異化。翻譯在“文化差異場”中進行,各類差異因素發揮相互作用,對翻譯產生影響。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影響翻譯的文化差異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文化語境、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美學觀詩學觀、語言觀、文化前結構、思維方式、社會系統差異、物質生活差異,等等。[14](P176-193)其中,文化差異是對翻譯產生影響的文化方面的差異,關涉翻譯中的源語與譯語所在的不同文化群落,對翻譯中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內容的傳遞起著重要作用。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意識形態為統治階級在統治過程中傳達的思想意識,而廣義的意識形態則包括政治意識、文化意識、經濟意識以及來自于被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意識形態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既可以是顯性而強勢的,也可以是隱性而“溫和”[15](P130-137)的,從而對翻譯進行全方位的“操縱”。
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模式存有異議,對于諸如將意識形態、語言和文化視作是第二屬性的,即將其視為被社會經濟過程決定的而非自主設定的概念表示不滿”[16](P254)。這種模式重視文本解讀主體在文字解讀與轉移中的積極作用。而美學觀的差異則表現為原作者、譯者和讀者在審美層面的差異。由于通過源語與譯語連接起的兩方讀者在審美習慣方面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一旦把翻譯視作審美活動,譯文就會受到審美差異的影響。在文化差異、意識形態差異和審美差異等構成的差異場中,各類差異不定點地發生“對接”,使翻譯這一文化活動持續地發生改變。翻譯作品的面貌不斷刷新,翻譯活動由此顯現出多元化的氣質,成品的創作沒有終點,永遠指向新鮮的未知。在這里,我們不難發現霍爾的差異理論與翻譯的差異性具有理論上的相容性。
翻譯還在倫理上與“差異性”趨向契合。翻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經歷多個階段。第一階段,對源語的強調引導譯者緊扣原本,其極端化的表現是譯者對原本亦步亦趨,譯語的特點無法得到伸張。第二階段,對譯語的強調則使譯者尊重譯語的規范,極端情況包括譯本丟失源語特色,譯作千篇一律等。無論是對源語還是譯語的強調,都反映了翻譯在源語與譯語的天平上如何進行取舍的問題,也顯示了翻譯倫理的指向問題。霍爾的差異性理論與編碼/解碼理論則彰顯了文本接受主體的主動性,在對文本進行解讀與翻譯的過程中,譯者主體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獨立的解讀,“在這個層面上,混合語、方言和黑人英語,通過策略變音、重新規定重音和再語義、句法和詞匯編碼方面的其他講話步驟,對英語——民族語言的宏大話語——的語言控制進行一系列的顛覆活動,如解構英語控制的中心、使英語控制失去穩定的效果以及進行邊緣話語的狂歡活動”[12](P222),從而推進了翻譯理論的后現代進程,進而走向了新的階段。
在翻譯進入后現代語境時,延異衍生的不確定性為平等意識的誕生提供了合適的土壤,為打破翻譯的“歸化”傾向做出了突出貢獻。而霍爾的差異性理論則將差異與文化進行了融會,為文化研究拉開了寬容的帷幕,也使翻譯作為一種文化行為與差異拉近了距離,更好地共生共處。翻譯是面對差異、解決差異的活動,更是搭建溝通差異的橋梁,寬容倫理是翻譯發展的倫理趨勢。霍爾的差異性理論對異質表示尊重,其間滲透出的寬容倫理為翻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啟示,使翻譯在解決文化沖突、促進文化溝通中發揮更廣泛的作用。
理解霍爾思想,將文化研究、哲學研究、翻譯研究、社會學研究和倫理學研究等流散于各領域的力量吸引到霍爾的理論場域中,為各場域之間的“接合”創造了機會,尤其是對霍爾文化思想的討論,為各領域的發展帶來了多樣化的啟示,將差異的永動性和創造性發揮到學科實踐的層面。其中,差異理論作為霍爾文化研究的核心之一,與翻譯研究保持著長久的對話。在全球化、本地化和中國與外國文化密切交流互動的大背景之下,差異性與翻譯研究將在更為廣闊的視閾中共進,為尊重差異、促進差異互動、靈活配置差異的積極文化氛圍做出巨大貢獻。
[1]張亮,李媛媛.理解斯圖亞特·霍爾[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2](美)格蘭特·法雷德.斯圖亞特·霍爾學術歷程中的加勒比流散群體與加勒比身份[J].張亮,李媛媛,譯.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4).
[3]Lisa Appignanesi(ed.).The Real Me:Post-Moder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ICA Documents 6.London: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1987.
[4]Helen Davis.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4.
[5]Chris Rojek.Stuart Hall.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
[6]Angela McRobbie.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A Textbook.London:Sage Pubications Ltd,2003.
[7]Ferdinand de Saussure.From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Tallahassee:UP of Florida,1986.
[8]Stuart Hall,(ed).Introduction to Formations of Modernity.London:Polity Press,1993.
[9]Stuart Hall.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London:Zed Press,2000.
[10]Lawrence Grossberg.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986,(2).
[11]Stuart Hall.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85,(2).
[12]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3]Stuart Hall.Encoding/Decoding.London:Hutchinson,1980.
[14]楊柳.《道德經》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接受與翻譯[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5]楊柳,易點點.溫和的意識形態操縱:從伊斯蘭頌詩到《利西翠旦》的改寫[J].外國文學研究.2010,(6) .
[16]J.Cruz&J.Lewis(ed).Viewing,Reading,Listening: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