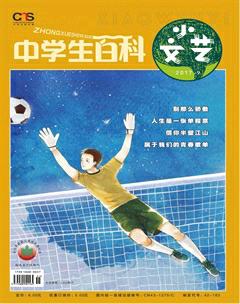江南過客
勞思琪
人人憶江南,江南便愈發似夢。
八月將盡時,我赴浙江,去會江南水鄉的柔情縹緲。
行程一早便定好了,從西子湖畔,到古樸烏鎮,再往湖州南潯。一點一點遠離城市、人群、車輛,一顆心仿佛一點一點放遠的風箏,雖然天際空蕩,卻也愈發寬廣。
西湖
我想象過無數次西子湖的模樣:坐落著石塔和斷橋,容納著映月與湖星,湖上島嶼綿延若獸的背脊,天光傾灑,便見煙波浩渺,綠柳白堤,湖水青碧,仍是古時風姿,舊日韻味。
深夜十二點抵達西湖邊下榻的酒店,車子駛過寬闊安靜的街道,統一的昏黃燈光,樹影繁盛而婆娑,像搖曳的夢魂。路過一些廣告牌,一些花木造景,都令我欣賞,處處感到用心,有不俗品位。
只是匆匆掠過,我便覺得這應該是杭州的模樣,一座文化與經濟并重的名城,在現代文明的簇擁里安然沉睡,絲毫不覺浮躁,因為那千年底蘊始終未變,支撐著它的靈魂。
我內心歡喜,但也學了幾分含蓄,不動聲色。
第二日夜晚,在西湖邊散步,游人如織,仍是城市中心的喧嚷。夜色深沉湖水闊,沒落下什么特別印象,只記得西湖邊名叫“外婆家”的餐館,所有菜都美味得不行,現在想起來還是嘴饞。可惜我此刻離西湖太遠了,但那里的水色湖光應當還是一樣的吧。
由于行程安排,只來得及用一天的時間與杭州相會,無法多做停留,我轉而向桐鄉去,懷抱西湖十景里的斷橋殘雪、三潭印月和柳浪聞鶯,希望有機會再歸來。至少“外婆家”的菜是不能只吃一次就罷休的。
烏鎮
桐鄉有烏鎮,不過大多數人只識烏鎮、不識桐鄉。
我最記得,下午四時,從烏鎮東柵景區出來,逛得乏了,坐在歇腳的亭子里。正想找個地方喝喝茶,本以為無用擺設的古戲臺里卻走來一位扮相嚴謹的角兒,一邁步一抬手,口中唱詞便“咿呀”地繚繞起來。風吹過古戲臺屋檐邊掛著的紅燈籠,燈籠搖曳,那紅裝的人兒也搖曳,身后一眾拉曲敲鑼的皆是中年人,或凝眸或閉目,端的是專心致志心無雜念。至于那襲紅衣,我只見她身姿輕柔曼妙,實在看不出年紀。
原來古戲臺每日下午都有表演,是幾位有共同愛好的人自發來做的,閑來無事演一場,觀眾有無,回報有無,全不在意。烏鎮雖被開發已久,可我以為這些人一定是此地的原住民,純粹的外來人做不到如此。他們認真而平靜,借著古戲臺,唱一曲煙云。臺下看客們不懂得喝彩,只是默默地,和臺上的人一樣認真。
斜陽余暉漸漸傾灑下來,我全然不知自己在聽什么在看什么,唯一的感知是——暮色如此蒼涼。暮色,戲臺,那一刻是一同老去的。誰也沒想要挽留它們。
后來我在烏鎮走橋看水,行船步廊,都沒有見古戲臺那樣的印象深刻。
照例在巷里街邊尋覓各種美食,在店里長板凳上喝了兩杯西梅汁,再加一杯打包帶走,覺得自己十分富有。
臨近傍晚時天色一變,風雨欲來,我沒有帶傘,倉皇逃竄,在書院別院發現一家書店,大多是二手書,都有翻閱和時間痕跡,外文中文皆有,文學色彩濃厚,偏于晦澀,也多各類畫冊,不乏抽象隱晦者。
店里沒有主人,偶爾有和我一樣為著躲雨的游客走進,立刻噤聲,退至檐下。
為這風雨所困,我心甘情愿。若是晚來天仍雨,能飲一杯無?
南潯
在南潯,所住的客棧很美,店主用詞牌名做房名:水調歌頭、江城子、滿江紅、浣溪沙、虞美人、西江月……
用鑰匙打開房門,好聞的熏香撲面而來,細看更加驚喜,仿古時閨房,設計精巧,有女子細膩妥帖的氣質。
相較杭州的繁華熱鬧、烏鎮的古樸大氣,我所看到的南潯一半是現代城市面貌,一半是舊時小鎮江南,兩者劃分并不涇渭分明,可能只隔著一條河兩條街,并立相視。
在南潯參觀景點是很舒心的,除了小蓮莊和藏書閣里看到過幾批游客,大多時候是清凈無人的。
我在古宅里獨自穿行,但見院落深深,早就沒了人的氣息,陽光明媚,可屋內還是一派陰涼。大約就是“小閣藏春,閑窗鎖晝,畫堂無限深幽”那般。我疑心自己當時如果見到什么鬼怪,也是合理的事。應該不會是厲鬼,因為整座老宅除了塵埃一般的寂寞,莊嚴得有些過分深沉,是沒有什么“戾氣”的,大約也只能殘存一些單純的執念和嘆息吧。
這樣的古宅在南潯有好幾座,只留下了建筑,家具裝飾什么的大多不在。我說里面沒有人的氣息,可能也和它們的空曠有關。不過,這么大的住宅,當年要多少人才能填滿而不感到寂寞呢?
南潯的街道上有一家“貓與天空之城”的連鎖書店,當真是我尋覓已久的。我從那里買了《密林中》。我喜歡那本書,那家店,也喜歡南潯。好在它們都是可以放在心里帶走的東西。
行程結束時我并未感到太多的留戀,即使離開,所心愛的那一切還會原原本本留在那里。況且我本就是過客,慕名而往,瀟灑而別,一身自如。
八月,我去江南走了一遭,謹以此文記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