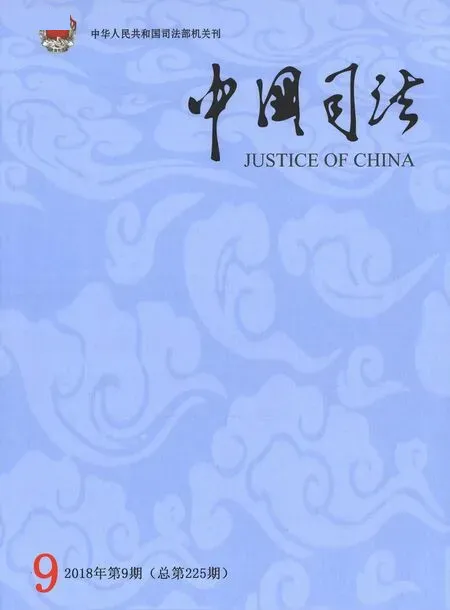關于公證證明標準若干問題的思考
楊 易(江蘇省南京市石城公證處)
2018年6月,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減證便民、優化服務的部署要求,做好證明事項清理工作,切實做到沒有法律法規規定的證明事項一律取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做好證明事項清理工作的通知》。進一步深化公證領域“放管服”改革,切實提高公證為民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水平,減少公證辦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循環證明、重復證明等各類無謂證明,最大限度減輕群眾的證明負擔,已成為公證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公證證明活動中,公證人員依據法定程序,通過收集證據材料,對證明對象進行認識和判斷。那么,如何保證證明對象的真實性、合法性,如何判斷出具的公證文書符合真實性、合法性的要求?就需要設定一個認定標準,即公證證明標準。設定合理的公證證明標準,既有利于指導公證人員的公證實踐,也為錯證追究中判斷公證責任提供了衡量的尺度。然而,各地對公證證明標準的認識尚未統一,各地公證人員在辦證過程中,出證尺度寬嚴不一,無形中加劇了群眾的辦證負擔,影響了公證行業的整體形象。因此,厘清并規范統一公證證明標準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公證證明標準的內涵、原則
(一)公證證明標準的內涵
公證證明標準是指按照法律規定認定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對公證證明要求所要達到的程度或標準。公證證明標準的概念衍生于民事訴訟證明標準,但又不同于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兩者在目的、形式、要求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
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解決糾紛,因此在民事訴訟中,證明標準主要在于理清紛亂,還原事實的本相;公證的目的在于預防糾紛,需要預測未來糾紛發生的可能,盡可能的收集、篩選、固定證據,將矛盾糾紛扼殺在萌芽之中,將一項或多項證據明確為一個或多個事實。民事訴訟是司法活動,法官處于中立地位,訴訟大多在事實發生之后,法官對雙方當事人所提交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及證明力的大小進行判斷與篩選;公證是準司法活動,公證所明確的事實大多產生于訴前,公證人員親歷法律活動,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與文書進行證明以及證據的固定,僅著眼于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民事訴訟中,法官面對的是雙方訴求相對立的當事人,需要對證據的證明力進行比較;公證活動中,公證人員面對的一般是訴求相同的當事人,需要審查的是證據材料的真實性、合法性以及是否足以支撐公證之主張。
(二)確立公證證明標準真實性、合法性的原則
《公證法》第28條規定:公證機構辦理公證,應當根據不同公證事項的辦證規則分別審查“提供的證明材料是否真實、合法、充分”“申請公證的事項是否真實、合法”。第32條規定:“當事人虛構、隱瞞事實,或者提供虛假證明材料的”以及“申請公證的事項不真實、不合法的”,公證機構不予辦理公證。
公證活動中的真實性原則,究竟應該是“客觀真實”,或者應該是“法律真實”,還是在不同公證事項中選取不同真實性標準,需要進行分析。在公證領域,“客觀真實”是指公證人員運用證據所認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符合公證時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客觀真實情況,即做到主觀認識符合客觀的真實情況。“法律真實”是法律制度規定的證明所要達到的真實程度和狀態,是指證明過程中,運用證據對公證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真實性的認定應當符合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應當達到從法律的角度認為是真實的程度①樊崇義:《客觀真實管見——兼論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公證證明材料與待證事實之間必須具有關聯性。證明材料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呈現為極為復雜的表現形式:當證明材料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確定無疑,只有一種可能時,哲學上稱之為必然性或確然性;當證明材料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不是確定無疑,而是存在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可能性時,則稱之為蓋然性②秦世平:《對公證證明標準的全面分析》,《中國公證》,2006年第3期。。
筆者認為,對公證證明標準真實性原則的把握,應當區分不同的公證事項確立相對應的標準。以證明現在正在發生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見證類公證事項,應堅持公證內容的“客觀真實”,將“必然性”作為此類公證的證明標準。以證明過去已經發生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非見證類公證事項,如比較典型的繼承權公證等非見證類公證事項,則應將“蓋然性”作為此類公證的證明標準③杜紅梅:《公證證明標準探析》,《中國司法》,2010年第10期。。
公證合法性原則是指公證證明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內容、形式及取得方式符合國家法律、法規、規章規定,不違反有關政策和社會公德。公證是一種法律活動,公證活動的第一要義就是“應當遵守法律”④中國公證協會編:《公證員入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這里“法律”的含義應不局限于廣義上“法律”的概念。公證人員依法辦證,應當首先假定每一個公證文書都將作為法庭證據,要著眼于法官的視角來看待公證文書。因此,對于能夠作為法官判案的“法律”依據,都應納入公證合法性原則的范疇。
二、公證證明標準適用規則
公證的證據效力是公證能夠發揮其社會作用的基礎。公證文書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材料,有助于糾紛的快速解決,使有限的審判資源發揮出最大的效益。在非訴訟方面,公證書也可以有效地解決當事人之間潛在的糾紛。公證文書較高的證明力,將會直接減少利害關系人對于公證當事人的各種疑慮,從而促進民間正常的民事和經濟交往,也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⑤王勝明、段正坤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頁。。公證這些社會價值的實現,均依賴于公證的證據效力。可以說,公證的證據效力是公證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石。為了保障公證的強證據效力,公證制度在制度層面設定一個較高的公證證明標準,有利于維持公證的強證據效力。
刑事審判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行政訴訟確立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公證證明標準衍生于訴訟證明標準,在公證活動中,許多公證人員對證明材料“真實”的認定上一概定格為“客觀真實”,并統一適用于各類公證事項之中。筆者認為,這點值得商榷。公證證明標準的統一適用導致了各類公證事項證明要求的失衡。例如,在繼承類公證中,被繼承人去世時年紀如果比較大,其父母生存情況經常成為辦理公證的一個難點。為了追求客觀真實,公證人員只能絞盡腦汁,去找尋連當事人都不知道的事實。因此,在不同公證事項中,區分不同的公證證明標準就顯得尤其重要。
理論通說認為,民事訴訟應適用“優勢證據”或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是將蓋然性占優勢的認識手段運用于民事審判中,在證據對待證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確實充分的情況下,如果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已經證明該事實發生具有優勢的蓋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對該事實予以確定。“優勢蓋然性”證明標準的確立,賦予了法官在審查判斷證據和認定案件事實上較大的自由裁量權⑥朱自全:《關于公證證明標準》,《中國公證》,2007年第11期。。民事訴訟證明中的“優勢蓋然性”是相對立的雙方當事人所提交證據的比較優勢,公證證明中的“優勢蓋然性”其實是當事人提交證據的充分程度,公證證明標準不能完全照搬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其源于后者,但應當高于后者。
筆者認為,公證證明標準可以借鑒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分為蓋然性占優勢、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和確實充分四大類,并可運用百分比量化心證程度。假設證據無任何證明力為零、證明完全符合客觀為100%,則上述標準應在大于50%小于100%之間。對于蓋然性占優勢,只要證明程度大于51%,即便為51%,亦可認定已獲證明,高度蓋然性需為75%以上.排除合理懷疑為90%以上,而確實充分則需95%以上⑦郝振汪:《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現代法學》,2000年第5期。。
筆者認為,對于公證申請人的主體識別需要較高的證明標準,需要達到充分的要求。公證申請人的主體適格,系公證辦理的根本,如果對主體的審核出現偏差,即使法律程序完備、文書材料撰寫出色,也無法逃脫公證文書被撤銷的命運。在公證財產方面,證明標準需要達到高度蓋然性或排除合理懷疑的要求。大部分的公證都是與財產有關的,因此,對于財產的所有人、財產現存的情況等都會影響公證的效力,但是又不必然導致無效。對于其他與公證內容不是密切相關的證明,只要達到蓋然性占優即可,無需無限度的提高證明要求。
三、公證證明標準與錯證追究
公證活動具有局限性,即使是公證人員盡到了審慎核查的義務,嚴格遵守法律法規,也無法保證所有的公證結果都等于客觀真實。公證活動僅能保證公證結果是在嚴格依據法律法規規定程序下認定的等于或者接近客觀真實的真實。因此,無法保證所有的公證結果都等于客觀真實,這樣就產生一個錯證的問題。如果發現公證對象的真實性、合法性與實際情況不符,則為公證錯誤。《公證法》第43條規定: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因其過錯給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由公證機構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在這里,確立了公證責任的原則,即為過錯責任。有過錯才有責任,無過錯無責任。這就避免了發生錯誤公證書,即不分青紅皂白,一律采取客觀歸責主義,強令公證員、公證機構承擔無過錯責任。
對于公證過錯,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界定,但一般認為包括故意和過失。故意指公證員有意地弄虛作假。過失一般指公證員沒有嚴格按照法律法規,或者沒有盡心盡職地盡到審慎的審查義務。公證的證明標準概念為確認公證責任提供了一個尺度,如果從出具公證書時所收集到的證據材料來看已經達到了證明標準,即使最后發現公證結果和客觀事實不相符合,公證機構只應當撤銷公證書,而不承擔過錯賠償責任⑧葉歡江:《論公證證明標準》,《中國司法》,2006年第8期。。因此,雖然公證的證明標準是審查證明材料的標準,錯證認定標準是對已出具的公證文書的檢測標準,但這兩個標準應當是相統一的,只有統一的標準,才能為公證活動提供一把相同的標尺來衡量。
根據公證證明標準的要求,在公證書出現錯誤時,應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判斷公證員、公證處是否應當承擔責任以及承擔責任的大小:一是從客觀方面看,公證員、公證處在證明活動中有無違反或在多大程度上違反了公證證明標準的具體規范要求;二是從主觀方面看,該項公證文書的承辦公證員(包括審批人員)是否已盡到一名普通執業公證員應盡的合理注意義務,即對證明材料的審查是否已達到足以使一名普通公證員排除合理的懷疑或內心確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