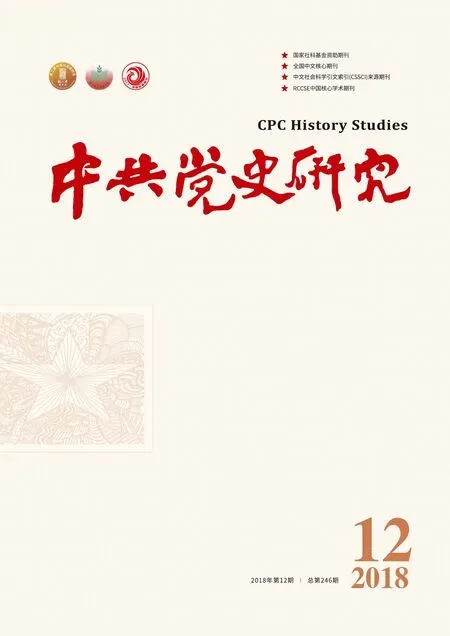“新史料與新視野:上山下鄉與知識青年”學術研討會綜述
易 海 濤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和潘鳴嘯(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等三本著作出版之后,有關中國知青史的研究既沒有呈現出想象中的繁榮,也沒有出現對已有研究模式的實質性突破,這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響是明顯不匹配的。之所以有此反差,與資料缺乏和理論視野狹窄(學科建設不足)有密切關聯。有鑒于此,2018年6月22日至23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組聯合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上海市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在上海舉辦了以“新史料與新視野:上山下鄉與知識青年”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江西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福建師范大學、廣州美術學院,以及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美國加州大學圣塔克魯茲分校、美國密歇根大學、美國埃默里大學、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的30余位學者,圍繞學科建設、資料開發、地域性研究以及傳統議題等四個方面,對知青上山下鄉這一問題作了深度交流和討論。
一、知青史研究的學科建設
任何一個研究領域想要取得長足發展,都需要對既有成果進行梳理、分析,對學科建設展開思考、探討,知青史研究也不例外。對此,與會學者紛紛提出,要建立起知青史研究的學科理論體系。而且,因為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課題,牽涉當代中國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建立學科理論體系的同時,要打破學科壁壘,以歷史學為主體,引入政治學、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視角。理論體系的建立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對具體研究案例進行總結和反思的過程。在具體研究中,我們既要重視延續既有范式(如將“知青”、“知青工作”和“知青運動”加以區分),也應努力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此外,對于沒有知青經歷的學者來說,總結研究方法、注重學術規范還可以有效彌補情感經歷方面的短板。與會學者認為,在知青史研究的學科建設中,以下兩點尤其值得討論:
其一,相關概念的重新梳理和界定。現在,很多知青史研究成果在使用“上山下鄉”“上山下鄉運動”或者“回鄉知青”“下鄉知青”等概念時存在混淆不清的現象。尤其對于前一組概念,許多人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青運動等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運動,這必然會影響到整個知青史的敘述和評價。與會學者紛紛指出,要注意時間性,既要看到兩段知青上山下鄉之間的關聯,更要看到其差異。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區分其背后的制度緣由和理論背景,才能對知青史的細節展開準確、恰當的考察。例如,有會議論文專門研究了回鄉知青問題。對此,不少學者就“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的概念進行了討論,認為除了身份認同因素之外,二者的差異主要是政策造成的,后來還受到“文化資本”的持續影響。由此可見,對類似概念的重新梳理和界定能夠拓展知青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助于實現學科建設的良性發展。
其二,知青上山下鄉與當代歷史諸多問題之間的關聯。就現有知青史研究成果而言,不少論述往往局限于知青史本身,割裂了它與其他諸多問題的關聯。事實上,數量龐大的知青群體所牽涉的問題涵蓋方方面面,包括城鄉關系、城市發展、文化沖突與調和、家庭關系、人口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顯然突破了傳統知青史的研究范疇。與會學者普遍認為,在研究知青史時,要超越具體“議題”,追問“議題”背后的“問題”;既要提出有關懷、有價值的“問題”,更要努力解答這些深層次“問題”。
二、資料的開發和利用
此次會議的一大亮點是新資料的開發和利用。會議論文都很注意利用地方檔案、日記、書信、回憶錄、地方志、圖像、口述訪談等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的解讀,學者們對知青的醫療衛生、日常生活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其中,與會學者以知青書信、日記為例,討論了新材料的搜集、整理、解讀方法,呼吁研究者在利用相關材料時注意儀式化與程序化、公共性與私密性等問題。具體而言,當時的日記往往存在一些儀式化的內容,給解讀帶來一定困難。書信方面,則往往只留下了通信雙方中單獨一方的材料,因而存在碎片化現象;加之在當時的環境下,書信內容具有某種公開性,這也會給利用帶來一定麻煩。因此,與會學者認為,目前亟待探討出一套解讀方法。相關高校、科研機構應該加強合作,就此類材料的搜集、整理、利用進行探討。可以反復研讀具體材料,甚至找到當事人進行口述訪談,追問其書寫時的心態,以及后來認識上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可以開辟知青史研究的個人史、心態史、情感史、記憶史等新領域。
有學者從美術史的角度對知青上山下鄉的圖像進行了分析和討論。這項研究發現,當時的美術作品盡管擺脫不了時代的影響,但也在一些細節上與社會美學思潮相呼應。對這種呼應關系的發掘,有助于追蹤知青圖像背后的思想史意義。當時,社會上存在著大量的圖像資料,這無疑有利于展開知青史研究中的圖像史研究,但要注意圖像背后的歷史語境。與會學者還對圖像資料的搜集和利用展開了討論——一方面要重視對已有圖像資料的研究;另一方面則有許多圖像資料正在消失,譬如知青安置點等,這要求我們加快對此類資料的搜集,同時加強知青博物館的建設。
與會學者普遍認為,要想實現知青史研究的長足發展,資料搜集和整理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要多從基層資料出發,拓展資料的搜集范圍。除文獻、圖像等資料外,口述材料、田野調查材料等也亟待搜集整理,以便彌補官方檔案之不足。這一點對于沒有知青經歷的學者尤為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偏聽則暗”的現象,使自己的敘述更為全面、客觀。在搜集資料的基礎上,還要努力建立起一套整理、利用資料的方法。此舉不僅有助于初學者避免陷入資料的汪洋大海,使其在史料面前既“沉得下去”,又“走得出來”,更可以由此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實現多學科對話,豐富對知青上山下鄉的認知。
三、區域性研究的路徑選擇
知青上山下鄉波及整個中國,有共性,更有地方性。因此,此次會議對如何開展地域性知青史研究進行了深入討論。事實上,知青上山下鄉本身就是一種跨地域的遷徙,這種遷徙并不局限于政治地理范疇,還牽涉經濟地理、文化地理。在此過程中,知青上山下鄉與原有地理格局之間的關系,包括與傳統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的因應等,都值得重新梳理和解讀。這樣的討論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其一,注意在時空交錯的視野下展開研究。以閩粵贛邊的知青運動為例,與會學者提出,要注意歷史上區域的形成,譬如“華北”“江南”等區域在學術話語中是如何生長起來的,其背后的經濟、文化、行政等因素起了什么作用;此外,還要考察知青與該地區的交融和對該地區的影響。只有通過追溯歷史,還原外來者與當地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展現出時空交錯視野下知青上山下鄉的豐富圖景,并最終回應一些學術界的經典命題,如革命與宗族社會、鄉村社會秩序等。事實上,知青從北京、上海等地到黑龍江、新疆、內蒙古等地,固然是一種跨大區交流,但整個知青上山下鄉更是一種跨地域、跨文化、跨經濟圈的交流,在此過程中所展現出的沖突與融合無疑值得進一步探究。
其二,注重揭示此前被忽略的邊緣地區和邊緣群體。以往關于知青上山下鄉的研究多從整體層面展開,其中往往又以大城市為中心,尤其是對知青安置較為集中的地區討論得比較多。此次會議上,部分學者注意到了一些偏遠地區的知青運動,相關研究成果展現了與主流敘述不盡一致的歷史面相。例如,有學者通過對廣西央務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考察,尤其是通過口述訪談,發現了這一邊緣地區知青運動的特殊性。又如,有學者考察了歸僑知青在安置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各地區安置歸僑知青的差異。對這些邊緣地區、群體的探討引發了學者們關于知青群體特殊性的討論。例如,“老三屆”與“新三屆”之間存在差異,各個地方的知青群體也各不相同,研究者在考察具體問題時,需要注意將其置于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各種異同背后的深層因素,包括政策、地域、文化、資本等,更是研究者必須尤為注意的問題。
關于區域性知青史研究,與會學者還指出,一定要避免就地方談地方,既要有全國性的宏觀關照,又要有類似區域的橫向對比,更要有區域內部的層級梳理,以實現區域性知青史研究的特殊化、立體化、多面化。
四、傳統議題的再出發
由于與會學者搜集到許多新的資料,采用了一些新的理論,因此不少會議論文對諸如知青上山下鄉的原因、知青婚姻之類的“舊問題”進行了新的解答。關于知青上山下鄉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為了“處置過剩勞動力”,也有學者認為根源在于“消減城市負擔”這一經濟因素,但在實行的過程中不斷有政治因素加入,隨著政策的持續推進,兩種因素不斷疊加,最終在中央、地方與知青個人(家庭)之間構成了一個安置系統。對此,學者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會學者紛紛指出,既要看到現實因素對知青上山下鄉的重要影響,也要注意意識形態因素與這場運動的緊密聯系;既要注意區分領導人之間的個體差異,更要注意把握計劃經濟體制下普遍的歷史背景;還要注意把握時間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差別。
有論文通過考察1966年至1968年上海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過程,發現了最高領導人決定發動知青運動的地方性因素。這種探討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以及知青上山下鄉究竟是如何具體展開的。
針對一篇重新考察知青婚姻問題的論文,有學者給出了新的分析視角,即從個人與體制關系的角度看待知青婚姻的演變;也有學者指出,要注意到知青婚姻的區域性差異,尤其是來自大城市的知青與其他知青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些問題已經突破了知青婚姻本身,需要對整個知青史展開一種“網絡化”的分析,即以知青婚姻為“連接點”,討論其他相關問題,如家庭、城鄉關系、身份,等等。
知青運動的評價問題也得到了重新討論。如今的學術研究越來越關注個人,但就知青上山下鄉而言,個人與整場運動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或許永遠無法得到清晰的解答,但學者們普遍認為,需要把握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定位,既要看到知青的共性,也要看到個性,要注意挖掘知青上山下鄉的具體影響,要對知青個人與知青運動加以區分。
總體來看,兩天的熱烈討論使與會者對知青史的研究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即以資料開發為路徑,通過對資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實現知青史研究的細化、深化、學理化,同時培養更多新人(20多篇會議論文中,有10篇是沒有知青經歷的年輕一代學者提交的),產出更多高水平成果,從而建立起知青史研究的理論體系,使知青史研究常做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