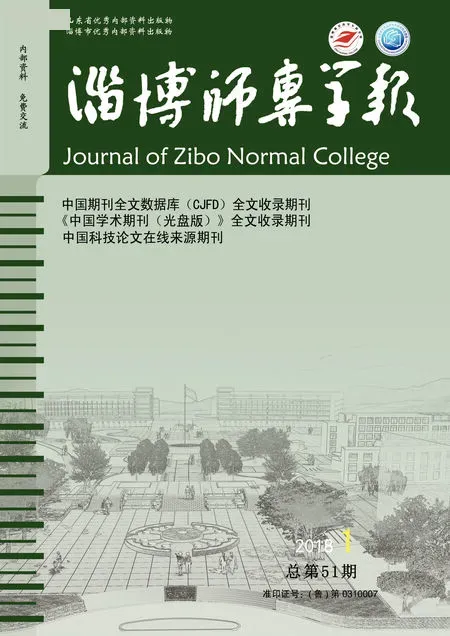《西游記》學術研究簡略
臧慧遠
(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山東 淄博255130)
清代張書紳曾說:“《西游記》一書,原是千古疑案,海內一大悶葫蘆。”的確,這個“悶葫蘆”隨著歷史和時代思潮的演變,出現的解讀觀點更是眾多,其中有明清時期的儒釋道觀點,有五四學術轉型時期的批判和突破,也有新時期縱深、多元的理解。面對《西游記》流傳時間久、爭論觀點多的客觀現狀,其研究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明清時期是古代《西游記》研究主觀評點期;1919年五四之際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是《西游記》研究現代轉型開創期;新中國建立至今是《西游記》研究復蘇繁榮并走向多元縱深時期。
第一階段,明清時期《西游記》的研究主要是評點式的批評研究,主要集中在哲理、宗教層次上,出現了釋儒、談禪、證道各派觀點。明代世德堂本《西游記》卷首所載的《刊西游記序》被認為是古代《西游記》評點的發軔之作。同時期李評本則用當時盛行的“心學”思潮來闡釋《西游記》,揭示其所蘊含的“心學密諦”,成為關于《西游記》的第一個成熟的評點本。后來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認為《西游記》的主旨意在“求放心”,“《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1](P446)此后,清代的評點在批評意識上出現了嚴重的差異,有以《西游證道書》《西游真詮》《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記記》《西游記評注》為代表的“證道”觀;以《新說西游記》為代表的“釋儒”觀,其間亦摻雜有三教合一的“談禪”因素。我們對明清評點的認識,尤其對清代評點的認識,多是認為“以《易》、以《大學》、以仙道來解釋《西游記》”,“戴上了一副著色眼鏡”,是“在大白天說夢話”[2](P34),對其間的曲解附會應清楚地認識,對其全盤否定亦失之偏頗。應認識到有清一代,評本蜂起是有其復雜的歷史原因和文化積淀,有著時代的烙印。
第二階段,1919年五四之際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實現了《西游記》研究的現代轉型。現代文學研究中,出現了魯迅、胡適、鄭振鐸等一批耀眼奪目的現代新文學大師,引進西方理論,闡釋全新的價值觀念、評價標準,重新闡釋與定位《西游記》。魯迅撰寫的《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在史學的背景下研究《西游記》,不僅將《西游記》納入神魔小說的發展軌道,而且認為“假欲勉求大旨,則謝肇淛之‘《西游記》漫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致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數語,已足盡之。”[3](P106)胡適的《〈西游記〉考證》對《西游記》的作者問題、成書問題、演化、人物來源、八十一難的歷史依據做了全面的考評,并且十分明確地“指出這部《西游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并沒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4](P15)其鮮明地提出了“游戲說”的觀點。此外,鄭振鐸的《〈西游記〉的演化》、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陳寅恪的《〈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等均對《西游記》從故事淵源、作者、版本、人物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闡釋與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績。比如在版本問題上,鄭振鐸認為永樂本是《西游記》的祖本,孫楷第則對版本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辨別,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對于孫悟空的原型,魯迅認為源于中國古代淮水水怪無支祁,胡適則認為源于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陳寅恪用中西比較的視角探討了孫悟空與豬八戒的原型;在故事演變上,鄭振鐸則在《〈西游記〉的演化》中作了詳細的論述。由于社會歷史環境限制,資料有限,現代研究者在認識上也會有些錯誤之處,但他們所取得的成績開創和奠定了《西游記》研究的現代轉型。
第三階段,當代《西游記》研究以文革為界又可劃分為三個階段,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當代的《西游記》研究與社會發展、時代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逐漸由單一的政治性走向全面的繁榮。文革前,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圍,《西游記》研究趨向于單一化,多用社會學、階級斗爭學說來解釋《西游記》,側重于探討主題思想。這一時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游記〉研究論文集》(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版)中。該論文集收錄了1949—1957年間《西游記》研究的主要成果,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批評的方法來評論《西游記》,共收錄論文十八篇。張天翼在《〈西游記〉札記》一文中首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批評的方法來評論《西游記》。此文認為孫悟空大鬧天宮象征著古代社會的農民起義,并認為取經過程中的神魔斗爭象征著封建社會農民階級對統治階級的反抗斗爭,而后來的西天取經則引申出孫悟空投降論的觀點。張天翼的這種階級斗爭學說的批評方法被認為是“撇開了一切玄虛、歪曲的舊說,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西游記》的客觀因素”,“應該是研究《西游記》以及其他一切神話小說的準則。”[5]自此以后,研究者深受影響,多充分運用社會學批評方法,對作者吳承恩的思想、小說主旨、取經人物的階級性等進行充分的探討。此時的《西游記》研究由于過分強調意識形態性,過多的政治附會,而侵蝕了學術固有的本性,偏離了正常的學術理性,觀點傾向于機械化和簡單化,淪為庸俗的社會學研究。
文革十年期間,由于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6]它不僅使國民備受摧殘,文學界亦是陷入萬馬齊喑的悲涼局面。《西游記》研究亦進入黑暗期,罕有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1973年郭豫適、簡茂森為人民文學版《西游記》撰寫的長篇《前言》,其中分析了《西游記》故事演變、成書過程以及思想主題、藝術特色等問題,此可以說是這一時期僅存的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文章。總之,十年文革不僅帶來民生的艱苦,也帶來學術研究史上的“真空地帶”。
文革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今,《西游記》研究呈現出全面復興與繁榮的景象。其不僅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反思,提出新的意見觀點,而且全新的學術觀念和科學方法的確立,使得《西游記》的研究多元化。1982年10月,首屆全國《西游記》學術討論會在連云港、淮安兩地召開,涉及到《西游記》的故事演變、主題、藝術、版本、作者思想等,并且編輯出版了《西游記研究》。此后第二屆、第三屆全國《西游記》學術討論會相繼召開,彰顯出《西游記》研究突破前期的單一化,開始逐漸走向全面、繁榮階段。此時期關于《西游記》的研究論文在數量和質量上均突飛猛進,出現了章培恒、張錦池、趙國華、吳圣昔等研究者的優質文章。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著作,比如胡光舟《吳承恩和西游記》、朱一玄和劉毓忱編的《〈西游記〉資料匯編》、劉蔭柏主編的《西游記研究資料》、張靜二《西游記人物研究》、蘇興《吳承恩年譜》、余國藩《西游記論集》、張錦池《西游記考論》等。80年代的反思性,使得《西游記》的主題研究有了較大的突破,這一時期出現了,李希凡的“主題轉化”說、胡光舟的“主題統一”說、朱彤的“歌頌市民”說、朱式平的“安天醫國”說、羅東升的“誅奸尚賢”說、朱繼琢的“反映人民斗爭”說、苗壯的“西天取經主體”說、胡光舟的“歌頌反抗、光明與正義”說、高明閣的“主題裂痕”說。同時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對主題研究的“哲理性”流向,比如金紫千、孟繁仁、陳民牛、鐘嬰、曾廣文、方勝、李欣復、王燕萍、張錦池、呂晴飛、姜云等均撰文將《西游記》與人生的意義、價值、前途、命運等聯系起來,探尋作品的哲理性內涵。
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術思想、理論、方法更為多樣化,更新更為迅速,《西游記》研究在更好地消化、吸收前代成果的基礎上,借鑒西方的理論學說,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王國光的“密碼”說,諸葛志的“將功贖罪”說,劉勇強、李安綱的“心路歷程”說,田同旭的“情理相爭”說,方克強、楊義的“神話母題”說,克珠群佩、王意如的“崇佛(禪宗)”說,竺洪波的“追求哲理和審美意義上的自由”說,康金生的“宣揚佛法及其政治作用”說,黃霖的“弘揚人的自由和人性”說以及李安綱的“金丹大道”說等,這些都對新時期《西游記》主題研究作出突出貢獻。但這些見解凸顯出一個重要問題,即如此眾多的主題觀似乎只有量的遞增沒有質的提升,始終沒有出現一個能夠全面涵蓋《西游記》整體的宏觀性主題觀。
在《西游記》研究史中,爭議最大的除了主題論外,其次便是人物論。《西游記》中涉及的人物除了取經四眾,便是神佛與妖魔。其中對主要人物孫悟空原型的探討:有魯迅首倡,張錦池、李時人、蕭相愷等人贊成的“國貨”說;胡適首倡,季羨林、陳邵群等人贊成的“進口”說;蔡國梁、蕭兵等認為的“混血”說;磯部彰認為的“佛典”說。其中,較為突出的文章有:陳寅恪《〈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蕭兵《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劉毓忱《孫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評“化身論”》、趙國華《論孫悟空神猴形象的來歷》等。關于孫悟空形象的代表性觀點主要有“心猿”說、“農民起義英雄”說、“作者理想體現”說、“時代精神代表”說、“民族精神象征”說、“超我意識體現”說、“悲劇形象”說等。主要研究論文有朱彤《論孫悟空》、嚴云受《孫悟空形象分析中的幾個問題》、曹炳建《孫悟空形象的深層意蘊與民族精神》、蕭相愷《孫悟空形象的文化哲學意義》、趙紅娟《從孫悟空的形象塑造看〈西游記〉對悲劇和喜劇的超越》等。關于豬八戒形象的代表性觀點主要有“普通勞動者形象”說、“時代形象”說、“滑稽形象”說等,其中方白的《談豬八戒》是豬八戒形象研究的一篇力作。對《西游記》其他人物形象研究則有蔡鐵鷹《整合的歷程:論唐僧形象的演變——兼及中國小說演變過程的理論意義》、竺洪波《論唐僧的精神》、張靜二《論沙僧》、王平《從二郎神形象略窺〈西游記〉創作心態》、陳洪《牛魔王佛門淵源考論》、吳男濱《〈西游記〉土地神形象的民俗考察》等,他們均對《西游記》中的人物形象做了深入精到的論述。
關于《西游記》的作者問題,自小說《西游記》問世以來便爭論不已。明代世德堂本《西游記》只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作者的模糊概念,“《西游》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7](P1)其并未指明《西游記》撰者為何人。一直到清代汪澹漪《西游證道書》將《西游記》的作者歸為邱處機名下,“曰:此國初邱長春真君所纂《西游記》也。”[7](P5)后來有清一代,邱處機作《西游記》深入人心,對此魯迅曾有批判“處機固嘗西行,李志常記其事為《長春真人西游記》,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為一書;清初刻《西游記》小說者,又取虞集撰《長春真人西游記》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談乃愈不可拔也。”[3](P102)。后來清代的吳玉搢根據明代天啟年間的《淮安府志》的記載,“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游記》。”[8](P164)還有,小說《西游記》中的淮安方言推斷出作者應為吳承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則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根據明清歷代的《淮安府志》以及錢大昕《跋〈長春真人西游記〉》、紀昀《如是我聞》、丁晏《石亭記事續編》、阮葵生《茶余客話》、吳玉搢《山陽志遺》等書中的記載,否定邱處機說,認為《西游記》最后加工成書者是吳承恩。吳承恩說一出便得到當時乃至今天學術界的肯定和認同。但在當時也有人存有質疑,提出不同的認識,比如俞平伯于1933年在《駁〈跋銷釋真空寶卷〉》中對吳承恩說提出了質疑,“現存《西游記》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寫著‘華陽洞天主人校’,有誰說校訂者是吳承恩?……或曰‘天潢’,或曰其門客,詞雖吞吐,均非吳氏明甚。”[9]但此一質疑并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章培恒先后發表《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再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文章,對魯迅、胡適考證的重要佐證(清代吳玉搢《山陽志遺》、阮葵生《茶余客話》和淮安方言),提出了質疑。魯迅、胡適二人“對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未作論證,他的論斷也就缺乏堅實的基礎。”[10](P63)。此文一出打破了國內沉寂已久的作者問題,引起了新時期關于作者問題的大討論。這場關于《西游記》作者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吳承恩說、邱處機說、陳元之說三者上。堅持吳承恩說的主要有蘇興、劉懷玉、鐘揚、楊子堅、陳澉、劉振農、蔡鐵鷹等,比如蘇興撰有《也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堅持認為“天啟《淮安府志》的《淮賢文目》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是指百回本小說;明刻《西游記》雖未署作者名,卻由陳元之的序透漏出作者是‘八公之徒’,與吳承恩身份合,其校者華陽洞天主人是吳承恩友人李春芳,證明作者是吳承恩。”[10](P87)蔡鐵鷹同樣在《關于百回本〈西游記〉作者之爭的思考與辯證》一文中認為百回本《西游記》的作者為吳承恩。章培恒、楊秉祺、李安綱、黃霖等人則否定吳承恩的著作權,但并未提出作者具體為何人。此一時期仍堅持邱處機說的則主要集中在海外和臺灣學者中,比如柳存仁、張易克、陳敦甫等,國內則有金有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研究者在對“華陽洞天主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陳元之說,重新審視華陽洞天主人、作者與陳元之之間的關系,提出三位一體的觀點。陳元之說的提出者為陳君謀,詳細考證論述者為張錦池,但這一說法同時也遭到了各方學術界的質疑和批判,主要有吳圣昔、宋克夫等人。在關于《西游記》作者吳承恩說、邱處機說、陳元之說三者中,不論如何地被質疑,吳承恩著《西游記》還是不能被輕易否定的,邱處機說則與文本有著牽強與難以融合之處,陳元之說雖有新意,但陳元之究為何人,仍是一大謎團。總之,對作者問題的探索與解決有待于研究者更深入的思考。
關于《西游記》的版本問題,也就是《西游記》的祖本之爭問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對《西游記》祖本便開始了初步的探索,主要研究者有魯迅、胡適、孫楷第等人。當時對祖本問題的研究雖然得出了一定的結論,但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做出客觀而詳細的分析、論證。建國以后十七年間乃至文革期間,由于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階級性批評占主導地位,《西游記》的版本研究幾乎停滯。但此一時期,海外學者杜德橋、柳存仁、太田辰夫等人則對《西游記》的版本研究付出了心血,比如杜德橋著有《〈西游記〉祖本考的再商榷》、太田辰夫著有《〈樸通事諺解〉所引〈西游記〉考》。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版本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并開始熱烈討論起來,直到今天主要形成了七種代表性的說法:“楊本說”“永樂本說”“朱本說”“前世本說”“《西游原旨》說”“《西游釋厄傳》說”“詞話本說”。在這七種說法中,最具生命力的是前三種說法,其他說法皆有模棱兩可、牽強附會之處。但任何一種說法要想獲得學界的普遍認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代代的研究者不斷的努力。
對于《西游記》這樣一部“說不盡”的“海內一大悶葫蘆”,因研究者所處的社會、時代環境不同,人們的認識水平變化,便催生出種種不同的主題觀、人物論、作者觀、版本論。各派新說在各領風騷之后便偃旗息鼓。對于四百年的《西游記》研究發展史總結過往成績、借鑒經驗、吸取教訓便成為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1]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鄭振鐸.《西游記》的演化[A].20世紀《西游記》研究 [C].梅新林,崔小敬(主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
[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4]胡適.《西游記》考證[A].20世紀《西游記》研究 [C].梅新林,崔小敬(主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5]沈玉成,李厚基.讀《西游記》札記[N].光明日報,1955-10-23.
[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A].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吳圣昔(編).《西游記》百家匯評本[C].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8]朱一玄,劉毓忱(編).《西游記》資料匯編[C].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9]俞平伯.駁《跋銷釋真空寶卷》[J].文學(創刊號),1933,(7).
[10]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A].20世紀《西游記》研究[C].梅新林,崔小敬(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11]蘇興.也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A].20世紀《西游記》研究[C].梅新林,崔小敬(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