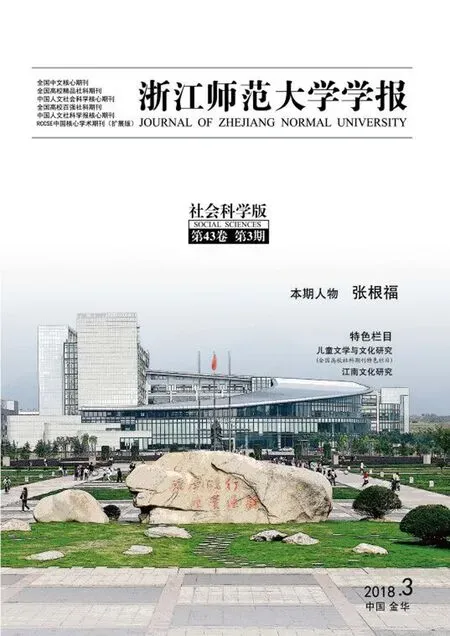王韜《扶桑游記》與日本冶游空間的建構
潘德寶
(浙江工業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4)*
王韜(1828—1897)《扶桑游記》見收于兩種性質不同的叢書,暗示著兩種不同的解讀角度。該書初版由日本人栗本鋤云訓點、東京報知社印行,上卷刊于明治十二年(1879),中下兩卷刊于明治十三年(1880),曾見收于王錫祺主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上海著易堂,1891),又見收于鐘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陳尚凡、任光亮點校)成為目前通行的版本。游記置于輿地叢書,則暗示了文學地理角度解讀的可能性;置于《走向世界叢書》,則暗示了歷史史料角度解讀的可能性。②
對比《扶桑游記》和王韜光緒五年(1879)日記手稿本③的文字異同,可以發現王韜《扶桑游記》有明顯的修辭策略和書寫意圖,絕不只是自然狀態下的保存史料。不過,目前學者多從“走向世界”即中日交流史的角度解讀《扶桑游記》,④或以此書為線索,考察王韜的日本交游圈,⑤或從近代中日比較、中西文化交流這些宏大敘事的角度切入,討論亞洲主義、中日關系等。⑥只有極少數論文從文學角度介紹、論述了游記本身的內容,⑦可以說《扶桑游記》文學尤其是冶游空間書寫這一層面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
本文認為王韜在《扶桑游記》中遮蔽了明治維新以來的彌漫在日本的近代感;反而以《山海經》為基礎的域外地理認識框架來定位日本,將日本披上神山仙鄉的外衣;同時也將自己塑造成游仙的文人形象,而且極力渲染醇酒婦人的旅居生活,突出自己的遇艷故事,還常常擬妓為仙,用中國“仙妓合流”的書寫傳統將日本定義成為一個冶游空間。貫穿三者之間的正是王韜的文人意識。
一、近代感的遮蔽
《扶桑游記》遮蔽日本的維新氣象,最值得一說的便在于主客對王韜旅日的不同期望。日人邀王韜旅日是因為《普法戰紀》一書。平安西尾《扶桑游記跋》說:“余始讀《普法戰紀》,喜其敘事之明暢,行文之爽快。”[1]511邀請王韜旅日的東道主栗本鋤云在其《王紫詮の來遊》一文說明得更為詳細,其子貞次郎隨大使巖倉具視出使歐洲,歸航途經上海時購書數部,中有王韜《普法戰紀》。栗本鋤云未讀其半,即認為此書于行陣之事、交戰之跡,寫得栩栩如生,至于中間所雜議論,不陳不腐,脫出漢人窠臼。于是公諸同好,不獨朱批圈點,且謀在日刊行。[2]392-393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士人因為文學上的欣賞而邀請王韜赴日,其實,明治士人重視《普法戰紀》并不只是因為此書的文學價值。
巖倉具視1871年開始出使歐洲各國,于1873年途經香港、上海返回日本。而《普法戰紀》由張宗良等人翻譯自1870—1871年普魯士與法國戰爭之新聞報導,由王韜編輯,自1872年起連載于香港《華字日報》,之后由上海《申報》轉載,普法戰爭結束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結集出版。可見,栗木貞次郎是第一時間就購得《普法戰紀》持歸日本,足見他們渴求海外知識,急于了解西方世界。所以龜谷行《扶桑游記跋》強調了王韜的海外經歷:“吾聞有弢園王先生者,今寓粵東,學博而材偉,足跡殆遍海外。曾讀其《普法戰紀》,行文雄奇,其人可想。”[1]509曾留學英國的學界名士中村正直《扶桑游記序》也強調“先生博學宏才,通當世之務,足跡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掛,宜其人人影附而響從也”。[1]390另外,《普法戰紀》記載的小國普魯士竟能數月間擊敗法國,這一以弱勝強的例子,正可以作為日本面對西方列強時的借鑒,王韜在書中指陳時勢,追溯源流,見識不凡。東京圖書館館長岡千仞《扶桑游記跋》中就強調了王韜的見識:“《普法戰紀》傳于我邦,讀之者始知有紫詮王先生之以卓識偉論,鼓舞一世風痹,實為當世偉人矣。”[1]513時任修史館編修的重野安繹曾當面贊賞王韜說:“(魏源)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龜,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徑庭。竊謂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1]413重野安繹、栗本鋤云等人籌劃邀請王韜赴日,目的即在于想通過“思想家”王韜進一步了解西方。
但是,王韜東游日本乃是自執“文士”身份以往,而并非“思想家”。勸其東游的斡旋者也深了此意,所以對王韜說:“至東瀛者,自古罕文士。先生若往,開其先聲,此千載一時也。”王韜“聆之躍躍心動”,[1]385恐怕正是因為“千載一時”的“文士”之譽。這一出發點與日本士人所求之間,便有了一定的距離,所以王韜1879年旅日期間唯醇酒婦人是求,頗引起非議:“口不說道學,議論不及當時,文酒跌宕,歌筵妓席,絲竹嘔嗚,欣然酣暢,不復以塵事介懷,……人皆曰:‘先生兒女之情有余,而風云之志不足’。”[1]513當然,王韜也并非完全閉口不談世界大勢,如曾在席間論中西諸法異同,曰:“法茍擇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則合之道矣。道也者,人道也,不外乎人情者也;茍外乎人情,斷不能行之久遠。故佛教、道教、天方教、天主教,有盛必有衰;而儒教之所謂人道者,當與天地同盡。天不變,道亦不變。”[1]438這位曾經受洗的基督徒卻借此機會宣揚中國儒教,體現了其幼時所承的庭訓,[3]他所接觸的“明六社”成員中村正直1876年已經翻譯出版了《萬國公法蠡管》,介紹歐美近代價值觀的天賦人權、功利主義等思想,王韜如此泛泛而談,實則無法反映當時日本法制改革的情況,反倒更像是陳腐守舊之論。
同時,與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等極力描摹明治維新后的新事物相比,王韜極少提及明治維新后的新事物。如王韜對日本風行一時的博覽會記錄得極為簡單,他參觀長崎博覽會,僅記錄:“會中陳設,光怪陸離。我國陳寶渠司馬亦自上海寄物至此。最奇者,一腎囊其巨如斗,割之而其人不死。繅絲之具,茲用西法,倍極敏捷。余則物產之外,書畫古玩雜陳。”[1]394后至大阪博覽會,記得更為簡單:“奇巧瑰異之物,幾于不可名識。較之長崎,既多且精。”[1]398至于往西京博覽會,認為勝大阪博覽會一籌,也僅有這樣的記錄:“物產之富,陳設之華,光怪陸離,幾有五花八門之觀。”[1]402這完全是一種文人好奇的筆調。
明治維新至此已歷十余年,關于日本學習西學、西法的成果最具體而微的展示場所便是博覽會。明治政府1873年才第一次正式遣團前往參加奧地利維也納世博會,當時赴會者就已經意識到舉辦博覽會具有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之效,[4]卷82-83而后博覽會急劇發展,1877年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試圖通過博覽會、博物館的展示來開啟民智。[5]119國雄行《博覧會と明治の日本》指出日本的博覽會展示的是歐美諸國先進技術的成果,展示的是日本未來的發展方向,以此激勵日本國民,打破了舊有的夷狄觀,逆轉明治維新以前“夷狄即野蠻”的價值傾向,可以說博覽會即是日本所展示的西洋和近代。[6]206-214博物館、博覽會所蘊涵的意識形態是極為明顯的,所以同一時期中國人李圭《環游地球新錄》記載他1876年赴美國參加費城博覽會時,一眼就看出博覽會所陳列的意識形態,展品位置再現著國族的位置,展品的形態揭示著國家或種族的進步與退步。[7]
王韜一再使用“光怪陸離”等詞來記述,可見他于此中所展示的日本轉型的視而不見。倒不是王韜對日本的改革毫無所知,其《弢園文錄外編·變法自強下》中說:“日本海東之一小國耳,一旦勃然有志振興,頓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國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倣效取則,惟恐其入之不深。數年之間,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槍炮;練兵,訓士,開礦,鑄錢,并其冠裳文字星宇之制,無不改而從之。”[8]40足見作為“思想家”的王韜是知其應知的,而作為“文人”的王韜,僅用“光怪陸離”來感嘆,是他面對新事物的一貫策略。王韜《漫游隨錄》也多次使用此一成語,[9]這一抽象感嘆看似修辭之妙,實則難辨其真實形象,應該是有意無意地忽視日本的近代化、西洋化的表現。王韜《扶桑游記》一書中或泛泛而論,或用詞抽象,有意無意間忽視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巨變,與傅云龍《游歷日本圖經》、黃慶澄《東游日記》、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等著重表現日本維新成果大相徑庭,實際上這正是王韜文人立場的體現。
當然,王韜《弢園著述總目》中對《扶桑游記》的上述現象解釋說:
己卯春,余為東瀛之游,日本諸文士以作日記請,遂排日編纂。既行,授之栗木鋤云,為刻于報知社。然中言日本海防兵政軍艦營壘處,悉被刪去,紀游之作有涉于載酒看花者,亦經沈梅史州守所節;蓋有所諱也。殊不滿鄙臆,尚待重刊。[8]385-386
從黃遵憲《致王韜函》(光緒六年六月底)[10]321可知,《扶桑游記》一稿刊刻之前還曾請黃遵憲刪改,黃遵憲說《扶桑游記》上中二卷“層出復見處,自可刪改”,并堅持認為下卷“不煩繩削”,后來只是刪去“階下小蛇”、“高麗之臣于明不臣于日”等數語而已。不過,對比《扶桑游記》與王韜的日記手稿就會發現,更多的刪改在于整體文學空間的營造,而所謂“諱語”的刪改不會影響《扶桑游記》所欲營造的整體文學效果,比如彌漫全書的“三神山”想象。
二、海上三神山的想象
王韜無意于記錄日本社會劇變,主要是因為他對日本的“三神山”形象定位,這兩者是無法調和的、沖突的形象。《扶桑游記》開篇的《自序》就是以三神山來定位“日本”的:
余少時即有海上三神山之想,以為秦漢方士所云“蓬萊諸島在虛無縹緲間”,此臆說耳,安知非即徐福所至之地,彼欲去而迷其途乎?[1]385
王韜離開日本之際的贈別詩中也有“瀛洲縹緲神仙居,百日因緣亦足喜”、[1]500“回帆重復指神山,前度歡悰今別顏”[1]505等句,用“三神山”等詞可謂首尾呼應。
而且,不只是首尾兩處,在整部《扶桑游記》所錄在日本詩酒唱和中,王韜經常用及“蓬萊”“徐福”“神山”等語詞,如和廖樞仙詩中有“三神山在縹緲間,嶺南仙尉其先謁。吾聞仙尉今詩豪,蓬萊作吏福尤高”等句;[1]405和日人和植村義詩中有“自昔神山多舊跡”句,有自注云“相傳徐福墳尚在紀伊國熊野山”;[1]414《芳原新詠》序中曰:“余偶從諸名士買醉紅樓,看花曲里,覽異鄉之風景,瞻勝地之娟妍,覺海上三神山即在此間。”詩又有“不數揚州花月盛,本來此處是蓬萊”等句;[1]431《分韻賦詩得“賦”字》中有“弗待千歲桃花開,且教兩月蓬山住”[1]429句;《依韻答梅史》中有“蓬萊已到尚思家,采藥不歸有王子”[1]434句;和石井南橋詩中也有“羈人只有神仙樂,不解清涼憶故鄉”句。[1]448
另外,不只收錄自己的詩文是這樣,王韜收錄同人詩作中也多有“三神山”等詞,如廖樞仙詩中有“神山云氣滃而深,神山芳樹郁森森”“蓬萊神仙把手招,掛帆又指扶桑國”等句;[1]404-405黃遵憲詩中有“神山風不引回船,且喜浮槎到日邊”句;[1]421石川鴻齋贈詩中有“飄然駕鶴下蓬萊”[1]429句。這似乎顯示了用“三神山”等語詞只是流行的風潮,并無特殊之處,但對照王韜日記的手稿本,可以發現這是王韜在《扶桑游記》中有意的營造,如日記手稿本原文照錄詩僧五岳詠西鄉的詩:“帷幄勛名善運籌,維新事業足千秋。天恩已忝正三位,人物原居第一流。末路鴟張臣節變,前功烏有賊名留。誰知卻使國威重,烈戰聲高五大洲。”(王韜日記手稿本“陽歷六月十七日”條)這里所詠的西鄉隆盛為明治維新三杰之一,明治元年,與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發動王政復古政變,建立明治新政府,功勛卓著,受封最厚。至明治十年(1877),又被薩摩藩士族推為首領,發動反明治政府的武裝叛亂,史稱西戰爭。此詩破壞了《扶桑游記》的“三神山”的空間建構,將讀者拉回到歷史現場,因此王韜刪去此詩,只錄自己的和詩,而和詩中有“蓬萊已到神仙杳,徑欲乘槎訪十洲”等語,[1]450與全書保持一致的氛圍。
將日本定位于神山仙鄉,其來有自。如“扶桑”本就是一個神話中的地方,《山海經·海外東經》中說:“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注’扶桑,木也。”[11]281《淮南子·道應訓》:“扶桑,日所出之木也。”[12]411《論衡·說日篇》:“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沐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13]508總之,“扶桑”是一大神木,因與日出有關,位于東方,又演變指稱為東方。《淮南子·天文訓》:“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箋文引《初學記》《太平御覽》舊注云:“扶桑,東方之野。”[12]108《論衡·說日篇》:“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13]496扶桑與日出相聯系,帶有濃重的神話色彩。王韜提到“縹緲”的“三神山”,見于《史記·封禪書》,不過故事來源應該更早: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14]1369-1370
《漢書·郊祀志》因襲之,另外,《列子·湯問》也有相近的描寫: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紱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種,一日一夕相往來者,不可數焉。[15]151-152
從上述引文看,三神山或五神山,皆在東方海中,《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曾派齊人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所以王韜渡海旅日,日本詩人小野湖山即有詩云:“雖云殊域豈其然,文字相通興欲仙;蓬島風光尚如舊,遲來徐福二千年。”[8]407
這種將日本視為扶桑、⑧三神山的論述,并非只是雅人風致、運用成詞典故而已,這也是中國傳統地理論述的一種習用框架。陳學熙《中國地理學家派》認為中國傳統地理論述,可以分為《禹貢》九州說為代表的“域中地理學派”和《山海經》為代表的“域外地理學派”,[16]宋明時期大量異國游記出現之前,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框架是由域內、域外組成,而《山海經》這類神奇論述,今天被視為神話傳說,卻是中國傳統地理認識的一個習用框架,雖然今天對《山海經》的性質仍有不同的認識,但《山海經》作為一種地理認識框架則是基本事實。王韜的扶桑、三神山論述正是這一域外地理認識框架中的符號,可見他將日本置于神山仙鄉其來有自。
不過,這一從《山海經》而來的“域外地理認識”框架早已被西方傳來的“萬國地理知識”所取代。自明神宗萬歷九年(1581)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傳教,帶來了西方最新的世界地理知識,至清中葉以后,西方地理知識更是一日千里,來華傳教士創辦的大量新式雜志,如《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馬六甲,1815—1821)、《東西洋每月統計傳》(初在廣州、后遷新加坡,1833—1837)、《遐邇貫珍》(香港,1853—1856)、《六合叢談》(初設上海,后遷日本,1857—1858)等,也及時傳播西方傳來的地理知識。另有史地著作如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志略》、慕維廉《地理全志》、郭實臘《貿易通志》《萬國地理全集》、培瑞《平安通書》、袆理哲《地球圖說》等,中國學者也在這一學術潮流與實際需求的影響下,編寫有林則徐《四洲志》、魏源《海國圖志》、梁廷枬《海國四說》、徐繼畬《瀛環志略》等。在這一背景下,且不說王韜在上海即已經大量接觸日本人,對于日本的地理認識,早已去掉神話想象。
所以,當時何如璋《使東述略》記錄其舟入長崎,見長崎“港勢斜趨東南,蜿蜒數十里,如游龍戲海,盡處名野母崎,北則群島錯布,大小五六,山骨蒼秀,林木森然,雨后嵐翠欲滴,殘冬如春夏時。沿島徐行,恍入山陰道中,應接不睱”,發出感嘆:“古所謂‘三神山’,是耶非耶?”[17]91張斯桂《使東詩錄》有句:“入海去尋徐巿裔,平倭還記戚元戎。”[18]142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立國》“立國扶桑近日邊”、[19]581《徐福》“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別有天”[19]585也都用到了徐巿、扶桑之典,但這些詩文的前后文往往立即展示出眼下的明治日本與傳說的扶桑并不相符,從而形成傳統詩語與現代地景(landscape)之間的張力,可見其對中國人世界觀的沖擊,所以這些文獻正是“走向世界”的史料。
而王韜本人早在1849年進入上海墨海書館從事翻譯工作,成為當時極少數與洋人工作和交往的中國傳統文人,成為所謂的“口岸知識分子”,早有機會接觸傳教士們帶來的西方地理知識;他因上書太平天國而逃亡香港,協助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中國經典》,后來又游歷西方世界,可以說他身經目擊現代地理知識;他還編譯了《普法戰紀》《漫游隨錄》等著作介紹世界形勢。另外,王韜在1879年旅日之前,已經與十多位日本人有直接交往,還有間接得之于理雅各等人或西方報紙的日本消息,還在其主編的《循環日報》上發表過近20篇有關日本的政論文,[20]可以說王韜有很豐富的日本知識,但在《扶桑游記》中卻有意無意地遮蔽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感,利用成詞典故,重拾傳統觀念框架,開篇即以“三神山”來定義日本,以暗示其日本之旅即游仙之行,可以說《扶桑游記》與這些文獻并非同一類型。
三、冶遊空間的建構
《扶桑游記》定義日本為“三神山”,不是王韜地理知識上的歷史倒退,而是文學空間的重新建構,而且,這個空間并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神圣空間”,[21]347因為“三神山”與王韜日常的“醇酒婦人”緊密結合,即是擬妓為仙,“三神山”是一個情欲世界。
旅日期間,王韜幾乎無日不攜妓,如吉原萬年樓酒宴時,“呼三歌妓侍觴侑酒,其一曰桃太郎,綽約可愛。……吉原亦曰芳原,東京之平康里也”。[1]411酒后尚有攜妓而歸者,如“宴罷……余偕白茅、茂吉攜歌妓小勝乘舟從流而歸,舟行墨川中,波平如鏡,于是暮靄銜山,新月掛柳。小勝臨流掬水,作旖旎態。白茅謂小勝獨戀戀予不忍別,故隨我歸耳。噫!此何異范蠡一舸載西施也”。[1]415且納妾不只一人,如在東京時:“有阿藥者,容僅中人,差可人意。……能略解華言,一月所索止七金,價亦殊廉,……遂納之。”[1]433書中贈妓之詩作亦復不少,其余可見一斑。
在神山仙鄉的環境中,王韜常以仙擬妓,如其致余元眉書中有“自別以后,片帆東溯,舟至神山,為風所引……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幾不知有人世事。……崎陽山水甲他處,正是蓬萊勝境,想其中綽約多仙子,必有深于情者。劉阮緣深,天臺重至,定當求導師偕往問津也”。[1]445也曾作詩自謂好色,有句云“三千年作蓬萊游,得遇仙姝緣不薄”。[1]457更有意思的是下面這則記載:
十八日晨……登山浴溫泉。有日本女子,能操西音,自言從西人自香港、上海至橫濱,今暫留神戶。因邀至其家,則室在山半,花木蕭疏,廬舍精潔。小憩久之,期以他日再來踐約。此何異劉阮誤入天臺而飽吃胡麻飯也。[1]398
這一段的最后,王韜的日記手稿本作:“今暫留神戶。因邀至其家,則室在山半,雖小亦甚精潔。春風一度,各自東西,亦可謂無端之嘉遇矣。”而《扶桑游記》這一修改將皮膚濫淫的遇艷提升為劉阮遇仙故事。劉阮是指劉晨、阮肇,剡縣人,漢明帝永平五年,入天臺山采藥,在山中迷路不得返,見溪中有蕪精葉和杯子從山腹流出,有胡麻飯糝,于是估計附近有人家,緣溪而尋,果見姿質妙絕二女子。劉阮二人被邀請至其家,歡宴作樂,半年后復還家中,則見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而子孫已歷七世。劉阮故事原出自劉義慶《幽明錄》,后迭經改編,成了遇仙故事。
王韜運用此典以劉阮自比,擬遇艷為遇仙,直將日本視為神山仙鄉,正是“仙妓合流”文學傳統的典型表現。陳寅恪《讀鶯鶯傳》考“會真”之名時云:“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會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謂也。又六朝人已侈談仙女杜蘭香萼綠華之世緣,流傳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艷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22]110-111李豐楙《仙、妓與洞窟》則進一步指出中唐社會流行以仙擬妓,在當時已蔚為風尚,就常成為夜宴、贈妓詩的新鮮意象。生活中與妓人交往,被目為一種唐型風流。[23]212-217孫遜《中國古代小說與宗教》指出唐代“遇仙”小說沿著世俗化方向發展,至明清變異為“遇艷”,展示了這一文學傳統的古今演變。[24]265王韜借由這一文學傳統,塑造了自己游仙窟的文人形象,也將明治日本定義為冶游空間。
而且,王韜《扶桑游記》建構的日本冶游空間,其實就是其《海陬冶游錄》的上海冶游空間的延伸。《扶桑游記》開篇第一天尚在上海,曾招“陳氏繡鳳校書”(“校書”即妓者雅稱),而后王韜渡海至長崎、東京。《扶桑游記》與《海陬冶游錄》《花國劇談》《艷史叢鈔》等書,在精神意趣上一脈相承。廣而言之,這與上海當時出版的一系列艷跡小說、筆記也是相呼應的,如《秦淮畫舫錄》《西青散記》《揚州畫舫錄》《宮閨聯名譜》《十洲春語》《竹西花事小錄》《燕臺花事錄》《白門新柳記》《鴻雪軒紀艷》《淞濱花影》等。上海早已經聲色大開,紛紛的情欲翩躚紙上,與都市的現代化進程彼此呼應。這些青樓風月書正是對城市冶游空間的塑造,一般我們往往以為文學是對世界的再現,但從文學空間的角度看,這反倒是對空間的重新定義。彼時,王韜與袁枚之孫袁祖志相善,正借助袁枚這一文化符號,建構著欲望都市的“上海學”。[25]
當日本人以好色相責時,王韜卻以“真風流”作答:
日東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復好色,齒高而興不衰,豈中土名士從無不跌宕風流者乎?余笑謂之曰:“信陵君醇酒婦人,夫豈初心?鄙人之為人,狂而不失于正,樂而不傷于淫。具《國風》好色之心,而有《離騷》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視資財如土苴,以友朋為性命。生平無忤于人,無求于進。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矯行飾節,以求悅于庸流,吾弗為也。王安石囚首喪面以談詩書,而卒以亡宋;嚴分宜讀書鈐山堂十年,幾與冰雪比清,而終以僨明。當其能忍之時,偽也。世但知不好色之偽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也,此真常人之見哉!”[1]452
才情鼓蕩的生命,本不拘于禮法,而將頹廢寓于身世之感,正是“上海學”題中的應有之義。王韜還在自我形象上追慕袁枚,《扶桑游記》中的逸事正可印證:
西京岸田湘煙女史,年有八十,識字工詩,皓齒明眸,豐神秀曼。寄詩求余筆削,謂愿仿隨園例,附絳帳女弟子之列。[1]479
文中的“八十”應該是“十八”之誤。若孤零零地看這一記載,似乎只是以詩會友的雅事,但聯系上海的冶游書寫,則此女詩人也被王韜視為遇仙題材。
另外,日本冶游空間的建構,除了借助“仙妓合流”的文學傳統和上海情欲世界的影響外,還因為日本的冶游敘事的觸動。王韜在《扶桑游記》中對日本各地平康(指妓女聚居地)尤多注目:
(福原)其地為妓叢,……間有如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儀態整齊,不可逼視,則名妓下樓邀客也。按此風如粵東、揚州皆如是。隨園所謂以一人掉臂游行其間,而彼之修容飾貌、爭妍取憐以冀得一當者何啻千百姝,如雖萬戶侯無是樂也。[1]398自古河驛始,每驛皆有娼樓,無色妓則以歌妓代,惟日光町一帶獨無佳人。蓋是山從古以來,傳為神仙所窟宅,故所在莊嚴潔凈,以示崇敬。是不知藍橋覓路,玉杵乞漿,胡麻飯熟,劉阮曾來,神仙眷屬,自古有之,況于世人乎哉![1]496
正是受到成島柳北《柳橋新志》的影響:
余聞東京柳橋多佳麗,與新橋相埒。近人成島柳北曾著《柳橋新志》,頗述其艷冶狀。會當一游,以領略此異地煙花、殊鄉風月耳。[1]410
成島柳北在《柳橋新志》的序言中說自己是仿效寺門靜軒《江戶繁昌錄》,從內容上看更可上溯至余懷《板橋雜記》,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明治日本與晚清上海共享著冶游的文學符號和文學傳統。日本隨著城市的現代進程,追求頹廢美學與感官快樂自有市場,甚至在留日學生郁曼陀《東京竹枝詞》還可覓其蹤影。
王韜《扶桑游記》不著意“表現”日本明治以來的種種社會變革,反倒以神話色彩濃厚的中國傳統域外地理認識框架來定位日本,似乎要將近代的日本寫成一個古典的扶桑,實質是意在將日本“定義”成為一個冶游的空間。這可以接續唐代以來以仙擬妓的文學精神脈絡,同時也可以視《扶桑游記》為上海冶游空間的延伸。可以說,《扶桑游記》是晚清上海冶游文學、青樓文學的變形。
注釋:
①文中所引日文文獻出版信息保留日文形式,所引日文內容則直接編譯成中文,除注明譯者外,皆筆者自譯。
②如錢鐘書《走向世界序》一文中直接稱這些著作為“史料”(見《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22頁)。
③目前出版的中華書局本《王韜日記》未見這一部分的內容,手稿本藏國家圖書館。承蒙浙江師范大學陳玉蘭教授贈賜王韜光緒五年日記手稿照片,為本文增色不少,深表感謝!
④關于王韜研究述評,可參見吳以義《王韜研究所提示的中國近代史的復雜性——評忻平〈王韜評傳〉和柯文〈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新史學》2000年總第11卷第2期),關于王韜《扶桑游記》研究述評,可參見徐興慶《王韜的日本經驗及其思想變遷》(徐興慶、陳明姿編《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⑤如布施知足《遊記に現われた明治時代の日支往來》(《東亜研究講座》1938年第84輯),實藤惠秀著、張銘三譯《王韜的渡日和日本文人》(《日本研究》1944年第3卷第6期),增田涉《王韜について:その輪郭》(《人文研究》1963年第17卷第7號),中田吉信《岡千仭と王韜》(《參考書誌研究》1976年總第13號),陶德民《明治漢文界における清代文章學の受容——星野恒編、王韜評〈明清八大家〉について》(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江戶·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東京:農山漁文協2000年版),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近代中國》第12輯2002年),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2006年5月)、《王韜的日本經驗及其思想變遷》(徐興慶、陳明姿編《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王曉秋《王韜日本之游補論》(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版)等文。
⑥如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東亜》2000—2001年總第1-3期)、李朝津《儒家思想與清末對外關系的再思考——王韜與日本》(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版)、薄培林《近代日中知識人の異なる琉球問題認識:王韜とその日本の友人を中心に》(《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2014年4月總第47輯)。
⑦如王曉秋《議王韜扶桑之游》(蘇州市傳統文化研究會《傳統文化研究》第17輯,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李勇華《紀行文における風景とエロス——森鴎外の『獨逸日記』と王韜の『扶桑遊記』を視野にして》(《日本漢文學研究》2010年3月總第5卷)、呂文翠《冶游、城市記憶與文化傳繹:以王韜與成島柳北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2年總第54卷)等。
⑧其實“扶桑即日本”的認識并非一成不變,如顧況《送從兄使新羅》:“扶桑銜日近,析木帶津遙。”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相見扶桑受恩處,一時西拜盡傾心。”張喬《送新羅僧》:“永向扶桑老,知無再少年。”貫休《送人歸新羅》“積愁窮地角,見日上扶桑。”這些詩中的“扶桑”皆指新羅。另外,章太炎《文始》中提出“扶桑”是指墨西哥,而非日本。
參考文獻:
[1]王韜.扶桑游記[M].長沙:岳麓書社,1985.
[2]栗本鋤雲.匏菴遺稿[M].東京:裳華書房,1900.
[3]段懷清.試論王韜的基督教信仰[J].清史研究,2011(2):22-30.
[4]久米邦武.特命全権大使米歐回覧実記[M].東京:博聞社,1878.
[5]吉見俊哉.博覧會の政治學[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
[6]國雄行.博覧會と明治の日本[M].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
[7]鄭毓瑜.1870年代中、日漢詩人的視域轉換——以博物知識、博覽會為認知框架的討論[J].淡江中文學報,2011(25):95-130.
[8]王韜.弢園文錄外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
[9]陳室如.王韜《漫游隨錄》的物質文化[J].東吳中文學報,2013(25):239-260.
[10]陳錚編.黃遵憲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5.
[11]范祥雍.山海經箋疏補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81.
[12]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13]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4]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5]楊伯峻.列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6]陳學熙.中國地理學家派[J].地學雜志,1912(17):3-7.
[17]何如璋.使東述略[M].長沙:岳麓書社,1985.
[18]張斯桂.使東詩錄[M].長沙:岳麓書社,1985.
[19]黃遵憲.日本雜事詩[M].長沙:岳麓書社,1985.
[20]王立群.從王韜看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文人的日本觀[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10(3):100-106.
[21]伊利亞德.神圣的空間:比較宗教的范型[M].晏可佳,姚蓓琴,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22]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23]李豐楙.憂與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0.
[24]孫遜.中國古代小說與宗教[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25]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游記[J].中外文學,2006,34(9):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