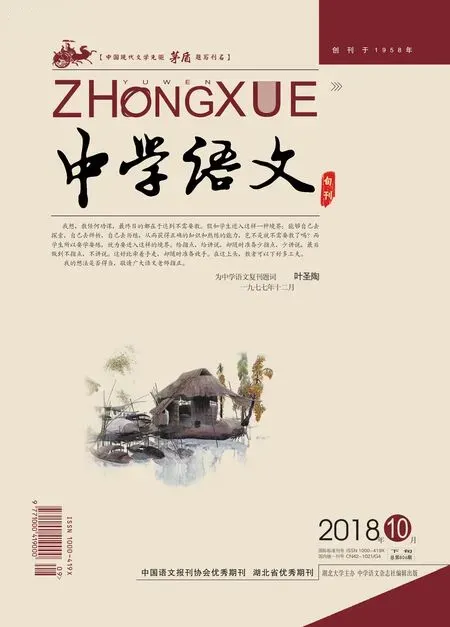荒謬舊時代 悲辛套中人
——別里科夫性格成因分析
焦淑紅
契訶夫小說《裝在套子里的人》的主人公別里科夫,是一個生活在19世紀中葉沙皇政府統治下的小人物。他是一所中學的古希臘文的教師,他性格孤僻,表現病態,總是把自己包裹在形形色色的套子里,從衣食住行到言行思想,甚至謀生的職業,他幾乎和外界隔絕,最后因為戀愛時發生了“漫畫事件”和“騎自行事件”,他和華連卡的弟弟科瓦連科爭吵了起來,在華連卡不明所以的笑聲中,他一病不起。縱觀他的言行和思想,我們會看到一個膽小、多疑、狹隘、頑固保守、害怕微小變革的人物形象。
那么別里科夫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果分析別里科夫性格的成因,我們首先要考慮作者為人物生活設定的時代因素。
別里科夫生活的時代,俄羅斯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沙皇具有絕對的權威,享有無限制立法、司法、行政權力。當時一些社會學家、政治家都認為: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沙皇,自由民主以及共和哲學不適合俄羅斯。
沙皇專制制度下的俄羅斯無法制、無自由、無理性,沙皇的意志代表國家的意志、社會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別里科夫之所以對政府的文書、法令等相關公文、告示格外重視,生怕一不小心觸犯政府的禁忌,是因為對沙皇制度生殺予奪的權利,至高無上的威嚴心懷恐懼。
別里科夫長期受沙皇制度的鉗制,已經從思想到言行都被固化。于是這類別里科夫們在自己的生活圈、工作圈里釋放自己對政府政策的解讀,受此影響學生不敢違反紀律、教師不敢騎自行車、教士不敢吃葷、人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由于沙皇制度的威懾力,借助于別里科夫這類人之手輻射到周圍的普羅大眾;同時沙皇專制制度如同章魚的觸腕吸附在百姓生活的各個角落,讓他們由于心懷恐懼,不斷放棄對自由與進步的追求。
但如果說別里科夫的性格是時代使然,也會讓我們心生質疑:為什么別里科夫深受環境影響,而科瓦連科姐弟這類的人卻很喜歡新事物,敢于享受美好的生活呢?
其實,科瓦連科等人的性格和習慣也是受環境左右的。
契訶夫在《裝在套子里的人》中說,科瓦連科原籍是烏克蘭人,而烏克蘭是近代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雖然在19世紀中葉同樣受沙皇的統治,但1917年底東烏克蘭地區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可見烏克蘭無論是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在古老的俄羅斯都是走在變革的先鋒地位。而科瓦連科騎自行車、穿繡花襯衫、在大街上拿著書走來走去……這些被別里科夫非議的生活或學習習慣確實有些新鮮時髦,有些先鋒派的特點,這都和她的成長環境息息相關。
其次我們也要考慮別里科夫周圍的人群對他性格的影響。周圍的人群,包括他的同事、學生、朋友、愛人、教區的人、城區的人,這些人都長期籠罩在沙皇專制制度之下。這些復雜的生活圈,別里科夫處在夾縫里,既不能享受鮮活生活的變革快樂,也不曾看到對沙皇制度的質疑反抗力量。其實別里科夫的生存狀況,也是沙皇制度下人群的生存狀況,別里科夫僅僅是一個典型罷了。
綜上所述,別里科夫的種種負面性格是客觀存在的社會政治環境和周圍人群制造出來的,他自己主觀上對這一性格的負面特點并沒有清醒的認識,所以根本不會拒絕排斥。
那該采取怎樣的態度來評價別里科夫呢?
有人認為他面目可憎,是沙皇制度的忠實順民,是衛道士,他用一些陳腐的套子套住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也希望不斷地套住周圍的人群,客觀上確實為沙皇制度的推行推波助瀾。
有人認為這個小人物,他是沙皇制度的受害者和替罪羊,作者向讀者展示的是他們堪悲堪憐的人生。首先作者為我們塑造的這個裝在套子里的小人物,讓我們了解他形形色色的套子,讓我們看到他的膽怯,看到他對日常生活的憂慮,看到他對社會微小變革的近乎神經質般的恐懼。而他這樣的性格和社會制度的威壓關系密切,就如同《小公務員之死》在一名大官的呵斥聲中被“嚇死”的小公務員一樣。別里科夫的神經質表現,也同樣反映了社會的極端恐怖造成人們的精神異化、性格扭曲、心理變態與行為荒誕的現象。其次,別里科夫的社會身份也僅僅是個小人物,并不能真正對周圍的人群構成威脅,至于他轄制中學、轄制全城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某些人因為他蒼白的臉、唉聲嘆氣的神情引發了自己內心對他的同情,或者引起了同樣對沙皇制度心懷恐懼之人的警覺,或者人們變革的勇氣還不是很大,最終才會受到他的“轄制”。這些被轄制的小人物,都是生活中真正的弱者,他們大多數人都需要為自己的軟弱,找一個借口,于是他們找到了比自己更弱小、更膽怯的別里科夫。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讀者們同情全城人被轄制的時候,是否也同時看到別里科夫也被全城人時刻驚擾著呢?讀者厭惡別里科夫想要告密卻自稱正人君子的時候,是否同情他的愛情被惡意關注給他帶來的恐懼?讀者欣賞科瓦連科姐弟個性解放的時候,是否同情別里科夫的生命已奄奄一息呢?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別里科夫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但他本質上只是個可悲可憐,又可厭可憎的弱者罷了。我們如果用魯迅的觀點評價“套中人”別里科夫的話,也一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