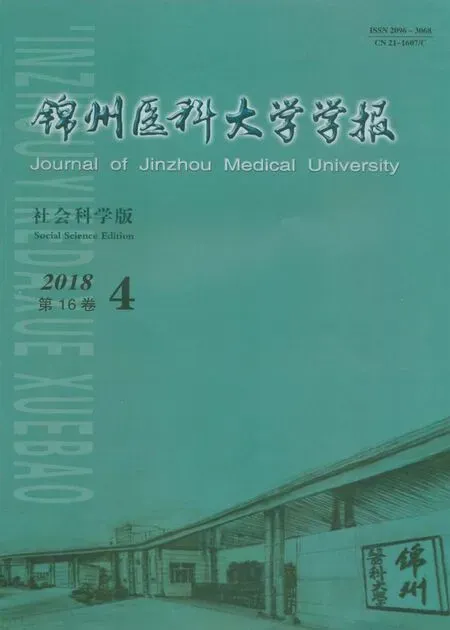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制度分析與完善
——以法經濟學為視角
王 翔
(皖南醫學院 人文與管理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俗語有云: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問題關系到每個普通人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食品安全與否,衡量著一個社會的道德誠信體系,關系到政府的執政形象。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不絕于耳,各類關于食品安全的“門”事件頻發,以至于每至年末,相關媒體都有年度若干大食品安全事件的總結報道。食品安全問題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的消費信心。國務院在關于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中也明確提出要推動完善嚴懲重處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相關法律依據,著力解決違法成本低的問題。在此背景下,2015年我國出臺了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確立了最為嚴格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實施食品安全戰略,讓人民吃得放心。對于食品安全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能否成為解決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劑良方,食品安全領域現行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還有否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值得進一步思考。
一、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規則的內容
所謂懲罰性賠償制度(Punitive Damages),是來源于英美法系一項損害賠償制度,具體來說,是來源于1763年Huckle v.Money一案的判決。[1]《布萊克法律詞典》中對其定義為:被告人由于魯莽、惡劣或欺詐,法院判決超出實際損失之外的賠償金額。[2]懲罰性賠償是與補償性賠償相對應的一項特殊民事賠償制度,它通過讓加害人承擔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以達到懲罰和遏制嚴重侵權行為的目的。[3]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隨之變遷,在整個法學領域,傳統民法中自由、平等、公平的價值之外又出現了新的價值,這就是安全與效率,懲罰性賠償制度正是對于安全與效率的回應。補償性賠償無法適應現實,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激勵和影響未來行為”,[4]其具有預防和懲罰的機制,能有效地防止同一風險的再發,在此意義上,懲罰性賠償制度有其存在的正當性。縱觀食品安全領域,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而導致人身損害的情況,可以適用《食品安全法》、《侵權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但是具體適用哪一種法律的規定,卻往往給當事人帶來不同的法律影響。在食品安全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要厘清三者的適用競合問題。首先,作為民事基本法的《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了缺陷產品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但是《侵權責任法》本身沒有對缺陷產品做一個界定,因此要適用本條,還需結合《產品質量法》的相關規定。此外,對于責任主體和保護的對象是人身權益還是財產權益都沒有具體規定,最重要的一點是《侵權責任法》對于懲罰性賠償數額未作明確規定。種種問題,均會導致其在具體適用中的困難,進而導致其被其他單行法架空的窘境。[5]在審判實務中,不同的法官對于《侵權責任法》與《食品安全法》的適用往往不同,而基于法律適用的基本規則,在食品侵權領域,食品應是產品的下位概念。簡言之,缺陷產品的規定應是一般規定,而食品安全規定是特別規定。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在食品安全領域應當首先適用食品安全法的規定。[6]其次,《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了產品和服務欺詐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五十五條第一款,關于欺詐行為作出了“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的要求。由此可知,經營者在提供食品或食品服務時,本著欺詐的主觀心態,應適用食品安全法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要求。而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五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經營者“明知”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費者提供,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情況下,沒有規定特別條款,可能會產生法律競合的問題。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食品安全法》是同位階的法律規范,不能適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適用規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賠償內容、構成要件上均有不同。因此,應當賦予原告自主選擇權,擇優行使。消費者意思自治規則的解決方式更優,由受害人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規范。[7]
二、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規則的法經濟學分析
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基于公私法二元分立的模式,認為私法是規范平等主體活動的,故而,私人遭受侵權時只能以獲得補償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而懲罰性賠償制度則是對這一傳統觀念的突破,彌補了民法與刑法的空白。懲罰性損害賠償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懲罰功能和威懾功能。[8]此外,對于食品安全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能否實現這一制度的功能,決定了這一制度的成敗。
1.侵權方的賠償成本與收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法經濟學中常見的一種分析方法,根據此方法,如果訴訟成本小于訴訟收益,那么多數人就會積極維權,如果反之,就會放棄維權。我們假設受害方的勝訴概率為Pp,能夠獲得的賠償率為Dp,其訴訟成本為Sp。侵權方的勝訴概率為Pd,賠償率為Dd,其訴訟成本為Sd。對于受害方來說,其期望值就是Pp*Dp-Sp,對于侵權方來說,其期望值是Pd*Dd+Sd。只有當受害方期望值大于0時原告才會起訴。而當侵權方的期望值大于受害方的期望值時,雙方也不會選擇訴訟,往往會通過調解解決爭議。在食品安全領域,受害方的維權成本主要體現在訴訟費用,而收益即是預期可得的賠償,即賠償率。那么侵權方的賠償成本就是受害方的預期可得的賠償。根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可知,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時,是單一消費者受到單一生產者生產的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侵害,表面上看來,是一個法律主體對另一法律主體的訴訟,可是現實中,食品生產是一個社會化大生產的活動,為了獲得最大的收益,食品生產者都是批量生產食品,按照新《食品安全法》規定,只有提起了訴訟的受害方才能獲得賠償,對于其他眾多未提起訴訟的受害方而言,侵權方式不需要負擔賠償成本的,一方面是大規模生產獲得的巨額利潤,一方面是單一案件中的懲罰性賠償數額,二者相差懸殊。在經濟上,侵權方無法感受到基于懲罰性賠償的痛苦,故而此制度懲罰和威懾功能可能落空。在食品安全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時,由于侵權法的不完善以及法律訴訟上的舉證責任問題,受害方也要承擔相應的訴訟成本,這種成本的存在,會導致學者所謂“理性的冷漠”,[9]根據《食品安全法》的規定,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時,受害方需要證明諸如自身損害、生產者的違法性和因果關系等問題,才可能獲得賠償,故而現實中即使消費者提出的訴訟請求,也未必會獲得懲罰性賠償金。這些獲得補償的消費者占全部受害者的比例就是履行差錯,[10]由于這種履行差錯的存在,侵權方在當下懲罰性賠償制度中,不需要為全部的侵權行為負責,侵權方仍然會存在僥幸心理,從而使得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威懾功能落空。在食品生產者選擇是否違法時,成本和收益至關重要,當違法收益顯著高于違法成本時,大多數食品生產者均會選擇違法,而當二者持平時,則會產生僥幸心理,也會選擇違法,只有當違法成本高于所得時,絕大多數食品生產者才會選擇守法。
2.受害方的維權成本與收益分析。第一,忽略信息成本,無法有效激勵消費者維權。食品安全領域中,受害方是否進行訴訟,往往關系到各種因素。在經濟學的視角下,受害方或者消費者被視為理性的經濟人,當其想要維護自身權益時,往往會考慮成本和收益問題,當收益大于成本時,受害方會積極地維護自己的權益。在一個簡單的博弈模型中,假定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理性的,選擇糾紛解決的方式只有訴訟。那么,當消費者獲得的賠償費用增大時,其訴訟的可能性就會增加。相應的,食品生產者的違法成本就會增加,其違法可能性就會降低。然而,現實的情況是,食品市場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市場,對消費者而言,食品生產者生產時所使用的原材料是否符合相應的國家標準,食品生產過程是否符合相應的衛生標準都不得而知,而食品生產者作為理性的經紀人必然會降低生產成本從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消費者無法通過一般生活手段知曉上述信息,反映在訴訟中就是消費者要支出大量的費用來維護自身的利益,最終無論是價款的10倍賠償還是損失的3倍賠償均不能有效激勵消費者通過訴訟來維權。第二,懲罰數額僵化,無法填補履行差錯的漏洞。對于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計算標準來說,新《食品安全法》規定,消費者可以請求食品價款的10倍賠償,或者選擇請求所受損失的3倍賠償。對于此規定,相比舊《食品安全法》而言無疑是進步的,但也僅僅是形式合理,并未從根本上提高食品生產者的違法成本。在實踐生產活動中,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的食品生產者會本能上追逐利益,由于大規模社會化生產的存在,無論是10倍價款的懲罰性賠償還是3倍的損失賠償,其均不可與食品生產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相比。因為履行差錯的存在,不可能所有受損害的消費者均能提起訴訟,這又進一步縮減了食品生產者的違法成本。顯然,無論是價款的10倍賠償還是損失的3倍賠償,均不能使企業完全地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從而使得食品生產企業基于恐懼巨額賠償金而采取有效的措施來預防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第三,懲罰的措施單一,缺乏邊際成本的制裁措施。食品生產企業是商品經濟的參與者,在經濟活動中無法避免的要進行各類經濟活動,有時候,違法行為的曝光對于不良食品生產企業的品牌形象和消費者信心的打擊比任何法律上的罰款來的更加有效。對于某些經濟實力雄厚的食品生產企業而言,一次巨額的懲罰性賠償金可能不會讓其充分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對于消費者的巨大傷害,可如果自己的品牌形象受損,消費者的購買信心全無,這對于食品生產企業而言是最致命的。這種成本就是經濟學中的邊際成本。遺憾的是,我們在新《食品安全法》中仍然沒有看到這些相應配套的懲罰機制。懲罰手段單一,僅僅有針對違法成本的制裁,缺乏對于邊際成本的制裁,最終的結果就是懲罰性不足,無法充分發揮懲罰性賠償的功能。
三、食品安全領域懲罰性賠償規則的完善
1.引入浮動限額制度,確立懲罰性賠償金標準。新《食品安全法》對于懲罰性賠償金的確立標準即是一個固定的倍數,當出現食品損害賠償的計算時,將食品價款乘以10即可算出懲罰性賠償的數額,但此種方法過于僵硬,而且如上文所述,也不能充分地使食品生產企業得到應有懲罰,在個案的處理當中也難以體現靈活性和能動性,無法充分體現合理性和公正性。而浮動限額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彌補上述不足,在具體標準確立時要充分考慮如下問題:首先,要考慮食品生產企業在生產不同批次產品時的售價和所有消費者所受的損失,如上文所述,由于存在理性冷漠和訴訟成本的問題,并不是每一個消費者都會對食品損害進行起訴,那么,即使食品生產企業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支付了懲罰性賠償金,但由于起訴的人數在所有受害者中不占多數,不良企業在總值上仍然不會受到懲罰。為了最大程度地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功能,應在計算懲罰性賠償金時,將所有生產的缺陷食品或所有受到損害的消費者作為基數,在此基礎之上得到一個估值,作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基礎。其次,保證懲罰性賠償標準使得違法人的成本遠遠大于違法所得,對于不良食品生產企業而言,其違法所得,往往即是其生產缺陷食品的利潤,而違法成本,應是扣除其生產成本之外的諸如訴訟費、賠償金等,如果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足夠高,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的食品生產企業就不會冒險選擇違法。最后,消費者單靠懲罰性賠償金本身,即10倍價款本身難以激發起訴訟熱情,只有足夠高的懲罰性賠償金才能激勵消費者積極維權,對于法經濟學者而言,懲罰性賠償金=(懲罰倍數-1)*補償性賠償金[11]方能充分保證消費者的維權所得大于其必要的維權成本。
2.引入相關因素考量,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懲罰性賠償制度在英美法系國家確定具體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時,除了考慮具體的懲罰性賠償標準,還會考慮相關因素,諸如被告的主觀過錯程度、財產狀況和獲利狀況,以便在個案中更加準確地確定賠償金數額。誠然,法律懲罰的是違法人的行為,而不是其本身,但是,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而言,一個富有的被告和一個貧窮的被告,在面對這一制度時,其威懾性是不同的。從法經濟學角度而言,財富的多寡對財富的認識也是不同的,在綜合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時,應當要考慮侵權人的財產狀況,對于侵權人財富的多少而變化不同的比例,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懲罰性賠償的威懾功能。因為,對于富人和窮人施加同等數額的懲罰性賠償金,比較而言,無法對富人造成足夠威懾,無法完全剝奪富人從侵權行為中所獲的利益。在實際司法活動中,某一侵權行為,往往會同時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在食品安全領域,同一行為,可能既要承擔民事賠償,也要承擔行政罰款,還要承擔刑事罰金。這樣一來,在確定民事領域的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時候,就必須要考慮到侵權人所受的其他經濟處罰,并相應地減少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不然,過度的威懾會造成不公和失序。所以,在實際進行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計算時,要通過浮動限額制度確定一個最高或最低限額,在此基礎上,考慮侵權人的相關因素,從而確定一個合理的賠償金數額。這一數額要既能體現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威懾功能,充分威懾被告,又能面對不同侵權情形,從而實現對原告的激勵功能。
3.引入邊際成本因素,提升制裁效果。懲罰性賠償制度作為一項民事法律規則,有其獨特的法律功能,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寄希望于懲罰的威懾性來遏制不法食品生產企業的違法活動,通過提高違法成本使食品生產企業守法。但是,對于某些經濟實力雄厚的違法者而言,懲罰性賠償金只是其違法成本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邊際成本也應當包括在其違法成本之內。因此,引入邊際成本因素,配套相關措施,加大違法者的邊際成本,能有效地遏制不法行為人去侵害消費者。對于某些被處以懲罰性賠償金的食品生產經營者,可以通過公開其不法行為的信息,將其違法狀況公之于眾,從而讓社會各界來監督。與此同時,針對不法食品生產經營者,要完善信用體系,將其與相關銀行、工商、質檢等部門共享,從而加大不法食品生產經營者在今后貸款、稅收、檢測頻率等方面的成本。通過邊際成本的引入,從各個途徑增加其違法成本,進而真正遏制食品安全領域的違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