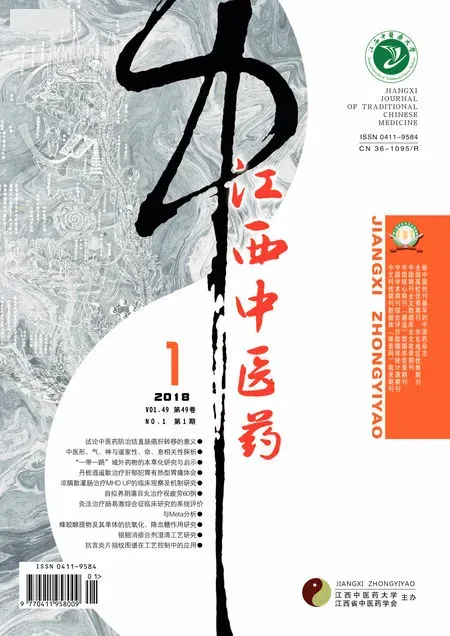“一帶一路”域外藥物的本草化研究與啟示*
★ 夏循禮(江西中醫藥大學 南昌 330004)
中醫藥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醫藥事業的根基和靈魂。通過研究中國歷代本草文獻中“一帶一路”沿線域外藥物輸入、融匯和轉化為本草藥物的歷史,可以了解中國醫藥學在發展過程中積極、有效吸納、轉化域外醫藥文明的歷史概貌、基本特征和發展規律,為《“一帶一路”中醫藥發展規劃》[1]實施提供借鑒,促進中醫藥傳承與創新、傳播與交流。
1 域外藥物輸入中國史略
域外藥物進入中國,主要源自中國和域外國家的文化交往與經濟貿易,中國和域外國家的交往最負盛名的是絲綢之路和漢武帝時期的張騫通西域事件,以及唐代的高僧玄奘赴天竺國取經的故事,其陸路和海上的交往和貿易線路今天發展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品物質上的交流與貿易主要通過政府交往行為的互相貢敬之品、以及非政府交往行為的民間商人貿易物品。其實,中國和域外國家的物產交流、至少是民間商品貿易交往(其中藥物占有很重要地位)應該追溯到更遠。域外藥物輸入中國的歷史概略如下[2-5]。
先秦至秦漢時期王充在《論衡》中云“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稚,倭人貢鬯草”,這是最早的中國接受域外藥物輸入的記載。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漢初相繼貫通,中國和中亞、西亞、以及東南亞諸國物產交流、商品貿易得以展開。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帶回大量域外藥物。同時,域外國家使節也貢獻一些域外藥物,如漢武帝時西湖月支國王遣使獻香(返魂香)事。除了西域諸國,東南亞國家也有藥物如“薏苡仁”等輸入我國。成書于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就收載有“薏苡仁、菌桂、葡萄、胡麻、犀角、戎鹽”等域外藥物,而外來藥物(物品)需要經過長期的中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認識、實踐過程才能進入本草著作,因此域外藥物輸入中國的歷史應在東漢之前很長一段時間。
魏晉南北朝時期梁武帝時期,波斯(今伊朗)與中國通商,其“薰陸、郁金、蘇合、青木”等香,以及“胡椒、蓽拔、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藥物輸入中國。該時期佛教興起,印度醫藥學伴隨著佛教傳入,并對我國醫藥學開始產生影響。朝鮮的醫療技術與藥物也傳入中國。陶弘景所著《本草經集注》收錄高麗、百濟的藥材有人參、金屑、細辛、五味子、款冬花、蕪荑、昆布、蜈蚣等數味。西晉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中,大量記載了從東南亞傳入嶺南的藥物,如豆蔻花、山姜花、蒟醬、益智子、蜜香、沉香、桄榔等。
隋唐五代時期隋唐時期,特別是盛唐,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海陸交通發達,對外交流頻繁。中外藥物學的交流在唐代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頻繁興旺,各類外來藥物源源不斷地傳入我國。這些外來藥物,有通過朝貢形式傳入的,如象牙、琥珀、人參、沉香、真珠、膃肭臍等,大多數則是由各國以貿易形式輸入中國的,朝鮮、東南亞、西域、印度等都有大量藥物輸入中國。
宋金元時期進貢是宋代外來藥物進入我國的重要途徑,尤以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的使節進貢最為突出。進貢藥物主要是香料藥,如龍腦、乳香、沉香、黃熟香、檀香、胡椒、丁香、豆蔻、茴香、檳榔、木香、蓽澄茄、龍涎香、蘇木、白梅花腦、白龍腦等。民間通商貿易輸入的藥物品種和數量更加顯著。元代,我國與亞非各國的交往比前代有了更大的發展。元代輸入藥物計有象牙、犀角、真珠、珊瑚、沉香、阿魏、血竭、高麗茯苓等。
明清時期明代中國的海上交通發達,為外來藥物的進一步輸入創造了有利條件。鄭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帶回數量驚人的珍貴的外來藥物。清朝前中期,社會穩定,國家強大,朝鮮和東南亞各國向我國進貢大量藥材,馬來西亞、文萊、印尼、菲律賓等同我國保持著藥物的貿易往來。
回顧“一帶一路”域外藥物的輸入歷史發現,外來藥物的輸入并為中國醫藥學所應用,經歷了長期的實踐與認識、以及中醫藥理論與臨床的轉化過程。多味優良的外來藥物,如犀角、檀香、沉香、木香、白豆蔻、乳香、沒藥等,已經成為中醫藥臨床應用必不可少的常用藥材,成為中醫藥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2 域外藥物分類及現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交往的互相貢敬之品一般為輸入國缺乏、輸出國珍視的貴重物品,禮儀性質重于實用價值,不占整個貿易規模和實際價值的主流;民間商人貿易則以牟利為主要目的,貿易商品以輸入、輸出國的有無、多寡(實質是價差)為依據,貿易物品主要以實際應用價值為重。藥物在政府交往的互相貢敬之品、特別是非政府交往的民間商人貿易物品中占有較大比例。“一帶一路”輸入中國的域外藥物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一是域外生產(生長),中國無生產(生長),全靠輸入者,如乳香、安息香、蘇合香、沒藥等。這些域外藥物不適合中國的生長環境,在中國沒有生產,只能依靠從域外輸入。這類輸入藥物占當前中醫藥臨床常用藥物的比重較小,并且有逐步減少應用、或者尋找替代品的趨勢。
二是域外生產(生長),中國也生產(生長),主要由域外輸入者,如高麗參、西洋參等。這類域外藥物在中國和域外國家都能生產(生長),但是域外生產(生長)的質量品質可能優于中國,或者域外生產(生長)產量更高、成本更低,適宜于從域外輸入。這類輸入藥物當前主要從域外輸入,在中醫藥臨床應用上供應基本可以保證,并且國內的栽培種植也一直在提高品質和增加產量。
三是歷史上域外生產(生長),中國無生產(生長),但是適于中國生產,開始時中國輸入商品,并且引種栽培成功,后來中國自己生產(生長),基本不再從域外輸入者,如白豆蔻、胡椒、金雞勒、薏苡仁等。這類輸入藥物當前基本上不再從域外輸入,國內引種栽培成功,無論產量還是質量都能滿足臨床應用,或者說已經轉化為道地的中國本草藥物品種了。不過,適當輸入少量該類藥物,進行域外品種和國內自產品種之間的比較研究,應該是有意義的探索。
上述的三種域外藥物之中,第三種情況的引種栽培可能主要是政府交往的使節行為(畢竟政府官員有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業收入的職責和意識),或者我國從事藥物輸入貿易的商人“由商轉農”思想和意識的自然滋生所致:中國長期的農業社會、“以農為本”的重農思想會“引導”盈利的商人去買地、引種栽培那些他熟悉的、貿易獲利的域外藥物,因為他知道這些藥物有很大的國內市場需求,栽種成功,獲利是有保障的。這與當前的中藥材GAP基地種植申報、地方政府和農戶踴躍種植道地、優質藥材是類似的。
3 域外藥物(物品)的本草化途徑
“一帶一路”沿線域外國家輸入中國的物產和商品,有一些在輸出國是藥物,有一些在輸出國不是藥物,而在輸入中國后被當成潛在藥物、進入中醫藥臨床實踐和應用、成為本草藥物、直至為重要的本草著作所載錄,值得探究其原因與途徑。
對于在輸出的域外國家是藥物的物品,從其輸出的目的和在輸入國的首選用途來看,當然都是藥用,是治病療疾的,比如底也迦。但是東西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上各自的醫學思想、醫學理論與臨床是不一致、有很大的差異。對于域外輸入的藥物,需要針對其所宣稱的主治病癥進行不同國家之間醫學理論與臨床方面的概念、術語的比照互參,以病癥為紐帶,謹慎試用,確有療效,方可推廣。比如“底也迦(鴉片制劑)”是世界醫學史上很有影響的藥物,是西方世界極其珍視的萬能解毒藥,主要用于各種動物咬傷的中毒癥。唐朝時傳入中國,唐本草載之云“胡人時將至此,亦甚珍貴,試用有效”[6]。
有些在輸出國家不是藥物,而是生活物品,輸入中國后轉化為本草藥物,如“阿魏”, 阿魏在印度為調味品,輸入中國后用于“殺蟲、消癥去積”,進入本草名錄。食物用途的輸入藥物,在食用的過程中發現其某些功效作用、通過對其進行中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重新認識與實踐,確定其符合中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性味主治、功效作用而收載為本草藥物。再如“蘇合香”,蘇合香等香料物質在域外用于熏燒房間、或者涂抹身體,輸入中國后成為“芳香開竅”的良藥,中國本草學家借其“辛竄芳郁”(本草術語)之特征,用于“理氣止痛、開竅醒腦、化濕避濁”(中醫藥學理論)之功效主治。
有些在輸出國、或者輸入國(中國),都是奢侈品,比如象牙、犀角等,用來擺放裝飾宮宇、府邸等以顯示門第、身份象征的,或者制作成高檔工藝品,后來成為“涼血解毒”的本草藥物。當然“涼血解毒”用象牙、犀角,不是一般病患者所服用。有可能是象牙、犀角在加工成裝飾工藝品時灑落的碎屑,醫藥學家對其物理化學特性的感知,首先被認識和實踐有“涼血解毒”功效。因為珍稀動物保護、象牙犀角的貴重稀缺,本草藥物名錄中的象牙、犀角等已經成為歷史。
總之,域外物品(藥物),輸入中國后,進入中國本草藥物名錄,成為中醫藥臨床常用藥物,是要經歷長期的、反復的、基于中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實踐和認識過程的;經過這個過程,域外的藥物、生活用品、或者珍稀的裝飾物品等,才會成為中醫藥學的本草藥物,為歷代的本草著作和臨床醫案、方書所收載。
域外輸入的各種生活物品、奢侈裝飾用品、以及藥品為什么會進入本草名錄,成為中醫藥臨癥的重要藥物?這可能與中國醫藥學的哲學基礎和傳統思想關系密切。中國最早的醫藥學傳說是“神農嘗百草”,“神農嘗百草”既是傳說,本質上更是傳統。中華民族的醫藥學哲學是“天人合一”,醫藥學傳統是自然醫學,中國醫藥學家、本草學者隨時隨地都有一種尋找、發現、認識和實踐增進人們身體健康、預防疾病、治療疾病的物品與方法的思維習慣,或者說基本品質。域外藥物的本草化過程其實也是中國醫藥學家、本草學者基于這一基本品質對外來物品進行中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認識和實踐過程、以及成果。
4 域外藥物本草化的啟示
“一帶一路”域外藥物本草化的歷史和轉化途徑表明世界人民是熱愛相互交往的,相互交往是各國人民文化與物質之間的交流與互通,每一個民族和國家的人民都愿意把自己優秀的文化和有益的、珍視的物質拿來同其他民族和國家的人民分享、交換;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從來都是樂于、勇于和善于接納、學習和吸收轉化外來優秀文化與有益的事物,在對外交往中既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也有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化與物質、發展壯大中華文明的智慧。
從域外藥物輸入中國史略的介紹可知,在清代晚期西醫開始進入中國之前,外來藥物的引進,沒有系統的醫學理論與技術輸入,都以單一的、或者零星單純的物品、藥物、技術形式引進,沒有對我國的中醫藥學體系產生多少影響,而是被中醫藥學說吸收和轉化,成為中醫藥學的組成部分。而到清朝晚期,西醫通過傳教士、中國留學生、以及西方職業醫生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正處于國家積貧積弱、列強霸凌、政府軟弱、民族自信心極度脆弱的處境,中國醫藥學受到內外打壓,在和西醫的交流與碰撞中,脫離了中國歷史上的對外來醫藥的基于中國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認識與實踐、吸收和轉化的軌跡,出現了一段時間內中西醫藥并行、西強中弱的局面,直接阻礙了中國醫藥學的發展[7]。
上述正反兩方面的情況表明,正是由于歷史上對外來醫藥本著“拿來主義”的精神,采取“開放”的態度,凡對人類健康有益的事物、防病治病的方法,皆可為我所用,在堅持中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基礎上充分消化、吸收外來藥物,使之與我國的中藥融匯為一體,轉化為中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藥才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斷地向前發展。事實上,發展壯大的中醫藥學也會為世界各國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健康服務,造福于人類社會。
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正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和世界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交流,中醫藥“一帶一路”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健康觀念和醫學模式的轉變,中醫藥在防治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及重大疾病中的療效和作用重新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接受,正在、并且必將越來越多地為促進人類健康發揮積極作用。
中醫藥“一帶一路”建設,既是中國向世界各國人民傳播與交流中醫藥學優秀文化,也是中醫藥學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吸收其他民族和國家優秀醫藥文化、發展中醫藥學的過程。中國醫藥學在和外來醫藥文化交往和傳播的過程中,要堅持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在遵循中醫藥學理論與臨癥的基礎上,大力吸收、轉化世界各國人民優秀的醫藥文化和醫學技術,發展壯大中醫藥學理論與技術,加快融入國際醫學體系,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世界各國解決醫療可持續發展、增強人民健康保障提供中國的中醫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