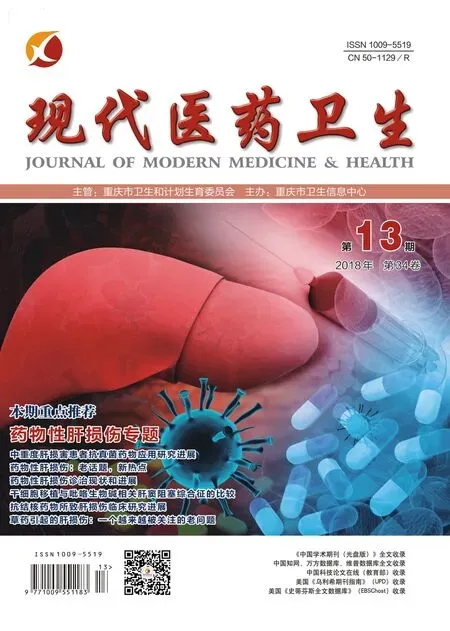藥物性肝損傷:老話題,新熱點*
趙 紅,王 琦 綜述,謝 雯審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肝病中心,北京100015)
藥物性肝損傷(DILI)是指由各類處方或非處方的化學藥物、生物制劑、傳統中藥、天然藥、保健品、膳食補充劑及其代謝產物乃至輔料等所誘發的肝損傷。據統計,DILI發生率高居所有藥物不良反應之首,是最常見和最嚴重的藥物不良反應之一,重者可致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
2014年美國胃腸病學院(ACG)發布《特異質性藥物性肝損傷診斷和治療指南》[1]是首部關于特異質性DILI的診治指南;其后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藥物性肝病學組發布中國首部《藥物性肝損傷診治指南》[2],2018年歐洲肝病學會(ESAL)頒布了首部DILI防治指南,但正式定稿文本尚未公布。三大指南均分別對DILI的定義、流行病學、危險因素、發病機制、臨床分型和表現、實驗室、影像學和病理檢查及診斷、鑒別診斷、治療、預后、預防、管理和展望進行了全面描述。
其后,各個學科中關于DILI的相關指南及共識陸續發表[3-6],提示DILI相關研究日益受到重視,DILI這一老話題,在近5年內隨著多部指南及共識的發表,關于DILI的流行病學、發病機制、診斷標準、治療藥物,以及中草藥所致的DILI等內容成了臨床研究的新熱點。
1 DILI的流行病學:發病率數據缺乏
由于缺乏普通人群的大規模DILI流行病學數據,目前,DILI的確切發病率尚不明確。冰島報道DILI的發病率估計在19/100 000[7],法國報道DILI的發病率估計在13/100 000[8]。我國人口高達13億,臨床用藥種類繁多,應用中草藥、中藥湯劑及膳食補充劑者人口眾多,并且人民群眾及醫務人員對藥物安全性問題,尤其是中草藥可能具有的毒性反應認識欠清楚,對上市后藥物出現的藥物不良反應,比如,DILI的報告缺乏規范的報告體系,現在對DILI的診斷缺乏特異性較高的診斷指標,認識不清,導致我國DILI的發生率呈逐年上升趨勢[9]。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藥物性肝病學組在2015年組織全國33個省市及自治區不同級別醫院進行的2012—2014年住院患者DILI回顧性研究結果即將發表,將提供中國的相關數據,今后應該進行更多相關前瞻性研究了解流行病學現狀。
具有潛在肝毒性、可以導致DILI的藥物種類現在全球報道有1 100種以上[10],中西方之間因為用藥差異,報道導致DILI的藥物類別差異較大。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最常見導致DILI的藥物為非甾體類抗炎藥(NSAIDs)、抗感染藥物、抗腫瘤藥物等,尤其是近年來方興未艾的程序壞死因子(PD-1)及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CTLA-4)等藥物[11-15]。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于2011年3月25日批準伊匹利特(ipilimumab)用于治療晚期黑色素瘤,但在上市3年后,此藥已有報道導致50余例嚴重的肝臟損傷,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藥物,因此FDA給予警告,提示在必須使用此類藥物時應高度關注其對肝臟的不良反應[16]。
在中國,導致DILI的藥物中,高居首位的為中草藥,其次為抗結核藥物,與歐美國家之間有較大差異。此外,現在中外學者均很關注膳食補充劑導致DILI的問題,在美國統計的導致DILI種類中,膳食補充劑所致的可以占到16%[17-19]。
既往DILI的臨床研究中發現,同一種藥物可導致不同類型的肝損傷。不同藥物也可導致相同類型肝損傷,在臨床上尤其應高度關注。
DILI的危險因素包括遺傳學因素、藥物因素和環境因素3個方面[8]。遺傳學因素主要是指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等的基因多態性與DILI相關,此外,藥物代謝酶、藥物轉運蛋白也可能與危險因素相關。不同種族的患者對DILI的易感性可能存在差異。HLA基因檢測在將來可能有助于DILI的診斷,但目前階段,僅限于非常有限的選擇性藥物,比如氟氯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維酸、特比萘芬和噻氯匹定等。目前,在臨床研究中有進行HLA基因檢測幫助診斷的研究報道[20-22],但在歐洲DILI臨床診斷及治療指南中,不建議推廣至其他藥物進行廣泛的基因檢測用于相關DILI的診斷。高齡、女性、妊娠、慢性肝病基礎、過量飲酒、肥胖等是DILI可能的非遺傳學高危因素,需要引起警惕。藥物因素是指藥物的化學性質、劑量、療程,以及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可影響到DILI的潛伏期、臨床表型、病程和結局。環境因素主要包括過量飲酒,可能增加某些藥物引起DILI的風險[2]。
2 DILI的臨床分型和表現
2.1臨床分型
2.1.1發病機制分型DILI根據發病機制可以分為特異質型和固有型[2]。特異質型DILI具有不可預測性,在臨床上更為多見,臨床表現個體差異顯著,并且與藥物劑量常無明顯相關性。固有型DILI具有可預測性,與藥物劑量密切相關,潛伏期短,個體差異不顯著。
因為藥物安全性問題現在已經引起高度關注,對于與臨床使用劑量有密切關系的固有型DILI,目前,各國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會定期發布相關信息,給予警告、黑框警告及退市等預防性處置,現在已相對少見。
對于特異質型DILI,臨床上可分為免疫特異質性DILI和遺傳特異質性DILI。免疫特異質性DILI臨床上可有不同表現,一種是超敏性,通常起病較快(用藥后1~6周),臨床表現為發熱、皮疹、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等,再次用藥可快速導致肝損傷;另一種是藥物作為半抗原誘發的自身免疫性損傷,臨床上常稱之為藥物誘導性自身免疫性肝炎(AIH),臨床表現多樣,體內可能出現多種自身抗體,對激素治療反應較為敏感,在臨床表現上難于與經典AIH相鑒別,通常需行肝臟穿刺術,通過病理組織學檢查來進行鑒別。
遺傳特異質性DILI通常無免疫反應特征,起病較為緩慢,再次用藥時可能出現類似臨床表現。
2.1.2病情恢復速度分型DILI在臨床上根據病情是否快速恢復,可以分為急性DILI和慢性DILI。慢性DILI是指DILI發生6個月后,血清酶學指標仍然持續異常,或存在門靜脈高壓或慢性肝損傷的影像學和組織學證據。現有研究報道,DILI患者如果在DILI發生后第2個月,總膽紅素(TBil)及堿性磷酸酶(ALP)仍持續升高,應關注此患者有可能成為慢性DILI[19]。此外,藥物誘導的AIH患者出現慢性DILI的概率升高,膽汁淤積型DILI患者出現慢性化的可能性增加。美國藥物性肝損害網絡(DILIN)報告顯示,DILI患者中,6%~20%的患者可進展為慢性DILI[19]。
2.1.3受損靶細胞分型DILI根據受損靶細胞類型可分為肝細胞損傷型、膽汁淤積型、混合型和肝血管損傷型。
DILI是肝細胞受損所致還是膽管細胞受損所致的膽汁淤積型,在臨床上主要依據R值進行分類,R=[谷丙轉氨酶(ALT)實測值/ALT(ULN)]/[ALP實測值/ALP(ULN)]。2018年歐洲肝病學會頒布的DILI診斷及治療指南中明確規定,DILI的分類應根據DILI首次檢測到的肝酶升高進行R值的計算,進而區分出此次的DILI是肝細胞損傷型、膽汁淤積型,還是混合型[23]。
肝細胞損傷型是指ALT≥3 ULN,且R≥5;膽汁淤積型是指 ALP≥2 ULN,且 R≤2;混合型是指 ALT≥3 ULN,ALP≥2 ULN,且 2<R<5。如果ALT和ALP 達不到上述標準,則稱為“肝臟生化學檢查異常”,而不能診斷為DILI。
肝血管損傷型DILI既往認為臨床相當少見,發病機制尚未確定,主要是藥物導致肝竇、肝小靜脈和肝靜脈主干及門靜脈等的內皮細胞受損所致。臨床上可見于含有吡咯雙烷生物堿的草藥,如千里光、土三七及某些化療藥物等導致的肝竇阻塞綜合征(HSOS)/肝小靜脈閉塞病(HVOD)、紫癜性肝病(PH)等。現在已引起臨床高度關注[24]。
2.2臨床表現DILI的臨床表現,總體來說缺乏特異性。不同藥物,不同人群,同樣的藥物在不同人群中的臨床表現差異巨大。使用藥物后至出現臨床癥狀的潛伏期差異很大,可短至1 d至數日,長達數月。多數患者可無明顯癥狀,僅有血清肝臟生化指標的異常。部分患者可有食欲減退、乏力、厭油、肝區脹痛及上腹不適等消化道癥狀。淤膽明顯者可有全身皮膚黃染、大便顏色變淺和瘙癢等。少數患者可有發熱、皮疹、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甚至關節酸痛等過敏表現,還可能伴其他肝外器官損傷的表現。病情嚴重者可出現急性肝衰竭(ALF)或亞急性肝衰竭(SALF)表現。在美國DILIN統計數據中,因ALF需要進行肝臟移植的患者中,DILI所致占到56%,尤其多見于對乙酰氨基酚所致的急性藥物性肝衰竭[19]。
慢性DILI的臨床表現多樣,可表現為慢性肝炎、肝纖維化、代償性和失代償性肝硬化,在藥物誘導的AIH患者中,可以出現肝外表現,也有部分患者可以表現為慢性肝內膽汁淤積,以及膽管消失綜合征(VBDS)等[25-26]。少數患者還可出現HSOS表現及肝臟腫瘤等。土三七所致HSOS,在部分患者可進展迅速,出現腹水、黃疸、肝臟腫大等表現,如果未能及時診斷,預后欠佳[2]。
3 實驗室、影像和病理檢查
DILI是典型的需要排除其他疾病而做出診斷的疾病,因此,在臨床上首先需要確定是否出現肝損傷,肝損傷與所用藥物的因果關系判斷尤為重要,同時應該依據受損細胞類型及DILI發病機制進行分型,進行相關影像學檢查,在仍然不能明確診斷的情況下,應該進行肝臟活體組織檢查明確診斷。DILI的病理損傷類型可以見于所有的肝損傷的病理表現,且缺乏特異性,需要臨床醫生及病理醫生共同做出診斷。
4 DILI的診斷
DILI的診斷目前仍為排他性診斷。診斷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確認存在肝損傷,其次排除其他肝病,肝活檢組織學檢查有助于診斷和鑒別診斷;(2)可通過因果關系評估來確定肝損傷與可疑藥物的相關程度。推薦Roussel Uclaf因果關系評估法(RUCAM)評分量表作為臨床實踐中DILI臨床診斷的應用量表:>8分為極可能(Highly probable),6~8 分為很可能(Probable),3~5 分為可能(Possible),1~2分為不太可能(Unlikely),≤0分為可排除(Excluded);(3)判斷DILI的臨床分型及嚴重程度。
在DILI的臨床診斷中應該關注存在自身免疫表現患者的確定診斷,在此類患者中實際上有著明確的異質性:第一是在已有AIH的基礎上因為用藥導致出現DILI,可以導致原有疾病的加重;第二是藥物作為半抗原誘導的AIH樣表現;第三是具有類似自身免疫表現的DILI。在此類患者中,通常需要進行肝臟組織學檢查明確診斷,必要時進行激素及免疫抑制劑治療,需根據治療的反應最終做出相應診斷。
5 DILI的治療
DILI目前仍然缺乏特效的治療方法,最重要的是發現可疑導致肝損傷的藥物時,必須及時停用。根據DILI的臨床類型選用適當的藥物治療,在病情進展至肝衰竭的重癥患者,需要及時考慮肝移植挽救患者生命。
5.1及時停用可疑的肝損傷藥物首先需要強調及時停用可疑的肝損傷藥物是DILI最為重要的治療措施。但因為患者所用藥物可能為多種,在我國,中草藥及中成藥中成分相對復雜,很難及時確定藥物與肝損傷間的因果關系,在此背景下,應該盡快停用一切可疑藥物。
關于何時停藥的客觀標準可以參考美國FDA于2013年制定的藥物臨床試驗中出現DILI的停藥原則。出現下列情況之一應考慮停用肝損傷藥物:(1)血清ALT 或 AST>8 ULN;(2)ALT 或 AST>5 ULN,持續 2周;(3)ALT 或 AST>3 ULN,且 TBil>2 ULN 或國際標準化比值(INR)>1.5;(4)ALT 或 AST>3 ULN,伴逐漸加重的疲勞、惡心、嘔吐、右上腹疼痛或壓痛、發熱、皮疹和(或)嗜酸性粒細胞增多(>5%)。
5.2根據DILI的臨床類型選用適當的藥物治療DILI
5.2.1N-乙酰半胱氨酸(NAC) NAC是針對乙酰氨基酚中毒的特效藥物,2004年美國FDA批準用來治療對乙酰氨基酚引起的固有型DILI。NAC可清除多種自由基,人們認為NAC對于非對乙酰氨基酚導致的DILI也是有效的,但是并沒有太多證據支持。
5.2.2糖皮質激素糖皮質激素對DILI的療效尚缺乏隨機對照研究。糖皮質激素治療DILI需要嚴格掌握治療適應證,對于超敏或自身免疫征象明顯且停用肝損傷藥物后生化指標改善不明顯或甚至繼續惡化的DILI患者,排除糖皮質激素治療禁忌證,在充分權衡利弊、告知患者相關風險情況下可以考慮應用糖皮質激素;對初次發病、用藥史明確、自身免疫特征明顯而不能排除AIH患者,在停用可疑藥物后,可考慮糖皮質激素治療。DILI相關ALF治療中是否應用激素尚存在爭議,缺乏高級別證據的支持。糖皮質激素治療DILI時需要選擇合適的病例、適當的治療時機,斟酌最佳的治療劑量,并強調病情緩解后逐漸減量直至停藥;在治療過程中密切監測不良反應。如隨訪過程中未再次應用肝損傷藥物病情復發則建議進行肝臟穿刺活檢,明確診斷為DILI還是AIH。
5.2.3抗炎保肝類藥物中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最近批準異甘草酸鎂可用于急性ALT明顯升高的急性肝細胞型DILI或混合型DILI的治療。經驗表明,甘草酸制劑、雙環醇、水飛薊素可用于輕-中度肝細胞損傷型DILI和混合型DILI的治療。熊去氧膽酸、腺苷蛋氨酸可用于膽汁淤積型DILI的治療。但是上述藥物的確切療效尚有待高級別的循證醫學證據支持。需要強調的是不推薦2種以上保肝抗炎藥物聯合應用,也不推薦預防性用藥來預防或降低DILI的發生。
5.3病情進展至肝衰竭的重癥患者需考慮肝移植藥物相關ALF/SALF的病死率高,對于出現肝性腦病和嚴重凝血功能障礙的ALF/SALF,以及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可考慮肝移植。
5.4關注肝病治療過程中對其他器官的影響2013年推出的以索菲布韋為代表的直接抗病毒治療(DAA)對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進行治療,徹底改變了既往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治療療程長、治愈率低、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不良反應發生率高等弊端,在12~24周治療過程中90%以上患者可以獲得持續病毒應答率。
但在臨床治療過程中,目前報道3例DAA前基線腎功能正常的患者,接受實體器官移植后,診斷為慢性丙型肝炎,開始接受丙型肝炎的DAA后,出現蛋白尿,且腎活檢提示為局灶性節段性腎小球硬化癥,該病是以蛋白尿為特征的一種臨床病理診斷[27-29]。在實體器官移植患者中,針對HCV的DAA過程中出現腎臟功能的損傷,已經成為臨床的新挑戰,應該引起臨床醫生的關注。
隨著CFDA對藥物臨床使用過程中相關不良反應監測的高度關注,我國對新藥臨床研究過程中的藥物安全性已有嚴格的防控政策及制度要求,但是在既往對已上市藥品的不良反應監控中,尤其是DILI發生的預防預警工作,由于DILI疾病的自身特點,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我國人口眾多,不規范用藥情況較為多見,尤其民眾有自行服用中草藥的習慣,導致DILI發病率逐年上升。因此,應該關注臨床合理用藥,避免濫用藥物。臨床工作中在及時診斷DILI的基礎上進行規范治療,對于改善患者預后、合理使用醫療資源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