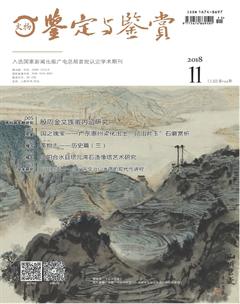陳莊遺址出土引簋銘文的兩點認識
楊云鵬
摘 要:山東陳莊遺址發現了大量青銅器,其中以兩件長銘文的引簋最為引人注目。引簋的銘文內容包含了西周中晚期許多方面的歷史問題,對于我們研究西周史以及推斷陳莊遺址的性質有極大的幫助。文章對引簋銘文的研究和一些相關問題的探討,主要從冊命制度、軍事制度、周與齊國這一時期的一些相關歷史問題三個方面入手,將金文材料與歷史記載相結合,探究銘文中提到的“齊師”的性質與這一時期齊國史的一些問題。
關鍵詞:陳莊遺址;引簋;齊師
陳莊遺址位于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陳莊和唐口村之間,考古發現了一座西周城址及多座西周貴族墓葬,出土50余件青銅器。其中M35出土兩件同形同銘的引簋,其銘文計8行73字,涉及冊命、軍事、齊國史等諸多內容。為方便討論,將其銘文摘錄如下:
唯正月壬申,王各(格)于龔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齊師,余唯申命汝,易(賜)汝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敬乃御,毋敗績。”引拜稽首,對揚王休。同追,俘金、兵。用作幽公寶簋,子子孫孫寶用①。
銘文中的“龔大室”即共王的宗廟,結合發掘簡報中對于墓葬年代的判斷(不晚于西周中期晚段)[1],將這兩件引簋定于孝王至夷王這一時期應是沒有問題的。銘文中涉及到的問題較多,在這里著重討論“齊師”的問題和銘文涉及的一些齊國史,并希冀通過這些討論,可以對陳莊遺址的性質有進一步的認識。
1 齊師的性質
關于齊師,在史密簋和師簋中也有相關記載。史密簋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636):“唯十又一月,王命師俗、史密曰:‘東征。……廣伐東國,齊師、族徒、遂人乃執鄙寬惡。師俗帥齊師、遂人□周伐長必……”師簋載(《殷周金文集成》4313):“……今余肇命汝率齊師、紀、萊、、夷、,左右虎臣,征淮夷……”
李學勤、李零等先生[2]據史密簋和師簋銘文中齊師直接由周王調遣這一點,認為齊師應當是類似于“大軍區”性質,直屬周王室管轄,是西周在東方的一支機動力量;而趙慶淼先生[3]則認為,引簋中的“齊師”不同于此二器,是屬于長期的冊命而非臨時的調派,又由引家族長期統領齊師,認為齊師可能是與齊國關系更加緊密。
首先我們應當肯定的是,引簋中“齊師”的記載確實與另兩器不同,是正式的冊命而非臨時的統帥。然而仔細分析引簋銘文我們可以發現,對引的冊命并非一次。首先是周王冊命引繼承父祖去統帥齊師,即“余既命”的內容。而后又出現了再一次的冊命,即“余唯申命汝”的內容,這是西周冊命制度中的“再命”現象。此次再命沒有明確說明冊命的目的,根據后文“同追,俘金、兵”可以看出此次冊命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去征討或追擊某軍隊。據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引是先接受了周王統帥齊師的冊命,后又奉命率軍出征。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何引簋銘文與另兩件器物的不同之處。
進一步分析周王對引的冊命,彤弓、彤矢一般是周王賜予諸侯或王室卿士的物品,從金文中來看一般是賜予地位較高或有特殊貢獻的王室卿士或諸侯,如《虢季子白盤》(《殷周金文集成》10173):“……丕顯子白,將武于戎功,徑維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陽,……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伯晨鼎》(《殷周金文集成》2816):“王命侯伯晨曰:嗣乃且(祖)老侯于。易女矩鬯一卣、玄袞衣、……彤弓彤矢、旅弓旅矢,……用夙夜事,勿廢朕令。……”此二例一為王室卿士授予引彤弓、彤矢,說明引的地位應當是與這些人相當。又由于引并非周王冊封的諸侯,可見引應當是相當于王室卿士一類的人物,是直屬于周王室的。統帥直屬于周王室,齊師的性質也就不言自明了,這點在師簋銘文中也可以得到佐證,其中直接提到“齊師”而非“齊”,將齊師與其他諸侯國相并列,可見齊師的地位應當是和其他諸侯相當的。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至少在這三件器物所對應的時期內,齊師應當是駐扎在山東半島直屬于周王室的一支部隊,其最高統帥是由周王親自任命的,其作用則很可能是代替周王鎮守和監督東方。
2 銘文所見的齊國史
引簋銘文中還有一點十分引人注意,那就是引出征的對象沒有記載。在西周金文其他描述戰爭的器物中,征伐對象大多是周王室周邊的戎狄、東夷、楚或是內部的叛亂,如前文提到的虢季子白盤中就明確提到了是征伐蠻方。又如,《多友鼎》(《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02500):“唯十月,用玁狁方興,廣伐京師,告追于王,……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于京師。……”說明了戰爭對象是玁狁。《鼎》(《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02489):“……王用肇使乃子,率虎臣御淮戎。……”說明了是對淮夷(淮戎)的戰爭。這類銘文都會詳細記載戰爭的經過、戰績等內容,至少也會說明征伐對象。引簋中齊師的征伐對象如果是東夷或淮夷,戰勝追殲本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應當像其他器銘一樣詳細記載。然而引簋銘文卻閃爍其詞,并沒有說明追殲對象,對于戰績也只是說“俘金、兵”,而沒有詳細記述。那么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一種可能,這次戰爭的對象很可能是其他的勢力,并且出于政治或輿論的需要不能具體說明,所以導致了銘文中出現這樣的現象。
聯系文獻的記載,在這一時期,齊國出現了很大的變動,即周夷王烹殺了齊哀公,強行冊立齊胡公。《史記·齊太公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4]這一事件在齊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齊胡公也因此把都城由營丘遷往薄姑。如果引簋銘文與這一事件有關聯,那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引打了勝仗卻沒有詳細記述了。結合前文對引簋的年代的判斷,即孝王至夷王時期,那么從時間上引簋銘文應當和史記的記載是吻合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出兩種可能:一是引簋的征戰對象就是齊哀公的殘余勢力,這也就可以解釋銘文中用“追”而非“征”這一點;一是由于齊國的動亂引來了淮夷或其他勢力的入侵,引奉命征討。無論是這兩種可能的哪一種,引簋銘文的內容都應當是與《史記·齊太公世家》中齊國君主變動這一事件的記載有很大關聯的。
參考文獻
[1]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高青縣陳莊西周遺址[J].考古,2010(8).
[2]李學勤,劉慶柱,李伯謙,等.山東高青縣陳莊西周遺址筆談[J].考古,2011(2).
[3]趙慶淼.高青陳莊引簋銘文與周代命卿制度[J].管子學刊,2015(3).
[4]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M].北京:中華書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