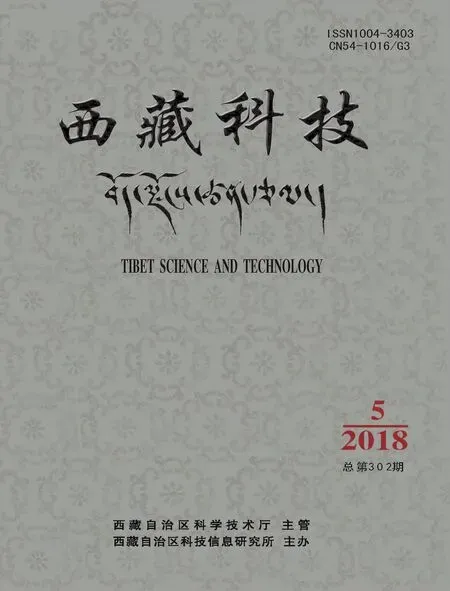淺談西藏制陶技藝的歷史與現狀*
楊明芬次仁羅布班覺
(1.西藏自治區科技信息研究所,西藏 拉薩 850008;2.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藏 拉薩 850000)
西藏新石器時代出土陶器的遺址或地點主要分布在昌都卡若和小恩達、拉薩曲貢、山南貢嘎昌果溝、瓊結邦嘎、乃東的欽巴村、林芝紅星、居木、墨脫的背崩村、馬尼等地方。這其中昌都卡若是西藏新石器時代陶器中年代較早,出土的陶片最多。卡若器類簡單,器形以罐、碗、盆三類為常見,均為平底,不見圜底和圈足器。陶器均是夾砂陶,以夾細砂的陶質居多,其中一件單口雙腹連體陶罐最具代表性。而拉薩曲貢遺址也出土了上萬件陶片,代表著西藏新石器時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1]。從挖掘的陶器來看,當時的曲貢先民已熟練掌握了慢輪修整技術,陶器的成型、焙燒、裝飾等技藝顯示出很高的工藝水平。陶器有泥質和夾砂兩種,器形種類較多,以罐為主外,還有缽、碗、豆、盂、盤、杯等,都是圈足器和圜底器,平底器罕見,器耳比較發達。大部分陶器雖均為手工制作,但明顯帶有慢輪磨制的痕跡,其中以磨光黑陶最為精美。
卡若和曲貢陶器的裝飾以各種線條構成的幾何紋飾為主,體現了高原先民用線條表達對生活的熱愛和生命的追求[2]。根據考古工作者對這兩處遺址的年代測定,卡若文化的絕對年代為距今4300-5300年之間,曲貢文化則是距今3500-3750年之間[3]。而阿里地區札達縣皮央東嘎遺址和格布賽魯墓地出土和采集的陶器屬于前佛教時期,距今2000-2400年左右[4],絕大多數為泥質紅陶,不見夾砂陶,但陶泥不純,器型單一,以單耳圜底為主,不見圈足器,平底器少見,大型器較少[5-6]。札達縣出土的陶器與卡若和曲貢遺址出土的陶器在器型、器表裝飾紋樣、制作技術、以及制作方法上形成迥然不同的風格,成為陶器在西藏發展中的多樣性。
到吐蕃時期,陶器更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佛教的傳播和弘揚,以及周邊民族文化的吸收,使西藏各地的陶器在產量和品種上不斷增多,陶器制造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和完善。在西藏發掘的吐蕃時期的墓葬內就發現不少陶器,如林芝地區出土泥質灰陶、褐陶、夾砂紅陶,器種為小口細頸平底罐。乃東普努溝出土有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幾乎全為素面,也有飾藍紋,器種大都是圓底罐,或有耳和流。這些出土的陶器都是手制成型,作為隨葬品可以證實陶器給當時吐蕃人的生活提供了眾多便利,也深受吐蕃人的喜愛和器重,陶器制造業自然成了吐蕃手工業中較為興盛的工藝之一[7]。據《漢藏史集》記載,吐蕃贊普赤都松為了得到飲茶的器具,曾派遣使者到唐朝求碗,唐皇帝沒有直接給碗,而是派了一位制陶工匠。這位能工巧匠利用贊普從內庫所取的陶土等原料,據說制造出連漢地都罕見的陶碗,其特點是“口寬,質薄,足短,光滑精細,有藍色光澤”,在碗上繪有當地關于茶的來源傳說和動物圖案等,贊普還給碗起了名字。這則故事說明吐蕃在發揮本民族獨特風格的基礎上吸收了唐人制陶技藝,積極完善和發展了本土的制陶技藝。隨著佛教的普及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吐蕃王朝大興土木,為建造寺院和宮殿燒制了許多磚瓦等建筑材料。值得一提的是現存于桑耶寺的磚有紅、綠、黑三種顏色,其中綠磚施釉,形制有長方形、方形、梯形、子母口形等四種,釉薄而富光亮,瓦的內外飾有非常精致的圖案和古藏文,施釉技術的出現將當時的制陶技術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顯示出西藏制陶技術達到了較高的工藝水平。
吐蕃王朝滅亡以后,西藏經歷了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這一時期各地的陶器品種不斷增多,出現了許多圖案及紋飾的內容與佛教密切相關的陶制宗教用具。據記載公元十一世紀修建夏魯寺時,屋頂的漢式琉璃歇山頂和建筑用瓦原料均采自夏魯寺附近的山上,釉藥孔雀石和藍銅礦則取自一個叫尼木彭崗的地方。當時瓦當的圖案有花、獅、塔、寶石等5種。此外,還燒制了高13層陶塔和施釉陶塑獅像等,可見,制陶工藝在這一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公元17至18世紀在墨竹工卡的塔巴制陶點也生產過各種工藝杰出的施釉陶器,成為全西藏制陶技術的典范。塔巴村曾出現過“雜堪欽莫”,是原西藏地方政府認定的制陶行業里的制陶大師,據說由“雜堪欽莫”施上等釉的陶器只有上等喇嘛及貴族才有權享用[8]。在1922年,塔巴制陶點就為修建羅布林卡金色頗章燒制了建筑用瓦。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解放前的舊西藏,塔巴村的陶匠們為西藏的地方政府、拉薩的大活佛、大貴族,以及各大寺院燒制過陶器,因而塔巴村在西藏享有類似于歷史上官窯燒造場的地位。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的很長一段時期,西藏的陶器藝術未能出現質的變化,相反,隨著交通的發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到,內地的瓷器、鐵制、玻璃、塑制生活用品源源不斷地進入西藏的市場,沖擊和制約了西藏陶器藝術的發展。根據上世紀90年代,西藏大學的其美多吉教授實地調查證實,當時西藏土陶器生產點有50余處,分布在拉薩的墨竹工卡縣、林周縣、尼木縣;日喀則的江孜縣、仁布縣、日喀則市、昂仁縣、拉孜縣、南木林縣、謝通門縣、薩迦縣、定結縣、朗縣;山南的曲松縣、瓊結縣、桑日縣、加查縣、隆子縣、錯那縣;昌都的察雅縣、洛隆縣、芒康縣、八宿縣、邊壩縣、貢覺縣;以及阿里的普蘭縣[9-10]。制陶點主要分布在西藏的農區和半農半牧地區,制陶人的生活主要以農耕為主,他們利用春耕前或秋收后的農閑時間燒制陶器來賺取副業的收入,而以制陶為生的職業制陶人非常稀少,陶器以露天燒制為主,包括平地露天窯、平臺露天窯、豎穴窯、墻角窯等。雖然陶器生產點數量較多,各地制陶技藝層次不齊,部分燒制點的技術和工藝仍停留在比較落后的水平[5,11]。
縱觀西藏制陶業的發展歷程,新石器時代的西藏陶器在其發展過程中達到令人矚目的高度,在工藝上與其他同期文化相比毫不遜色,之后的幾個歷史時期在陶器的裝飾上不斷地豐富,在制陶技術上不斷地完善和提升。令人惋惜的是西藏陶器生產仍然是品種有限,工藝也處在手工狀態,制陶業未能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鏈。究其原因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是吐蕃時期佛教的傳入,也把印度的種姓等級制度帶到了藏區的社會,使得西藏手工業中的陶器和鐵器等行業被列為社會最低階層受到歧視,制陶技術只能在小范圍中世代沿襲,僅僅停留在制陶人除了農業之外生計補貼的渠道之一。隨著時代的變遷,制陶村里年輕人愿意繼承祖輩制陶技藝的越來越少,嚴重制約了西藏制陶業向技術型、專業化產業發展,遠未形成獨立的制陶手工業。其二是雖然上乘的陶瓦在部分寺廟和宮殿的修建中得到運用,但是陶器在制作上的粗糙和工藝上簡陋使其未能成為上流社會和文人墨客所珍愛的工藝品,使得陶器制作僅僅停留在滿足生活中的基本需求,缺少強有力的刺激因素。其三是藏陶技藝在歷史的長河中未能得到有效的傳承和發展,如公元7世紀出現的釉陶燒制工藝到了20世紀末瀕臨失傳的窘境。最后,日新月異、價廉物美的現代化生活用品沖擊著這一高成本低收益的手工陶器的生產和創新,使傳統手工制陶業已失去其原有的優勢。
基于藏陶發展面臨人才短缺、工藝退化、經濟效益不高等瓶頸,政府加大了保護與發展這一傳統手工技藝的力度,墨竹工卡縣塔巴村燒陶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謝通門縣“牛”村陶器制作技藝、扎囊縣陶器制作技藝、曲松縣陶器制作技藝和西藏紅陶燒制技藝已列入西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一些民間力量也參與到藏陶工藝的保護、傳承和發展中,個別制陶村也嘗試著通過既保留藏民族傳統文化特點,又融入現代審美元素的新理念在開發貼近時代發展的新產品,以滿足現代人的更高生活需求和時尚追求。相信西藏這一古老制陶工藝在新的時期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