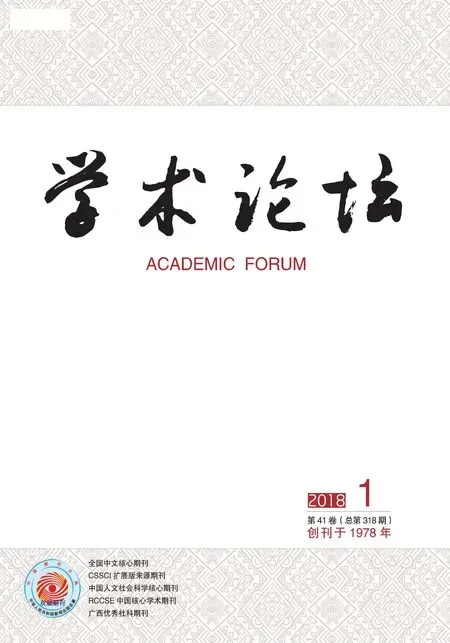里夫希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旅行
傅其林
里夫希茨(俄文Михаил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Лифшиц,簡稱 Мих.Лифшиц,英文譯為 Mikhail Lifshitz或Mikhail Lifshits,1905-1983)是蘇聯時期和盧卡奇齊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美學文獻進行過系統的整理,也對馬克思主義藝術哲學與美學進行了深入的建構,在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獨樹一幟。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本土化旅行的過程主要呈現出三種形象:作為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編撰者的形象,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身份,作為當代俄羅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復興者的角色。他對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整理和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對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系統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到文獻整理缺失、研究片面、文藝觀念偏執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富有創造活力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合法性建構。
一、作為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編撰者的形象
里夫希茨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主要是以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編輯摘錄者的身份到來的。里夫希茨從20世紀20年代起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與文藝理論,在1933年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文獻著作,為世界馬克思主義美學與文藝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不僅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而且對中國本土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論文藝的經典著述的編輯整理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里夫希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在中國本土化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第一,漢語翻譯。中國學者較早對里夫希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的新舊版本進行翻譯,把他的俄文文獻翻譯成漢語的本土化文獻。由蘇聯共產主義學院(又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文藝研究所編,里夫希茨和希萊爾具體負責,盧那察爾斯基審定的《科學的藝術論》,1940年10月由上海讀書出版社出版。《科學的藝術論》不是從俄文原文翻譯過來的,而是樓適夷從日文版本轉譯過來的,這是舊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20多年之后,米海依爾·里夫希茨編俄文兩卷本《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由蘇聯國家藝術出版社1957年出版,3年后被譯成中文版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于1960-1965年出版,這被稱為新版本,著名的俄語文藝理論翻譯家曹葆華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翻譯對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文,有的由他自己翻譯,形成具有權威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文獻版本。
第二,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編輯整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論文藝的工作。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較早編輯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文獻,瞿秋白和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做了開創性工作。瞿秋白1932年根據蘇聯公漠學院的《文學遺產》第一、二期的材料,編譯了《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主要輯錄恩格斯、普列漢諾夫、拉法格論文藝的部分文獻。1936年魯迅把此文集與瞿秋白翻譯的其他馬克思主義文章以《海上述林》出版,此文獻被認為“三十年代中國最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對于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包括馬恩的文藝理論觀點,發揮過巨大作用”[1]。但是這與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實際文獻比較起來,仍然還有諸多缺失。1939年歐陽凡海編譯了《馬恩科學的文學論》,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四封論文藝書信,但顯然在內容上還相當有限,沒有很好地反映馬克思恩格斯豐富的文藝思想。
而1940年里夫希茨等人的《科學的藝術論》漢語翻譯出版,實質是1933年他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是他多年研究和輯錄的結晶,對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整理具有標志性的意義。正如劉慶福所評價的:“該書分為三部:第一部社會生活中藝術的地位,第二部關于文學的遺產,第三部觀念形態的藝術。三部共輯錄馬恩的文藝論述四十多個片斷,他們的幾封著名的文藝書信是全文收入的。原書1933年出版,是蘇聯也是世界上較早摘錄輯集的一部馬恩的藝術論,它反映了馬克思恩格斯文藝觀的基本面貌。這本書在我國翻譯出版,第一次為我國讀者提供了較為系統的馬恩的文藝論述,標志著馬恩的文藝論著在我國的翻譯出版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有了里夫希茨的理論框架和文獻基礎,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的文獻開始走向系統化和科學性的路徑,為系統總結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文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40年,由曹葆華、蘭天譯,周揚編校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藝術》,其中有馬恩著名的5封文藝書信,列寧論托爾斯泰的4篇文章,此外還有蘇聯學者寫的馬列藝術研究論文2篇。1944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周揚編輯并經過毛澤東審閱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普列漢諾夫、高爾基和魯迅的有關文藝的論述,按照內容分為五輯:(1)意識形態的文藝;(2)文藝的特質;(3)文藝與階級;(4)無產階級文藝;(5)作家,批評家。另外,還有一篇周揚寫的闡發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序言》,并附錄了4篇文章。劉慶福認為,這本書把馬恩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分專題匯編,易于顯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和內在聯系。“這本書可以看作是全國解放前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論著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文藝論著在中國的譯翻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觀點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的集大成的精粹表現。”[3]周揚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待經典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態度、方法、框架與理念,突出了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文獻整理特色,突出了中國具體問題,突出了階級革命的特點。但是其把文學觀念和文獻分類相結合的框架以及某些文學觀念,都延續著里夫希茨的文獻整理范式。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獻整理進一步強化了里夫希茨的范式,主要翻譯了模仿里夫希茨范式的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文獻整理情況,譬如法國讓·弗萊維勒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中文翻譯1951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這些文獻著作的出版與翻譯顯示了里夫希茨在西方世界的重要影響力,強化了中國學界對里夫希茨的認同。
在里夫希茨在中國旅行的過程中,1940年版本的《科學的藝術論》是樓適夷從日文版本中轉譯的,無疑隔著一層,這是舊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的局限性,而且舊版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獻視野與美學觀點的總結還不夠全面深入。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重視從俄文原本來引入里夫希茨的文獻整理,深化其關于馬克思主義文獻整理的本土化進程,以曹葆華等學者翻譯里夫希茨1957年的新版《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為標志。里夫希茨的新版《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是在舊版基礎上的進一步完善,從舊版三個部分變成新版的四個部分即“藝術創作的一般問題”“唯物主義的文化史觀”“階級社會中的藝術”“藝術與共產主義”。新版出版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根據俄文本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進行專題整理,有曹葆華、程代熙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1958年),曹葆華翻譯的 《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與共產主義》(1959年)。陸梅林、程代熙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及時地介紹里夫希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譬如程代熙在1959年的專門研究新版本的文章中比較新版與舊版的關系與差異,強調了新版的創新之處,認為里夫希茨的新版本雖然主要還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的材料編輯的,但也從《全集》第二版的前幾卷中摘錄了一些新的材料,同時新版在編輯方法方面有很多改進,“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從一般問題的論述到個別問題的分析說明(從一般到個別),即從美學理論的一般問題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文學史及藝術史的個別問題的論述。這樣的編輯方法就使得全書內容堅實豐富、結構嚴密、層次分明,而且還具有科學理論著作的十分嚴格的邏輯力量。可以這樣說,《論藝術》的新版本是目前唯一比較完善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美學理論問題的一部專著”[4]。
1960年開始的新版的翻譯與進一步本土化工作,促進了中國本土更為全面、更為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文獻整理工作。之后中國本土的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獻整理有:林煥平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廣西師范學院出版社,1978年),全國十九所高等院校中文系《馬恩列斯文藝論著選講》編寫組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文藝論著選講》(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1981年),陸梅林輯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程代熙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四卷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1985年),劉慶福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文藝論著選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1986年)等。可以說,隨著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跨文化能力的提升與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意識與話語系統的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文獻整理取得獨特的本土地位,在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文獻整理中具有獨特的意義,尤其突出中國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文獻的分量與意義。
第三,里夫希茨的文獻資料深入到中國學者的文藝美學的研究過程之中。我們不難看出,里夫希茨1933年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所總結的文藝思想即“社會生活中藝術的地位”“關于文學的遺產”以及“觀念形態的藝術”,與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尤其是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藝反映論觀念有著內在的類似,后者不僅強調社會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而且強調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里夫希茨的“觀念形態的藝術”與毛澤東的“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相契合。里夫希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的中文翻譯被中國文藝研究者廣泛地引用,1962年的文章《中國傳統園林藝術創作方法的探討》把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中國傳統園林美學結合起來,認為中國傳統優秀的園林藝術造景,既然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就必然包涵了革命的浪漫主義,因而在反映自然風景的同時,也就必然會把概括了人民對自然的意愿和理想的“詩情畫意”反映在園林的造景之中。馬克思說:“一件藝術品——任何其他的產品也是如此——創造一個了解藝術而且能夠欣賞美的公眾。”[5]該引述出自于里夫希茨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的中文版。
二、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身份
里夫希茨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編撰者,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與文藝理論家,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身份主要體現在里夫希茨的學術研究在中國本土得到接受。從時間上看,里夫希茨在1950年代的中國形象主要是修正主義者,他的著作《談維德馬爾的“日記片段”》研究19世紀的文藝理論家維德馬爾的文藝思想,被丹青翻譯成中文,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被歸屬為“外國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批判資料”,所以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家這種中國本土身份的建構主要在1980年代形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里夫希茨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版本。翻譯是本土化的重要途徑,里夫希茨的代表專著《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這是由中國著名的俄羅斯文學與文藝理論研究專家吳元邁等人組織翻譯的,1983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俄文版1979年出版。此書的中文版本得到中國學者廣泛引述,據初步統計有72次。二是對里夫希茨的美學思想進行介紹與研究,確立了其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者的權威地位。
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陸梅林在1982年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崛起》中深入研究1844年的巴黎手稿的美學思想,其中涉及到人與動物的審美差異問題,借鑒了里夫希茨關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研究成果,認為18世紀德國啟蒙學家萊瑪魯斯(Reimarus)在《論動物的藝術本能》一書中,也說人的藝術創造性的活動和動物的藝術本能并無二致,至多是量的差別。據里夫希茨說,馬克思在青年時代曾鉆研過他的這部著作[6]。根據里夫希茨的著作《卡爾·馬克思的藝術哲學》,我們可以發現陸梅林的引述是符合事實的,但是里夫希茨所涉及的書名不是《論動物的藝術本能》,而是《關于動物本能沖動的一般性思考》(Allgemeine Betrachtungen uber die Trieben der Thiere)[7]。
程代熙真正把里夫希茨提升到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地位,主要集中于《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一書的解讀上。通過對里夫希茨的文本細讀,并結合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現狀,程代熙高度肯定了里夫希茨文藝理論的本土化意義。他的文章深入地論述了里夫希茨的兩個主要思想:
第一,對庸俗社會學的批判,通過詳細梳理弗里契的《藝術社會學》的庸俗社會學思想,指出里夫希茨對庸俗社會學模式的三點批判。一是批判以階級觀點作為一切文藝現象的極端化思想,因而否定了文學傳統的積極意義,正如里夫希茨所言:“庸俗社會學具有自己的價值體系,這種體系是借助于簡單地否定傳統而形成起來的。全世界的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的最有價值的成分,在這里遭到了嚴重損害。”[8]二是批判了庸俗社會學對資產階級文化的極端性批判,根據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生產對詩歌和藝術的敵視態度就簡單地得出,資本主義生產只能生產落后的、墮落的文藝,從而完全否定了資本主義文化傳統的積極意義。三是批判了庸俗社會學關于藝術生產與社會生產的簡單認識,即庸俗社會學認為藝術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成正比例。程代熙肯定了里夫希茨的解釋,面對正反兩種論題,正題:技術的進步,即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的經濟繁榮導致藝術的繁榮,因為藝術的發展取決于經濟的發展;反題:技術的進步導致藝術的覆滅,因為合理化、標準化、批量化等諸如此類的生產條件,與個性化很強的藝術生產不相調和,里夫希茨作出了辯證的思考,因為在實際生活中,經濟的發展可以促進藝術的繁榮,也可以使某些藝術趨于沒落,這實質上是遵循馬克思關于藝術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平衡的思想。里夫希茨事實上在1933年的著作《馬克思的藝術哲學》中也作了詳細的論述,早在1927年的文章《關于馬克思的美學觀點問題》中,里夫希茨認為:“一般來說,藝術的繁榮不直接取決于經濟發展的數量水平,在正反兩種意義上都是如此。藝術的繁榮只能從人們借以進行生產的特殊條件、從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質量、從生產方式中孕育出來。”[9]程代熙認為里夫希茨關于庸俗社會學批判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仍然具有意義,并結合中國文藝實際加以具體闡釋,批評了中國學界某些人主張通過現代派來反映中國經濟現實的觀點,認為這種現代主義觀點包含著內在的矛盾,雖然肯定了革新的意義,但實質上也是步庸俗社會學的后塵。
第二,程代熙較為深入地分析了里夫希茨的《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論現代主義》等著述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西方現代主義的批判。他認為,里夫希茨明確地指出了現代主義文藝是資本主義衰退時期資本主義文藝的主要流派,它誠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物,但又不是其簡單產物,除了經濟原因之外還有階級和社會心理的原因。現代派藝術家大多出生于小資產階級,有的是下層的貧民或貧困學生、小職員,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受到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像生活在一個被無情的鐵箍緊緊箍起來的封閉世界里。他們苦悶、失望,但又找不到出路,這就形成了他們身上特有的一種情緒,否定一切,蔑視一切,打倒一切。如果他們能夠投入人民群眾的戰斗,那么就可以糾正他們的情緒,但是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反抗不能越出資產階級的范疇,因為無政府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因而無法動搖資產階級的根基。不論是20世紀初的達達主義,抑或1960年代以來法國的新浪潮,都無法改變這種狀況。程代熙認為,藝術是一種理性活動,藝術家通過審美的方式來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世界,并且激勵他們為理想起來改變周圍的現實,然而現代派不是這樣,而是聚集于藝術技巧的革新與視覺的革新。里夫希茨結合現代派藝術的實際進行了批判分析,指出了其否定造型,否定反映現實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最基本的原則,“現代主義完全喪失了描繪客觀現實生活的特征,而成了里夫希茨所指出的‘表達藝術家觀點的符號系統’。所以現代派文藝著力宣揚的是藝術家的主觀世界,即那個‘自我’的世界”[10]。程代熙還結合中國本土學者關于現代派的認識來確證里夫希茨的觀點,主要涉及到林小平的文章 《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繪畫》所揭示的“恐懼”主題,古元的文章介紹中國學者邀請華裔意大利籍的抽象派畫家訪華所揭示的否定社會生活的特征。程代熙還結合現代派文學、戲劇、詩歌和音樂來說明其否定反映社會的問題,使詞語失去表達思想的意義,失去所指的具體性,后現代主義小說只是能指語言的符號,語言的隨意組合打亂了傳統小說的情節的連續性。所以程代熙認為庸俗社會學和現代主義在里夫希茨那里獲得了類似性:“庸俗社會學割斷歷史,否定傳統,結果走向了虛無主義;西方現代主義也割斷了文學發展的歷史,否定、排斥現實主義傳統,結果走上了‘反藝術’一途,庸俗社會學和現代主義從不同的方向,即一個從左邊,一個從右邊,它們繞了一個圓圈,最后還是在破壞藝術規律這一點上合流在一起了,這就是兩者的必然結局。”[11]由此可以看到,程代熙不僅對里夫希茨的文學觀點進行闡述,而且結合中國學者和具體的藝術現象進行佐證,維護了其現實主義文藝觀點,高度認同其對庸俗社會學和現代主義藝術的批判,這在中國本土建立起里夫希茨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在凌繼堯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確認。作為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美學有著深入研究和翻譯的學者,凌繼堯在1980年代也關注里夫希茨的馬克思主義美學觀,他認為里夫希茨是馬克思的美學觀的最早研究者。凌繼堯認為里夫希茨是蘇聯著名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享有世界性聲譽。他關注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時期:一是20世紀30年代對庸俗社會學的批判以及里夫希茨與盧卡奇的交往,肯定了兩者美學觀點的相同點,注重列寧的反映論,有共同的美學觀點:“后來,當盧卡契把他離開蘇聯、在匈牙利寫成的《美學》寄給里夫希茨時,他稱這本書闡述了他們于30年代共同研究的理論觀點。”[12]二是介紹1950年代里夫希茨對社會思想、哲學和藝術的古典傳統的研究,關注他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卡岡系統論符號學的尖銳批判。借助于對蘇聯的本土交流與對里夫希茨妻子的訪問,凌繼堯第一次給中國學界較為全面呈現了里夫希茨這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形象。但是其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本土化的學術深度還不夠,屬于介紹性、描述性的,正如文章副標題所示“記米·亞·里夫希茨”,文章也說“本文分兩個階段描述了其一生的重要學術活動和成果”[13]。
不過,我們也注意到,里夫希茨在中國本土的形象也有負面的影響,一些中國學者對其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進行批判。劉夢溪在1980年的文章中批判了里夫希茨在《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對普列漢諾夫的不公正評判,認為“普列漢諾夫的努力,遭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對馬克思主義持教條主義態度的人的非議。直到一九五七年,蘇聯的文藝理論家米海伊爾·里夫希茨在為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撰寫序言時,還指摘普列漢諾夫不重視馬克思恩格斯的美學遺產,并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聯系起來。這對普列漢諾夫是不公正的。追溯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還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了教條的結果”[14]。胡義成在1987年的文章中梳理了蘇聯與東歐的審美控制論,主要有卡岡的審美系統理論、斯托洛維奇關于審美價值的系統理論、捷克斯洛伐克的伊·列維在《信息論和文學過程》中提出的宏觀審美控制論模型,這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特征的文藝理論與美學在當代蘇俄和東歐帶來了生機與活力,也贏得了廣泛的影響,而這就超越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使里夫希茨的理論面臨危機。胡義成明確認同卡岡等人提出的審美控制論,而對里夫希茨的文藝觀加以批判,視之為教條主義模式,認為里夫希茨以大量的著述在美學和文藝理論等領域,為捍衛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出了不少貢獻,他的代表作《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曾使整整一代年輕人受益。但是,如同當年許多老一代理論工作者一樣,里夫希茨在自己的文論中把階級分析絕對化,甚至拒斥在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中使用階級分析以外的有關新方法。里夫希茨把馬克思主義同符號學、價值說等現代科學處于絕對對立之中,所以卡岡也與之針鋒相對。胡義成指出,卡岡“曾針對里夫希茨的教條主義,辛辣地寫道:‘靈學’的方法被里夫希茨置入美學禁用的方法序列中,只不過是為了‘敗壞’符號學和價值說方法的‘名聲’,‘要是在二十年前左右,這張清單中顯然還會列入控制論、遺傳學,社會心理學……’。正是在指責里夫希茨的這篇論文中,卡岡明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于藝術活動作為受控信息系統的研究結論,并在科學水平上贏得了群眾。自此以后,里夫希茨的看法,基本上成為歷史陳跡”[15]。對里夫希茨的批判至今仍然在延續,孫文憲在2016年的文章《試析里夫希茨<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分類學研究里夫希茨編輯整理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論文學的言論話語特征,一方面指出里夫希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貢獻,“里夫希茨試圖通過由大量的客觀材料構成的文本證明,馬克思廣泛地涉獵和思考過各種各樣的文學藝術問題,只要掌握并認真研讀這個文本,不難發現他對文學藝術問題的闡述已形成了系統的理論格局。而且,為了強化人們的認知,里夫希茨還撰寫了一部討論馬克思藝術哲學的專著,對他收集、梳理的重要材料作了幾乎是一一對應的解讀。他顯然是想通過自己的闡釋,更清晰地勾勒出馬克思文學研究的理論架構。由里夫希茨開創的整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文學藝術和美學言論的工作,為研究馬克思的文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提供了具有實證意義的文本基礎,因此受到各國學者的普遍關注”①參見孫文憲:《試析里夫希茨〈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存在的問題》,33屆全國馬列文藝論著研究會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當代性學術會議論文集,2016。。另一方面認為,里夫希茨立足于現代文學理論知識框架來整理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文獻,帶來了嚴重缺失,“如此操作的分類梳理確實凸顯了馬克思的文學言論不乏理論的系統性,可是對馬克思文學思想的認知來說,里夫希茨的梳理卻是用現代文學理論的知識遮蔽了馬克思在文學問題上的獨到見解,模糊了馬克思主義批評不同于現代文學理論的異質性”,“至于馬克思的文學思想而不是研究方法與一般的文學理論究竟有什么區別,似乎并不在里夫希茨梳理工作預設的目標之內,他顯然還缺乏尋找馬克思批評話語特質的自覺意識。若從這個角度看,作為研究馬克思文學思想的基礎文本,《論藝術》還有待完善,更何況用現代文學理論的知識來分類梳理馬克思的言論,實際上只能誤導對馬克思批評話語的讀解”①。孫文憲的研究在知識考古學的框架下清理里夫希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有較為深刻的啟示意義,是中國學者對里夫希茨文藝思想的創造性解讀,但是也忽視了里夫希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突出價值,尤其是沒有看到1933年的《馬克思的藝術哲學》和1957年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之間的重大區別,這是里夫希茨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形象在中國本土化建構中的問題。
三、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復興的人物
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馬克思主義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制度性功能在蘇聯東歐國家被瓦解,民眾普遍對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形態深惡痛絕,對之進行了情緒化拒絕。馬克思主義美學與文藝理論也因此急劇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齊澤克、朗西埃、巴丟等人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但是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俄羅斯開始復興,其中里夫希茨占據重要地位,中國學界也開始重新認識里夫希茨,重視里夫希茨的文獻整理與研究,更為全面的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復興的人物定位開始在中國本土建構。
陳世雄在2016年的文章《里夫希茨的回歸》中通過與里夫希茨的學生、合作者和繼承人阿爾斯諾夫教授的談訪交流,獲得有關當代俄羅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現狀,尤其涉及到里夫希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復興。他認為,里夫希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有重要影響:“米哈伊爾﹒里夫希茨的名字對中國人來說并不陌生,他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等著作被譯成中文,并產生過廣泛影響。”[16]陳世雄的文章主要介紹了里夫希茨的主要成就及其在當代俄羅斯的回歸,從而確證近年來俄羅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復興。里夫希茨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美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批判庸俗社會學,展開盧卡奇-布萊希特論爭,在六七十年代批判現代主義,確立了文藝反映論的現實主義美學體系。陳世雄的文章探討了里夫希茨的主要著述,深化了中國學者對里夫希茨的認識——以往主要集中于《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等著作,這是相對有限的;而阿爾斯諾夫主編的俄羅斯政治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16部里夫希茨著作,其中有里夫希茨與艾瓦爾德·伊里因科夫從1951年開始圍繞20世紀最著名的攝影家貝爾松的作品的對話《與艾瓦爾德·伊里因科夫的對話》,包含著攝影文藝美學思想演變的觀點,有討論作為客觀現實中的理想或者范例的經典思想的著作《什么是經典》,有對自由主義和文化現象的辛辣批判文集《自由主義與民主》,還有對現代主義進行批判的評論文集《為什么我不是現代主義者?》這些介紹無疑改變了中國本土學者對里夫希茨的相對簡單的認識,一種較為真實的豐富復雜的里夫希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開始在中國本土形成。陳世雄的文章還關注里夫希茨和盧卡奇的文藝思想的關系,雖然前者比后者年輕20歲,但是結成最好的朋友,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知己和戰友,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和里夫希茨的著作在書店并排出售,所以文章認為,“里夫希茨和盧卡契同為蘇聯馬克思主義美學與文藝學方面的權威,系統地研究、宣傳、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論是他們共同的事業”[17]。這種評價是較為客觀的。但是也說明里夫希茨與盧卡奇文藝理論在中國的研究的不對稱狀況,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本土的影響要深入復雜得多。
里夫希茨與盧卡奇文藝理論的關系在傅其林和出生于保加利亞的英國倫敦大學提哈諾夫(Galin Tihanov)教授的對話《東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場對話》(《外國文學研究》2016年第6期)中受到關注。提哈諾夫長期研究蘇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尤其重視里夫希茨和盧卡奇、巴赫金關系的研究,他在2002年出版著作 《主人與奴隸:盧卡奇、巴赫金及其時代觀念》,2011年與多布倫科(Evgeny Dobrenko)編輯了《蘇聯及其之后的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史》。提哈諾夫在對話中認為,在當代解體之后的俄羅斯學界出現了里夫希茨的復興,里夫希茨和盧卡奇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好朋友,都屬于蘇聯最著名的《文學批評》雜志的核心撰稿人,共同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與文學理論,但是兩者有區別,“里夫希茨后來演變為一個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與盧卡奇相比較,他更固執,更教條。盧卡奇更為精進,能夠接受創新,盡管他堅定地反對現代主義和先鋒派”[18]。所以盧卡奇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生密切關聯,顯示其理論的廣泛影響力。
四、里夫希茨文論在中國旅行的問題
里夫希茨文論在中國80多年的旅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系統建構,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化了中國學者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獻的系統整理與深入研究,中國現代一批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樓適夷、曹葆華、周揚、陸梅林、程代熙、吳元邁等參與其中,不斷推進本土化進程。但是在本土旅行過程中,也出現一些需要進一步反思和推進的本土化問題。
第一,在里夫希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文獻整理本土化過程中問題還是存在的。中國學者對之早已有所認識,這主要體現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跨文化能力的局限性,樓適夷翻譯《科學的藝術論》是從日文轉譯的,而曹葆華等翻譯的新版完全是里夫希茨俄文翻譯與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錄的,這與原本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相比還是有一些距離或歧義。康之鳴在1978年就從拉丁語翻譯問題仔細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堅持魯迅的翻譯原則——“待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認為“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都精通許多種語言,并且使用許多種語言著書立說。恩格斯在《不應該這樣翻譯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俄文版230-231頁)一文中寫道:‘要翻譯這樣的書(指《資本論》),很好地了解德國的規范語是不夠的。馬克思自由地運用日常生活的言詞和內地方言的成語,他創造新詞,他從一切科學領域借取自己的例證材料,而從整整十二種語言的著作中做出自己的引證。’恩格斯自己也是這樣。他在寫給威·格勒伯的一封信中,在一段192個詞的文字中使用了德、拉、英、意、西、葡、法、荷等八種語言。”[19]因而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必須具備廣泛而卓越的跨文化譯介能力,而曹葆華對里夫希茨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的翻譯雖然有較之里夫希茨更為優越之處,但是與里夫希茨一樣都存在拉丁語文種識別、歇后語翻譯等問題,無疑成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本土化的一個問題。
第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接受里夫希茨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過程中,存在著簡單片面的情況。沒有全面地、辯證地、歷史地研究里夫希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成就,沒有深入吸收里夫希茨文論的積極養分,豐富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美學建設。一些人以其修正主義、教條主義的典型代表而不作具體分析加以簡單的拒絕。通過梳理里夫希茨在中國旅行的文本痕跡,我們不難看出,在翻譯文獻方面和引述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到他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的新舊版本即1933版本和1957年版本和著作《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1979第二版,匯集1927-1967年之間的部分著述,1972年第一次完成),還翻譯一篇里夫希茨給《蘇聯百科全書》撰寫的《論現代主義》的詞條,發表在《外國文學報道》1983年第3期上。程代熙探討里夫希茨的庸俗社會學和現代主義文藝思想批判時所關注他1927年寫的論文《關于論馬克思的美學觀的問題》和1960年的德文版《卡爾·馬克思與美學》序言,實質上包括在《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之中。就是針對此書,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還沒有展開深入具體研究,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現象學、符號學的復雜糾結,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現代性的問題(《卡爾·馬克思與當代文化》,1958年;《藝術與當代世界》,1978年),馬克思主義審美教育問題(《馬克思與審美教育》)都無人問津。因此,里夫希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在中國的本土化研究是很有限的,缺乏對里夫希茨著述全面研究與系統翻譯和整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里夫希茨1933年出版的代表著作 《藝術與哲學問題》(《Вопросыискусства и философии》),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1938年被拉爾夫·B·溫(Ralph B Winn)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名為《卡爾·馬克思的藝術哲學》(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Karl Marx),1976年根據1973年的重印版再次修訂出版的時候,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伊格爾頓專門為此寫了序言,認為里夫希茨并不是搜集馬克思論藝術的片段,而是把馬克思的“審美判斷視為其普遍理論體系的元素”,因而是根據馬克思“總體思想的有機聯系來梳理其著作中一些關鍵的美學主題的”[20]。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此書在民主德國(1960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1961年)、匈牙利(1966年)等社會主義國家被翻譯[21]。里夫希茨在此書中重點建構了馬克思的藝術哲學思想,從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文本到成熟時期《資本論》的分析建構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美學,主要分析馬克思對浪漫主義美學的敵視,對出版自由論述的辨析,受黑格爾美學影響與唯物主義轉型、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感性論美學、對藝術不平衡關系的深入分析、對藝術與商品的復雜關系的理解,對個體性、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學建構。該書分析嚴謹,不乏重要的文獻發現與精彩的觀點,對席勒、黑格爾、馬克思的理論走向具體實踐的分析很深刻,對藝術不平衡的理解可以與捷克共和國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柯西克的《具體辯證法》相媲美。書中談到,早年的馬克思非常重視形式問題。雖然《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也包含了《卡爾·馬克思的藝術哲學》,但是沒有得到中國學者的深入研究。譬如,里夫希茨認為馬克思1842年從法國作家布羅瑟斯(Charles de Brosses,1709-1777)1760年出版的著作《來自拜物神靈的膜拜或者古代埃及宗教與現在尼西亞宗教的類似性》(Du culte des dieuxfétichesouParallèle de l'ancienne religion de l'Egypte avec la religion actuelle de Nigritie)中,獲得了拜物教概念,“缺乏藝術的人工性是宗教膜拜的前提”[22]。最近十幾年,俄羅斯出版了里夫希茨的不少新文獻,舊版也創新出版,諸如2015年出版的《藝術理論演講稿》(Лекции по теории искусства)《俄羅斯文化文集》(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Проблем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2012年出版的《論黑格爾》(О Гегеле),2011年出版的里夫希茨與盧卡奇 1931-1970年之間的《通信》(Переписка),2004年出版的《什么是經典?》(Чтο тακοе классика?)2003年出版的《與艾瓦爾德·伊里 因 科 夫 的 對 話 》(ДиалогсЭсвальдом Ильенковым)等等。對里夫希茨豐富的著述的深入研究,不但不會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帶來教條主義弊病,而且會激發理論之創新。
第三,關于里夫希茨反現代主義文藝觀念的問題。里夫希茨以現實主義反映論對現代主義進行了長期的尖銳批判,并將其與庸俗社會學文藝理論內在關聯,這本身是值得反思與批判的。對現代主義的拒絕是里夫希茨、盧卡奇等蘇聯與東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理論特點,也是傾向于正統官方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特點。盡管里夫希茨和盧卡奇一樣并不是完全依附于官方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制度,而表現出獨立思考和探索的特征,顯示出其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獨特魅力和卓越貢獻,但是他們對現代主義的嚴重貶損是值得批判的,他們沒有辯證地思考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優劣與復雜性。這本身是一個理論缺失的問題,而更為嚴重的是,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旅行的過程中又被強化和接受,或者是完全肯定地接受,或者作為教條主義被完全拋棄。從已知的文獻來看,中國完全接受里夫希茨的現實主義文論是主流,因而中國本土的里夫希茨解釋也基本認同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也認同現代主義和庸俗社會學文藝思想的一致性。可以說,這種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本土化是適合中國社會主義文藝意識形態的,是適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判斷的,也是適合中國一些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然而,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之后現代派文藝思潮的崛起中,在西方現代派蜂擁而至的潮流中,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派的復雜分析與辯證思考的熱浪中,在東歐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現代派的實驗中,中國學者對里夫希茨的這種簡單化的本土接受無疑失去了內在的合法性。這意味著,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合法性建構必須對現代派乃至后現代主義進行辯證的反思與合理吸納,顯示其仍然可以理解當代新的現實實踐和新的文學現象、新的人的存在狀況的有效性。
總之,里夫希茨促進了中國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整理與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念的建構,其歷史性價值不容抹殺,但同時也遭遇到理論本身的合法性危機,存在著被邊緣化的困境。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過程中,應該充分地吸收里夫希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合理因素,進一步推進本土化,并結合中國傳統和現實實踐與現代性、當代性的問題意識與現實情境,對已有的本土化理論模式加以反思和總結。里夫希茨文論本土化研究顯示出,本土化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性的描述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價值可能性思考的規范性設定,只有建立在描述性和規范性基礎上的本土化,才能更好地確立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本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合法性。
[參考文獻]
[1][2][3]劉慶福.馬克思恩格斯文藝論著在中國翻譯出版情況簡述[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3(2).
[4]程代熙.介紹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J].讀書,1959(22).
[5]孫筱祥.中國傳統園林藝術創作方法的探討[J].園林學報,1962(1).
[6]陸梅林.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崛起——《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讀后[J].文藝研究,1982(5).
[7][22]Mikhail Lifshitz.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Karl Marx.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Ralph B Winn[M].New York:Pluto Press,1976:12,36.
[8][10][11]程代熙.庸俗社會學與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讀里夫希茨的《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J].江淮論壇,1983(5).
[9]里夫希茨.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M].吳元邁,張捷,佟景韓,劉寧,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296.
[12][13]凌繼堯.馬克思的美學觀的最早研究者——記米·亞·里夫希茨[J].南京大學學報,1988(1).
[14]劉夢溪.關于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幾點意見[J].文學評論,1980(1).
[15]胡義成.蘇聯東歐審美控制論研究簡述[J].遼寧大學學報,1987(6).
[16][17]陳世雄.里夫希茨的回歸[N].人民日報,2016-9-18.
[18]Fu Qilin.East-European MarxistLiteraryTheory:A Conversation[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016.num.6.
[19]康之鳴.略談《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一書俄中譯本中拉丁語的翻譯問題[J].山西大學學報,1978(2).
[20]Terry Eagelton.“prefece”,in MikhailLifshitz,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Karl Marx.trans.Ralph B Winn[M]. NewYork:PlutoPress,1976:7.
[21]Мих.Лифшиц.Кармркс Искусство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идеал[M].Москв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