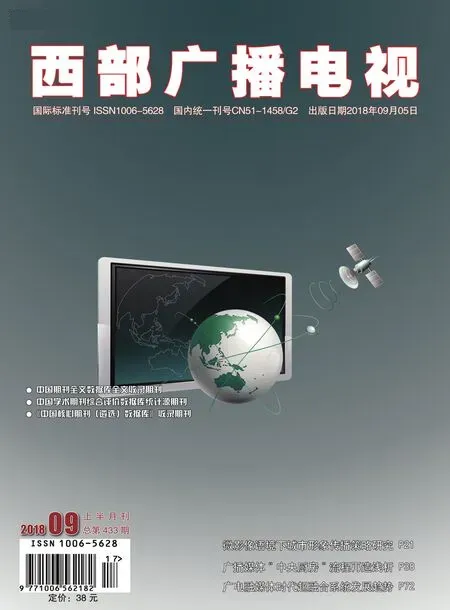電視中的文化記憶
——以電視系列片《紀念趙鶴清先生誕辰150周年》為例
張 惠
(作者單位:昆明廣播電視臺)
1 文化記憶理論的提出
文化記憶理論由德國學者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夫婦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來。文化記憶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是從文化傳承方式的角度來解釋文明的發(fā)展規(guī)律,經過文化精英的外化維護處置而外化為文本和儀式,并對民族主體性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共同塑造著一個民族的整體意識和氣質。總之,“文化記憶”,并不單是個人記憶的集合,是文化層面的集體記憶的表現[1],它不止于關注人們所共同經歷的過去,更關注于那些遙遠的過去,那些人民所共享,應該一起傳承、建構、記憶的文化關懷,目的是在現代建構中為未來提供一個方向。
文化記憶是以文化體系作為記憶的主體的,因為記憶不只停留在語言和文本中,它還存在于各種文化載體當中,如電視就是其中一種。電視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權體現,電視也是讓文化傳承下去的媒介之一。法國學者諾拉將這些能夠傳承文化記憶的載體形象地稱為“記憶的場”。近年來,大眾媒體中不斷涌現對歷史符號的展現,這正是一種典型的文化記憶現象。例如,一些為紀念歷史人物的電視專題系列片就是其中一個代表,對于后世來說,歷史對后世的影響往往被賦予了超越自身價值的意義。而作為電視人的我們,所創(chuàng)作的《紀念趙鶴清先生誕辰150周年》電視系列片,正是出于文化記憶這種價值和文化傳承憂心忡忡的情況下,對滇中名士趙鶴清先生進行了重新建構。
2 趙鶴清的文化記憶“場”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而記憶也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產生。提到趙鶴清先生必然與昆明大觀樓的園林、與民族傳統(tǒng)文化相聯系,趙鶴清記憶與大觀樓記憶,更或者說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記憶緊密聯結在一起,共同凝造了一個記憶的“場”。
《滇中文化論(人物篇)》[2]一書記述了滇中的九位名士,包括高量成、楊升庵、李贄、王錫袞、劉聯聲、高奣映和趙鶴清等。滇中地區(qū)自古以來處于邊疆文化與內地文化交流的中心,這也是自古名人輩出的原因。處于滇池與洱海之間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屬于滇中的一個重要區(qū)域,姚安府就是其中之一。趙鶴清先生就出生在楚雄州姚安縣,或許正因為如此,他的藝術特征才廣泛吸收多元文化的要素,并在跨越清代、民國、新中國的大背景下呈現出了特別的一面。
趙鶴清先生在近代云南藝壇上曾被譽為詩、書、畫、園藝、篆刻五絕的滇中奇才,他的一生留下了許多詩歌、園藝、書法和繪畫等作品。趙鶴清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讓后人記憶,一是他博古通今、學識淵博、多才多藝和開拓創(chuàng)新;二是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有對時代的責任,對民族存亡的愛國精神,作品內容均與中國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三是其書畫作品走出中國,并在國際上獲得大獎,使中國人引以為傲,即使是像秋瑾的女兒王燦芝、女書法家肖嫻也甘心拜于他的門下;四是他的《滇南名勝圖》具有的重要文獻價值和影響,其中包含的177幅描繪云嶺大地山川景物的書畫作品,不僅具有當時的人文地理知識,而且還有極大的審美享受;五是他創(chuàng)作的大觀樓公園,以“道法自然”的境界,直到今天,都對昆明的園藝具有重要影響。趙鶴清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波瀾壯闊,他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心路歷程的寫照,從他的人生軌跡和藝術成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那仁人志士的心,還有他那思念故鄉(xiāng)的山水之情,更有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奮發(fā)圖強的精神,這樣的情,是永遠都不會過時的。
趙鶴清寫的字,造的園,是一種外化了的文本,他的作品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同時又在強烈的中西方融合之下超越了這種屬性,體現出了對傳統(tǒng)文化的宣揚,又不排斥對西方的學習,書寫中國詩詞之美,又留心于民族吶喊的文人精神,可以說趙鶴清介入了整個社會,與其他的文化精英一起共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這些文化精英的文人精神,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tǒng)文化,依舊在熏陶和培育著一代代文人志士和青年才俊,使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得以延續(xù)。
3 電視中的“趙鶴清”影像建構
通過電視的影像建構,過去的歷史符號成為了現在的文化記憶,它表現為以“濃縮”的方式,精簡地呈現出歷史的脈絡和經過。這種在“凝聚性文化結構”上,不斷地對結構進行復制的呈現,已然以民族的文化記憶的濃縮,超越了個體記憶的集合,成為了文化記憶的有效載體。然而,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消費主義話語體系的存在,有很多大師都已漸漸從我們的記憶中消解。遺憾的是,這或許一部分原因與我們所從事的大眾傳媒的話語宣傳有關。
知識分子精英所塑造的歷史文化,是人類傳承文明的源泉,也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正如趙鶴清這樣的,過去時代的文化精英,他們對于人們的意義應該是跨越了時代的,跨越了地域的,他們作為優(yōu)秀文化的創(chuàng)造和繼承者,應該成為一座城市的歷史文化的延續(xù),也是一座城市文化命脈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承載著國家進程中重要的文化信息。他們既是優(yōu)秀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又是當今文化事業(yè)的積極推進者,他們對于后人來說,不僅是一種智慧的源泉,更是一種驕傲的存在,而不是一種即將消解的記憶。在當前社會對趙鶴清記憶缺失之時,影像話語對歷史的“濃縮”呈現,就成為了保護和傳承這份記憶的有效手段。同時,由于趙鶴清在昆明本地的播出,即在文化記憶發(fā)生地的推廣和播出,會帶給特定地域人們親切感和自豪感,從而更有利于昆明歷史文化命脈的傳承和延續(xù),以及城市文化名片的打造,對社會的經濟發(fā)展起著一定的意義。
在影像對文化記憶的建構中,“他者化”建構是很重要的一點。很多影像將文化變成了一種模式,變成了電視人心里的文化,一種虛設的文化象征符號,而并非真實的文化自我,以滿足其他話語體系對于“他者”的想象。作為邊疆的云南省,自古以來由于地域的特點,薈萃了眾多少數民族的文化,由于歷史和大眾認知的原因,對于滇中名士的文化承載或許已被巧妙地避開,而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文化宣傳是遠遠不夠的,這種文化話語權的影響其實是很深遠的,它會影響到一個受眾甚至一個社會對這個區(qū)域的看法。因此,向世界輸出云南的文化,全面而真實地了解云南,應該成為文化記憶新的趨勢。云南自古有著地方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也有著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的交融,將民族文化與歷史文化的特色鮮明結合,發(fā)掘生生不息的多元文化生命力,符合當今全球化、多元化趨勢下建設民族文化大省建設的發(fā)展戰(zhàn)略的目標,也讓云南的文化具有了特異的風采。
4 文化記憶是電視當之無愧的責任
文化記憶是不可磨滅的,正如戴錦華所說:“歷史是一種權力的書寫,而記憶則似乎是個人化的,或者用福柯的說法,是人民在某種意義上對抗歷史的場域,或者說記憶是歷史所不能吞沒、規(guī)范的場域。”[3]與其迎合消費主義,不如主動去保護文化記憶。大眾傳媒作為文化記憶的媒介,它以獨特的方式對文化進行提取,成為傳承民族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并對文化的輸出和傳播實施著控制權。從某種角度講這種控制權一方面意味著話語權力不斷地在影像中層層編輯著過去,以符合當前話語的需要,但最重要的是責任和義務。正如當代傳媒文化研究者尼爾·波茲曼所說的,電視的一般表達方式是娛樂,“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4]。電視作為大眾傳媒,作為當今最具有話語霸權的載體,文化的傳承成為它的責任,當之無愧,它應該將“知識、價值觀和規(guī)范在一代一代的社會成員中傳承下去”[5]。
不論是哪個時代的文化精英,也不論我們處于怎樣的時代,對民族的文化失憶是可怕的。令人扼腕的是,隨著文化精英的相繼遠去,他們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并且現在還有很多的歷史名人文化資源沒有很好地融合到整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流中,影像就是如此。因此,作為大眾傳媒,作為昆明廣播電視臺《盛世典藏》欄目,如何重新拾起我們的文化記憶,科學合理地利用好“趙鶴清”這一文化資源,成為了我們的迫切任務。因此,我們在如何把時代精神賦予到文化記憶,從而不斷煥發(fā)新的活力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我們在通過影像盡可能地去搶救、保護、留存那些即將消解的文化記憶,也試著用影像的藝術美感重構記憶,來讓那些陳舊的記憶散發(fā)出文化的香味。同時,在當前電視泛娛樂化的今天,我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這樣的文化記憶挖掘能夠源遠流長。我們深知一點,那就是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影像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更重要的是做到讓影像真正地為普通民眾服務,使云南優(yōu)秀的文化資源得到共享,讓歷史文化精英與時代同行,讓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得以延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