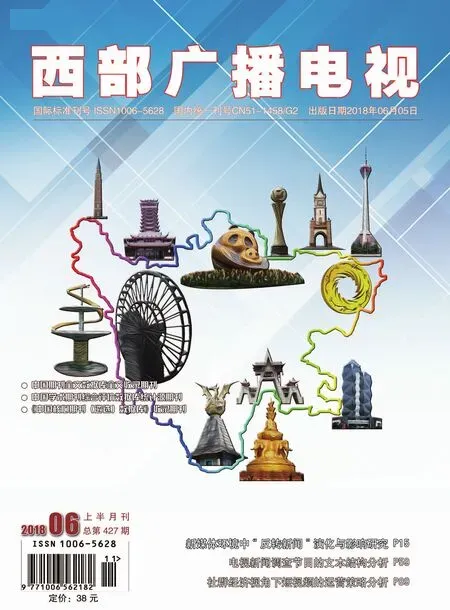紀錄片的故事化探究
陳 嶺
紀錄片是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并對其進行藝術加工與展現的電影或電視藝術形式。一直以來,關于紀錄片是否應該故事化、導演或者攝制組能否參與事件進展一直存在爭議。
當代美國著名電影理論家大衛·波德維爾認為:“紀錄片只在呈現關于這個世界的真實信息,而能夠達此目的的方式,和劇情片只有些許差異。”[1]觀眾對紀錄片的期待是寫實,但是鏡頭和攝制人員在場本身就會影響被拍攝對象的行為,完全真實的影像大概只存在于安保監控之類的鏡頭里。可是,觀看安保視頻資料顯然并不能給予觀眾良好的觀影體驗。
我國早期的紀錄片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考慮故事性,鏡頭拖沓、解說生硬,所以一直以來紀錄片都處于一種幾乎無人問津的境地。到了20世紀末期,紀錄片開始呈現故事化趨勢,才日漸受到觀眾認可,造就了一批廣受歡迎的節目。比如中央電視臺的《生活空間》,其廣告語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上海電視臺的《紀錄片編輯室》,廣告語是“聚焦時代大變革,記錄人生小故事”,從廣告語就可以看出來,“故事”正是他們著力表現的焦點。
那么,紀錄片的故事性作用該如何實現,有沒有什么技巧和準則呢?筆者認為,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 紀錄片要求真實
電視藝術美學研究者高鑫這樣認為:“電視紀錄片的美學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以直接記錄的方式,通過面對真實的呈現表達出對現實的關注和思考,現實既是它的內容,也是他的形式,更是他的工作態度。”[2]這就告訴人們,真實是紀錄片的生命,為了節目效果偽造事實無異于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比如,某紀錄片為了制造震撼場景,攝制組指揮建造一些本不存在的建筑,事件曝光后,觀眾們紛紛表示受到傷害。而該紀錄片制作單位多年來建立的良好形象也受到極大損害。這件事的核心問題就在于攝制組有意混淆“重現場景”和“捏造事實”的界限,用一個不存在的事件欺騙了觀眾。
2 做好前期挖掘工作
沒有準備的戰爭注定是要失敗的,沒有前期大量的走訪、踩點、挖掘和整理工作,做出的節目必定是粗糙的,也是會被觀眾拋棄的。應從前期采集到的大量信息中,選擇最有代表性、最能突出主題的人或事,用它們編織成一個真實而又引人入勝的故事,才能使后續的攝制工作有的放矢,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3 紀錄片“講故事”的策略
3.1 設立主人公
以人物為主角的片子自然就擁有主人公;而展現社會變革或者歷史變遷的片子也需要由人物作為連接體;甚至以動物為主角的片子也需要圍繞著一個主角來展開故事。
日本紀錄片《小鴨子的故事》,講述的就是一只瘦弱的小鴨子“奇比”如何克服種種困難,跟隨鴨媽媽數次遷徙的故事。“奇比”是片子的主角,而訓練孩子的鴨媽媽、比“奇比”強壯聰明的兄弟姐妹們、甚至阻擋鴨子們前進的車流都成為它的配角。通過這只小鴨子發生的故事告訴人們“只要生命在,奇跡就在”的主題。
3.2 設置矛盾和懸念
故事需要跌宕起伏,平鋪直敘是講不好故事的。發現并放大生活中的矛盾和戲劇性是傳統影視作品中常用的手法,也是可以借鑒的手法。還是以《小鴨子的故事》為例,鴨子們的出生地是一個離地23 cm的水池,想要遷徙,首先必須要跳出這個水池。隨著“奇比”的兄弟姐妹們成功上岸,觀眾的心情也由輕松轉為焦急;當看到小鴨子一次次接近成功又一次次跌落,觀眾開始擔心小鴨子會被拋棄;當鴨媽媽最終下定決心轉身離去時,觀眾的情緒急切又緊張,這時,沒有退路的“奇比”放手一搏終于跳出水池,追上了前方的家人,觀眾的情緒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釋放。
3.3 善于發現和捕捉細節
“細節決定成敗”,不論是對人物形象的刻畫,還是對事件的推動,細節都是最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比如筆者創作的人物紀錄專題片《城市排水“小黃人”》中的主人公排水所長黎軍,他雖然是單位的一把手,但常年奮戰在一線。因為要隨時投入排水工作,他常年穿著一雙老式塑料涼鞋,只有去正式場合時才會換上皮鞋,這個細節很好地體現了一位基層干部身先士卒、踏實肯干的形象,讓觀眾記憶深刻。
紀錄片的故事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紀錄片制作人員也應該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在真實的前提下講故事,用自己的所思、所學努力講好故事,激發觀眾的興趣,滿足觀眾求真求美的需求。
[1]大衛·波德維爾.電影藝術:形勢與風格:第8版[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2]高鑫.電視藝術美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