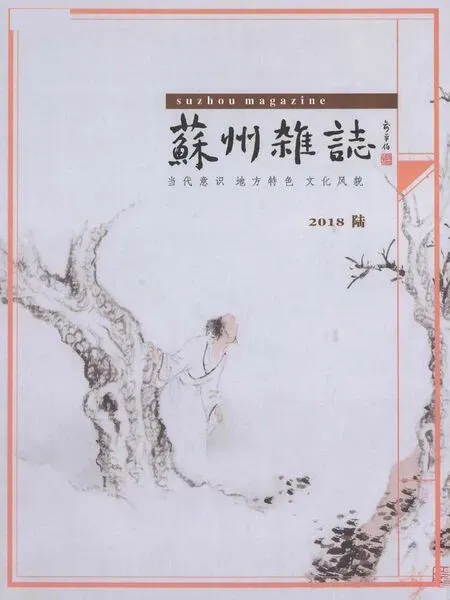訪談余克危(下)
余克危 陳浩 謝曉菁 鄭倩瑤

余克危
陳:您創作了大量中西融合、神韻兼備的油畫及中國畫,您是如何做到在中西兩個畫種之間靈活切換的?這里有著怎樣的個人審美考慮?
余:剛才你們看到的九寨溝寫生,是畫得挺好,從寫生的角度來說,風景對象都搬到我的畫面上來了。我一直是畫油畫的,近年開始畫中國畫。用油畫家的眼光來畫中國畫,用國畫家的心態去畫油畫。中國人的油畫是中國人的感情,而中國畫是傳統文化。我最近畫梅花,看到一篇關于我的報道,說是“余氏梅花”。其實我畫梅花和傳統中國畫家的區別在于,我是用畫油畫的眼光去畫梅花的。我喜歡畫梅花,特別是畫梅林。我畫的梅花沒有花瓣、沒有花心,就是表現一種梅花、梅林的感覺。今年還在杭州超山開了一個梅花展覽,我畫了很多年梅花,但沒豎起來看過,展覽的時候都掛起來以后,觀眾反響很好,我也很滿意。我覺得我追求的就是這些,我認為繪畫就是表現我的感受。傳統的梅花我也看過很多,但我絕對不跟別人畫一樣的,我要按照自己對梅花的感覺去描繪。真正搞藝術搞繪畫,要走自己的路,必須要用自己的語言去作文章,這是我搞創作的體會。
陳:您一直是面對大自然去寫生,跟很多人拿照片寫生或者是憑想象寫生肯定是不同的。您有沒有臨摹過古畫?您是怎樣臨古畫的?
余:寫生和臨摹古畫是不一樣的,我很少臨摹古畫,學生時代臨過《八十七神仙卷》等課堂習作,之后就很少了,但我很喜歡看古畫,就是不太臨摹。我覺得還是要到大自然中去觀察去寫生。近年在書法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我從小畫油畫,覺得自己的字要提高,所以我是認認真真臨摹的。我要學習書法,學透這門藝術。為了寫好字我還描紅或者摹寫碑帖,通過這樣的方法,把字的間架就搭好了,這樣寫了好幾年,我覺得收獲很大。我臨過唐寅《落花詩》,文徴明、董其昌的行書也都臨過。我就想多學一點,提高自己,反而對外界的事情很少關注。
陳:多年來,您由于身體原因,深居簡出,以畫為樂,以畫養生。現在藝術界不少人存在一味追求金錢而不惜放棄藝術本真,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余:我自從因生病切除了胃以后,我覺得自己在藝術上有進步就感到開心、感到滿足。我就想著要做好繪畫這件事情,至于做好以后怎樣,和我沒有關系。我就不斷挖掘自己哪里沒有做好的地方,我認為自己的字寫得不夠好,所以我花了十幾年時間去寫字。等到字寫好了,我就很開心。我就一個目的,我看到今天的自己比昨天好,我就滿意了,就是這樣簡單。人到世界上來走一圈,各人有各人的目的,沒有誰對誰錯,不要去隨意批評別人。我就認為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我很坦蕩,也心安理得。連醫生都驚嘆我能活到今天。因為我沒有負擔,還有兩個優秀的子女。現在很多畫家看重名利,這樣是畫不好畫的。現在這個時代是藝術家最好的時代,我們要花時間在藝術創作上,要是想著拿作品去換名利,這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情。就算我在家里很少跟外界接觸,作品的影響力不大,這其實也沒什么,我只覺得自己有進步我就高興。你們邀請我舉辦這個展覽,讓家鄉人看看我的作品,我覺得很開心。我的這些畫我自己認為是很金貴的,像自己的兒女一樣。
陳:在書法臨寫上下了那么多功夫,又畫國畫這么多年,那再回頭看自己現在的油畫寫生和您早期的油畫寫生有什么差異嗎?

余克危作品
余:這個差異是很大的。我現在已經畫不動油畫寫生了,這個黃金時代對我來說已經過去了。我現在的油畫是想怎么畫就怎么畫,很多作品就叫《無題》。我現在畫的大多是很現代很抽象的作品,但還是在追求美術的理念,畫面色彩的對比,矛盾的統一,點線面的處理等等,我現在追求的是這些東西。我自己感覺這幅畫很完整,表達了我自己的感覺。藝術家要追求美,繪畫要追求美。現在的繪畫是五花八門,有的很丑,有些人就追求丑,我是不懂他們為什么要追求丑,我想他們也有自己的主導思想,但我不理會這些。我對自己的畫,不管怎樣,美是第一位,我現在畫的油畫幾乎全是抽象的,所以這次展覽我想挑一部分寫實的,一部分抽象的。
陳:您作為長輩,怎樣看待當下年輕人的藝術創作?
余: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代,現在搞藝術是最理想的時候,我們那時候就沒有現在這么好的條件。我們年輕的時候很可憐,畫畫要隨著政策的需要,完全是和政治聯系在一起,很大一部分藝術家不懂政治,但仍舊要迎合這個社會、迎合政治,很多時候就是用你的手畫不是自己想表達的東西,當時受到題材繪畫的影響,不能自由發揮,這是很痛苦的。現在這個時代對畫畫的人來說是很自由的,可以隨心所欲地畫。當下這個時代你畫丑的行,別人看不懂的也行,想怎么畫就怎么畫,我覺得這都沒什么錯,因為藝術沒有高低之分,也很難說有好壞之分,搞藝術是人心靈的一種反映,所以我就追求自己想表現的東西,至于好壞留給后人去評價吧!現在我的作品加起來大概有上萬張,其他東西可以丟掉,但是這些作品我都收好了。我總有一天是要離開這個世界的,現在活著已經是很幸運了,我的這些作品就讓后人去研究和評價。如果認為是好的,就讓這些留存下來,如果認為是不好的,就淘汰好了。本來每個人都是鋪路石,每個人都像齊白石、張大千那樣是不可能的。現在有個風氣不好,就是隨意炒作,齊白石、張大千假畫很多,但我們不能把這個當做時代的主流,這是時代進程中難免會遇到的,政府現在把條件都放寬了,每個人都可以高高興興地干自己的事情,可以畫自己想表達的東西,這才是最重要的。我現在也出去看年輕人的作品,有畫得很認真的,也有看不懂在畫什么的,當然也許是我孤陋寡聞看不懂,我也不會去批評人家。我一直是這個態度,我從來不批評年輕人,我覺得年輕人都很了不起,從前我們搞藝術就一條路,想要學素描就是蘇聯的契斯恰科夫體系,現在是條條道路通羅馬,路很廣,機會很多。現在有些人好像社會影響很大,但他們的作品我都看不懂,我只能怪自己學識淺。
時代在不斷發展和變化,總是按照以前提倡的古典主義,人越畫越像,像照相機拍照一樣,大家如果都朝這個方向發展,藝術就像一潭死水。如果有人創造出另外一套方法也挺好的,就像當年印象派那批人,他們沖出了牢籠,而現在我們就欣賞、喜愛他們的作品。
陳:印象派、現代主義等一批西方藝術也受到東方藝術的影響。特別是中國畫中對線條的處理,這種靈活寫意對西方的影響是很大的。余老師您在油畫、國畫和書法之間相互借取,有所突進,也是我們年輕人要學習的地方。怎樣把中西糅和,借取西方的理念為我創作所用,特別是要表達藝術家內心的快樂感、滿足感,這都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要學習的,但是,現在年輕人面對的誘惑太多,生存壓力也很大。
余:這也不能責怪他們。我現在不喜歡賣畫,這是因為現在我有飯吃,日子好過。年輕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不賺錢怎么養家糊口?所以應該理解的。所以說現在年輕藝術家可能為了生存有一段時間要去迎合市場,但在生活穩定以后還是要按照自己藝術的方向去發展,不要沉溺進去。不能把發財致富看得太要緊。正如我八十年代時,孩子大學畢業要去國外深造,沒有經濟條件怎么辦?那時還得賣畫。等到孩子長大自立了,生活條件好了,再賣畫就沒意思了。就是到現在為止,我一張畫都不賣也不現實,有時候一些人情往來你就還得賣畫。我對賣畫毫無興趣,但我也不得不賣畫。孩子上學、要出國,那個時候我也賣畫。但是過了那段時間,我就只想安心創作,很多人認為我畫了那么多堆積在那里毫無用處,我就是享受這個作畫過程的樂趣。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靠這點樂趣。
陳:余老師您是蘇州國畫院的畫師,現在國畫院里創作的群體您了解嗎?
余:現在畫院里很開放,原來蘇州有吳門畫派,一看就是蘇州的味道。現在不一樣了,院里面都是全國各地的人,畫也是別開生面各有各的風格,不分南北界限,也不分地域風格,非常開放,我也不反對。總是捧著吳門畫派,沒有突破也不見得是好事。
陳:上海現在也是面臨這樣的問題,每一代人應有每一代人的氣象,有他遇到的問題,有他要去解決的問題。
余:我很少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其實我是愿意參加的,但因為身體不好,出門比較麻煩。這次蘇州國畫院為紀念許十明先生誕辰120周年舉辦了一個活動,邀請我去參加,許十明先生的作品曾登上1957年《美術》雜志的封面,當年圍繞他這件作品,業內討論了一年,那時他是很超前的,他畫的是江南婦女在繡花,旁邊幾只雞,背景點綴了一些桃花,挺美的一張畫,還非常生活化。他的這幅作品很有時代氣息,而且構圖很新穎,他用一枝桃花把這幅畫上下隔斷。大家討論,有的說他不遵循傳統,有的則說他能這樣畫很了不起。我認為《美術》雜志之所以刊登這張畫,目的是要引領大家的創作方向,去創作現代作品。后來北京有大型的創作活動也會邀請他去。但是這位老師到五十多歲就得了帕金森,不能畫畫了,后來就去世了。到今年正好是他誕辰120周年,蘇州美協要為他辦展覽,他們來征詢我的意見。我就覺得這樣做真是太好了,這位老先生一生就投入在藝術創作中,曾經也是紅極一時的,但他一直很平淡,不張揚,一直到最后手不能再畫畫了。這樣的人就是努力地投身藝術,他想要創作出新的作品。現在很多人都不了解這位畫家,舉辦這樣的展覽是很有意義的。這樣的畫家值得年輕人去學習,活在這個世界上忙忙碌碌,自己到底想做些什么有意義的事情,一定要清楚。像這位許老師就是引領大家去搞新的藝術創作,這很了不起。年輕人做的事情只要不是極端的,我認為都是對的,沒有錯,只要他們想做事并且付諸行動,也是很了不起的。
陳:現在很多年輕人也在回望傳統,他們在走一段試驗探索的路途,但同時他們也要回到老先生們的時代去看一看他們是怎樣創作出經典的作品的,他們會反思,他們也會去臨寫一些書法及繪畫作品,通過這種不停地回望的方式來充實自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從藝術館的角度來說,近年來我們也一直在做與上海、松江相關的一些老先生們的書畫藝術展覽和文獻的梳理。通過對前輩以及老先生們的藝術歷程作梳理、搜集、整理工作,希望為更多的人留下一個展覽、一本圖冊以及文化的記憶。這次邀請您和沈老師的作品回家鄉展出,其中的機緣,既有您們和程十發先生之間的書畫因緣,也有您們同上海和松江文化界的密切聯系,這眾多的因素促成了今天這個展覽。非常感謝余老師接受我們的訪談以及對我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