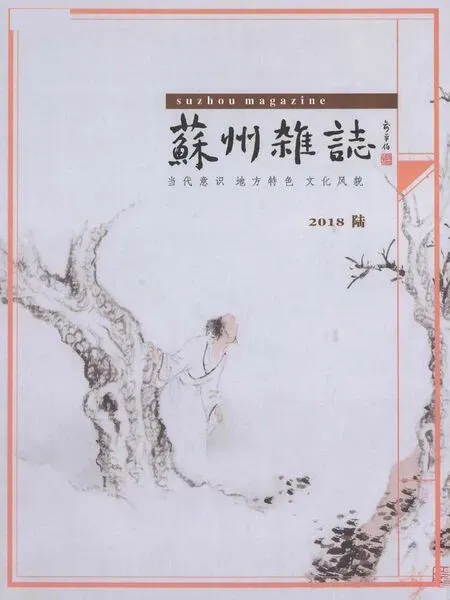吃煞太監弄
吳鳳珍

半個多世紀前,蘇州的街巷各有特色,就像有首民謠形容的——“曬煞北街,餓煞倉街,著煞舊學前,吃煞太監弄。”北街有我的娘家,那時行道樹剛種,太陽死曬。舊學前多估衣莊,倉街少吃食店,而太監弄里最多的就是吃食店。故有此說。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恰住在宮巷的一條橫巷內。那時居民中大辦食堂,宮巷內有居委會辦的“三八食堂”。我午餐在單位吃,而家中的午餐則由丈夫扶老攜幼去“三八”食堂解決。晚餐全家也就在這食堂里解決了。這食堂價廉物美,太受大眾的歡迎了。就在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那當兒,不知為何一夜之間上面有令,命居民食堂全部關門歇業!這下,我這個主婦抓瞎了。我白天要上班,哪顧得了家中的廚房呢?下班回家若再要做飯為時已晚,而且人已精疲力盡。我只得把兒子打發到我娘家去,婆婆回家鄉,我與丈夫設法到太監弄尋了家飯店包月飯,暫時解決了吃飯問題。后來這店回絕了我們,無可奈何之下,每天的晚餐只得在觀前附近尋找,于是吃遍了太監弄!

那兒有爿素菜館,價廉物美,我們便常去。可常吃素菜不吃葷也不是個事兒,于是,就拿了只大號塘瓷杯,去尋尋覓覓買葷菜。其中有宮巷內著名的雞鴨血湯、有太監弄與宮巷交叉處潘萬成醬園門檻內的熏胴攤,還有宮巷里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的羊肉湯。許多點心也可當晚餐,譬如吳苑茶館第一進的蟹殼黃與生煎饅頭,觀前街上觀振興的油氽饅頭和菜包子,黃天源的炒肉面,后來在松鶴樓的后門開了一爿松鶴樓面店,創出了名牌——鹵鴨面。據說,這種鴨子是另外專門飼養的,肉頭嫩而鮮,上澆紅彤彤的鹵汁。我外婆吃雷祖素的,凡開葷必是一碗鹵鴨面。本來在玄妙觀內的五芳齋搬到太監弄了,基本賣面,熱天賣楓鎮大面還較正宗,有時還放一些兒酒釀的飯粒在內。唯有一爿店我們沒踏進過,那就是菜飯店。我們嫌這飯太油了。當然,口袋羞澀的我們對那些著名的酒樓是不敢踏進的,連門口都不敢站,因為那兒的五香辣味太有誘惑力了。其實,整個太監弄的上空都是迷漫著這味兒,一嗅到,肚子里的腸胃會咕咕作響!我家的小巷口還有個油氽臭豆腐干攤,攤主像小人書上畫的王先生,他很敬業,也勇于自我革命,掛著批斗的牌子仍然在氽臭豆腐,夏天里若是一聞到這兒氽臭豆腐干的氣味,并非夸口,實堪讓你順氣、開胃通七竅!
有資深乞丐徹悟后道:“叫”了三年的“化”,連官都不想做!我與丈夫為吃晚飯流浪了一段時間后,也不思正規的第三餐了,其道理也一樣——就是圖個自由!
若是有人問:你自由吃遍了太監弄,感覺那兒什么食品的味道最佳呢?那個時候,在我的心中只有潘萬成門檻內的熏胴攤上的食品為最好。此小販的食品弄得極清爽,豬內臟頗難弄清,而此人的食品最為清潔,鮮而香,此物的湯一絲絲油也沒有,清澈得像自來水,太誘人了,實不容易。松鶴樓面店里的一碗鹵鴨面也是值得稱道的,可惜曇花一現。現在人的口福未免缺了那么一絲絲。
很少聽說過挑個駱駝擔能發跡的,但確實有。那時在宮巷內擺副駱駝擔賣小餛飩的就發了跡。說穿了也沒什么名堂,原本小餛飩就是在皮子內放一點兒肉醬,此擔主忽發奇想,用一粒鮮蝦仁代替它,這一來,名稱就不同了,一下子有了身價,上了檔次。當然,味道也確實鮮了些,模樣兒也俊俏了,半透明的皮子內一粒粉紅的鮮蝦仁,瞧著就饞了。后來這副駱駝擔發跡了,送餛飩的孩子當上了大面店聯鎖店的大老板。“一粒蝦仁發了家!”瞧起來似乎沒什么,難的是,誰能摸準蘇州人的胃口——講究精致和淡鮮的口味,誰就能贏。這幾年蘇州有些面店開發出了“三蝦面”,約一百元一碗,吃客照樣排隊。我就想,既然傳統食品在發掘出來,那大家惦記著的熏胴攤不也可跟著來一下嗎?曾有人拿來了不知從哪兒買來的熏胴到我這兒來求證一下是否正宗,我一嘗之下說真味的成分不到兩成!有些老蘇州遷居香港,還專程來蘇尋求熏胴,我竟無法提供任何有關的訊息,有些抱歉了。人是有記憶的,美食的記憶有時也能是一輩子的。時隔七十年,直到今天,在我的鼻際猶飄拂著過去潘萬成門前那熟悉的、香鮮的且特親切的味兒。嗚呼,太監弄若再想崛起,那最好是能發掘出人們在記憶深處的蘇州民間的傳統食品。我想,若有一天,在太監弄里突現了一個像潘萬成醬園門口那樣的熏胴攤,會出現啥光景?會不會漸漸地形成真正的吃煞太監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