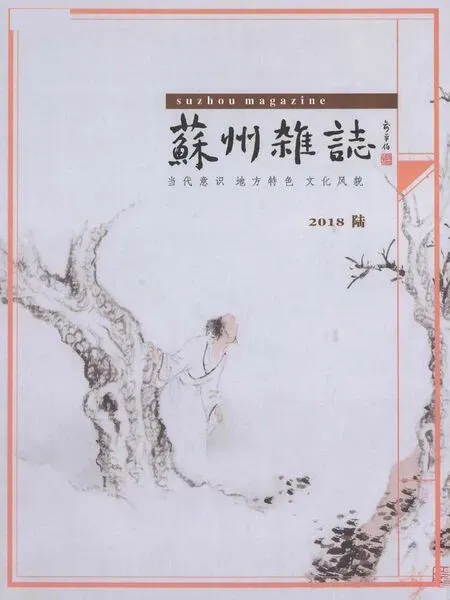再憶興隆橋
王喜華

興隆橋坐落在蘇州城南的運(yùn)河支流上。在那里,在那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橋邊,我生活了30年,從上世紀(jì)的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
2015年,我來到離別已20多年的興隆橋。那里早已物是人非,不僅橋已荒廢,不能通行,附近民居也已全部搬遷,據(jù)說要開發(fā)成小游園了。當(dāng)時(shí)即興寫了一篇《興隆橋雜憶》,承陶文瑜先生厚愛,刊于《蘇州雜志》2015年第4期。
一晃又是3年過去了,今年夏天的一個(gè)傍晚,我興之所至,再次來到興隆橋。
興隆橋周邊的環(huán)境變了。吳門橋矗立在西邊,而東邊的裕棠橋則重修以后,形成了新舊兩座橋:新橋交通繁忙,舊橋則保持著近百年來的原狀。
興隆橋也變了,原來破敗不堪的橋面已經(jīng)整修過,但還是盡量保持著原來的泥石橋面,以至于橋面上到處都鉆出了長短不齊的青草。
興隆橋,承載著我太多的回憶。
一
好像是我11歲那年春天吧,我家隔壁搬來一家姓董鄰居。那家有一個(gè)男孩,比我大2歲,長得比我高些。他叫志遠(yuǎn)。
我是很少有朋友的,因?yàn)槲壹彝コ煞植缓茫赣H是歷史反革命,我是被教育改造的對象。那時(shí)候講究家庭成分,別的孩子在大人的指示下,很少會(huì)與我玩耍的。只有志遠(yuǎn),他會(huì)常常跑來找我玩,顯得無所顧忌。于是我們就慢慢熟悉了。
那時(shí)的興隆橋是充滿生機(jī)的。
春天到了,陽光暖暖的,遠(yuǎn)望一片晴明,空氣很通透。志遠(yuǎn)會(huì)與我一起到橋邊的空地上挑野菜。
志遠(yuǎn)告訴我,野菜是一個(gè)大家族,有茼蒿、蒲公英、蕨菜、薺菜、清明菜等等。它們的顏色不同,有碧綠的,有淡綠的,有鵝黃的,有深紫的,有淺灰的;它們的形狀也不同,有鋸齒狀的,有鴨舌狀的,有圓狀的,有卵狀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當(dāng)然,它們也有各自的味道,或芳香,或清甜,或微苦。它們各自展現(xiàn)著自己的形象,期待人們?nèi)テ疯b。
我真沒有想到野草還有這么多的學(xué)問。
野菜生在路邊,根本不起眼,卻終究難逃一劫。野菜的生命很短暫,不過一春吧。有時(shí),就在它們出土后的短短十來天光景,就被人看中,挑走了。這不免有些悲壯,但或許那就是生命的價(jià)值所在吧。人們用一個(gè)“挑”字,留下了一絲人性化的余溫。如果是“挖”,那就帶有斬草除根的意思了。說不定,根脈尚存的野菜在一夜之間,又會(huì)長出一株嫩生生的新苗來。
那時(shí),我們最盼望的是夏天。
到了夏季,門前的小河就迎來了最熱鬧的時(shí)光。小孩子都會(huì)來河邊玩。太陽是暖暖的,水流是緩緩的。我和志遠(yuǎn)把鞋放在岸邊,然后光著小腳丫,挽起褲腿,在河中來回趟水玩。那種從腳和小腿傳來的絲絲涼涼,讓我感到格外舒服,也格外興奮。
我很喜歡“削水片”,雖然只屬于中等水平。
所謂“削水片”,就是在地上挑一塊小而薄的瓦片,用大拇指和中指夾住,食指勾在瓦片一端,捏緊,伸臂,揚(yáng)手,低身,轉(zhuǎn)體,緊貼著水面用力將瓦片水平旋轉(zhuǎn)著扔出去。只見那瓦片在水面上有節(jié)奏地彈跳著飛行,便如活的一般。如遇無風(fēng)晴日,水平如鏡,那次第出現(xiàn)的漣漪,鮮艷地蕩漾著,盛開在綠陰映襯下的小河里,趣味盎然。
削水片需要相當(dāng)?shù)募记伞O鞒鑫辶鶄€(gè)或七八個(gè)水花當(dāng)屬正常發(fā)揮;失手也不奇怪,瓦片飛出,常常咕咚一聲潛入河底,永無消息。好在碎瓦隨手可拾,揀個(gè)十多片一氣扔出,毫不可惜。削得好的小伙伴,削出十多個(gè)水花也稱平常,個(gè)別水平高的,甚至能控制兩個(gè)水花之間的距離,隔一兩米便漂亮地開上一朵;如要使瓦片平安渡河,扔出三四朵花后,那瓦片便已輕巧地到了對岸,就像田徑場上三級(jí)跳遠(yuǎn)運(yùn)動(dòng)員。一般而言,扔出的那串水花呈直線狀逐個(gè)開放,也有因瓦片厚薄不勻或手式控制上的原因,水花會(huì)呈弧線形出現(xiàn),那是比直線形更加好看的,我們往往會(huì)開心得哈哈大笑!
有時(shí),我和志遠(yuǎn)也會(huì)追尋并捕捉河中的小魚。這些小魚成群結(jié)隊(duì),卻非常機(jī)警,即使慢慢接近它們,也都會(huì)被它們發(fā)現(xiàn),因而驚慌失措地四散游開。于是,志遠(yuǎn)先將這些小魚趕到事先設(shè)置好的一片半圓形區(qū)域,然后用水草堵住出口并逐步縮小區(qū)域,最后成功地將所有小魚一網(wǎng)打盡。這些小魚個(gè)頭不大,不能食用,只能觀賞。志遠(yuǎn)把捉到的小魚全都裝進(jìn)事先準(zhǔn)備好的瓶瓶罐罐中,就高高興興地跑回家。
有時(shí),志遠(yuǎn)會(huì)光著身子到河里去玩水。我不會(huì)游水,就坐在岸邊的樹陰下看著志遠(yuǎn)在河里鉆上鉆下,仿佛一條泥鰍。我心里非常羨慕,但我膽小,始終不敢下水。
夏季的河邊總是能看到孩子們的身影,聽到孩子們的笑聲。
不僅是孩子,大人也會(huì)下河洗澡。記得有個(gè)40多歲的阿姨,也會(huì)下河玩水。她說是學(xué)游泳。每當(dāng)看到她雙腳在河里撲通撲通地打水,她肥胖的身子卻始終浮不起來時(shí),我們都會(huì)發(fā)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而她卻依然故我,認(rèn)真而執(zhí)著地?fù)浯蛑铀@得那樣的勇敢而無所畏懼。
夏天的夜晚,河水是黝黑的,星星和岸邊的燈光映在水里,小船駛過時(shí),就會(huì)激起粼粼的銀光。岸邊,小小的螢火蟲閃著淡綠的冷光,在草叢里飛來飛去。而我和志遠(yuǎn)呢,在家里拿出兩張長凳,安放在興隆橋堍,擱上一塊寬木板,我倆并排躺在木板上,仰面看著星空。誰也說不清楚那些星星的名字,只看到夜空中無數(shù)的星星在不規(guī)則地閃光,忽明忽暗,很是神秘,激起許多遐想。
秋天很快就到了。薄暮時(shí)候,橋邊的草叢中、磚頭瓦片底下,便會(huì)傳來蟋蟀的鳴叫。到了晚上,我與志遠(yuǎn)便在月光的映照下,翻動(dòng)磚頭,尋找蟋蟀。那時(shí),就可以看見蟋蟀正振翅高唱著。志遠(yuǎn)兩只手疾速扣下,大多時(shí)候它會(huì)霎時(shí)跳開,一跳再跳地逃跑了。我的手笨,動(dòng)作遲鈍,這時(shí)候,我就是一個(gè)看客。偶然,志遠(yuǎn)一次扣下去,小小的蟋蟀居然被他雙手罩著了。志遠(yuǎn)便警惕地把它攏在手心里,放在蟋蟀罐中,讓我拿回家養(yǎng)起來。有時(shí)候,志遠(yuǎn)會(huì)讓我把蟋蟀拿出來和別的孩子斗蟋蟀玩,那時(shí)候我就蹲在旁邊饒有興趣地觀賞。
深秋的夜晚,躺在床上,聽著家里的蟋蟀和屋外墻角草叢的蟋蟀構(gòu)成合唱,此起彼伏,在寧靜的夜晚,合奏一曲天籟。正如白居易在《夜坐》詩中說:“斜夜入前楹,迢迢夜坐情。梧桐上階影,蟋蟀近窗前。”
后來讀初中時(shí),學(xué)過一篇課文是蒲松齡的《促織》。每讀到成名那九歲的兒子化成促織替父完成上貢任務(wù),我就非常感動(dòng)。于是,我對蟋蟀便平添了一種特別的情感,不僅不去傷害它,反而多了幾分親近。
與志遠(yuǎn)在一起的時(shí)光是快樂的,也是短暫的。幾年后,志遠(yuǎn)因?yàn)榧彝ソ?jīng)濟(jì)困難而輟學(xué)了,又過了幾年他報(bào)名參軍了。
再后來,我在十年浩劫中蒙受冤案,與志遠(yuǎn)就失去了聯(lián)系。冤案平反后,我去興隆橋那里找過志遠(yuǎn),他家已經(jīng)搬走了。
二
直到新世紀(jì)。
我在一所中心小學(xué)當(dāng)校長,那年初夏,一年級(jí)新生的招生工作緊張進(jìn)行著。
下午,校長室的門被推開了,一個(gè)老頭領(lǐng)著一個(gè)小孩走了進(jìn)來。
“你是為孫子報(bào)名吧?”我主動(dòng)招呼。
“是的。”那老頭說,然后走到我的辦公桌前,“王校長,你不認(rèn)識(shí)我了吧?”
我不覺一怔。他是誰?認(rèn)識(shí)我?我不由得注意起來,這個(gè)老頭確實(shí)有點(diǎn)面熟,但一時(shí)卻記不起到底是誰了。
“王校長,我是志遠(yuǎn)啊!”那老頭顯得有點(diǎn)尷尬。
志遠(yuǎn)?志遠(yuǎn)!啊,真是志遠(yuǎn)!
我驚喜地招呼:“啊,志遠(yuǎn)!趕快坐!”
志遠(yuǎn)坐下了,又接過了我給他沏的茶,然后關(guān)照那小男孩叫“校長”。
“志遠(yuǎn),這么多年一直沒有見面。我記得上次見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時(shí)我正蒙冤,你來我家看望我。”我動(dòng)情地回憶,“那時(shí)是1971年,離開現(xiàn)在已經(jīng)30多年過去了!”

“是的。”志遠(yuǎn)仿佛沉浸在那段歲月中,“我那時(shí)剛復(fù)員不久。時(shí)間過得真快啊!”
“你后來怎么樣了?現(xiàn)在過得好嗎?”
“唉,一言難盡。”志遠(yuǎn)嘆了一口氣,“我是部隊(duì)里入的黨,復(fù)員回來進(jìn)了廠,當(dāng)了車間主任。誰知道后來是禍不單行!”
“怎么啦?發(fā)生了什么事?”我禁不住問。
“唉,說來話長啊。起先我的大兒子參了軍,我們一家兩代當(dāng)兵。1979年1月對越南的戰(zhàn)爭打響以后,大兒子的部隊(duì)去了云南前線。起先幾仗還打得可以,攻下了諒山。后來,到了1984年,在收復(fù)者陰山戰(zhàn)斗中,兒子受了重傷,一條左腿整個(gè)炸掉了,成了殘廢。送回家時(shí)敲鑼打鼓,很是光榮,很多領(lǐng)導(dǎo)都來慰問,還送了不少慰問金。可是時(shí)間一長,誰還會(huì)牽掛一個(gè)殘疾人呢?沒有辦法,他只能坐在輪椅上出去擺小攤。唉!到現(xiàn)在他還沒有成家!”說到這里,志遠(yuǎn)不禁有些哽咽。
我不知該怎么安慰,只默默地遞過去一張抽紙。
“志遠(yuǎn),那你身體還好吧?”
“我啊,下崗幾年了。下崗以后,我就與大兒子一起擺了一個(gè)修車攤,順便幫小兒子帶帶孩子。喏,這個(gè)孫子就是小兒子的。”
“那我嫂子呢?她不帶孫子嗎?”
“唉,別提了。她去年去世了。”志遠(yuǎn)的情緒明顯低落了。
啊,屋漏偏逢連日雨!
“真對不起!”我感覺心里有點(diǎn)堵。真沒有想到幾十年來志遠(yuǎn)的變化這樣大。
“現(xiàn)在還是你好,”志遠(yuǎn)苦笑了一下,“苦盡甘來,還當(dāng)上了校長。”
我苦笑了一下,趕緊轉(zhuǎn)了個(gè)話題。“對了,志遠(yuǎn),你孫子報(bào)名有什么難處嗎?”
“哦,說了半天,忘了正事。我那孫子報(bào)名材料都全,可剛才那報(bào)名老師說要做張卷子。我孫子做得不好,老師說不能收,所以我才來找校長。哪有還沒上學(xué)讀書就要做卷子的道理呢?”
“哦,就這事啊,那沒問題,我來給老師說一下。你放心,肯定會(huì)收的。”
“那就謝謝你了,王校長。”
“你怎么也叫我校長呢?就叫我喜華吧!”
“那怎么可以呢?我隨便叫了你名字,孫子聽了會(huì)覺得我對老師不尊重。”志遠(yuǎn)一本正經(jīng)地說,“在學(xué)校里你是校長,我是家長,那可不能亂了稱呼。”
聊了一會(huì),志遠(yuǎn)帶著孫子走了。
留下的是如煙的往事,是無法釋懷的惆悵。
后來,我多次讓那孫子帶信給他爺爺,希望一起吃頓飯,聊聊家常。但志遠(yuǎn)始終沒有回復(fù)。
一天傍晚,我按照家長留給老師的聯(lián)系地址,找到了志遠(yuǎn)的家。
那是一個(gè)新村三居室,家具不太新,但收拾得還算整潔。
那小孫子見我來了,趕緊叫“王校長”。
志遠(yuǎn)聞聲立刻從廚房里走了出來。看來,他正在準(zhǔn)備晚飯。
對于我的突然到來,他顯然沒有思想準(zhǔn)備,有點(diǎn)局促不安。他一面招呼我坐下,一面關(guān)照孫子趕緊去把他父親叫來。
“別去叫了。”我制止,“我又不是老師來家訪,我是來看你的!”
“哦,你,那你今天怎么有空過來呢?”
“幾次帶信給你,約你見個(gè)面,你都沒有回音,只能我過來看看你了。”
“啊呀,王校長,你太客氣了。”志遠(yuǎn)給我倒了一杯茶,誠懇地說,“我每天幫兒子擺攤,回來已經(jīng)不早,實(shí)在沒有多少時(shí)間陪你一起吃飯。但我怕這樣回答會(huì)使你不開心,所以就……”
“你怎么還叫我校長啊!你忘了我們小時(shí)候就是兄弟啊!”我有點(diǎn)生氣。
“那時(shí)小孩子的話,當(dāng)不得真。”志遠(yuǎn)淡淡地說,“現(xiàn)在我們都老了,怎么還能像小孩一樣不明事理?你當(dāng)了校長,就應(yīng)該稱呼你校長,這很正常。”
“可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謝謝你這樣牽掛我。但是,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志遠(yuǎn)長嘆一聲,“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不一樣,交往的圈子也不一樣,我們還有什么共同的話題呢?”
我一時(shí)語塞。
就這樣坐了一會(huì),我發(fā)現(xiàn)確實(shí)找不到大家感興趣的話題,只能告別了。
我知道,以后很難與志遠(yuǎn)再見面了。
大家都在慢慢變老,從起點(diǎn)走向終點(diǎn),自然而必然。成長的途中,匆匆而又忙忙,跌跌而又撞撞,奔波而又小心,勞累而又費(fèi)心。
人生是一場旅行,在歲月中跋涉,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花開了,會(huì)謝;時(shí)光走了,卻不會(huì)再來。
時(shí)間在變,人也在變。但總有一些名字舍不得刪去,因?yàn)閬磉^的痕跡;總有一些曾經(jīng)再不能忘記,源于溫暖的交集。也許一輩子再也不聯(lián)系,卻會(huì)記一輩子;也許不再有心動(dòng),卻仍然有心痛。留下一個(gè)永不更改的位置,看著,念著;守候一個(gè)遙遠(yuǎn)卻清晰的名字,記著,存著。不是不想,只是不再打擾;不是不愛,只是不再期待。舍不得的不是名字,而是人;忘不了的不是曾經(jīng),而是感情。原來緣分最痛的結(jié)局,就是人走了,感情還在;時(shí)間變了,心沒變。
現(xiàn)在,興隆橋還在,興隆橋下的河水變得清澈了,正在不知疲倦地流淌,興隆橋周邊的小游園里,老年人興致勃勃地跳著廣場舞,幾個(gè)小孩在奔跑,無憂無慮。
現(xiàn)在的興隆橋已經(jīng)告別了過去,正煥發(fā)出新的活力。
只是,再找不到往昔的影子了。
對了,矗立在興隆橋橋洞邊那對石幢呢?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