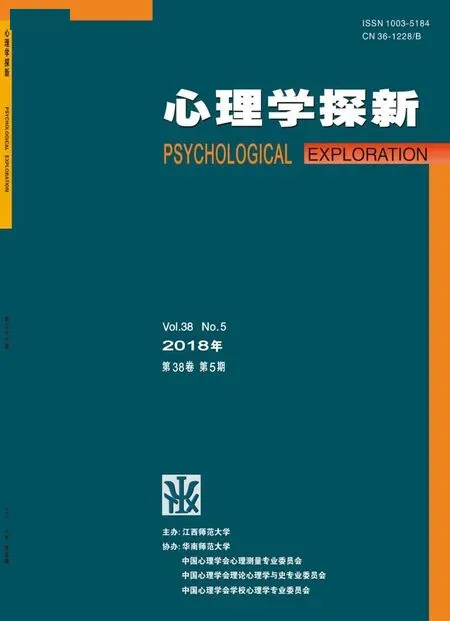道教文化與心理健康研究芻議*
郭碩知
(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大理 671003)
探索宗教心理作用的研究作為心理學的課題之一在此學科大輅椎輪之時已經受到了關注。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二度降生”(twice-born)理論將宗教的視作擁有“病態的靈魂”的人在封閉痛苦的經驗中釋放的需要(James,1902)。精神分析、人本主義等心理學派都或多或少地承認宗教的作用。相關研究顯示了宗教或靈性(religiosity/spirituality)與心理健康存在相關,其中大部分的結論表明更高的宗教或靈性水平通常伴隨著更好的心理健康狀態(Wong,2009;Ganga & Kutty,2013)。但也有研究指出具有明確宗教歸屬的老年人會更少去治療自身心理健康問題(Tze Pin Ng et al.,2011)。可見在心理健康的視域下,宗教常是一把雙刃劍,宗教心理學研究可以尋找宗教中促進心理健康的方式與抑制不良效果的措施。道教心理學研究理應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無論歷史還是現狀,道教的皈依人數與世界性的影響均有限,但不可否認其內蘊了中國人的文化底色,具有本土性的鮮明特點。它作為精神生活的深層與中國人的心理相互塑造。心理分析、人本主義、超個人主義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等領域都關注了道教文化與心理健康的關聯。
1 分析心理學的詮釋
研究道教心理學,首先需要跨文化的概念詮釋。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道教的基本概念“道”與心理的幸福和療愈息息相關,因此需要在心理學語境中得到恰當的解讀(Justin,2016)。長期以來,“道”被西方心理學界詮釋為道路或途徑,然而中國古人將之視作貫穿宇宙和生命的力量,與此最為接近的西方概念為“上帝”或“實在”。實質上,“道”既無法定義又永恒變化,是一種至大無外又至小無內的力量(Tong & Benjamin,2016)。道教由“道”這一最高實體和終極追求衍生出諸多修行、儀式、倫理等理念與實踐,同時汲取中國傳統中如陰陽等重要觀念,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概念體系。其中蘊含著道教對超越性身心健康理解的內丹學說較早得到了心理學家的關注。
分析心理學的開創者榮格(Carl Gustav Jung)是以心理學解讀道教的先行者。他曾研讀過《道德經》、《易經》、《慧命經》等經典。1928年,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送給他道教內丹經典《太乙金華宗旨》的德文譯本《金花的秘密》讓他寫作書評。榮格則以心理學徑路對此經典進行了評述。《太乙金華宗旨》系托名呂洞賓,的清前道教內丹經典,或為扶乩所成(丁培仁,2006)。這部經典讓榮格體會到了一種共鳴,此事被他認為是“打破隔離狀態的第一個事件”(Jung,1979)。
榮格察覺到了道教內丹學說中所涉及的陰陽、魂魄和回光諸元素,并將之容納到分析心理學的框架之中。內丹經典為他的集體無意識原型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他將“魄”定義為“無意識的人格化身”,其與人的解剖結構有著超越種族的共性相同。并認為人的心靈也擁有超越文化和意識的共同基底,這被他稱之為集體無意識。此外,借鑒“道”的整全性中陰陽和合的整體觀念,榮格的評述在心理整合的層面可以被認為具有意識與無意識相互和解的理想。并且榮格受到《易經》中問掛與回掛之間關聯的啟發,提出了他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原則,認為因果原則在解釋無意識心理活動時不夠充分,需要需求另一種解釋原則,即共時性,它不受制于時間和空間的法則(高嵐,申荷永,1998)。
衛禮賢在翻譯這部內丹道經時已經應用了榮格的心理學概念,將魂譯為animus,魄譯為anima。榮格取用這兩詞的目的在于使情感特征人格化。他認為這是可感知的心理對象,男性的無意識中存在著一個女性形象,因此會有anima這樣的陰性?拉丁文詞綴中常以“us”表示陽性,“a”表示陰性。名詞,它是無意識的人格化身。而魂則在需要表達向道回歸的理性時,“logos”是更恰當的譯法。animus則是與男性的anima相對應的女性的人格化情感特征(榮格,1998)。這實質上關照了完整的人格與情緒,試圖在東方文化中尋求意識的無意識根源,避免片面地依賴意識所造成的過度緊張。
道教文化對榮格之后的分析心理學亦有深刻影響,如黑爾曼(James Hillman)的“原型心理學”中取用太極圖作為重要的原型意象。“愛諾斯基金會”主席利策瑪(Rudolf Ritsma)對《易經》亦有所評述等(申荷永,1996)。
榮格對道教文化的心理學關照獲得了后世學者的關注。他們對榮格道教心理學的切入點大多是相關概念的進一步詮釋。
他的學生托馬斯·科施(Thomas Kirsch)曾于1994年夏季在北京同仁醫院做關于榮格與道教的學術報告,將衛禮賢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榮格的影響相提并論。他指出衛禮賢最主要的工作在于與勞乃萱合作翻譯《易經》。當榮格看到此譯本后,放棄了列奇(James Legge)的譯本,轉而在衛禮賢本這里發現了《易經》對于心理工作的意義。尤其問卦與回卦之間的一致性被榮格認為與其心理學模式相吻合,這種陰陽平衡意味著分析心理學中意識與潛意識的和解。他認為:“中國人的思維不在于搜集細節,而是把細節視為整體的一部分。……因而細節被置于宇宙的背景——陰陽的相互作用之中。”(Kirsch,1994)
隨著對榮格關注度的進一步提高,相關研究通過心理學與道教的概念比較,對榮格的理論提出批評。有學者認為榮格對元神作為“人的意志和理智明辨秋毫的靈光”的理解不恰當,而應該更多地作無意識的解讀(郭建,楊玉輝,2002)。或指出榮格將西方的“無意識”狀態與東方的冥想中的更高意識等同是錯誤的,并需要新的概念取而代之(Jeremy,2009)。此外,榮格決定將魂、魄分別翻譯為logos和anima,這在當代學者的眼中也可能是錯的。因為來自榮格的文本分析的術語可以看出這里隱含著相對的先驗推理。換言之,如果榮格所做的是基于文本的定性分析,那么他的方法就是在文本中強加某種限制的標準,而不是根據文本自身的含義來翻譯如魂、魄等術語(Cott & Rock,2009)。
榮格對于道教丹道實踐概念的心理學解讀旨在分析和表達其中的心理狀態。然而對其道教心理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文本層面。所謂內丹的概念的在道教的話語體系中原本就存在著各種派別之間的爭議。對道教實踐是否能影響無意識或意識層面的心理健康狀態則進展有限,學者們對榮格的回應也從側面證明這一古老的心理學問題依舊方興未艾。
2 人本主義與超個人心理學
羅杰斯(Rogers)和馬斯洛(Maslow)在上世紀50年代促成了人本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的興起。他們認為自我實現是了解自我所含有的巨大潛能的過程。而當無法實現這種潛能時,就會導致心理的痛苦,以及自我和世界的壓迫感。潛能的實現,以及在此過程中獲得的滿足感是人本主義者所追求的心理健康狀態。這需要軟化身心的盔甲,使人們能夠承受和支持更大的心理能量(Cortright,2011)。
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希望將自我實現的范圍擴大。它被定義為靈性傳統與現代心理學知識的結合(Cortright,2011)。這使它很容易成為宗教的盟友。它主張超出人本主義對個體自我的關注,并進一步延伸至超越性的精神領域,向更高的生命層面成長。因此超個人心理學也被稱為“精神心理學”(mental psychology)。而人類文化傳統中超越性的理念通常由宗教文化所塑造,如禪定、正念、蘇菲等。
二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啟發。20世紀50至60年代,存在主義思潮盛行,存在主義哲學家在經歷對二戰等苦難歷史的反思后希望直面人的生存狀態。現象學主張“回到事物本身”,存在主義則將現象學“先驗自我”的領域轉到了“人的存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區分了“存在”(Being)與“存在物”(beings)的觀念,并提煉了此在(Dasein)的狀態“煩”或“操心”(Sorge)。薩特(Jean Paul Sartre)則對意識與自我意識作出區分,指出自我意識并非指向某物,而是通過反思把意識變成完整的對象,即自我。反思中人們所經歷的戰爭和意義缺失的處境無疑與恐懼和焦慮相伴,迷茫與瑣碎成為了常態。由此為基礎生出了人本主義和去病理化的心理學思路。同時孕育了超個人心理學這樣的超越處境限制的心理學運動。它在存在論的哲學思潮之中希望重新發掘神秘的靈性文化資源,并整合行為主義、精神分析和人本主義的三種心理學勢力,試圖形成一整套的治療技術。
人本主義的道教心理健康學說通常將道家道教的概念與自身的理論相對比,并且注重通過道教實踐對普通人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學者將道家哲學的七項原則(無為、自然、上善若水、柔弱、節制、小國寡民以及不爭)與人本主義心理學作為比較(Lee,2003)。或將榮格、埃里克森(Erikson)以及馬斯洛的基礎理論同道教的基本觀念如“返璞歸真”等對比。事實上,他們每個觀點都在強調人成為一個完整的、平衡之個體的重要性(Rosen & Crouse,2000)。然而這更多是心理學理論對道教的詮釋,實質上道教信仰目標的本質和達到它的過程不同于西方理論。道教認為通過修煉的方式,人們可以逆轉某些心理發展過程,達到最初的、先天的純凈狀態。它與人本主義的理論的區別不僅在階段劃分,更在于逆轉的觀念(Cott & Rock,2009)。
然而,道教依然被認為可以在當下境遇中更好地服務于人本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心理健康研究與臨床實踐。如果心理學在求真的同時關注人類福祉,那么作為文化資源的道家道教便與之相關。其中有兩個主要主要問題值得關注,其一為人類如何與他者和平相處;其二在于人們與世界中除人之外其他部分的關系。近年來關于《道德經》的心理學分析以及對道家大五人格(the Daoist Big Five)或若水人格(the Water-like Personality)的討論就是道家道教面對這些問題所可能采納的心理學徑路(Lee,2014,2015,2016)。
超個人心理學更重視宗教與神秘傳統,根據丹尼爾斯(Daniels)的超個人心理學定義?他提出了兩種超個人心理學的定義方式。第一種——或者說是一種冗長的描述方式,它列舉了各種超個人的現象,允許世俗常態中的個體逐步轉變為他所理解的超個人的對象。第二種——或者說是一種簡潔的表述方式,它使用了一系列被丹尼爾斯稱為“s”的詞(例如,spiritual,就是s開頭詞)。參閱:Daniels,M.S.(2005).Self,spirit:Essays in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Exeter,UK:Imprint Academic.,在道教中可以發現大量超個人現象,如司馬承禎的《坐忘論》中記載的上清教法。同樣,這些現象也可以被置于格羅夫(Grof,1975,1988)的超個人圖譜(transpersonal map)之中(Cott & Rock,2009)。曾有一項針對自1968年到2002年間的超個人心理學定義的專題分析,匯聚了來自于公開出版的文獻和該領域內的心理學家所提出的定義。將這些定義綜合起來包括了“超我”、“整合”以及“變化”三個概念(Hartelius,Caplan,& Rardin,2007)。道士劉一明所著《悟道錄》等經典正可對應其中超越自我之外的特性,《易經》、《悟真篇》、《參同契》等則詮釋了超個人心理學中的整體性與變化性(Cott & Rock,2009)。
道家理念,如莊子“心齋”、“坐忘”同超個人心理學都論述了如何破除自我中心從而達到自我超越的內容,但仍包含一定的差異。超個人心理學中的自我超越是沒有“自我意識”的“自我”,當它與宇宙合為一體,“自我”即為“宇宙我”。而莊子中的“自我超越”還是以“自我”為出發點,要達到順其自然的“自我”(李樹軍,張魯寧,2011)。學者亦將白玉蟾等人傳習的南宋鐘呂金丹派的修行理念與超個人心理學進行對比。認為南宗(相對于北方全真道)修行是一種超個人水平上的自我實現,這種修行的體驗呈現出“轉換的意識狀態”(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其立論的旨歸則是促進當代社會大眾的心理健康(張海濱,2012)。
超個人的心理研究思路的局限在于將靈性傳統與現代心理學對應,從而可能走向神秘主義,模糊了超驗與經驗的界限。心理健康研究并不局限于哲學世界觀的爭論,而更需要將超越性的文化或實踐視作變量觀察它對心理健康或正或負的作用。作為科學的心理學屬于經驗世界,須通過各種方法測量人的心理狀態和心理能力。所謂超個人或許只能被視作一種追求或人格的屬性。在這樣的心理過程中,人的認知能力、情緒效價等心理相關指標有會發生與之相關變化的可能。
3 具身性研究與測量
理論與概念的討論使得道家道教與心理學各流派所宣稱的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日漸明朗。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則觀察了其可能存在的具身性影響,明確了道家道教的變量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心理參數的變化,以及制定了相關的干預手段。
將身體、心理與世界相互合一的理念(body-mind-world)古已有之,維持這一系統使之相互勾連的元素被認為是“氣”,且可以通過煉養達到對氣的控制。莊子曾主張釋放自己的身體用來知覺世界與道(筆者按:《莊子·人間世》載:“乘物以游心”)。通過身體認識自我和世界在中國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認知觀念,身心完整性的共同塑造也是儒道二家的共同追求(Li & Ye,2015)。
道家的陰陽學說能夠對應積極和消極的心理過程。孔麗維(Livia Kohn)、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學者對道教理論的研究表明,它具有積極的心理取向,其目標是生活的長壽與健康。但道教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則包含了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的心理體驗。道教所追求的心理健康為對身心以及消極和積極心理的平衡與整合,這需要接受相關練習。在道教中,心性修煉的目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匯聚積極的心理資源,這類似于西方的“認知—行為”療法。對道教而言,這只是一個開始,更大的健康產生于走出個人內在的獨白(monologue)的時刻。這種注意力訓練是從外在客體思維開始的,通過呼吸、內觀等多種方法,最終得到注意的積極轉化(Reggie Pawle,2011)。
在西方心理健康學科的實踐中,道教煉養與其他心理療法可以融匯。Rhee Dongshick教授結束了在美國的研究生涯后回到韓國,沉浸在祖先的古老的道、釋、儒與禪的傳統中,并在此獲得了很大成就。他在1974年發展創立了“道心理治療”(Tao Psychotherapy)方法。這既是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方法,也是日常生活中尋求連接東西方心理療法要素的重要見解與實踐(Erik Craig,2014)。
并且,道家道教被視作一種可測量的人格成分。近期的一項研究指出“辯證應對”(Dialectical Coping)是道家道教的人格特點,與之相對的是儒家的“和諧關系”與釋家的“不執著”。此研究測量了262名臺灣大學生,結果顯示三種CIWB(Chinese indigenous well-being)構造的不同與心理健康相關。儒教的和諧關系與消極的心理痛苦和積極的人生意義或幸福相關;道家道教的辯證應對追求更高層次上的積極情感與生命意義;而佛教的不執著則是唯一或最強的應對負面情感與心理痛苦的保護機制。針對道家的辯證性,作者開發了《辯證應對量表》(Dialectical Coping Scale,DCS),測量個體應對挑戰性環境時利用辯證思維的程度。(Wang,Wong,& Yeh,2016)。內地學者較早設計出《道家人格量表》作為相應地測量工具(涂陽君,2012)。
上述研究大多從文化理念出發,然而如同佛教徒不一定舍棄執著,現實上看,道教信仰者也不一定接受甚至接觸過道家的辯證思維。在中國的文化場域之中,道教認同者更多追求行為的有效性。雖然“道”作為終極實體與神學合法性的保障,但直接受到敬拜的卻是功能神。大部分儀式與修煉更多為達到所求的目的,其直接的指向是效果的靈驗。“自宋代以來普通人不甚刻意分別何為道教,何為佛教,何為傳統祭祀宗教。此類例子不少,有的祈祝‘合家清吉,人眷平安,壽命延長,萬事如意,福有攸歸’等等。”(丁培仁,2010)民眾以“靈驗”作為心理底色接受佛道二教,而非追求終極的超越性真理,具有本土文化的突出特點。因此理念與心理指標相關性的測量固然重要,但這種指標尚缺乏有實踐維度。
已經有學者在研究氣功、太極拳等與緩解焦慮、情緒效價等指標的相關性(Lee et al.,2001)。事件相關電位(ERP)的研究表明,太極拳練習使精神分裂癥患者的P300與AEP潛伏期縮短,波幅增加,其信息加工速度、記憶力及思維邏輯性等均有所改善(甘景梨等,2010)。對普通人而言,太極拳的訓練也取得了類似的ERP波相關效應,促進了其心理健康程度的提高(李煥玲,2014;張曉斐,2015)。
道教之于心理健康的研究不僅存在于觀測個體直接受到道家文化與道教實踐的影響之后心理指標的相應變化,也須考慮到能夠對個體施加影響的相關群體認同與文化浸潤的因素。
4 群體心理與認同
宗教的群體形式既表示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宗教自身,也意味著群體之中的個體心理健康受到群體的心理、結構和文化的影響。根據社會認同論(SIT),人以其所屬的社會群體資格(social group memberships)來定義自身,且依群體而界定的自我感知會對其社會行為產生獨特的心理影響。群體被自我歸類的范疇所認定,其過程并非個體組成群體,而是群體存在于個體之中(Hogg & Abrams,1988)。相應地,整體的社會文化心理也影響著其中的宗教群體與個人,并且被這些群體的自我歸類所塑造。有研究發現,個體對不同種類群體的認同,以及群體認同的數量與其心理健康水平顯著相關。其中宗教具有相應的的作用,它能夠在短期幫助人們更好地應對恐懼、焦慮等負面情緒。并且宗教認同所增強的支持感,也是信仰者長期幸福感的重要來源。但當宗教團體認同受到挑戰時,個體會表現出悲傷、對抗等負面情緒與行為傾向(王勍,俞國良,2016)。
歷史表明,組織化宗教通常會對精神病人首先提供富有同情心的照料,但數百年來某些宗教機構也在迫害著他們。盡管如此,出現在西歐和美國的第一種精神治療的形式被稱之為“道德療法”(moral treatment),宗教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Koenig & Larson,2009)。國內也有如王鳳儀的痛悔療法等與之類似。它既借鑒了宗教組織為了保全自身和適應社會所構建的倫理與戒律體系,也秉承了一些宗教將心理乃至身體健康倫理化的思路。
道教早在組織化初期,已經具備了三官手書等思過儀式。《三國志·張魯傳》注引魚豢《典略》曰:“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陳壽《三國志》,卷八《魏書o張魯傳》,中華書局 1964年,第264頁。此意在將個體與社群的異常狀態一同重新歸入正軌。此種倫理性科儀實踐試圖統合身心健康,以近似于道德療法或性理療病的機制對人的心理施加影響。
倫理在社會結構和文化內造就了個體的處境與規范。個體對于所處文化與社群的認同對其心理健康的作用早已得到了心理學的關注。埃里克森于20世紀40年代在青少年心理分析中發明了“自我認同”(ego identity)一詞,并將之與群體心理現象掛鉤。其著作《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開篇提出了“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的概念,認為青年時代最大的危機即認同危機,而宗教是尋找認同的主要意識來源(Erikson,1958)。這種認同主要向自我內部發生,與個人的生命史以及個體宗教心理的發展息息相關。在《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Identity:Youth and Crisis)一書中埃里克森將認同危機與其人格發展八階段理論(Eight Stages of Development)相結合,認為每一個階段就是一次危機,而認同的作用在于“有活力的人格能經受住任何內外沖突,在每一次危機之后再次出現且逐次增強統一感”(Erikson,1968)。在這里出現的是轉換與統一的張力,既是個體發展的過程,也表現了個體的社會身份與認同的分裂與回歸。道教作為宗教群體,同樣存在著心理發展的過程。它不但呈現出從在文化史中由邊緣朝向中心的歸屬趨勢,而且具有獨立性自覺,二者形成了認同的心理張力(郭碩知,2016)。
上世紀末,認同在社會心理學領域中成為了一個范式。泰弗爾的“社會認同論”(SIT)可以為道教與心理健康研究在社會心理學的領域內提供新的思路。該理論區分了人際與群際范疇,指出認同產生于群際關系之中,并創造“最簡群體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1970)實驗程序(得出內群最大化的結論)。并試圖通過范疇化、社會比較、認同建構、以及解構與重構等理論建造,超越了還原主義和個體微觀的解釋路徑。特納及其后學豪格和阿布拉姆斯等人豐富并改進了社會認同的理論范式。尤其以特納的“自我歸類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1987)及“元對比原則”(meta-contrast principle)最具影響。這些思路的基本假設在于人以其群體資格定義自身(Hogg & Abrams,1988)。人對群體文化的認同成為了人的自我詮釋,一旦其所獲得的群體資格(身份),與認同發生沖突,其自我與自我實現之間的鴻溝會變得難以逾越,這勢必會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
宗教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蒂利希指出:“宗教是人類精神生活所有機能的基礎,它居于人類精神整體中的深層”(蒂利希,1988)。宗教認同即個人或群體如何理解、經驗和塑造自己宗教身份的過程,或被心理、社會、政治等因素塑造的虔誠的宗教歸屬或從屬。這種認同通過神圣化構筑了超越的穩定性,并與世俗身份共構了多重身份的樣態,跨宗教的認同有著更為豐富的理解和實踐維度。
歷史上的道教是各個道派和信仰形態的統名,并非勻質的共同體,存在著明確的中心、松散的外延以及模糊的邊界,教外看待道教同樣亦難免產生相應的刻板印象。依據自我歸類論及元對比原則能夠對松散的道教信仰群體進行了多重的層次劃分,即居于核心的“與道合真”,中間層的“倫理追求”,直至最外層的“生活技術”層面,更外擴則存在著道教廣泛的文化影響。其核心的位置顯示為道教群體的部分刻板印象,通常的行為表現則是另一部分。外部的松散形態意味著具有更多容納多元宗教身份的可能。這就解釋了道教歷史上“雜而多端”?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10頁。的群體表現形態(郭碩知,2016)。
與此相對應的心理狀態與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與穩定性的獲得在一定程度上可發現相關。并且認同的層次越接近中心,道教的教義、倫理等因素對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越大,這時整個道教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就會在更大的程度上決定個人的心理健康程度。
5 小結
道教中蘊含著豐富的心理資源,既塑造了自身的文化樣態,也影響著信眾乃至更多人的心理結構。盡管它在心理學中的影響力尚未完全展現,但自榮格起,道家道教的各種理念與實踐引起了心理學界的關注。人本主義、存在主義、超個人心理學等流派都或多或少地自覺與道教文化的諸多因素對應。作為文化群體的道教也已經成為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近年來,伴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等領域的發展,道教實踐對人腦等具身性成分的塑造已經越來越多地得到研究。道教作為一種中國本土生長的信仰與文化體系,既受到心理學普遍規律的制約,又具有一定的本土特性。道教心理學研究需要學習和借鑒對西方宗教心理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但并不一定囿于其文化架構之內,而是在追求普遍規律的基礎上注重特殊文化因素的作用。道教內蘊的道家精神,對于信仰效果的追求,及生命中心主義等特性都構成了它對心理的獨到理解。道教的認同形式亦多樣而松散,這會形成不同的心理預期,結果與預期的吻合程度,解釋體系以及信仰動機自身都會成為心理健康的相關變量。總體而言,道教心理學可以豐富本土心理的研究,并在一般與特殊之中探索道教對個體、群體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心理的塑造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