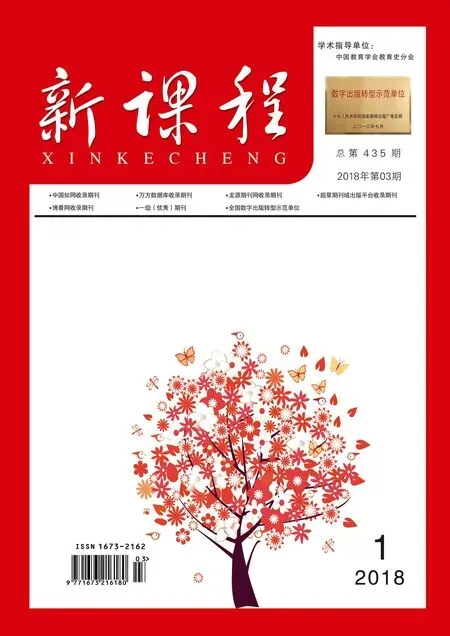淺議高中歷史教學中教師主動性的發揮
桑玉坤
(安徽省渦陽第一中學)
一、保持自我,掙脫機械的模仿學習之絆
德國著名哲學家萊布尼茨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模仿學習只能是教師入門之初所做的事情,教師自身想通過簡單的模仿學習訓練,而有大的成就是不現實的。當下,有很多名師和專家在做著心得交流活動和經驗推介活動。當他們的經驗心得蜂擁而來的時候,我們是應該簡單地模仿學習全盤接受,還是經過思考之后的批判學習呢?毋庸置疑,絕大多數教師會選擇后者。
對于專家名師的講座,我們當然要抱著學習的態度去聽,但這僅僅是第一步,接著是自我吸收和轉化,這是連結“聽”的理論與“做”的現實之間的紐帶和橋梁。上文已經言明,我們不能全盤地接受專家名師的經驗心得,那么吸收的資源自然要是能順利轉化并適合自我開展教育活動的知識。因為專家名師的講座不可能像我們在開展教學活動時會盡可能地考量學生的學情,事實上,并不是他們不做,而是很難做到,就算是同屬于一個學校的教師,他們不同的地緣背景和學習經歷,在吸收轉化知識上也會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簡單的模仿名師專家的模式學習,或者是模仿他人的教學方法,對于成長中的老師來說,是弊大于利的,甚至會使我們在這種學習之中丟失自我,像沒有導航的帆船一樣在大海之中迷失方向。
二、開闊視野,觸摸歷史學科之外的世界
在20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的年鑒學派,他們的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就認識到了,歷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會的歷史,是“總體史”,主張融合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各門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為一體,重理論、重解釋、重綜合。雖然,我們當下使用的歷史教材,已經是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內容,但是,關于教學的模式和方法依然是停留在政治史的窠臼之中。著名歷史學家何兆武也指出,“歷史學包括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兩者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于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于藝術,從而有別于科學的東西,或者不妨說是某種有似于直覺的洞察力的能力。”從中不難看出,歷史學科本身具有科學和藝術的雙重性。因此,我們不妨借科學和藝術之“石”,攻歷史教學有效開展之“玉”。
在本校開展的教學開放周活動中,筆者帶著求知好奇之心聽了語文、化學、政治等學科的名師公開課以及專家思維導圖推介課。從中我深受啟發,比如語文課上,老師經常讓學生朗讀課文,體會文學表達之美。這一點應用到我們歷史教學中,一樣可以發揮作用,多讀讀歷史課本不僅是學生識記基本歷史知識的有效手段,而且有助于對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教學目標的完成。又如化學公開課上,教師帶領學生利用實物儀器開展化學實驗,以已知導出未知,直觀展示中間的變化過程。我們歷史教學,倡導的探究歷史、情境再現層層分析不謀而合。控制變量的實驗科學的精神,恰好也為我們演繹歷史提供方法論上的借鑒和指導。另外,對于被奉為“世界上最高效記憶工具”的思維導圖,其在歷史教學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它的使用將會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三、體悟歷史,理清其中的“骨”與“魂”
歷史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研究“人”或者是“人性”的學問,任何的歷史現象、事件時刻離不開歷史的人物,不管這個歷史人物是王侯將相還是普通民眾。正是由于此種原因,歷史就成了一個“魂”與“骨”相結合的學問,我們的教學自然也不能是厚此薄彼,兩者應該同樣受到重視。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實在在地點明了課程性質、基本理念、設計思路、課程目標、內容標準以及實施建議等內容。這就需我們在教學過程中要嚴格遵守,并以之為指導的原則標準,也是筆者所說的“骨”。這也是高中歷史的骨架之所在、結構之所宗。但是,每一條實在的標準背后,又都有“魂”的影子。如,關于必修一中對“列強侵略與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這一知識模塊,課程標準采取了“列舉1840年至1900年間西方列強的侵華史實,概述中國軍民反抗外來侵略斗爭的事跡,體會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斗爭精神。”這樣的提法,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這里邊既有實實在在的史實,又有精神價值觀層面的精神體會。與之相比,過去的教學大綱基本上是史實內容和事件影響的堆砌,而忽視“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斗爭精神”這樣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教育。
新的課程標準正在為當下的歷史老師開辟一條區別于以往的道路,不能是一味地只講知識點,而要重視學生思維的鍛煉和價值觀的培養。歷史老師不應是歷史材料的播撒機,而應是承擔新課程改革的中堅力量。體悟歷史,理清其中的“骨”與“魂”首先要從老師自身做起,然后才是帶領學生,開拓創新。這樣的歷史教學才更加有意義,更加富有生命力。
[1]何兆武.何兆武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12.
[2]陳志剛.試論歷史情感教育的實施策略[J].歷史教學(中學版),2008(3).
[3]單懷俊.歷史教育的演進:從歷史教學大綱到課程標準[J].歷史教學,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