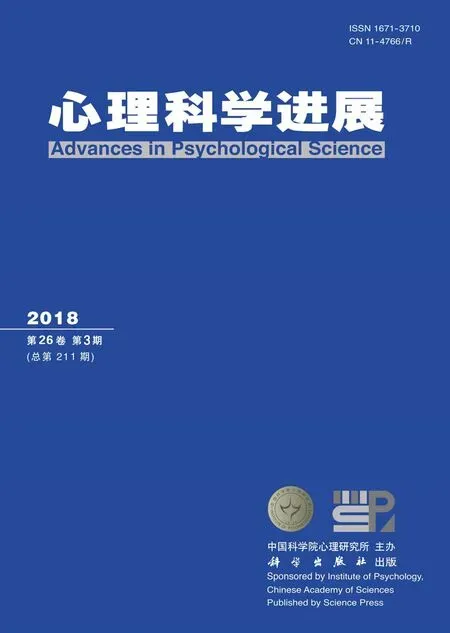為人父母者更幸福?*
徐華春 崔碧穎 張文婷
(四川師范大學教師教育與心理學院,成都610068)
為人父母者都了解,孩子可以帶來最大的快樂與滿足,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辛勞與付出。從整個生命歷程來看,生兒育女又是人生中一項極具挑戰性且影響深遠的重要生活事件。現代人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則已從傳統經濟層面上的“養兒防老”觀念轉而更重視其心理意義。事實上,為人父母者的幸福狀況也遠不只關乎他們自身,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和決定大多數家庭的和諧穩定以及每個子女的健康成長。人們在此方面的預期與實際結果也將直接影響其在生育與否以及生育子女數量等問題上的決策。因此,社會大眾以及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乃至經濟學家都關心一個問題:生兒育女究竟與個人幸福是怎樣的關系?
在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目前正進入調整和轉向階段以應對人口紅利消失、臨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等社會問題。以往在相關問題上的研究也更多以人口學的視角來進行。而當前,基于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證,統合個體、家庭與社會等諸方面來理解生育?幸福等相關問題已成為趨勢。
本文將對該方向上已有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以便于未來進行立足于我國文化與現實的實證研究。
1 大眾信念
首先,關于生兒育女與人生幸福的關系,大眾中廣泛存在一些樸素的觀點與信念。它們為人們提供先入為主的看法和行為指導,同時又可能作為輿論和社會期待直接影響為人父母者以及無子女者的幸福水平。Hansen (2012)總結了三種相關的大眾信念,同時也強調這些信念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和族群差異,并可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改變。
信念1:有孩子讓人更快樂。生兒育女被廣泛認可為個人獲得圓滿和幸福人生的重要經歷。擁有孩子的傾向是強烈而內隱的,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年輕人(90%~95%)都計劃未來擁有孩子。盡管主動選擇不要孩子的人在一些西方國家有所上升,但其比率仍然很低,僅為2%~6%;絕大多數無子女者是因為結婚或生育計劃的一再推遲而被動形成的。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廣泛信念是:孩子促進婚姻的圓滿。比較而言,年輕人和受教育程度較高者更少認同這一說法。信念2:沒有孩子是凄涼的。普遍的觀點認為沒有孩子的成年人生活空虛, 尤其是在老去以后。在東歐及很多非西方國家, 這一比例達到了 55%~70%, 但在荷蘭、美國發達國家, 僅有10%~25%的人認同這一點。信念 3:無子女者是自私的享樂主義者。尤其是為人父母者常常會將那些不要孩子的人視為不成熟的、自我中心的人, 認為他們只專注于工作、休閑娛樂和浪漫關系, 而逃避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 也有人開始用“無孩自由族”等中性或偏積極的詞匯來稱呼無子女者。
2 心理學理論觀點
心理學研究者分別從人的本性、個體發展、幸福的來源等不同視角對生育?幸福關系提出了各自的理論觀點。總結起來, 這些觀點可以分為三類, 即生育對幸福無持久影響, 生育對幸福有積極影響以及生育對幸福存在程度和方向上不確定的影響。
2.1 生育對幸福無持久影響
該觀點又稱為調定點理論, 認為一個人的幸福水平其實是穩定的; 個體不論經歷怎樣的生活事件, 其幸福水平總是會在生活事件發生后不長的時期內就會恢復到從前的基線水平(Headey,2010)。從長遠來看, 幸福僅取決于個體的人格特質和其它生理遺傳因素。比如, 在大學期間表現出更多積極情緒的女性更可能在畢業幾年后就結婚, 并在隨后30年表現出更高的婚姻滿意度, 更少經歷婚姻問題或者離婚, 而最終離異或分居的人大多在婚前就不幸福(Lucas, 2007)。
就具體的生活事件而言, 已有研究證實, 喪偶、失業會顯著且持久的降低個體生活滿意度,不符合調定點假設(Headey, 2010)。而在生兒育女方面, 已有的基于德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縱向追蹤數據的研究(Clark, Diener, Georgellis, &Lucas, 2008; Clark & Georgellis, 2013; Myrskyl? &Margolis, 2014)均發現, 在第一個孩子誕生前后,父母的生活滿意度水平會達到高峰, 但在孩子 2歲前就會明顯回落。但在不同的研究中, 回落后的幸福水平與懷孕前幸福水平的比較結果不一。
2.2 生育對幸福有積極影響
2.2.1 心理發展論
Erikson (1963)從心理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生兒育女的行為。眾所周知, 他將人的畢生發展劃分為 8個階段, 每個階段都面臨特定的發展危機,需要解決相應的核心任務。當核心任務得到恰當的解決, 個體就會獲得完整的同一性。其中, 個體在第七個階段成年期所面對的就是繁衍對自我專注的沖突。他認為, 如果個體順利地度過了前面幾個發展階段, 成年人在此階段會自然的生兒育女, 關心后代的繁衍和養育。生育感可區分為生和育兩層含義:沒有生孩子的人也可以通過關心,教育和指導下一代獲得生育感。相反, 前期自我同一性發展的不完善可能形成沒有生育感的人,其人格發展將出現停滯, 表現為只考慮自己, 不關心他人。這也將帶來個體在人生最后階段的絕望感。由此觀點來看, 生兒育女是個體心理發展中必要的或者至少需要去替代性彌補的經歷, 其對個體后半段人生的健康、幸福的影響不言而喻。
2.2.2 進化心理學的觀點
以 Kenrick為代表的進化心理學家將生兒育女視為人類基本需要。他們將生兒育女置于人性需要金字塔結構的頂端, 認為它不是低級的生理需要, 而是高于即時生理需要、自我保護、人際關系、自尊、配偶尋求以及配偶維持等需要的最高級需要(Kenrick, Griskevicius, Neuberg, & Schaller,2010; Kenrick & Griskevicius, 2015)。人類與動物一樣, 其所有心理與行為的終極功能是成功繁衍。人類諸多行為, 包括藝術創作、慈善行為以及致力于改善后代的未來環境等積極行為都是由這一本能的無意識目標所催發的。只是人類對此缺乏了解。與人本主義觀點不同, 進化論認為所謂積極高尚的行為只是在追求終極繁衍目標時帶來的“副產品”, 也只有在進化論觀點基礎上充分認識人的本性, 才能真正促進積極心理學的發展。
當然, 進化注重的是基因遺傳率的最大化,而不是個體幸福。而從適應的角度來說, 基本需要的滿足自然會帶來獎勵性或心理愉悅性的結果。但需要注意的是, 對需要滿足的追求過程和需要的滿足狀態是兩回事, 很多與養育孩子相關的行為本身并不具有獎賞性質。生兒育女的心理收益可能要直到該目標全部完成——即將孩子撫養成人——之后才能完全獲得(Schaller, Neuberg,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0)。其次, 該理論也強調低級需要的優先地位。如果低級需要(如溫飽、安全)無法滿足的話, 作為高級需要的生兒育女是不會帶來快樂的。況且, 養育孩子是可能影響到低級需要(如安全、人際關系、配偶維持等)的滿足的, 其過程有可能對個人幸福帶來消極影響(Nelson,Kushlev, & Lyubomirsky, 2014)。
2.2.3 恐懼管理理論
恐懼管理理論認為, 相比于動物, 人類獨有的高級意識功能使得我們知曉自己終將死亡, 并隨之產生深深的恐懼。死亡恐懼是人類動機的核心源泉, 堅持自己的文化世界觀和維持自尊則是兩個基本的恐懼管理機制。而具體的實證研究則猶以死亡凸顯效應的研究為盛(陸可心, 沈可汗,李虹, 2017)。已有研究發現, 孩子是緩解個體死亡焦慮的一個重要途徑。在死亡凸顯下, 個體的生育意愿更強, 也更關心家族中的年幼者(Zhou, Liu,Chen, & Yu, 2008)。但這種效應并不僅限于自己的后代, 廣泛意義上后代的概念甚至新生動物的照片都能起到這樣的效果(Zhou, Lei, Marley, &Chen, 2009)。Zhou 等人(2008)認為, 一方面, 親生子女本身就意味著自己生命在某種形式上的延續,而在符號意義上, 嬰兒或后代也代表著死的反義詞——生和延續。另一方面, 孩子也可以通過傳遞個人的文化世界觀和提高其在社會上的認同和自尊來緩解死亡焦慮。總而言之, 在該觀點看來,生兒育女的行為以及對孩子和新生命的廣泛關注是人類應對死亡焦慮的有效防御。
但也有研究發現這種效應可能存在文化差異。比如, 對于荷蘭女性被試而言, 死亡凸顯與生育意愿的關系受到其事業心的調節作用影響。具體而言, 對于事業心強的女性來說, 只有當為人母與事業相和諧時, 死亡凸顯才會增強其生育意愿, 否則反而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Wisman &Goldenberg, 2005)。但這一調節作用并沒有在德國和中國女性中表現出來。
2.3 生育對幸福存在不確定的影響
2.3.1 比較理論
幸福的比較理論認為, 幸福感來源于自己目前實際的生活狀況與個體所認同的價值觀與目標之間的比較。比較的標準包括他人、過去、理想中的狀態、主觀設定的目標等等。各種比較之后的結果又相互影響, 最終決定其幸福水平。如果個體的現狀達到或超過個體期待, 就會產生幸福感(Plagnol & Easterlin, 2008; Easterlin, Morgan,Switek, & Wang, 2012)。
如前所述, 就目前而言, 生兒育女是被絕大部分人認可的生活目標。因此, 為人父母本身就會帶來社會認同感、自尊感以及生活滿足感。同時, 養育孩子的過程還為父母提供了其它非常有價值的目標去追求(如為孩子提供食物、居所、情感、監護和教育等) (Delle Fave & Massimini, 2004),并幫助父母以更加宏觀和深刻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生活的目的。該觀點強調即時積極情緒與幸福的不同, 認為只有個人達成目標后所獲得的長期穩定的滿足才能叫做幸福。但是, 對于那些不將生兒育女作為生活目標的人來說, 生兒育女的意義就另當別論了。
歐洲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就認為, 社會的發展已經帶來公眾價值觀的改變, 人們越來越看重個人自由和自我實現。其中, 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工資薪酬的普遍提升被認為是主要原因。Aassve,Mencarini和 Sironi (2015)則分析認為, 更高的受教程度確實促使女性人生志向發生結構性改變,但女性生育意愿并沒有降低, 只是對職業生涯的成功有了更多期待, 對平衡工作與家庭有了更多要求。總而言之, 基于幸福的比較理論, 生育的必要性以及生育?幸福關系可能會隨著社會發展和大眾觀念的變化而變化。
2.3.2 自我決定理論
自我決定理論強調自主、關系和能力是人類三種基本心理需要(Deci & Ryan, 2008), 生兒育女并不是人類的基本需要, 但該行為會以三種心理需要為中介顯著而持久的影響個體的幸福。首先, 關系需要方面, 孩子為父母提供了持續的愛與親近感的來源。尤其是, 與孩子積極相處的母親表現出總體上更多的快樂與愉悅。與此同時,與孩子的沖突則與父母總體上更低的幸福感相聯系(Kiecolt, Blieszner, & Savla, 2011)。除此之外,生兒育女還為父母提供了進一步發展親屬關系、朋友關系和社區關系的機會。有研究表明, 相對于無子女者, 為人父母者表現出更好的與親屬、朋友和社區的社交融合(Nomaguchi & Milkie,2003; Hartas, 2014)。其次, 在自主需要方面, 為人父母是個體邁向成年和獨立的重要標志, 同時也預示著個體開始可以管控自己的行為及結果。另一方面, 生兒育女也將帶來父母精力的消耗, 休閑時間的減少, 從而可能降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感。能力需要方面, 身為父母的效能感被證實非常顯著的預測個體的家庭生活滿意度(Bandura,Caprara, Barbaranelli, Regalia, & Scabini, 2011)。總而言之, 該理論認為生兒育女作為一項重要的生活事件, 將以顯著而又間接的方式影響個體幸福。
2.3.3 收益?代價的觀點
很多家庭領域的研究者則綜合各觀點認為,為人父母者從生兒育女中既獲得了諸多益處, 也要付出各種代價, 二者之間的中和決定特定個體與家庭的生育?幸福的關系。隨著社會發展進步,現代人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成年人并不重視也較少從子女那里獲得經濟性收益, 心理性收益的重要性更加凸顯(Pollmann-Schult, 2014)。如前所述,孩子可以滿足父母的心理需要, 帶來諸如歡快、逗趣、興奮等直接的積極心理體驗, 幫助父母新建或加深人際關系, 還有助于成年人以父母的身份增強社會認同。
生育代價則主要區分為三大類(Pollmann-Schult,2014):(1)時間代價。生兒育女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用于照料孩子和做家務。為人父母者的休閑時間、睡眠時間以及夫妻二人相處的時間都可能隨之大幅減少, 進而影響自身的健康與生活質量。對于社會經濟地位較高者, 這種時間成本顯得更大(DeVoe & Pfeffer, 2011)。(2)情緒代價。較之于無子女者, 為人父母者總是對自己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問題過度擔心, 從而更多感受到害怕、不安和擔憂。而從進化論視角來看, 父母這種高度的警惕和擔心狀態是具有適應性的(Hahn-Holbrook,Holbrook, & Haselton, 2011)。另一方面, 為人父母者也會因為孩子對自己權威的挑戰, 而更容易感受到憤怒, 也更多的感受到工作與家庭生活的沖突。(3)經濟代價。它包括家庭開支的增加, 也包括父母一方辭職帶孩子或減少工作時間所帶來的家庭經濟收入的減少。
在無子女者方面, 已有研究表明, 他(她)們表現出較高的且穩定的經濟和休閑方面的滿意度,較少的擔憂、壓力以及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使用方面的靈活性(Keizer, Dykstra, & Poortman, 2010)。但從另一角度來講, 適當的挑戰、負擔有助于個體的發展以及對穩定深刻幸福的獲得, 責任方面的缺乏則可能帶來“空虛的生活” (Karlsen, Dybdahl,& Vitters?, 2006)。現實中自愿放棄生育的人群比率其實很低, 這從側面反映出, 對于大多數無子女者而言, 他們確實錯失了一項重要人生目標的達成。最后, 無子女者也可以對自己無子女的狀態產生適應。研究發現他(她)們在發展和深化替代性的社會關系方面富有創造性(Wenger, Dykstra,Melkas, & Knipscheer, 2007)。
3 直接的實證研究及總體結論
目前, 直接探討生育?幸福關系的實證研究多為人口學調查, 也有少量研究基于心理學視角。主要研究途徑包括跨群體比較研究、跨期追蹤研究和育兒體驗研究三種, 另有一些研究涉及到有關的生理機制。
3.1 跨群體比較研究
該取向的研究將父母與成年無子女者在總體幸福狀態方面進行比較。但是, 相關的結論并不一致, 有的研究發現父母群體幸福感水平更低,有的發現父母群體幸福水平更高, 也有的發現沒有差異(Aassve, Goisis, & Sironi, 2012; Nelson,Kushlev, English, Dunn, & Lyubomirsky, 2013)。這些矛盾結果可能跟樣本類型、幸福的測量指標與工具的差異性有很大關系。
一些基于全國性大樣本的調查與比較(Nelson et al., 2013; 李婷, 范文婷, 2016)則顯得更具價值。這些包含了各種年齡段、職業、收入、婚姻狀況等的樣本數據使得研究者從整個生命歷程角度考慮生兒育女與幸福感關系, 以及對二者關系中的很多復雜調節變量的探究成為可能。缺點則在于, 這種大樣本調查中對幸福感的考察通常只是基于某個單一題項而非信效度完善的完整量表。
3.2 跨期追蹤研究
這種方法主要追蹤考察為人父母者生育前后的幸福感變化, 相關研究結果也不盡一致。有研究結果表明初為父母者的幸福感在孩子出生前后短期內急劇上升, 但在隨后的兩年內回歸到懷孕前的幸福水平(Dyrdal & Lucas, 2013)。也有研究表明為人父母者的生活滿意度變化確實是先增后減,但其積極情緒總體上是增加的(Luhmann, Hofmann,Eid, & Lucas, 2012)。也有研究得出結論, 初為父母者的喜悅極其短暫, 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壓力和煩惱, 快樂程度和生活滿意度再也不能恢復到先前水平了(Clark et al., 2008)。
Pollmann-Schult (2014)則在對德國大樣本的跨期十幾年的縱向調查數據進行重新分析后發現,在控制了生育的經濟和時間成本因素后, 生兒育女顯示出對父母生活滿意度顯著而持久的積極影響作用。相對于調定點理論, 該結論支持收益?代價的觀點。進一步的分析還證實, 對于父親而言, 這種積極效應主要受到了經濟壓力的抵消; 母親則同時受到時間代價和經濟壓力的影響。Lyubomirsky和 Boehm (2010)則強調, 孩子年幼時, 父母付出的代價和成本確實很大, 但從長遠來看, 尤其是考慮到老年以后, 生兒育女的積極影響才是更加顯著的。
但是, 總體上而言, 在這些研究中, 對父母幸福基線的測量時間通常在生育前的 1年左右,而隨后的追蹤期限則都在 5年內, 相比于父母對孩子將近20年的實際養育來說, 已有研究的時間跨度無法完整說明生育與幸福的關系。由此得出的生育對父母幸福感的消極影響就可能被夸大(Nelson et al., 2014)。
3.3 育兒體驗研究
該方法將育兒行為體驗與其它日常活動中的體驗進行比較。具體來說, 研究者要求父母回顧一天的不同時間段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對各個時間段的情緒體驗進行評價。有研究要求被試對各種活動就其積極體驗程度進行排序, 結果有的發現母親僅將照顧孩子置于 16種日常活動的第 12位(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2004), 有的研究則得出更積極的結果(Nelson et al., 2013)。Kushlev, Dunn和 Ashton-James (2012)的心理實驗則發現, 金錢啟動會降低父母陪伴孩子時的意義感, 但對積極情緒的體驗沒有影響。
相比于前兩種方法, 該方法關注的是個體實際與孩子相處時的即時體驗而不是對自己總體幸福感的反思和評估。也正因為如此, 它不能說明為人父母者的整體幸福感狀況, 也無法與無子女者進行對比。
3.4 生理機制研究
有研究比較個體對嬰兒面部與成人面部的加工機制發現, 對兩者的加工都能激活初級和高級的視覺區域神經活動, 而對嬰兒面部的加工能激活更多的腦部神經活動區域。使用fMRI和NIRS(Minagawa-Kawai et al., 2009)的研究都發現, 母親看著嬰兒的臉時, 積極情緒增加并伴隨眶額皮層(OFC)神經活動增強; 而 OFC神經活動的增強被認為與獎勵處理機制相關。事實上, 這種反應在父母與非父母群體中都普遍存在, 生育行為的產物——嬰兒能激活“養育腦”區域的神經活動,增加人們的愉悅度, 提高人們的幸福感(Strathearn,Fonagy, Amico, & Montague, 2009; 張茂楊, 彭小凡, 胡朝兵, 張興瑜, 2015)。
另有研究發現, 嬰兒的哭聲會激活父母群體被試右側杏仁核的活動, 該神經活動與壓力癥狀相關, 如焦慮或強迫性的想法和行為(Kim, Strathearn,& Swain, 2016), 非父母群體則不會有相同的反應。高皮質醇激素水平的父母對嬰兒的需要更加敏感, 而皮質醇是唯一與認知的準確性相關以及對嬰兒產生積極情緒的的激素(Parsons, Young, Murray,Stein, & Kringelbach, 2010)。
這些研究從生理層面描述了人類普遍會從生育中獲得的復雜體驗, 而這些或積極或消極的情緒在進化論觀點看來均具有適應性。當然, 此類研究也無法觸及人類的意義感、整體幸福感等概念。
3.5 復雜調節變量的影響
如前所述, 各種研究范式都得出了不那么統一的結論。研究者也普遍認可, 生育?幸福關系會受到多種調節變量的復雜影響, 但具體的影響結果也不一致。Nelson等人(2014) 主要基于西方的研究結論, 梳理出比較統一的幾個調節變量的影響:(1)父親比無子女的男性更幸福(Keizer et al.,2010; Nelson et al., 2013)。(2)中年或老年的父母相對于無子女者同等幸福或更加幸福, 年輕的父母相對于無子女者則幸福感較低(Nelson et al.,2013); (3)子女年齡方面, 孩子較小的父母幸福水平相比于無子女者更低, 這種狀況可能持續到孩子5歲左右(Clark et al., 2008); (4)家庭經濟地位。生兒育女對家庭經濟地位高的父母帶來了消極的影響。高階層父母較之于低階層父母, 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感受到的意義感和目的感更低(Kushlev et al., 2012)。這與高階層父母更追求個體性目標, 感受到更大的時間壓力與機會成本有關(DeVoe & Pfeffer, 2011)。除此之外, 還有其它一些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素的影響, 比如非婚父母、社會支持度較低的父母的幸福水平更低等。
國內人口學研究多關注子女的數量及性別因素的調節作用, 結論也不一致。比如, 王偉、景紅橋和張鵬(2013)發現對于中老年人來說, 孩子數量減少并沒有降低其幸福感。穆崢和謝宇(2014)則發現, 更多的孩子對父親、母親的自信心、生活滿意度等各方面均有積極影響。王欽池(2015)發現, 子女數量對幸福感的影響是非線性的, 子女的性別結構和性別次序對父母幸福感均有影響。李婷和范文婷(2016)則發現, 更多的孩子對處于中青年時期的父母產生負面影響, 卻會顯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時期的幸福感。除此之外, 對農村父母來說, 生育兒子會在其整個生命周期內產生略微正向的幸福效應; 但是對城市父母來說, 生育兒子會顯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
4 其它爭議性問題
4.1 幸福的定義與測量
事實上, 心理科學對其幸福結構的定性也就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徐曉波, 孫超, 汪鳳炎,2017)。西方研究者普遍強調其廣闊內涵, 并使用幸福(well-being)、主觀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和快樂(happiness)等相關概念。在具體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對父母幸福的測量會各自圍繞情緒體驗(emotional experience)、主觀快樂(subjective happiness)、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生命意義感(meaning in life)中的一種或幾種, 有時也包括了自尊、抑郁和其它心理癥狀。因此, 對幸福的不同定義與測量也導致生育?幸福關系結論的不一致。
其中, 生活滿意度被普遍看作是基于理想和現實狀況比較后的結果, 屬于幸福(Well-being)的認知評價成分。快樂(Happiness)的概念則可能有不同內涵, 有的將其視為一種情緒狀態, 類似于積極情緒而非生活滿意度, 有的則認為它與生活滿意度是相似的概念。Hansen (2012)總結認為,兩者之間僅有25%~50%的共變, 應當被視為相互獨立的概念實體, 分別與生育有不同的關聯路徑。其中, 生活滿意度具有較大的認知成分, 因此親生子女的存在普遍會促進為人父母者的生活滿意度, 而不論其是否與他們生活在一起; 這種效應在那些對孩子賦予極大價值的社會群體中尤其明顯。相反, 快樂(happiness)則對消極或積極的日常育兒體驗更加敏感, 也因此更容易在繁重的生育壓力和責任面前表現出負面的結果。
另一方面, 盡管積極情緒與生命意義感呈現穩定的高相關, 但生兒育女被認為更有利于促進個體的意義感而非快樂或者積極情緒(Hansen,2012)。從概念上來說, 意義感被定義為對生活的目的感和方向感, 它使得個體的行為與努力在大于自己的某些概念或層面上顯得有意義。縱向研究證明, 向照料者身份的轉換盡管付出心理健康和快樂方面的代價, 但卻同時促進意義感(Marks& Fleming, 1999)。養育子女過程中所包含的挑戰與犧牲可能正是為人父母者的意義感提升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 Kushlev等人(2012)證實, 金錢啟動對父母陪伴孩子時的情緒體驗和意義感體驗作用不同。
Hansen (2012)認為, 生兒育女對于促進自我實現的幸福(eudaimonic well-being)效果更大, 因為這一概念包含了例如成長、發展等存在主義的概念。但相關的實證研究還很少見。Lyubomirsky和 Boehm (2010)則認為, 為人父母者在生兒育女中獲得的獨有的積極體驗——深沉的愛、美妙而復雜的情感等——是傳統紙筆測驗無法測量的。幸福也并不是所有積極情緒的簡單相加。生兒育女拓寬了個體生命體驗的廣度, 其中包含了極大的積極情緒(比如驕傲的看著孩子走出人生第一步), 也可能包含極大的消極情緒(比如痛苦于孩子的痛苦)。人生的意義就在于獲得多樣的情緒和體驗, 而不僅是積極的情緒——“深愛然后失去也好過從來沒有愛過”。
4.2 社會變遷中的生育?幸福關系
近幾十年以來, 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日益呈現出生育率大幅下降的趨勢。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越來越關注社會的發展進步對現代人生育決策以及生育?幸福關系的影響(Aassve et al., 2012)。
Lyubomirsky和Boehm (2010)指出, 現代撫養孩子的環境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 孩子自青春期就已開始獨立出來, 而現代法律要求父母必須承擔撫養子女的義務到至少18歲。此外, 從歷史上來講, 撫養子女本是一項集體任務。祖先們通常是在一個大的村莊、宗族或部落的環境下撫養后代, 育兒責任由所有大家庭成員甚至鄰居們共同分擔。而在當代普遍性的小家庭環境下, 只有兩人來承擔撫養孩子的一切, 其壓力程度大增。除此之外, 受教程度的廣泛提升促使女性開始重視個人自由和事業的成功。對財富的關注則被證明會啟動個體的能動目標(agentic goals), 它與生育相關的共生目標(communal goals)相沖突(潘哲,郭永玉, 徐步霄, 楊沈龍, 2017), 導致個體專注于個體性的和獨立性的目標, 從而降低人們在生育活動中的意義感(Kushlev et al., 2012)。該結論支持幸福的比較理論。
但 Aassve等人(2015)強調, 現代人日益重視能動目標的趨勢并不一定直接影響生育?幸福的關系的發展, 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社會體制是否能夠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在他們看來, 這種變化就是在北歐國家所呈現出的從傳統社會向平權社會(egalitarian societies)的轉變。平權社會以男女在制度和社會文化上的平等為核心特征, 在生育相關的方面上則具體表現為, 家庭分工模式從傳統的“男人養家”模式(male bread winner model)向夫妻共同負擔模式(dual earner model)轉變, 以及對傳統家務(包括照顧孩子和老人)的外包化。基于歐洲社會普調的數據分析結果間接的支持了該觀點。在他們看來, 面對現代人能動目標日益凸顯的必然趨勢, 傳統社會向平權社會轉變與否以及轉變的快慢將直接決定不同國家和地域人們生育?幸福關系的不同發展趨勢。而這其中, 一個社會的總體社會信任度、文化規范以及政治形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 在社會信任度高、文化和宗教約束少以及水平型政治組織框架下,這種轉變更容易發生。
Nauck (2014)則在結合了社會生產功能理論(Theory of Production Functions)和生育價值觀點(Value of Child)的基礎上, 從社會學的觀點提出,生育行為是人類追求總體社會福利(生理健康和社會期許)最大化的一種重要途徑。具體的社會環境與條件決定了生育行為在實現這一終極功能中的效能, 也影響了此文化下有關生育的主流觀念與規則, 最終決定了生育行為發生的概率和代際關系模式。在此觀點之下, 某個文化下每一個個人的體驗和感受并不重要, 所謂生育決策是一套暗合社會功能最大化要求的內隱機制。在這樣的觀點下, 一些研究者已開始討論, 隨著社會發展進步, 在更好的追求總體社會福利的前提下, 由其它活動或社會關系來替代生兒育女這種社會行為的可能性。
5 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 生育?幸福關系是一個關乎每個個體與家庭, 也關乎整個社會的復雜問題。相關理論中有的關注人類本性和基本需要, 有的注重社會制度、大眾觀念的影響, 還有的則強調個體自身特質的決定性作用。已有研究中, 以寬泛的人口學調查居多, 而以心理學理論為支撐的對生育?幸福關系的心理機制的探索或實證較少。已有研究結論在某些方面已得出共識, 但在更多方面仍留下矛盾或未明之處。未來的研究可以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5.1 人性哲學的深入探討
我們非常認同 Kenrick等人的這一看法:即只有充分認識人的本性, 才能真正促進人類的幸福。生兒育女是否是人類的天性或必要的成長經歷?它是一種人性的基本需要還是一個實現其它功能的工具?這種行為與關系是否可替代?
進化心理學家以基因延續為終極功能闡述了人類這一行為背后與動物相同的本能基礎, 并將其視為人類最高層次的基本需要。積極心理學和恐懼管理理論則強調人類相對于動物所獨有的特征。比如, Peterson和Park (2010)堅持認為, 自我實現(創造、認知好奇心、藝術)才是人類獨一無二的高級需要, 它可能是進化而來的, 但已經完全獨立出來, 成為人類獨有的高級需要, 對這一需要的追求絕不是為了安全, 為了炫耀以獲得配偶或者為了生兒育女。恐懼管理理論則將人類對新生命的廣泛喜愛與照顧視為對抗死亡焦慮的防御性措施之一, 是具有可替代性的。當然, 后兩者之間仍然有極大的沖突, 即生兒育女究竟是一種成長中的主動傾向, 還是被動防御性的行為。Kesebir,Graham和Oishi (2010)則在承認“沒有人能夠真正意義上脫離生物性”的同時也認為, 不同于動物,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受到文化的重要影響。文化會通過創造不同的環境來對人類在進化過程設定不同的優勝劣汰的選擇模式, 從而影響人類的基因組變化, 帶來人類相對于動物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質變。對理智與意義感的追求才是人類最高級的基本需要; 而對理智和意義感的定義則受到文化的影響。在此觀點看來, 自我實現或是生兒育女都只是不同文化下人獲得理智感或意義感的一個選項之一。
心理學關于人類本性及其與自然、社會環境關系的探討, 應當是幸福領域研究中永恒的主題。一方面, 對人性哲學的探討將促進我們對生兒育女?幸福關系的深刻理解; 另一方面, 從生育行為出發, 我們也可以對各種人性動機理論進行獨特的比較、分析和驗證。
5.2 對社會群體異質性的充分考慮
在未來研究中, 研究者需要充分考慮各社會群體的異質性。事實上, 所有有關生育動機的心理學理論(包括進化心理學的理論), 都承認不同社會文化或經濟條件對生育行為及其影響的制約作用。
已有的絕大多數實證結論都基于歐洲、北美的數據, 而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國情更會帶來大眾在生育的年齡、典型的子女數量、父母對子女的關注程度、性別角色、父母親自養育的程度、生育動機、產假與陪護假制度以及兒童福利狀況等等諸多方面的廣泛差異(Nauck, 2007)。況且, 文化也會導致個體對幸福感、生活滿意以及意義感的不同理解以及對情緒的不同體驗和表達。因此,我們在借鑒已有西方研究結論時要格外審慎。具體而言, 首先, 我們應當對當前中國人的生育觀念進行廣泛調查, 因為它不僅反映大眾的主觀態度, 更將作為輿論和社會期待直接影響為人父母者以及無子女者的幸福水平。另一方面, 更為重要的是, 我們要積極實施基于我國人群大樣本的系統追蹤調查和橫向比較。目前,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等項目為此提供了可能。已有國內研究者基于這些數據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結論(穆崢, 謝宇, 2014; 王欽池, 2015; 王偉等, 2013)。但是, 由于起步時間較晚, 測量幸福的問題單一等問題, 國內研究仍需要更長時間數據的積累以及在調查中對生育?幸福問題上的格外關注。最后, 我們還要重點考察我國特有的文化和社會現象如孝道思想、隔代教養現象等對生育?幸福關系的影響。事實上, 在考慮到與這些因素相匹配的情況下, 我國有關生育的理想政策、制度乃至社會形態可能會與西方存在一些差異。
即便是在同一國家內, 不同人群在生育?幸福關系上的異質性也很明顯。Galatzer, Mazursky,Mancini和 Bonanno (2011)曾基于這一視角對Clark等人(2008)的研究所得出的消極結論進行質疑。他們使用潛變量增長混合模型對同批數據進行重新分析, 發現生育對不同群體的生活滿意度有三條完全不同的影響軌跡, 多軌跡模型比單軌模型表現出更好的數據擬合度。如前所述, 國內研究(李婷, 范文婷, 2016)也發現了生育?幸福關系的異質性現象。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強調, 以過度概括化方式來探討研究生育?幸福關系已經缺乏意義(Galatzer-Levy et al., 2011; Nelson et al., 2014)。這提醒我們,在進行大樣本調查和分析的同時, 依據不同年齡性別、不同階層或其它亞文化群體的特征進行更加細致和有針對性的調查實證是非常必要的。比如, 對具有較高和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女性進行對比研究應具有前瞻性。一方面, 女性在生和育的方面都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 基于這兩類群體的對比, 我們可以更加深刻的探討不同人類需要、自我發展以及社會進步對生育?幸福關系的影響。
5.3 基于心理學視角的實證研究
未來研究者應在已有人口學研究基礎上, 以心理學的視角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理解。雖然已有諸多心理學觀點就生育行為的功能以及生育?幸福關系進行了解讀, 但已有的實證研究——尤其追蹤研究——更多只考慮了人口學變量或者基于較為簡單甚至單一題項的測量工具完成。這導致相關研究結果零散甚至矛盾, 不好解釋, 也無法為進一步的干預給予指導。未來需要更多結合基礎心理學理論與嚴謹范式, 以探索內部心理機制為前提的研究, 對已有理論觀點進行檢驗和發展。對生育?幸福關系中各種心理性的中介變量的研究應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而已發現的起到顯著影響作用的人口學變量背后的心理原因值得進一步追究。也許未來, 生兒育女可以被進一步精確描述為一個包含了各種心理壓力、體驗與收益的系統概念和過程。
還需要注意的是, 幸福是一個動態多維的開放系統(黃希庭, 李繼波, 劉杰, 2012)。心理學在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意義感等概念及其關系方面的研究都應當被充分納入對生育?幸福的考察。在對幸福的評定中, 還要更多包含對自我實現的幸福、精神幸福感(徐曉波等, 2017)的測量。另一方面, 圍繞生育的體驗, 未來應展開更多探究。現有觀點更多以類似于“實物消費”的角度探討有或沒有孩子的代價與收益, 有關體驗研究也只是針對零碎的育兒活動進行表面化的排序和打分。事實上, 體驗而非實體性的占有將更大程度促進個體幸福, 也與自我聯系更緊密(Carter & Gilovich, 2012; Kumar, Killingsworth, &Gilovich, 2014)。并且, 在當下的體驗本身之外,體驗前的期待和體驗后的回憶也對個人幸福感有很大影響。如前所述, 生兒育女的體驗是獨一無二的, 其持續時間較長, 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較之于其它生活事件顯得更加復雜且影響深遠。它混合了各種積極和消極的情緒, 涉及到個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連系起了個人、家庭和社會, 更暗含了生與死的意義。從完整歷程上來看, 個體在生育之前的期待以及伴隨其間的對自我的重新定位與反思, 生育過程中的辯證情緒體驗與角色適應以及在孩子成年獨立后的思念與回味, 乃至在暮年之后從后代身上獲得的希望與永恒感都值得我們逐一研究。事實上, 心理學家對于幸福本身的研究也遠沒有終結, 其內涵源于人類在各種活動中的體驗和反思, 并可能隨著人類發展而不斷豐富。對生育體驗的深入研究也將促進我們對幸福概念本身的理解。
5.4 干預與管理對策研究
對生育?幸福關系內在機制的探討以及對生育行為的心理功能的研究將有助于有關心理健康服務的開展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 研究者還需要更好的融合多學科的理論和扎扎實實基于我國國情的探索性研究。
在心理健康服務方面, 我們需要結合更加充分的本土化研究數據和實際案例解決至少以下一些問題:對于有生育意愿者, 如何幫助其在生育時間、生育數量方面作出理性決策?對已為人父母者, 如何幫助他們正確認識和對待生兒育女中所謂的收益與代價?對無子女者或失子女者, 如何幫助其獲得和維持有效的替代性活動與關系?
從形式上而言, 以“第一接觸”和長期性為特點的社區心理健康服務應當成為此方面的重點。在實踐中, 國外還有很多專業人員指導社區普通居民共同參與一些綜合性社區項目, 對居民心理健康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促進作用(徐華春, 黃希庭,2007)。從另一角度而言, 一些社區中已存在的好的育兒互助模式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 檢驗并進行科學化推廣。正如 Lyubomirsky和 Boehm(2010)所言, 從傳統上來看, 撫養子女本是“一個村莊集體的責任”。未來以科學理論為基礎, 以專業的社區心理服務中心為支點, 重新發揮集體的作用來解決生育代價問題以及無子女老人的社會支持問題應當是一個好的途徑。當然, 社區心理服務在此方面的工作不能單獨開展, 它依賴于完整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和自上而下的專業指導和監督。
除此之外, 未來研究者需要針對一些重點人群進行嚴謹的干預研究。基于已有調查結果, 女性、年輕父母、單身父母應當是可能的重點人群;成年無子女者、失子女者中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較低者也應當格外關注。而在具體的干預設計上, 研究者需要從基礎研究中獲得指導, 在對生育的基本心理功能以及生育的代價機制的深刻了解基礎上, 針對不同亞群體發展出有針對性的、步驟明確的干預項目。事實上, 基礎理論與實證的研究也需要從這些干預實踐中獲得再驗證, 也勢必從中獲得完善與發展。
宏觀上而言, 個體的生育?幸福關系與國家制度、政策及輿論引導密不可分,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又與每個個體的生育行為息息相關。在中國, 未來如何因應時代變化, 調整人口政策, 改革福利分配制度, 提高社會信任, 解決就業中的性別平等問題, 才能達到個體與國家在此問題上利益的最大化, 將是未來需要心理學、人口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多領域研究者共同努力的問題。
黃希庭, 李繼波, 劉杰. (2012). 城市幸福指數之思考.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5), 83–91.
李婷, 范文婷. (2016). 生育與主觀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歷程的視角.人口研究,40(5), 6–19.
陸可心, 沈可汗, 李虹. (2017). 恐懼管理理論中情緒的作用.心理科學進展,25(1), 76–85.
穆崢, 謝宇. (2014). 生育對父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社會學研究, 29(6), 124–147.
潘哲, 郭永玉, 徐步霄, 楊沈龍. (2017). 人格研究中的“能動”與“共生”及其關系.心理科學進展, 25(1), 99–110.
王欽池. (2015). 生育行為如何影響幸福感.人口學刊,37(4), 12–24.
王偉, 景紅橋, 張鵬. (2013). 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嗎——80后一代視角的研究.人口研究, 37(2),102–112.
徐華春, 黃希庭. (2007). 國外心理健康服務及其啟示.心理科學,30(4), 1006–1009.
徐曉波, 孫超, 汪鳳炎. (2017). 精神幸福感: 概念、測量、相關變量及干預.心理科學進展,25(2), 275–289.
張茂楊, 彭小凡, 胡朝兵, 張興瑜. (2015). 寵物與人類的關系: 心理學視角的探討.心理科學進展, 23(1),142–149.
Aassve, A., Goisis, A., & Sironi, M. (2012). Happiness and childbearing across Europ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08,65–86.
Aassve, A., Mencarini, L., & Sironi, M. (2015). Institutional change, happiness, and fertility.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6), 749–765.
Bandura, A., Caprara, G. V., Barbaranelli, C., Regalia, C., &Scabini, E. (2011). Impact of family efficacy beliefs on quality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atisfaction with family life.Applied Psychology, 60,421–448.
Carter, T. J., & Gilovich, T. (2012). I am what I do, not what I have: The differential centrality of experiential and material purchases to the self.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6), 1304–1317.
Clark, A. E., Diener, E., Georgellis, Y., & Lucas, R. E.(2008). Lags and leads in life satisfaction: A test of the baseline hypothesis.The Economic Journal,118(529),F222–F243.
Clark, A. E., & Georgellis, Y. (2013). Back to baseline in Britain: Adaptation in the BHPS.Economica,80(319),496–512.
Deci, E. L., & Ryan, R. M. (2008).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A macro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health.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49,182–185.
Delle Fave, A., & Massimini, F. (2004). Parenthood and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in daily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7, 75–106.
DeVoe, S. E., & Pfeffer, J. (2011). Time is tight: How higher economic value of time increases feelings of time pressur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 665–676.
Dyrdal, G. M., & Lucas, R. E. (2013). Reaction and adaptation to the birth of a child: A couple-level analysi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 749–761.
Easterlin, R. A., Morgan, R., Switek, M., & Wang, F. (2012).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25), 9775–9780.
Erikson, E. H. (1963).Childhood & society. New York:Norton.
Galatzer-Levy, I. R., Mazursky, H., Mancini, A. D., &Bonanno, G. A. (2011). What we don't expect when expecting:Evidence for heterogeneity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esponse to parenthood.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5(3),384–392.
Hahn-Holbrook, J., Holbrook, C., & Haselton, M. G. (2011).Parental precaution: Neurobiological means and adaptive ends.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5, 1052–1066.
Hansen, T. (2012). Parenthood and happiness: A review of folk theories versus empirical evidenc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08(1), 29–64.
Hartas, D. (2014). The social context of parenting: Mothers’inner resources and social structures.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 30(5), 609–634.
Headey, B. (2010). The set point theory of well-being has serious flaws: On the eve of a scientific revolution?.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7(1), 7–21.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A., Schwarz, N.,& Stone, A. A. (2004).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Science, 306(5702), 1776–1780.
Karlsen, E., Dybdahl, R., & Vitters?, J. (2006). The possible benefits of difficulty: How stress can increase and de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47(5), 411–417.
Keizer, R., Dykstra, P. A., & Poortman, A.-R. (2010). Life outcomes of childless men and father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15.
Kenrick, D. T., & Griskevicius, V. (2015). Life history,fundamental motives, and sexual competition.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 40–44.
Kenrick, D. T., Griskevicius, V., Neuberg, S. L., & Schaller,M. (2010). Renovating the pyramid of needs:Contemporary extensions built upon ancient foundations.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5(3), 292–314.
Kesebir, S., Graham, J., & Oishi, S. (2010). A theory of human needs should be human-centered, not animal-centered:Commentary on Kenrick et al. (2010).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3), 315–318.
Kiecolt, K. J., Blieszner, R., & Savla, J. (2011). Long-term influen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on midlife par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3, 369–382.
Kim, P., Strathearn, L., & Swain, J. E. (2016). The maternal brain and its plasticity in humans.Hormones and Behavior,77, 113–123.
Kumar, A., Killingsworth, M. A., & Gilovich, T. (2014).Waiting for merlot: Anticipatory consumption of experiential and material purchases.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0),1924–1931.
Kushlev, K., Dunn, E. W., & Ashton-James, C. (2012). Does affluence impoverish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6), 1381–1384.
Lucas, R. E. (2007). Adaptation and the set-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happiness change after major life event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6(2), 75–79.
Luhmann, M., Hofmann, W., Eid, M., & Lucas, R. E. (2012).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daptation to life events: a meta-analysi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02, 592–615.
Lyubomirsky, S., & Boehm, J. (2010). Human motives,happiness, and the puzzle of parenthood: Commentary on Kenrick et al. (2010).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5(3), 327–334.
Marks, G. N., & Fleming, N. (1999). Influ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well-being among Australian young people:1980-1995.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6(3), 301–323.
Minagawa-Kawai, Y., Matsuoka, S., Dan, I., Naoi, N.,Nakamura, K., & Kojima, S. (2009). Prefrontal ac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social attachment: Facial-emotion recognition in mothers and infants.Cerebral Cortex,19(2), 284–292.
Myrskyl?, M., & Margolis, R. (2014). Happin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kids.Demography, 51(5), 1843–1866.
Nauck, B. (2007). Value of children and the framing of fertility: Results from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urvey in 10 societie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5), 615–629.
Nauck, B. (2014). Value of children and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welfare.Demographic Research, 30, 1793–1824.
Nelson, S. K., Kushlev, K., English, T., Dunn, E. W., &Lyubomirsky, S. (2013). In defense of parenthood: Children are associated with more joy than misery.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3–10.
Nelson, S. K., Kushlev, K., & Lyubomirsky, S. (2014).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of parenting: When, why, and how is parenthood associated with more or less well-being?.Psychological Bulletin,140(3), 846–95.
Nomaguchi, K. M., & Milkie, M. A. (2003). Costs and rewards of children: The effects of becoming a parent on adults' live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5(2), 356–374.
Parsons, C. E., Young, K. S., Murray, L., Stein, A., &Kringelbach, M. L. (2010). The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the evolving parent–infant relationship.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91(3), 220–241.
Plagnol, A. C., & Easterlin, R. A. (2008). Aspirations,attainments, and satisfaction: Life cycl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women and men.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4), 601–619.
Peterson, C., & Park, N. (2010). What happened to selfactualization? Commentary on Kenrick et al. (2010).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3), 320–322.
Pollmann-Schult, M. (2014). Parenthood and life satisfaction:Why don't children make people happ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76(2), 319–336.
Schaller, M., Neuberg, S. L., Griskevicius, V., & Kenrick, D.T. (2010). Pyramid power: A reply to commentaries.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5(3), 335–337.
Strathearn, L., Fonagy, P., Amico, J., & Montague, P. R.,(2009). Adult attachment predicts maternal brain and oxytocin response to infant cues.Neuropsychopharmacology,34(13), 2655–2666.
Wenger, G. C., Dykstra, P. A., Melkas, T., & Knipscheer, K.C. P. M. (2007).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late-life parenthood - Community activity, close ties, and support network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11), 1419–1456.
Wisman, A., & Goldenberg, J. L. (2005). From the grave to the cradle: Evidence that mortality salience engenders a desire for offspr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1), 46–61.
Zhou, X. Y., Lei, Q. J., Marley, S. C., & Chen, J. S. (2009).Existential function of babies: Babies as a buffer of deathrelated anxiety.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40–46.
Zhou, X. Y., Liu, J., Chen, C. C., & Yu, Z. H. (2008). Do children transcend dea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terror management function of offspring.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5), 413–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