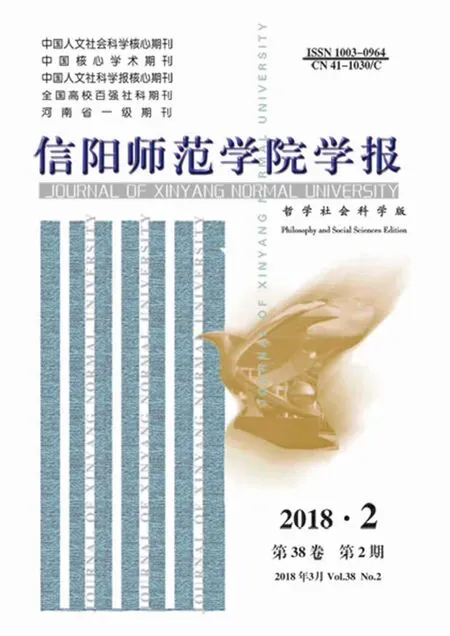國外認知科學哲學中的認知表征問題研究述評
張鐵山,張 琳
(1.信陽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2.西南大學 三峽庫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
認知表征問題是認知科學哲學研究中的基礎性論題和前沿性論題,也是當前國外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和難點論題。在認知表征問題研究的過程中,由于研究者的學科背景各不相同,研究視角各有差異,表征的形式和內容也在不斷更新,故而學界的爭論始終異常激烈。在非涉身認知科學時期,認知科學家們圍繞著心智的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和心智的聯結主義計算—表征范式對認知計算—表征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到了涉身認知科學時期,由于在對認知是否需要表征、是否存在著表征以及如何表征等問題上的不同認識,進而產生了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和溫和的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之間的論爭,目前這兩種認知表征觀的論爭仍然持續著且較激烈。本文將著力呈現當代國外有關認知科學哲學中的認知表征問題研究的演進脈絡和重要觀點,并對它們予以評價。
一、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認知表征問題
非涉身認知科學也稱為第一代認知科學,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認知革命,是對行為主義心理學的一種反叛和取代。作為傳統心靈哲學中的認識論在當代的延展,非涉身認知科學是“當代回答長期未解決的認識論問題所做的以經驗為基礎的努力”[1]6。正是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形成了心智的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和心智的聯結主義計算—表征研究范式。
(一)心智的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及其局限性
心智的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是非涉身認知科學的第一個研究范式。這一研究范式不但從傳統的心智哲學中汲取計算—表征思想的養分,而且也把這些思想融入非涉身認知科學的形式邏輯學、人工智能、認知心理學和生成語言學等具體學科之中,為自己的發展打下了思想基礎。
20世紀50年代,西方邏輯學形式化思想在早期的人工智能中得到了運用,從而產生了阿蘭·圖靈(A.Turing)檢驗及紐厄爾(A.Newell)和西蒙(H.Simon)的“物理符號系統假設”。圖靈檢驗認為,參與“游戲”的計算機經程序化之后能表現出和人的智能一樣的智能。在這一思想得到檢驗之后的1976年3月的《計算機協會通訊》雜志上,紐厄爾和西蒙發表了一篇題為《作為經驗探索的計算機科學:符號和搜索》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們提出了享譽人工智能界的“物理符號系統假設”。這一假設指出,我們可以用計算機操作的二進制數據串來表征現實生活世界中的任何“存在物”。人的大腦與心靈和計算機是一樣的,都不外乎是一個由一組符號的實體組成的物理符號系統。圖靈檢驗和物理符號系統假設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在思考如何讓計算機具有智能中并不需要考慮人的身體和身體之外的環境方面的參與。
20世紀70年代,心理學領域發生了一場反叛行為主義的“認知革命”,這場革命產生了以信息加工為主要特征的認知心理學。這種心理學認為,人們的大腦和心智是一臺信息處理裝置。對信息的處理就如同對計算機程序中的無意義的形式符號進行操作。這種形式符號操作的實現使兒童心理學中的思維或內化思維變得可能。除了心理學領域的“認知革命”外,在認知語言學領域也出現了以喬姆斯基(N.Chomsky)為代表的“認知革命”。在這場認知語言學革命中,喬姆斯基在《評斯金納著<言語行為>》一文中,通過對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作用學習說”進行透徹剖析和批判,提出了他的“轉換生成語法”和“管轄—約束”理論。“轉換生成語法”理論是在理性主義哲學的影響下提出來的。這一理論認為,我們語言分析的目的必須是發現人的內在能力中具有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普遍性及規律性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用有限的規則去生成無限的句子。在生成無限的句子中,體現出“管轄與約束”的語言本質特征。
上述這些思想對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而出現了符號主義(symbolism)、功能主義(functionism)和認知主義(cognitivism)等名稱不同但核心范式類同的認知范式。這些研究范式具有共同的特征:(1)一切認知系統都是通過處理符號而獲得智能的符號系統,心智對于大腦正如計算機軟件對于硬件。(2)認知處理過程遵循精確的、無例外的、用計算程序表示的規則。人類思想系統的語義融貫性在本質上依賴于對某類表達的計算操作。(3)這些研究范式都是基于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并受規則限制、邏輯驅動的,都是被動復制性的認知,都強調計算隱喻的重要性,都是自上而下的心智數字計算—表征,都是一種無視身體的認知觀。與此同時,正是由于上述這些共同特征使心智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遭遇了符號接地(symbol grounding)和符號表征問題、常識知識問題、規則描述與專家系統問題(如CYC程序問題)以及“框架問題”等難以擺脫的困境,導致其難以說明和復制人的復雜行為,暴露出能行可計算假設的局限性,從而陷入發展的瓶頸。
(二)心智聯結主義計算—表征研究范式及其局限性
為了克服心智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自身的困境,20世紀80年代,一些認知神經科學家提出了一種新的計算—表征研究范式:心智聯結主義計算—表征研究范式。
心智聯結主義計算—表征研究范式是探討心智和智能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這種研究范式和方法是通過建立各種人工神經網模型來研究大腦中的神經網絡之間是如何分布和運行的。它的核心概念為大型“并行分布處理”,它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人的認知或智能是從大量的神經元之間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并行分布處理”這一概念起源于1943年沃倫·麥卡洛克(W.S.McCulloch)和沃爾特·皮茨(W.H.Pitts)的“神經網絡”概念。后來,到了1982年,約翰·霍普菲爾德(J.Hopfield)又提出了“霍普菲爾德網絡”(Hopfield network)。這些人工分布式網絡模型堅持唯物主義路線,以還原論為哲學基礎,側重于結構模擬,是一種“灰箱式”的研究方法。這一研究范式和方法主要是對大腦內部的結構和功能進行分析和探究,因此,它是一種“自下而上”的 “涌現論”研究。在對待表征和計算問題上,這種研究范式和方法與心智的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不同。它放棄主要符號,而采用亞符號,是局部式與分布式的表征。特別是心智聯結主義計算—表征研究范式產生的“涌現”思想對涉身認知科學中的動力學范式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盡管上述心智聯結主義神經網絡模型在某些方面和大腦的神經網絡具有相似性,但是,二者之間也存在著很大差異,特別是這種神經網絡模型并不具有真正神經學意義上的合理性,它沒有揭示出心靈和認知的本質細節,不能充分說明一個系統怎樣可能獲得它的內在意義。加之心智聯結主義計算—表征研究范式和心智數字計算—表征研究范式一樣,并沒有揭示出心靈與認知的本質細節,忽視了認知主體的大腦、身體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因此,它在非涉身認知科學研究中仍然困難重重,步履維艱。總而言之,由于非涉身認知科學這兩種研究范式僅僅關注認知的內在表征,忽視了認知的生物學、神經科學研究,忽視了人的身體和外部環境對人認知的作用,難以解釋生活世界中的認知活動,故而受到諸如大腦、情緒、意識、外部世界、身體、動力學系統和社會等諸多方面研究的挑戰,致使認知科學研究不得不尋求新的研究范式。
二、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認知表征問題
20世紀80年代,由于受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胡塞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思想、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思想和皮亞杰與維果斯基的相互作用論等思想的影響,認知科學領域發生了從非涉身認知科學向涉身認知科學的轉向。在這個轉向過程中,涉身認知科學采取反笛卡爾的哲學立場,強調認知是大腦、身體和環境的系統整體交互作用的結果。另外,在對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非涉身計算—表征觀進行反思和批判過程中,涉身認知科學在圍繞是否放棄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認知計算—表征這一形而上學硬核的論爭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新表征觀:一是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二是溫和的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其中前者批判解構了傳統表征觀,后者修正拓展了傳統表征觀。
(一)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
“激進的涉身認知”(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一詞來自于英國愛丁堡大學的認知科學哲學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激進的涉身認知觀認為,要對大腦、身體和世界之間的復雜交互作用給予理解,就必須用動力學系統理論及其研究方法。認為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結構、符號思想及其計算—表征觀是錯誤的,且妨礙了從功能角度對傳統人腦—身體—世界進行區分。所謂“物理符號系統假設”也是有缺陷的,其表征和計算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必須給予拋棄。另外,這種激進的涉身認知科學對傳統認知科學中的計算—表征思想及其形而上學硬核予以堅決的批判。因此,激進涉身認知觀本質上是一種反表征主義的“強耦合”的非計算—表征觀。
這種“激進的涉身認知”思想的產生有其重要的哲學來源。如在激進的涉身認知思想產生過程中,海德格爾對日常認知內在機制和外在環境的描述是一個關鍵的中介環節。該描述展現出了對人類認知活動的一種整體和原初的理解。這種理解明顯區別于以主客二分對立為本質特征的非涉身認知的認知主義模式。正是由于海德格爾在心靈、智能和認知的理解上與笛卡爾主義存在著實質性差別,并且他的現象學體現了對認知主義等經典理論框架的基礎性修正,所以,他所描述的日常認知觀就可能為認知科學研究的發展提供一種新的建構性解釋。海德格爾的日常認知理論具有明顯的反笛卡爾主義的特征。因此,它成為批判非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等經典理論框架并推動認知科學發生轉向的哲學原動力。在海德格爾之后,梅洛—龐蒂通過分析身體對知覺認知活動的意義,深化了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梅洛—龐蒂通過對傳統知覺分析中二元實體論的批判,重點對知覺現象學給予了深入分析,從而將知覺分析建立在存在論的基礎上。基于實體二元論的知覺觀,梅洛—龐蒂指出,傳統的知覺分析掩蓋了參與認知的身體的作用。但是,身體的確在人們的知覺活動中起著知覺、行為的主體的重要作用。他說:“身體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臟在肌體中:身體不斷地使可見的景象保持活力,內在地賦予它生命和供給它養料……如果不通過身體的體驗,我就不可能理解物體的統一性。”[2]261除此之外,梅洛—龐蒂還明確地提出了知覺具有非表征性特征。在他看來,正是因為身體運動功能的“原點”性,我們日常活動的認知才是始于“我能”而不是“我認為”。“身體的運動就是通過身體朝向某物體的運動;就是讓身體對物體作用做出回應,而這一回應是獨立于任何表征的”[3]139。概言之,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思想為激進的涉身認知的非計算—表征思想提供了直接的哲學基礎。
在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現象學和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思想的直接影響下,一大批認知科學家提出了他們激進的涉身非計算—表征思想。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專家羅德尼·布魯克斯(R.Brooks)在《沒有表征的智能》和《沒有推理的智能》兩篇文章中指出,機器人的活動是嵌入在世界中的。但是,它們并沒有解決抽象的描述,而是應對直接影響系統行為的當下環境。當我們研究非常簡單低等智能的時候,實際上關于世界的明晰符號表征和模型對我們了解智能并沒有起到推進作用,而是起到了阻礙作用;當我們從生物種系演化和個體發育尺度來追溯人類認知發展的時候,發現我們具有非常不同的認知能力,并且這些能力是功能主義或計算—表征無法充分說明的。因此,“表征在建構智能系統方面是錯誤的抽象單元”[4]81。世界是它自身最好的模型。另外,認知動力學家馮·蓋爾德(V.Gelder)指出:“表征概念對于理解認知是一種不充分的、詭辯式的東西。”[5]6發展心理學家艾斯特·西倫(E.Thelen)和林達·史密斯(L.B.Smith)宣稱:“我們根本不去建立什么表征!”[6]338認知神經科學家和神經生物學家瓦雷拉(F.J.Varela)認為:“表征觀念不僅僅遮蔽了人類經驗中許多認知的基本維度,而且表征觀念也妨礙了人們對這些維度的科學解釋。”[7]134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克默羅(A.Chemero)指出:“認知系統的本性是非表征性的(認知系統不包含表征)……我們對認知系統的最好說明不包含表征。……因為動力系統理論不包含表征,對認知過程的說明也不包含表征。”[8]比利時的邁因(E.Myin)對認知科學的傳統表征觀念也發起了挑戰,認為“我們的認知能力并不必然以負載內容的內部狀態為前提”[9]36,我們可以訴諸動力系統理論中的吸引子概念、內部控制參數以及耦合關系等。
上述這些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對于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計算—表征觀給予了超越和取代,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自覺的學術努力和理論超越。但是,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并未揭示出認知的本質。從耦合機制來看,也不能說明各種各樣的復雜認知現象,更不能說明諸如高級語言之類的認知能力。從動力學方法論來看,在解決低層次復雜認知方面也沒有提出統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這種非計算—表征觀尚處于一種超越說明基本經驗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論的發展階段,可以說更像是一種理論觀點而不是一個成熟的經驗研究綱領。
(二)溫和的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
“溫和的涉身認知”(wean embodied cognition)一詞也是安迪·克拉克提出來的。克拉克發現,激進的涉身認知無法解決“表征渴求”問題,“在涉身模型中,表征根本沒有完全消失。……而是更經濟的、更加受行動導向的表征”[10]36。這種表征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節省計算成本的辦法,并且這種表征也是克拉克的溫和涉身認知觀中的一個重要觀點。也就是說,涉身認知可能仍然存在表征,只不過這種表征是一種局部的、行動導向的表征。因此,我們應該重新思考表征和計算的本質,以便我們能夠反映出身體運動在產生和簡化要解決的信息處理問題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克拉克不但主張在知覺活動中存在行動導向表征的可能性,而且認為我們的抽象認知活動也是離不開傳統計算—表征的解釋模型的。僅僅從涉身認知的模型來看,這種模型對于意識形式的解決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另外,克拉克還認為:“理解身體、大腦和世界之間的復雜且大量實時交互需要一些新的概念、工具和方法來研究涌現的、離散的、自組織的現象。”[11]511克拉克通過提出上述最低限度表征(minimal representation)的思路,“把行動導向的內在狀態的機體納入連續的模擬信號處理,識別各種變異發生的內在和外在因素……通過克服表征渴求的問題從而間接地達到解決表征不確定性問題的效果”[12]。在復雜多樣的系統的諸多要素中,由于一些行動并不是從中央控制器或者明確編程中產生的,而是在系統諸多要素間的交互作用中“涌現”出來的,所以我們需要運用一些新的概念、方法和工具來探究這種“涌現”現象。正如貝克特爾(W.Bechtel)所說:“認知科學探究的是多種形式的表征。動力系統理論通過引進如:軌跡、動力吸引子這些新的概念來不斷地探索。”[13]62
認知科學哲學家羅伯特·威爾遜(R.Wilson)認為,涉身認知科學和計算主義之間并不是完全對立的。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從涉身認知科學的理論中找到“調和”的方案,這個方案就是寬計算主義(Wide Computationalism)。因為這個寬計算主義中的“計算認知過程是能夠跨顱的,并非如計算主義所倡導的那樣僅僅局限于腦或顱內,它能由腦延展于環境之中”[14]。寬計算主義基本上符合了克拉克對最小化笛卡爾主義或最小化表征的要求。法國索邦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系的皮埃爾·斯特奈(P.Steiner)也認為,“在表征主義和延展認知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的合理性”[15]。這種合理性意味著“內在事件和外在表征之間存在著差別也存在著聯姻”[16]。這表明,皮埃爾·斯特奈反對傳統的表征主義觀點,但是他贊成沒有內容和意向性的心理表征存在的合理性。
除此之外,主張溫和涉身認知的認知科學家還有加拉格爾(S.Gallagher)、克里斯·埃里亞斯密斯(C.Eliasmith)、邁克爾·安德森(M.L.Anderson)等人。加拉格爾認為,在涉身認知框架下,身體圖式的作用是無表征的,而身體意象的作用則是有表征的。僅僅強調身體圖式的作用則是一種狹隘的涉身認知,只有兼顧身體意象的作用,才能成為一種整體的涉身性思想。埃里亞斯密斯和安德森在反思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符號主義模型、聯結主義模型和動力主義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認知理論——認知的表征—動力學理論。他們認為,由于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動力主義這三種認知理論都受到各自所依賴的隱喻的制約和限定,因此,它們不能對認知和智能給予完全的說明。我們如果要對認知和智能給予全面的理解,就必須超越它們各自所依賴的隱喻的限制,用認知和心智的本然屬性去理解它。于是,他們對表征、計算和認知的概念給予了重新詮釋,認為表征是認知神經系統的編碼—解碼過程,計算是認知神經系統在表征基礎上的有偏解碼,認知是神經生物系統通過表征和計算的動力運作過程。他們的這些新解釋對于激進的涉身認知放棄計算—表征是一種挑戰。
總之,溫和的涉身認知既對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計算—表征思想給予質疑,同時又與根本放棄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計算—表征思想的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和態度。它旨在將涉身進路和表征性分析結合起來,在認知觀的計算硬核更加可實現層面上做出調整,以獲得比傳統計算—表征觀更多的解釋力。在一定意義上,溫和的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既超越了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計算—表征觀的局限性,也彌補了激進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的缺陷,“發展了較為完善的解釋性理論,如不完全表征、模擬的表征原則、行動導向的局部表征等”[17]。因此,它是一種“溫和的理性主義”、修正主義、改良主義或廣義的計算主義。然而,這種溫和的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也存在著非涉身認知科學中的計算—表征與被擴展的認知表征之間的“不可通約”困境。如如何將動力系統理論方法和符號方法結合來建構“混合模型”,以及如何解決該模型的可行性問題,如何解決認知主義機制和涉身框架機制之間存在的斷裂并將之聯系起來等。
三、 結 語
通過對上述西方認知科學哲學中的各種認知表征觀思想的辯證考察分析,我們發現,由于認知本質和表征的種類是復雜多樣的,各種類型的表征在其所研究的范圍內都既有其合理性又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完全放棄計算—表征的思想,從耦合機制來看,它不但不能說明各種各樣的復雜認知現象,而且更不能說明諸如高級語言之類的認知能力;從動力學方法論來看,它在解決低層次復雜認知方面沒有統一可行的解決方案,“是一種‘盲目’和停留于感性的初級認知,它無法解釋‘人在對世界的認識過程中認識者本身還具有一個內在的想象世界’。這正是激進的涉身認知理論的先天 ‘缺陷’”[18]。所以,目前這種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并沒有揭示出認知的本質。另外,這種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尚處于一種超越說明基本經驗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論的發展階段,尚不是一個成熟的經驗研究綱領,現在把它作為認知中唯一工具還有很大局限性。在沒有出現更充分的概念化語言之前,這種新的認知科學研究進路只能采取溫和的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的理念和方法對這種計算—表征問題進行修補。但是,這種小修小補僅僅是在目前涉身認知科學處于不成熟階段所表現出的較為合理的研究路徑,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完備性,如這種溫和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還存在著傳統計算—表征觀和被擴展的認知表征之間“不可通約”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可能用一種表征就能夠完全揭示出認知的復雜本質。
總之,在對待認知表征問題上,認知主義計算—表征觀、聯結主義計算—表征觀、激進的涉身認知非計算—表征觀和溫和的涉身認知計算—表征觀都可以從不同側面對人類認知進行說明,但都不夠完備。所以,我們不應該采取那種非此即彼的態度來看待它們,而應該采取“既—又(both—and)”的綜合方法,遵循多元論思想。不同理論觀點的競爭者通過潛在的證偽促進理論發展對科學研究路徑的完善是有益的。
[1] GARDNER H.The Mind’s New Science:A Histroy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M].New York:Basic Books,1985.
[2] 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 MERLEAU—PONTY M.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2.
[4] BROOKS R A.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Cambrian Intelligence: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ew AI[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9.
[5] VAN GELDER T, PORT R F.It’s about time:an overview of the dynamical approach to cognition.In Robert F.Port and Timothy Van Gelder(eds).Mind as Motion: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
[6] THELEN E, SMITH L B A.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and Action[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4.
[7] VARELA F J, THOMPSON E T.ROSCH E.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1.
[8] 安娜·何布勒.對激進的具身認知科學的一個批判[J].陳 虹,譯.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1-9.
[9] 魏屹東,等.認知、模型與表征:一種基于認知哲學的探討[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10] CLARK A.Embodime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 O’HEAR. Current Issues in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1] CLARK A.Embodied,situated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 c//.B.Graham.Companion to Cognitive Scien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8.
[12] 彭超宇.論克拉克對表征不確定性問題的解決[J].心智與計算,2013(1):38-43.
[13] BECHTEL W.Philosophy of Science:An Overview for Cognitive Science[M].Hillsdale,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1998.
[14] 劉 川.涉身認知科學視域下的計算主義研究[J].未來與發展,2017(6):39-43.
[15] STEINER P.A Problem for representationalist versions of extended cognition[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5(28)2:184-202.
[16] STEINER P.The bounds of representation:A non—representationalist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model of extended cognition[J].Pragmatics&Cognition,2010(18)2:235-272.
[17] 張 博,葛魯嘉.溫和的具身認知:認知科學研究新進路[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19-28.
[18] 張鐵山.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西方涉身認知[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4):9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