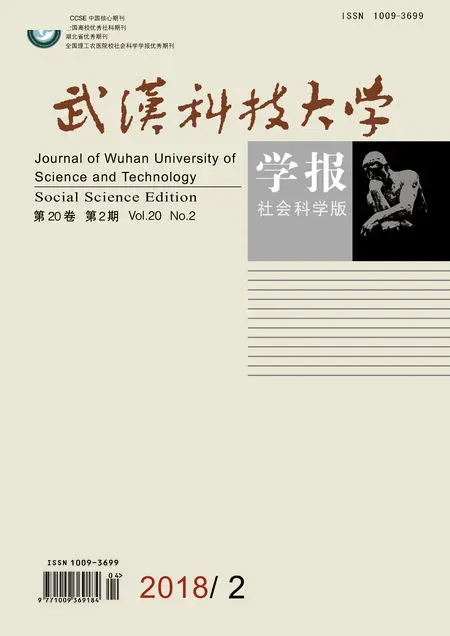孔氏家學中的《尚書》學
——《兩漢〈尚書〉學研究》的一個獨特視角
王鈞林
(1.孔子研究院,山東 曲阜 273100;2.山東師范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014)
近年來,隨著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和發展,《書》學研究日益興盛,《尚書》展現出其愈久彌新的文化張力,現代人從對《尚書》的現代闡釋中可以發現歷史的規律、觀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現實意義。其中,馬士遠著《兩漢〈尚書〉學研究》從清理基本術語、學術文獻等基礎上,對西漢《尚書》學研究、東漢《尚書》學研究、《書》教傳統與漢代政教、漢代稱說《尚書》學文獻輯考等進行了系統闡釋,考據詳實,論述精到,是近年不可多得的《尚書》學研究力作。其中,該著關于“孔氏家學研究”,尤其值得關注。相比之前的《尚書》學研究論著,《兩漢〈尚書〉學研究》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尚書》學中孔氏家學的正本清源
《尚書》學中的孔氏家學研究存在諸多爭議,馬士遠著《兩漢〈尚書〉學研究》在厘清學術淵源的基礎上,堅持“論從史出”原則,力求做到正本清源。由于孔子及其家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孔氏家學成為包括《尚書》學在內的諸多學術研究無法回避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兩漢時期,《尚書》學與孔氏家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不能弄清兩者的關系,很多疑難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例如,孔安國問題是兩漢《古文尚書》學研究中至為關鍵的一環[1]208。關于孔子與《尚書》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學術界懸而未決的難題。馬士遠采取了看似笨拙卻非常可靠的辦法來梳理文獻,將相關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等匯總整理,可謂“一網打盡”“涸澤而漁”,發現了新的線索和思路。馬士遠經過縝密考察后發現,雖然孔子撰寫《尚書》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但據《史記》等文獻記載,孔子確實曾對《尚書》進行過整理,而且將其用于教授弟子和子孫,是真正以《書》為學的第一人。馬士遠論著的依據是出土文獻中的《孔子詩論》《易傳》等,以及傳世文獻中《易》的《系辭》、傳述《春秋》的《左傳》、傳述《禮》的《禮記》等,而這些都屬于“述”,因此,孔子對于《尚書》的詮釋,完全可以稱之為“傳”。
《史記》關于《尚書》時間斷限問題,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說,馬士遠認為這在本質上是一種取舍,孔子“刪”《尚書》的說法是成立的。馬士遠認為,由“文”到“字”再到“書”,特別是用于政教、記言的、較長的《尚書》必定經歷了漫長的歷程,即使已經產生《尚書》,也是非常少的。另外,《左傳》《國語》所引《尚書》一類資料又有唐堯虞舜之前的資料,孔子在編撰《尚書》時自然會剔除荒誕不經、不雅的資料。因此,《史記·五帝本紀》言皇帝之文“不雅訓”,孔子皆“雅言”,可以作為孔子編《尚書》斷于唐虞之際的證據之一。而“下至秦繆”的文獻是受秦漢時期“秦繼周朝正統”影響的產物,并不符合史實,但不等于說孔子未編過《尚書》,《孔傳》所言“迄于周”更有可能是孔子編次《尚書》的時間下限。更為重要的是,孔子在諸侯爭霸、《詩》《書》等文化消亡的危急時刻,積極倡導周代禮樂文化,對早期《尚書》進行整理、傳播和詮釋,將官方順《尚書》以教的傳統下移至民間。
孔子《尚書》學觀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變化,孔子之于《尚書》可以分為幾個時間段。馬士遠根據《史記·孔子世家》等文獻記載,認為孔子在四十二歲之前、四十二歲至五十歲之間、五十歲之后至六十七歲返魯之間三個時間段以不同的態度和觀點詮釋和傳播《尚書》。其中,孔子兩次對《尚書》進行了系統研究,孔子以《尚書》為學,其《尚書》學觀主要體現在其“《書》教”思想中[1]213,而《書》教是與《詩》教、《禮》教、《樂》教等同時由孔子提出的。孔子把《尚書》的教化作用概括為“疏通知遠而不誣”(《孔子家語·問玉》),把《尚書》當作歷史來看待,通過《尚書》的歷史文化價值,可以汲取上古諸侯能臣在復雜的斗爭實踐中總結的先民智慧,從中可以探尋王朝更替、歷史變遷的原因,從而促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實現,這基本可以概括孔子早期的《尚書》學觀。馬士遠根據《藝文類聚》《孔叢子》等文獻的解讀,認為晚年孔子《尚書》學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孔子在以《書》為史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以《書》為訓”的“《書》教”思想,《書》對于孔子思想體系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孔子《書》學思想對于后世儒家思想影響甚大。
正是因為《尚書》對于孔子思想的重要影響,孔氏《尚書》家學的創立過程,也是孔子教授弟子門人的過程,馬士遠認為兩者是同時進行的。孔門儒學的傳播不是一帆風順,在孔子死后受到嚴峻挑戰,依靠弟子門人的努力才加以傳播,到戰國時期成為兩大顯學之一,其中就得益于《尚書》的傳播。孔子“《書》教”傳統被漆雕開、子張、子夏、子思等孔子弟子傳承,對儒學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馬士遠專門考察了孔子后裔學習《尚書》的情況,認為孔子后裔多精熟于《尚書》學,包括孔伋、孔白、孔穿、子順、孔鮒等一代代的孔氏后人逐漸形成了周秦孔氏《尚書》家學傳統,為后世《古文尚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為了厘清西漢《尚書》孔氏家學傳承,馬士遠考證了孔鮒、孔騰之后還有一個弟弟孔袝,并對三者世系進行了詳細考證,尤其再三考證了孔安國一支,確定孔安國為孔氏第十二代孫、孔襄之后,孔延年、孔霸、孔光等祖孫三代皆治《尚書》今文學[1]229-230。
孔氏家學的傳承是孔子后裔的責任和使命,孔子后裔也因為孔氏家學而得到很高的地位,以孔安國為代表的孔氏后裔為了治學、功名等目的大都致力于研習儒家經書,尤其是在《尚書》學領域世代相傳,分支較多,也存在很多爭議。例如,馬士遠重點考證了孔安國傳授《古文尚書》問題,認為孔安國開創了《古文尚書》學派,而且在孔氏子孫和弟子中形成了兩支傳授系統和譜系,這些考證基于《漢書》《后漢書》《孔子世家譜》《闕里文獻考》等文獻的相互印證,思路清晰,論證縝密。
二、《尚書》學研究史中的孔氏家學
只有把《尚書》學放在更為宏觀、更為開放的視野里審視,才能站在學術史的高度看待《尚書》學研究,把《尚書》孔氏家學研究推向深入。馬士遠認為,兩漢《尚書》孔氏家學研究之所以不夠深入,就是因為受到所謂“偽書”公案、疑古思想的影響和制約,李學勤[2]、黃懷信[3]、李存山[4]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推進了東漢《尚書》孔氏家學研究,應該大膽借鑒。馬士遠據以考證的資料,除了《孔叢子》等書籍文獻之外,還有洪適《隸釋》《隸續》所錄存的漢碑,以及曲阜現存的部分漢碑。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西漢今文經學是鼎盛時期,儒學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且設立了五經博士——所傳經典皆為今文。到了漢宣帝,博士經學從一家分化為一經數家,僅《尚書》經學就從武帝時歐陽一家發展為歐陽、大夏侯、小夏侯等三家博士。在經學分化發展過程中,孔氏家族學者中就有孔安國、孔延年、孔驩、孔子立等順應學術潮流研習今文經學,被立為《尚書》今文學博士。其中,孔安國與孔延年為叔侄關系,由于漢武帝在位時間較長,孔延年出于長房,叔侄兩人年齡差別很可能不大,這樣叔侄同為博士的可能性非常大。承續前面所定西漢孔子后裔世系脈絡,馬士遠仍以孔鮒之后、孔騰之后、孔袝之后為脈絡考辯東漢孔子后裔世系,兼有《尚書》今文學、古文學之分。馬士遠對照了《漢書·孔光傳》《漢書·夏侯勝傳》等文獻,可知孔延年之子孔霸為孔子第十四代孫,曾治《尚書》今文學,師從夏侯勝,漢昭帝時期為大夏侯學博士,漢宣帝時期為皇太子即漢元帝師。孔霸又繼承家學傳統,傳《尚書》今文學于第四子孔光,開大夏侯學派中的“孔氏之學”。孔光為孔子第十五代孫,學識淵博,三世官居高位,在西漢時期孔氏家族中官職最高,《漢書》有《孔光傳》,記載孔光曾以《尚書》授徒講學,其弟子很多成為博士、大夫。因此,孔霸、孔光皆為經學大家,而且都因明經高行成為帝師。無論是叔侄同列博士,還是父子皆為帝師,都說明兩漢時期孔氏《尚書》家學的影響之大、地位之高。另外,孔霸長子孔福之后的《尚書》孔氏家學以今文《尚書》大夏侯學為主,孔安國一系在東漢傳有《古文尚書》家學無疑。
對于漢代《尚書》孔氏家學的貢獻,馬士遠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孔氏一族保存并整理了《古文尚書》,傳承周秦“《書》教”傳統、創發完善了《古文尚書》經學,豐富了漢代《尚書》學詮釋體系,對《尚書》今、古文學融通等多有貢獻。漢代《古文尚書》學的發展建立在孔氏家族保持和整理的《古文尚書》之上,孔壁出書是中國經學史上無法回避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周秦時期孔氏家族藏書就顯得至關重要。孔壁所出的《古文尚書》資料可靠,對當時流行的伏氏今文《尚書》有著重要的匡謬補缺的版本勘校價值。孔氏家族不僅及時保護了出世的珍貴文獻,而且能夠根據自身具有的今文《尚書》功底和古文獻基礎進行整理、釋讀,適時上獻朝廷、下傳民眾,推動了整個文化學術的發展。
從學術史發展來看,馬士遠認為,有經未必有學,而孔氏家族學者承繼“《書》教”傳統,對《古文尚書》的詮釋直接造就了《古文尚書》經學,孔安國為《古文尚書》經學的開創者,其嫡系后裔傳承其學,到西漢后期逐漸興起《古文尚書》經學。孔氏家族學者在傳承《尚書》學過程中,堅持學術理念,不因權貴世故喪失立場,對于當時的學術風氣和文化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馬士遠認為應該從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經學史等角度去認識《尚書》孔氏家學的地位和作用。
從學術融通的角度來說,《尚書》孔氏家學大師輩出,能夠融會貫通、古今兼治,為后世學術融通樹立了典范。孔氏家族學者在漢代學術史上地位顯赫,漢惠帝時期的博士有孔騰,漢文帝時期的博士有孔忠,漢武帝時期的博士有孔武、孔延年、孔安國,等等。可以說,孔氏家族學者大都在《尚書》學上有所成就,無論是專治古文,還是專治今文,還是古今兼治,很多是當時學界翹楚。我們知道,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古文經學有學風嚴謹的優點,也有食古不化的弊端;今文經學有經世致用的優點,但是也有繁瑣化、讖緯化的弊端。如果能將古文經學、今文經學的優點加以發揮,同時克服兩者的弊端,就會大大促進經學的發展。孔氏家族學者能夠做到古今兼治、取其優點,拋棄古今缺點、缺陷,馬士遠指出,孔氏家族學者不是僅僅為了功名利祿而治學,而是能夠兼容并包,取長補短、相互糾偏,為后世《尚書》古今文學合璧創造了條件。
三、孔氏《書》教“七觀”說思想
把《尚書》學提升到理論層面進行考察,全面分析孔氏《書》教“七觀”說思想,這樣才能比較準確地把握《尚書》孔氏家學的內涵和意義。馬士遠將《書》教“七觀”說視為兩漢孔氏家學的核心理念,并聯系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篇中有“《書》標七觀”的說法,指出《孔叢子·論書》篇中也有《尚書》“七觀”說的相關內容,這與孔子論《詩》提出“興、觀、群、怨”說同出一轍。《書》教“七觀”說并不是漢晉時期的產物,而是早在周秦時期就已經存在。孔子作為《尚書》的整理者和傳播者,并且用于教授弟子門人、后世子孫,完全有可能創立或發展了《書》教“七觀”說。根據《尚書大傳·略說》《孔叢子·論書》等文獻記載,“七觀”說確由孔子提出,雖然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但是恰恰說明孔子詮釋《尚書》的言論以不同的學派流傳下來,更為可信。
關于《尚書大傳》,有的認為是漢代《尚書》今文學派的開山始祖伏生所編,有的認為是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等根據記錄伏生教授《尚書》之大義所成[5]。馬士遠從文獻記載考論《尚書大傳》成書后在漢代流傳很廣,夏侯勝曾進行過闡釋,鄭玄的《尚書大傳注》曾轉引過夏侯勝的闡釋,劉向的《洪范論》是其“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的結果,《白虎通義》更是多見其內容,等等。學界多認為《漢書·藝文志》的“《傳》四十一篇”為《尚書大傳》,大概是受到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等體例影響。馬士遠認為,劉勰所見《尚書大傳》應該是漢代鄭玄所注的八十三篇本向隋唐時期的三卷本轉變時期的版本,至宋《尚書大傳》的流傳本還出現過四卷本,而且已經出現前后不倫、版面殘缺的現象[1]370。到元明兩代,公私書目都不曾著錄《尚書大傳》,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版本多為清人輯本。馬士遠認為,《尚書大傳》作為溝通周秦《尚書》學與漢代《尚書》學的橋梁,內容廣博,可以據此推斷先秦《尚書》學說的具體模式,很有史料價值。“七觀”說見于《尚書大傳》七卷之一的《略說》卷,雖然《尚書大傳》已經失傳,但是“七觀”說的內容得以保存在一些相關傳世文獻之中,包括《路史·外紀》《太平御覽》《困學紀聞》等都明確引用了《尚書大傳》,可以視為《尚書大傳》文本。
關于《孔叢子》及其“七觀”說問題,馬士遠首先考辯了《孔叢子》真偽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闡發。《孔叢子》在宋、明多視為偽書,當代學者李學勤、黃懷信等認為此書不是王肅等偽造,而是孔子家學,可能是孔子第二十世孫孔季彥或其后的孔氏后裔搜集先人言行所編。王鈞林則認為《孔叢子》沒有作者,只有編者,編者可能是孔鮒,孔鮒沒有完成,由其后人繼承未竟的事業,連帶將孔鮒的言行一并編入書中[6]。根據馬士遠的統計,“七觀”說在《尚書大傳》中包括“六誓”六篇、“五誥”五篇以及《甫刑》《洪范》《禹貢》《皐陶謨》《堯典》等,共計十六篇;而《孔叢子》中包括了《帝典》《大禹謨》《禹貢》《皐陶謨》《益稷》《洪范》《秦誓》《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甫刑》等,其中《帝典》無法確定是《堯典》還是《堯典》《舜典》的合稱,因此共計十三篇或十四篇。根據其他傳世文獻考證,《益稷》應該統一于《皐陶謨》,《舜典》可以統一于《堯典》。可以說,《尚書大傳》與《孔叢子》有差異篇名只剩下了《禹貢》與《大禹謨》《禹貢》以及“六誓”與《秦誓》的差異。這種差異不能說明《尚書大傳》和《孔叢子》就是偽作,反而說明《尚書》學傳播的年代久遠及學派差異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馬士遠在考辯了《尚書大傳》和《孔叢子》中所記《書》教“七觀”之后認為,《尚書大傳》所記“七觀”為觀義、觀仁、觀誡、觀度、觀事、觀治、觀美,《孔叢子·論書》所記“七觀”為觀美、觀事、觀政、觀度、觀議、觀仁、觀誡,兩種“七觀”雖存在“義”與“議”、“治”與“政”的字面差異,且次序不一,但涵義相同,都體現了孔子《尚書》學的基本主張。
馬士遠認為,孔子“《書》教”思想是孔子教化思想與《尚書》所蘊含的政治思想的有機結合,義、仁、誡、度、事、治、美等七者是孔子實施王道政治的基本主張,“七觀”中的仁、義、美是孔子對《尚書》中所倡導的“德”“治”“事”“政”等命題的擴展與深化,儒家早期的中庸思想也是孔子對《洪范》之“度”命題的把握、提升的結果。馬士遠用提問的方式,論述了孔子如何可以從“六誓”中觀“義”、從“五誥”中觀仁、從《甫刑》中觀誡、從《洪范》中觀度、從《大禹謨》《禹貢》中觀事、從《皐陶謨》中觀治和政以及從《堯典》或《帝典》中觀美,這“七觀”集中體現了孔子對《尚書》大義的詮釋,這是對孔子《尚書》思想最為核心和本質的認識。
此外,馬士遠著《兩漢〈尚書〉學研究》全書體現出學術史的宏觀大氣,全面系統地梳理了兩漢《尚書》學研究的背景、淵源、著述、成就、問題等,善于結合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論析、且敘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據、據必足考,在堅實的史論資料基礎上展示兩漢《尚書》學的整體風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相關研究空白。尤其是在文獻考證方面,體現了嚴謹治學的態度和孜孜以求的學術精神,下大功夫梳理《古文尚書》等經典文獻,以史料甄別真偽、以理性辨別是非,盡量還原歷史原貌,避免了盲信或盲疑兩種極端和偏激。對于證據不確鑿或孤證的材料,或大膽猜測,或指明存疑,都力求客觀全面。在資料使用上,除了書籍文獻資料之外,還充分運用新出土的簡牘資料、漢碑文獻等,將多種文獻交互印證,再用多種學術觀點推演、判斷,補正或修正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不確和謬誤,澄清了困擾學術界的很多盲點,具有理論深度和視野廣度。馬士遠著《兩漢〈尚書〉學研究》還附錄了漢代《尚書》傳本及其篇名目次總表、漢代《尚書》今文學派傳承表、漢代《古文尚書》學派傳承表、漢代《尚書》孔氏學世系傳承表、漢代學者《尚書》著述總表等,對于繼續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馬士遠.兩漢《尚書》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2]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J].孔子研究,1987(2):60-64.
[3]黃懷信.《孔叢子》的時代與作者[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1):31-37.
[4]李存山.《孔叢子》中的“孔子詩論”[J].孔子研究,2003(3):8-15.
[5]鄭裕基.談談《尚書大傳》和它對語文教學的助益[J].國文天地,2006,22(5):17-29.
[6]王鈞林.論《孔叢子》的真偽與價值[J].齊魯文化研究,2009:19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