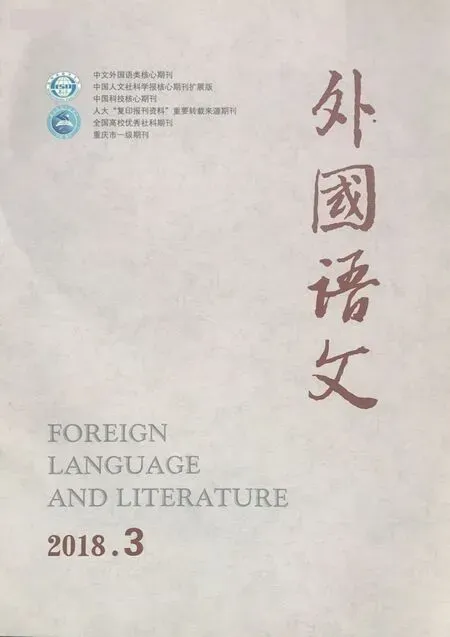豪薩語書面詩歌的起源及其社會功能研究
——以娜娜·阿斯瑪烏的作品為例
孫曉萌
(北京外國語大學 亞非學院,北京 100089)
0 引言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詩歌很長時期是以口頭傳播形式流傳的,但構成了包括價值觀念、英雄神話、歷史紀年等在內的元敘事。豪薩語詩歌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以說唱配以鼓樂的“口傳贊歌”,隨著豪薩阿賈米文字的出現,口傳贊歌的元敘事解體,書面詩歌產生,這個過程因此也成為理解豪薩傳統社會伊斯蘭化的重要途徑。豪薩語書面詩歌無疑是“吉哈德”運動過程中的一種“文化策略”,受到阿拉伯語詩歌在形式和題材方面的深刻影響,但伊斯蘭教還在西非創制了詩歌書寫的載體豪薩阿賈米(Ajami),使原本作為口語表達的豪薩語發展為使用阿拉伯語字母書寫和記錄的語言。因此,使用經過外化的語言創作的豪薩語書面宗教詩歌具有了深厚的伊斯蘭文化根基。本文試圖呈現豪薩語書面詩歌產生的歷史,將這一文學現象的發生置于豪薩地區伊斯蘭化的背景下進行闡釋,探析其與豪薩口頭文學及傳統文化、阿拉伯語文學之間的繼承關系,勾勒豪薩傳統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交流互動的軌跡,考察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對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發展產生的沖擊。研究豪薩語書面詩歌的產生及其文化語境將對系統理解和把握非洲本土語言文學的嬗變過程具有一定的啟發。
1 “吉哈德”宗教改革運動與豪薩語書面詩歌的興起
豪薩語書面詩歌產生于“吉哈德”伊斯蘭教改革運動之中,是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的文學表達。早在14世紀之前,伊斯蘭教已在豪薩地區傳播,但很大程度上是僑居商人、少數本地商人和統治階級上層的宗教,草根民眾仍信仰傳統宗教。直到15世紀伊斯蘭教才逐漸強大。豪薩本地的穆斯林學者群體自16世紀開始出現,并與遠至博爾努、東蘇丹、北非甚至西班牙的穆斯林都有學術交流。在各種宗教文化的滋養下,豪薩這個西非相對貧瘠的伊斯蘭文化凹地,逐漸成為伊斯蘭文化高地(李維建,2011:98)。在豪薩地區,大量蘇菲派學者使用阿拉伯語創作,內容涉及伊斯蘭神學、教義學、經注學等宗教題材。值得關注的是,此時伊斯蘭知識的傳播僅限于規模有限的學者階層,他們精通阿拉伯語,對缺少書面文字、說豪薩語的主體人群影響有限。與東部非洲包容開放的海洋性斯瓦希里文明相比較而言,地處內陸的西蘇丹地區則較為封閉保守,對于傳統宗教和文化的依附程度也更高,外來的伊斯蘭教扎根當地需要作出較大的妥協和讓步,因此,西非穆斯林選擇性地接受伊斯蘭教中與傳統宗教不沖突之處,同時也并未放棄對傳統宗教的信仰,從而信奉的是“混合”伊斯蘭教。非洲傳統社會是以家庭—社會—信仰—倫理為基礎的社會形態,與伊斯蘭教自身對于社會生活的指導相契合,因此二者可以相互影響和作用。但是在前“吉哈德”時代,伊斯蘭學術中心廷巴克圖(Timbuktu)遭受洗劫,西非伊斯蘭教的發展受阻,“混合”伊斯蘭教更為盛行。
1804年,為了純化豪薩地區的伊斯蘭教,消除該地區長期以來的分裂割據狀態,建立一個強大的伊斯蘭政權,富拉尼(Fulani)穆斯林領袖謝赫領導發動了“吉哈德”(Jihad)宗教改革運動。在改革之初,他需要獲取軍隊中豪薩追隨者的信任,他們由豪薩傳統政權壓迫下的農民和平民階層構成;其次,需要通過伊斯蘭教育鞏固改革運動的成果。1808年至1809年期間,謝赫家族逐步取代了豪薩傳統酋長的位置,并將索科托(Sokoto)確立為行政首都。這場運動產生了巨大而曠日持久的文化影響。
基于統治需求和溝通便利等因素考慮,豪薩語作為被征服者的語言不僅未被禁止使用,反而被宗教改革者加以利用和推廣,成為一種地區通用語。宗教改革者的母語富拉尼語在地區內的使用占比很小,他們雖然使用阿拉伯語創作詩歌,并同區域內和遠至馬格里布(Maghreb)的伊斯蘭學者之間進行交流,然而阿拉伯語始終只能在宗教和知識精英階層流通,在當地的使用范圍十分有限。于是,豪薩語索科托方言被樹立為權威的詩歌創作語言,進而凸顯了其相較于其他豪薩城邦的權威地位,以及此后作為哈里發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并淡化了謝赫及其追隨者的伊斯蘭“外來屬性”。然而,豪薩語書面詩歌創作中的語言策略并非一成不變,根據詩歌創作的功能而有所差異,并以此來劃分作品的受眾階層。例如,作為整個“吉哈德”運動的思想綱領和行動指南的經典詩歌作品,謝赫只使用阿拉伯語創作;娜娜熟練掌握富拉尼語、豪薩語、阿拉伯語和圖阿雷格語(Tamacheq)及詩歌的寫作技巧,在創作正統詩歌時多使用阿拉伯語,當需要與追隨者進行直接交流時則使用豪薩語。據統計,娜娜創作的富拉尼語詩歌共計46首、豪薩語詩歌22首、阿拉伯語詩歌10首,在娜娜創造的詩歌中,75%的勸誡詩使用豪薩語書寫(Yahaya, 1988 :52)。截至19世紀60年代,已有大量的富拉尼語和阿拉伯語詩歌被翻譯為豪薩語,反映出哈里發內部所歷經的文學、文化的豪薩化進程。蘇非主義作為一種溫和的伊斯蘭流派,其主要特征與非洲本土文化傳統之間具有融合性。因此,宗教改革者在豪薩傳統文化面前采取的“妥協”和“屈尊”策略,反而為伊斯蘭教的傳播奠定了更為深厚而穩固的根基。宗教改革運動催生了使用非洲本土語言創作的書面詩歌,最初在戈比爾(Gobir)和贊法臘(Zamfara)以手抄本形式流通并被廣為傳頌,隨著索科托哈里發的建立而迅速傳播開來,并逐漸發展為印刷本。“吉哈德”運動及此后建立的索科托哈里發政權具有典型的家族統治特點,謝赫家族成員的詩歌創作相當可觀,包括勸誡詩、傳記詩、史詩、經文批注、悼亡詩等大量作品,其中以謝赫之女娜娜·阿斯瑪烏(Nana Asma’u)的作品在數量和影響方面最為顯著(Mack et al., 2000: 7)。
2 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豪薩語書面詩歌的傳播
在豪薩語書面詩歌出現之前,豪薩語口傳贊歌和經典的阿拉伯語詩歌已經在豪薩社會的不同階層中長期唱誦流傳。可以說,豪薩語書面詩歌在承繼豪薩語口頭文學與阿拉伯語文學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種創造性轉化,并演變為“精靈”崇拜的豪薩傳統社會與信奉伊斯蘭教的索科托哈里發之間的過渡性溝通媒介,呈現出豪薩文化伊斯蘭化的典型特征。這一轉化過程,雖然是一種文學樣式的變化,但體現了豪薩傳統宗教與伊斯蘭教、傳統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融合的過程。豪薩社會中存在著諸多與伊斯蘭教相背離的文化傳統,諸如不分場合的鼓樂伴奏、精靈崇拜、不合時宜的富拉尼成人儀式“沙羅”(sharo)習俗、隱匿長子或長女的姓名等。謝赫所倡導的“吉哈德”運動旨在反對“混合”的伊斯蘭教,力圖恢復西非伊斯蘭教的純正性。娜娜是謝赫家族宗教思想和治國理念的繼承人,她通過創造性地轉化創作形式和題材,將豪薩語書面詩歌作為知識載體,在地區內廣泛傳播卡迪里蘇非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2.1對阿拉伯語詩歌的模仿與轉化
詩歌是阿拉伯最古老而重要的藝術形式,阿拉伯語口傳歌謠自遠古時代就在阿拉伯半島中部和東北部的貝都因牧民中長期流傳,此后在前伊斯蘭教時期又發展為具有特定格律和節奏的“蓋綏達”(Qasidah)詩歌體裁,其中以“懸詩”(Mu’allaqat)為代表。伊斯蘭教建立初期,充滿部落文化色彩的古詩受到抑制,出現了大量具有強烈政治和宗教色彩的詩歌,這種詩歌服務于宗教和政治的功能長期延續下來。豪薩語書面詩歌無論從書寫載體到形式、題材、創作手法等皆受到經典宗教語言阿拉伯語及其詩歌的深刻影響,豪薩詩人因此在創作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模仿與轉化,他們的作品具有明顯的宗教色彩及道學隱喻,通常會借助象征、釋義、嚴格的韻律形式,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獨具特色的豪薩語書面詩歌。
作為”吉哈德”運動中重要的宗教宣傳工具,豪薩語書面詩歌是教化、詮釋和論爭的工具。在創作題材方面,一類是“勸誡詩歌”(wa’azi),通過描述死亡與復生、地獄折磨與天堂享樂的情境,對比宗教信徒與無信仰者的生命歷程,進而建立宗教社會(al’umma)的理性與道德傳統,用以傳道、授業、解惑;另一類則為“神愛詩歌”(maduhu),多數創作者是受蘇非主義知識傳統長期浸淫的知識分子,豪薩語神愛詩歌通過廣義“愛”(kauna)的表達來展現對真主的摯愛之情(Furniess, 1996: 197)。此外,伊斯蘭法律條文(farilla)、神學(tauhidi)、星象學(nujum)、占卜學(hisabi)和先知傳述(hadith)等伊斯蘭宗教知識也使用詩歌表達。
在創作手法方面,娜娜展現了作為蘇非學者深厚的學術造詣,將阿拉伯語詩歌的創作技巧淋漓盡致地發揮在豪薩語書面詩歌創作之中。為了使勸誡詩更具宗教的教育性和普及性,娜娜采用了阿拉伯語詩歌的慣用技巧“釋義”(takhmis),即在原作對句之前添加額外三行同樣格律與韻律的注釋。《懼怕》就是娜娜以這種方式創作的一部蘇非模式詩歌,告誡異教徒在過世后會遭遇的恐懼。此外,娜娜還借用了阿拉伯文學傳統中用于保存歷史知識而使用的先知傳記(sira),她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范疇,試圖將謝赫的宗教改革運動比作是對先知穆罕默德七世紀推廣伊斯蘭教行為的模仿。對于散文作品的詩律化(Manzuma)也是阿拉伯語詩歌中的常見技巧,娜娜將哥哥貝洛針對蘇非婦女的《建議之書》(Kitabal-nasihah)詩律化并創作出《蘇非女性》。作品以娜娜視角對蘇非女性角色進行了重塑,彰顯了其在哈里發內部樹立的知識權威;在創作《贊頌穆罕默德》時,她通過重復使用“穆罕默德”(Muhammad)作為尾韻,一方面吸引朗誦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強調先知與信徒時刻同在,通過詩歌言語的表達傳遞著伊斯蘭教的神圣性,作品同時借鑒了13世紀柏柏爾蘇非詩人阿爾·布西里(al-Busiri)的詩歌,通過翻譯阿拉伯語經典作品及回溯,試圖將豪薩語詩歌置于文學經典之列。
2.2創作形式的轉變:從口傳贊歌到豪薩語悼亡詩
作為豪薩社會價值觀表達的一種制度化模式,豪薩語的口傳贊歌傳統由來已久,唱誦口傳贊歌在豪薩社會中被視為一種職業(sana’a),然而不同于靛染(rini)、編織(saka)等傳統職業,贊歌不具備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及手工匠人與客戶間的“契約關系”,這種非經濟和非協議的特點使口傳贊歌成為具有一定間接調節功能的社會機制,展現出豪薩社會與文化的復雜性,及其與社會權力結構之間的密切聯系,作為傳播贊賞與羞恥觀念的非正式調節機制,也同時實施社會控制,表達關于權力、權威、權位、世系、繁榮、傳統等價值觀念(Smith, 1957:27)。這恰恰與傳統“博瑞”(bori)精靈崇拜中表達的價值觀相一致,加之口傳詩人自身通常被認為具有神賦能力,二者同謀構成了豪薩傳統社會的根基,口頭贊歌因此與豪薩傳統統治者形成了某種共謀關系。因此,對于口傳贊歌的否定,就等同于對豪薩宮廷、傳統文化和精靈崇拜的全盤否定。伊斯蘭教譴責贊頌個體的行為,唯有對于先知的頌揚是被允許的,“傳頌者應避免頌揚個人,其中的萬劫不復不言而喻。歌頌先知則功德無量,歌者應盡可能展示先知美德”(Boyd, 1990:2)。相對于完全排斥口頭贊歌,娜娜以悼亡詩的形式取而代之,并賦予豪薩語詩歌真正的伊斯蘭根基,進而顛覆了豪薩傳統文化根基,用于進行宗教意識形態的傳播,大幅縮減了伊斯蘭價值觀與豪薩傳統文化之間的疏離。
娜娜創作的悼亡詩數量介于16首到20首之間,詩歌中具有明顯的教育傾向,她放棄了伊斯蘭教的經典語言阿拉伯語,運用大量的豪薩語索科托方言詞匯和表達方式,語言風格簡潔凝練,與”吉哈德”時代的其他詩人相比較而言,也較少運用來自阿拉伯語的外來詞。作為外來的伊斯蘭文化與豪薩本土傳統文化交流互動的文學產物,豪薩語悼亡詩具有如下典型特點:首先,悼亡詩的內容不涉及家族譜系、軍事和政治行為,而更加強調宗教行為,如在《哀悼布哈里》(SonnoreBuhari)中,娜娜對于兄長布哈里的描述是:“他是一位勇敢而杰出的學者,慷慨且耐心,他是人類的一盞明燈。他一生善言善行,品行完美無瑕。”其次,悼亡詩將“求知”置于特殊的地位,在《哀悼穆斯塔法》(SonnoreMustafa)中,娜娜表達了對于一位偉大學者逝去的特殊情感以及對于社會影響的關切,“如今燈已熄滅,黑暗陡增”。再則,悼亡詩十分強調維系先知穆罕默德和真主之間聯系的精神紐帶。娜娜在《死亡真相》(AlhininMutuwa)中追溯了自蘇非卡迪爾教團(Qadiriyya)創始人謝赫·阿卜杜卡迪爾(ShehuAbdulkadir)到弗迪奧蘇非教團的發展歷程。她寫道:“謝赫·阿卜杜卡迪爾,我珍視他們,以他們為榮。魯法伊、阿赫邁德·巴德維、阿爾·達蘇基和丹吉爾的謝赫讓我與他們同在。”除此之外,悼亡詩也是娜娜個人的蘇非主義思想的體現,她強調人的品行和價值觀,忽視身份和地位,甚至為一些普通人書寫悼亡詩,并在其中頌揚美德,這些皆與豪薩口傳贊歌強調被歌頌者個體的地位和成就形成鮮明的對比。娜娜為一個權威社會創造了完整的文學文本,為“吉哈德”理論進行了現實書寫(Merritt, 1994: 92)。
2.3顛覆豪薩傳統文化中的精靈崇拜
“吉哈德”宗教改革運動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讓恪守傳統宗教的豪薩人真正信奉純正的伊斯蘭教。其中精靈崇拜作為一種傳統的、異教徒式的咨詢與康復手段,在豪薩傳統社會中長期占有主導地位。娜娜并未完全禁止精靈崇拜,而是提供了一種伊斯蘭式的替代方案。豪薩語書面詩歌因此承擔了“思想勸導者”的角色,娜娜1839年創作的作品《先知醫藥》(Tibbal-Nabi),對于如何消除由疾病、焦慮、恐怖行為和不良環境引發的痛苦和壓力進行了闡釋。作品主要面對知識精英,試圖以一種宗教導向和高度精神化的治療系統取代精靈。其中作者引用了《古蘭經》中的五個婦科章節,包括分娩(第69章)、孕婦護理(第69章)、斷奶(第85章)、成功孕育男性后代(第89章)及新生兒護理(第90章)。涉及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疾病還包括偏頭疼、眼部發炎、燙傷、痔瘡、耳聾、痢疾、肝炎、牙痛和抑郁,也包括由于貧窮、貴重物品安全、即將到來的行程、當權者暴政和債務而產生的擔憂與焦慮(Mack et al., 2000:37)。在《雨的禱告》中,她呼吁人們向真主禱告,而非向異教徒精靈求助。“水的存在是世間悲憫,如同火與鋼的價值一樣不可估量。主啊,請施與我們大雨,救贖我們,你的恩賜是無限的。為糧食帶來生機,諸多請求讓您施展手中的權力。我們以先知穆罕默德之名,祈求幫助并堅信會如愿。”作品也關注普遍存在于精靈崇拜儀式的鼓樂,她認為除了在召集會面、軍隊出征等可被認可的鼓樂場合外,婚禮上的鼓樂和狂野舞蹈是罪惡的。詩歌面向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妾、家仆和農村婦女等人群,主要功能是用于記憶和傳唱,因此語言相當簡潔明了。
此外,豪薩語書面詩歌作品也努力構建與世俗社會相關的內容,試圖將日常生活細節融入伊斯蘭教形式之中,消除民眾對于精靈崇拜的精神依附。受伊斯蘭教義學家、法學家安薩里的《兄弟的職責》影響,娜娜將群體的物質、心理和精神訴求作為其詩歌的指導原則,向穆斯林強調物質援助、個人幫助、慎言、坦誠、諒解、禱告、忠誠和解脫的八項義務。她同時著眼于伊斯蘭教的內在化,對伊斯蘭教核心奧秘的個人體驗,以及關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生平的穆圣傳記。如《真理之路》(GodabenGaskiya)中寫道:“我們行走在天堂,遇到穆罕默德,從此獲得永恒的愉悅與平靜。樹蔭下擺滿各種食物,先知告訴我們盡情享用。房子使用黃金蓋造,衣服則是絲綢編織,與先知共飲天堂的泉水。”(Boyd et al., 1997:185)
2.4傳播載體的轉變:從“伊娜”(Inna)到“佳吉”(Jaji)
蘇非教團經常在伊斯蘭教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提加尼教團(Tijanni)與卡迪里教團中都擁有相當數量的女性成員。女性在謝赫的宗教改革運動中也扮演了直接而關鍵的角色。貝洛曾基于13世紀阿爾·賈瓦茲(al-Jawzi)撰寫過一篇關于蘇非婦女的長文,他認為純正的婦女應該是“虔誠、正直及淡泊名利的”,他同時列舉了包括謝赫時代在內的36名婦女典范,娜娜無疑是這些女性中的杰出代表。作為蘇非的導師,她并非追求離群索居,而在索科托哈里發內部廣泛參與宗教、政治、教育事務,恪守師道承傳。伊娜(Inna)是戈比爾(Gobir)傳統的女性統帥和首領(Sarkinmataduka),負責與精靈進行溝通對話,以此為豪薩人提供咨詢和治療,為了彰顯其權威,通常佩戴大頂帽子(malfa),在著裝方面趨于男性化。1808年后,哈里發首領納戈比爾女性為妾的現象十分普遍,倘若精靈崇拜依舊存在,對整個哈里發的統一將會構成威脅,因此如何使這些女性融入哈里發社會是面臨的一大挑戰。
娜娜的豪薩語書面詩歌在傳播方面依靠女性為主體,她指定地區內接受過良好教育、有凝聚力的成熟女性作為首領佳吉(jaji),成群結隊到娜娜家中接受教導,娜娜則專門為這類人群創作商隊詩歌(ayari poems)。娜娜將佳吉的形象效仿伊娜,同樣包裹紅布的大帽子。通過這種方式消除了這種裝束的特殊性并成功轉化了其中的含義,她們在鄰里間及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中傳播知識,內容包括《古蘭經》章節輔導、定時禱告、蘇非女性歷史事跡、戰事勝利、祭奠虔誠信徒的悼亡詩和先知穆罕默德傳記。以豪薩語書面詩歌作為載體,索科托哈里發建立起系統的教育體系并有效進行知識的傳播,取代了豪薩傳統社會的“伊娜”對”后吉哈德”時代的人群進行心靈治愈的角色,“佳吉”成為代言人,向無法到索科托求學的女性治愈心理恐懼和疾病等問題。由佳吉所組成的娜娜的門徒(’yantaru)也使以游牧為主的富拉尼民族具有了相對的固定性宗教生活,地區內相對分散人口也因此建立了相對統一的穆斯林身份認同。
3 豪薩語書面詩歌的社會功能
豪薩語書面詩歌從產生伊始,就突破了文學自身的功能,成為政治代言的工具,并形成相應的創作和傳播機制,最終演變為宗教改革運動中重要文化策略。豪薩書面詩歌在伊斯蘭教的傳播與動員、教育普及、蘇非主義傳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索科托哈里發政權的建立、穩固與發展、強化了哈里發內部宗教身份認同,在豪薩地區伊斯蘭統治合法性的話語建構及豪薩知識社會的建構方面發揮了不可限量的作用。
維護和鞏固了索科托哈里發政權的合法性。索科托哈里發建立后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合法性建立,即獲得當地民眾認可的基礎上實施統治的正當性,謝赫從“圣徒”(walaya)和“天恩”(karamat)中汲取了宗教權威和政治權威,進而建構起其統治政權的合法性并以豪薩語詩歌作為文本載體進行傳播。蘇非主義理論中,天恩是真主意愿的神圣賜予,因此,在謝赫宗教運動及此后的政治發展中,天恩成為統治魅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圣徒名望、影響力、權力等。圣徒通過虔誠和宗教修行獲取真主賦予的高尚地位,在社會實踐中,圣徒也成為權力的來源,用于祝福、治療、審判、預見、轉化、代主實施詛咒與懲罰。伴隨著謝赫和貝洛兩人的相繼離世,通過”吉哈德”運動和建立索科托哈里發政治實體所樹立的權威與影響力不復存在,為了確保他們原有的圣徒地位,繼續維系哈里發政權的合法性,娜娜和基達多開始撰寫圣人回憶詩歌。1831年,娜娜翻譯了謝赫在世時創作的有關社會治理結構及解釋索科托哈里發政權體系下責權的詩歌作品《確信真主真理》(TabbatHakika)。其中包含從初級認識到高度象征的豐富內涵,更深層次的內涵為“神圣真理”(hakika),蘇非領袖通過沙里亞教法(shari’a)通向真主之路,描述了哈里發神學組織的原則。除此之外,娜娜在此基礎上創作了一部全新的《確信真主真理》,號召社會各階層人民在伊斯蘭國家中履行特定的職責,詩中通過不斷重復“確信真主真理”尾韻,對“極致真理”進行反復強調。1837年和1838年,娜娜先后創作了兩部關于貝洛的悼亡詩。娜娜意識到通過神賦信仰維系哈里發內部政治內聚力的重要性,1839年她在紀念姐姐法蒂瑪的悼亡詩中(ElegyforMySisterFadima),首次將謝赫與卡迪里教團創始人同在天堂的概念引入詩歌創作,此后的創作中也明顯增加了作品中圣徒的數量。通過這種方式,娜娜維護和鞏固了索科托政權的合法性,維系了后”吉哈德”時代哈里發內部的凝聚力,強調了謝赫作為精神領袖與蘇非教團圣徒的緊密而永久聯系。
推動了伊斯蘭教知識的普及及豪薩知識社會的建構。19世紀的豪薩社會,知識階層權威與宗教權威并駕齊驅,伊斯蘭知識體系由神職人員所壟斷,獲取的唯一途徑是接受漫長的伊斯蘭教育。豪薩語書面詩歌的出現使宗教領袖在其大量作品中書寫伊斯蘭教義、日常祈禱、信徒行為等基本知識,通過豪薩語詩歌的形式傳遞給普通民眾,改變了此前僅有阿拉伯語詩歌具備書面語形式的局面(Hiskett: 157),打破了原有的伊斯蘭教對于知識的壟斷,使宗教知識由稀缺資源轉變為面向大眾的一般性資源。除宗教知識外,占星術、祈雨術、魔法術等也不再以口頭形式傳播,所有能讀寫豪薩阿賈米的人都能掌握這些知識。娜娜通過詩歌創和傳播在索科托哈里發建立起的系統性婦女教育體系也一直延續至今,成為西蘇丹地區知識普及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豪薩語詩歌創作者采用了阿拉伯語詩歌的編年體形式,用于記錄和書寫歷史,使豪薩社會具備了相對穩定的文字記載歷史,是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
西非地區蘇非主義傳播的有效途徑。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撒哈拉以南的卡迪里教團經歷了文學作品的激增,“打碎墨水瓶和撕爛書本”被某些蘇非視為實踐蘇非主義的第一步,強調了蘇非主義對伊斯蘭教核心奧秘的個人體驗,詩歌成為傳播蘇非神秘主義的嶄新方式。蘇非社團吸納新成員的過程也借助了學習宗教文本的方式,娜娜編譯了富拉尼語和豪薩語版本的《古蘭經》,使用簡短描述性詩歌將真主的語言僅以30對句呈現,此后,娜娜通過“佳吉”(Jaji)在各階層對《古蘭經》進行深度詮釋,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幫助學生記憶和理解。娜娜的作品對于知識分子或者文盲、男性和女性、穆斯林和異教徒都提供了《古蘭經》的基本理解指導及對于神學問題的細致討論(Mack et al., 2000:23),通過豪薩語書面詩歌為哈里發社會各階層提供了文本選擇,更為重要的是,詩歌的創作者使用本土語言對宗教題材進行創作,進而使西非伊斯蘭教演變為一種基于地方性知識的信仰。
4 結語
伴隨著19世紀”吉哈德”宗教改革運動及豪薩書面文學發端,20世紀早期迎來了兩股力量的沖擊:一是謝赫宗教思想的追隨者與馬赫迪(Mahadist)學者間的意見分歧催生了大量的書面論爭;二是英國殖民統治伊始激發了一批豪薩學者為前殖民地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書寫歷史(孫曉萌,2014:59)。盡管如此,豪薩語書面詩歌歷經了伊斯蘭化的洗禮形成了豪薩語“經典文學”的范本,與口頭文學發展而來的“大眾文學”平行發展,書面詩歌演成為“吉哈德”宗教改革運動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并演變為豪薩社會中的永久性文學機制,是豪薩穆斯林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史的變革通常是社會政治環境在文學和文化領域的映射,是深層次的變革。因此,探討豪薩語書面詩歌起源及其發展也必將為深入理解北尼日利亞伊斯蘭社會和政治提供了嶄新的維度。
參考文獻:
Boyd, Jean. 1990.TheCollectedWorksofNanaAsma’uFodioinTranslation,SOASLibraryCatalogueNo.PPMS36[M]. Penrith: SOAS Library.
Boyd, Jean & Beverly Mack. 1997.CollectedWorksofNanaAsma’u[M].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Furniss, Graham. 1996.Poetry,ProseandPopularCultureinHausa[M]. Edingburgh: 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
Merritt, Nikki. 1994. Nana Asma’u: Her Elegi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sider Alternatives’[J].AfricanLanguagesandCultures,7(2):91-99.
Mack, Beverly B. & Jean Boyd. 2000.OneWoman’sJihad:NanaAsma’u,ScholarandScribe[M].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mith, M. G. 1957.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Hausa Praise-singing [J].Africa:JournaloftheInternationalAfricanInstitute, 27(1): 26-45.
Yahaya, Ibrahim Y. 1998.HausaaRubuce:TarihinRubuceRubucecikinHausa[M]. Zaria: Northern Nigerian Publishing Company.
李維建.2011. 西部非洲伊斯蘭教歷史研究[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孫曉萌.2014. 語言與權力:殖民時期豪薩語在北尼日利亞的運用[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