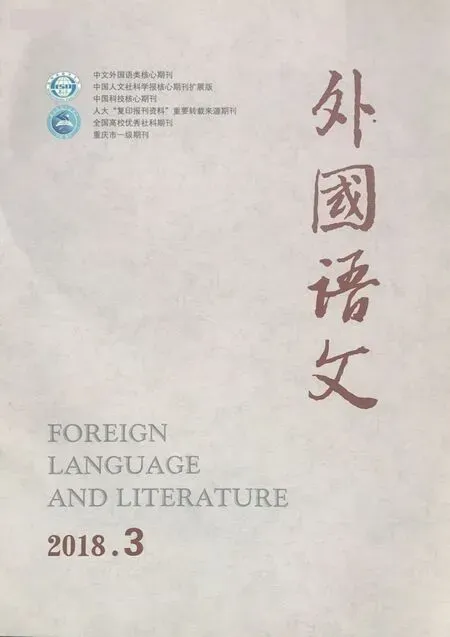麥琪·吉《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中的生命敘事
楊曉霖 陳 璇
(1.南方醫科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515;2.愛丁堡大學 文學、語言與文化學院,英國 愛丁堡)
0 引言
21世紀,西方創作界出現了文學家歷史人物虛構化創作熱潮,諸如《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VirginiaWoolfinManhattan,2014)和《馬洛和莎士比亞在丹麥》上、下部(TheCaseOfTheDeadDane,2013,2015)之類的作品源源不斷進入讀者和評論家的視野,形成生命虛構創作趨勢(Kr?mer,2003:11)。這類作品雖與作家傳記虛構有一定相似性,都以真實作家為虛構對象,但在虛構策略和創作模式方面又比傳記虛構更加開放,采用明顯的虛構敘事框架,大膽地偏離史料記載的作家生命軌跡或延長他們的生命故事。此外,不同于傳記虛構的是,這類作品更注重采用當代社會文化視角來重新闡釋新語境下文學家生命主體的人生故事。它們已然形成一種獨具風格的文學形式,佛克馬(Aleid Fokkema)(1999:39)聲稱作家已成為后現代主義虛構作品中的類型化人物(postmodernism’s stock character),對作家為中心的迷戀成為當代文學文化的基本元素(Bennett,2005:108)。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是麥琪·吉(Maggie Gee)順應以作家為中心的文化迷戀的巔峰之作。這部生命虛構小說寄生于伍爾芙的生命因子,不僅讓20世紀最杰出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穿越到21世紀的紐約,而且塑造了一個迥異于伍爾芙傳統傳記形象的特異互補形象,是一部生命延展型非自然生命虛構敘事作品。作品大膽地虛構文學先輩,其語言風格在極力模仿伍爾芙的同時,又不失麥琪本真的風格,在克服“影響的焦慮”的同時,超越了自己。
1 麥琪·吉與《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
當代女作家麥琪·吉是英國皇家文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2004—2008)首位女主席,目前任教于歷史悠久的巴斯泉大學(Bath Spa University)。麥琪·吉從事小說創作30余年,創作伊始便被遴選為1983年度格蘭塔英國最佳新銳小說家(Granta’s “Best Young British Novelists”),并成為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UEA)的文學創作專員。此后,陸續出版12部小說和一部短篇小說集,廣受評論界和讀者好評,包括《優雅》(Grace,1988)、《冰人》(TheIcePeople,1998)、《懷特一家》(TheWhiteFamily,2002)、《我的清潔工》(MyCleaner,2005)和《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VirginiaWoolfinManhattan,2014)等。
麥琪的作品屢獲文學大獎。其中,《懷特一家》獲選進入2002年英國柑橘文學獎和2004年全球獎金最高的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The 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短名單。2004憑借小說《水患》(TheFlood,2004)再次入圍英國柑橘文學獎;2012年因其杰出的文學貢獻被英女王授予大英帝國騎士勛章中的官佐勛章(OBE)(?zyurtkilic,2014:1-2)。
麥琪大多數小說以英國本土為故事背景,圍繞英國中產階級的社會關系問題,如消費文化、破碎家庭、迷失一代、階級矛盾、種族歧視和同性戀恐懼等展開,但《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這部巔峰新作卻遠離英國本土,以美國曼哈頓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為背景,講述兩位女性作家人物——虛構化的伍爾芙和當代小說家安琪拉(Angela Lamb)之間的故事。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是一部關于20世紀最杰出小說家伍爾芙的生命虛構作品,也是麥琪創作耗時最長的巔峰之作。之所以稱其為巔峰之作,一方面因為作品大膽地虛構文學先輩,在極力模仿伍爾芙的同時,又不失麥琪自己的風格,在克服“影響的焦慮”的同時,超越了自己;另一方面因為作品中融入了麥琪的其他虛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創作精髓——少女時代的安琪拉首次出現在《燃燒之書》(BurningBook,1983)里,接著作為一位非常自我的作家出現在《水患》中,在《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中至少是第三度出現。借此,麥琪將伍爾芙的現實世界與伍爾芙的虛構世界以及麥琪的多個虛構故事世界聯通了起來。
麥琪創作《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既屬偶然,也可謂必然。早在17歲時,麥琪就曾閱讀《雅各的房間》(Jacob’sRoom)和《一間自己的房間》(ARoomofOne’sOwn)等伍爾芙作品,之后她的博士論文也以伍爾芙為研究對象,繼而發表過對伍爾芙相關作品的評論,在她的回憶錄《我的獸生活》(MyAnimalLife,2010)中伍爾芙的影響也隨處可見,伍爾芙理所當然地成為指引麥琪進行文學創作的“女前輩”(foremother),但她從未有過將這位真實作家虛構化為自己筆下的人物的創作念頭,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麥琪赴位于曼哈頓的紐約公共圖書館查閱伍爾芙文獻,卻被告知由于它們非常珍貴,她無法翻閱實物,只能通過縮微膠片觀看。萬分沮喪的麥琪極度渴望伍爾芙從堆放著她曾朝夕接觸的書本的書架中走出來,授予她直接翻閱她的文獻的權力,這時她突然萌生了寫一部讓伍爾芙出現在她從未到過的伯格藏書館的小說的念頭(Gee,2014:21)。
在《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中,英國小說家安琪拉受邀作為發言人參加在伊斯坦布爾召開的以“二十一世紀的弗吉尼亞·伍爾芙”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為使講座發言更具深度,實現自己從暢銷小說作家到學者型作家的轉變,安琪拉赴伍爾芙的眾多日記、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存放地——曼哈頓的伯格藏書館(Berg Collection)感受伍爾芙的一手文獻,結果被告知即使是預約的參觀者也無權翻閱這些珍貴資料。沮喪之中的安琪拉抬頭間突然發現書堆中走出一個女人,“這個女人。這個奇怪的女人。那個充斥在我大腦的每一個角落里的女人竟然就在我眼前。高挑個子,滿身泥濘,一套灰綠的衣服還濕漉漉地貼在身上”。冥想成真的安琪拉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眼前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伍爾芙,帶著“淡酸的泥土和水草味道”的伍爾芙。
21世紀的紐約一切照常,只是多了一個弗吉尼亞·伍爾芙。盡管對伍爾芙有著強烈的學術好奇和研究興趣,安琪拉對這位突如其來的非凡新伴侶并不待見。對于伍爾芙來說,眼前的一切也突如其來,從未到過紐約的伍爾芙在一個人地生疏、光怪陸離的新世界里無所適從,時而焦慮萬分,時而興奮不已,安琪拉不得不煞費周章地多番解釋。伍爾芙對陌路相逢的安琪拉直呼其為“弗吉尼亞”的做法大感不滿,直言不諱地訓斥安琪拉缺乏教養,而安琪拉則因處處要為伍爾芙買單付賬而心生怨氣——看上去優雅的伍爾芙一頓能狼吞虛咽六個漢堡;她在著名的布魯明戴爾百貨店(Bloomingdale’s)看上一頂優雅且價格不菲的帽子,戴上就走,只顧著說“我買了一頂帽子,它簡直就是一首詩”,留下不情愿的安琪拉獨自刷卡。盡管如此,伍爾芙與安琪拉從此形影相隨,互利互惠。在生活上伍爾芙依賴于安琪拉,而安琪拉則從伍爾芙那獲取文學養分。
伍爾芙對現代世界的新事物,如整容手術、移動電話、手提電腦、維基百科、互聯網等的反應總能讓安琪拉忍俊不禁。伍爾芙敏而好學和孜孜不倦的探究態度感染了安琪拉。手提電腦是現代文明的象征,在安琪拉的幫助下,一開始用水果刀去撬手提電腦的伍爾芙學會使用了電腦和網絡。在高價賣掉塞在口袋里的除石塊之外的《奧蘭多》和《去燈塔》原始手稿之前,伍爾芙將它們笨拙地敲進了電腦里保存了起來。沒想到她的書稿價值不菲,以$90 000的高價賣出,這讓剛剛聽聞紐約的兩大標志性書店從當日起不再運營的消息的兩位女性感到一絲慰藉。她們一起談論性別政治、地理政治和文學。她們一起參觀自由女神像,伍爾芙欣喜地將它視為“女性斗士的典范”(a model of the just female warrior),當伍爾芙壯著膽子問她的長篇論述《三枚金幣》(ThreeGuineas)是否對警醒世人防范父權制的危險發揮作用時,安琪拉只好裝聾作啞,避而不答。她們來到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追尋格蘭特(Duncan Grant)、弗萊(Roger Fry)和文妮莎(Vanessa Bell)的畫像,卻一無所獲,當意識到她再也見不到他們時,伍爾芙陷入短暫的抑郁。
雖然小說的主要故事發生地是在紐約,但麥琪也讓伍爾芙跟隨安琪拉來到伊斯坦布爾。與紐約不一樣,少女時代的伍爾芙曾經到過伊斯坦布爾,而且這個當時仍然被稱為“君士坦丁堡”的地方正是伍爾芙的“奧蘭多”變性的地方,因而算得上是故地重游。不同的是,這一次伍爾芙幾乎與一位賓館前臺接待經理墜入愛河,伊斯坦布爾成為冷漠的伍爾芙欲望再次覺醒之地。通過設置伊斯坦布爾這條故事線,一方面讓伍爾芙重獲了某種地域上的熟悉感,另一方面將紐約與這個異國風情的城市的過去與現在聯系起來,這也是連接安琪拉和伍爾芙的女性身份和作家身份的認同之地。
2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的文類屬性及敘事特點
2.1 文類屬性:傳記虛構抑或生命虛構
在歐澤約奇里克(Mine ?zyurtkilic)對麥琪的一次采訪中,麥琪提到當代小說家所熱衷的寄生創作現象。麥琪援用布萊克摩爾(Susan Blackmore)的概念,認為這類創作者為了提升作品的品質和對讀者的影響力,將虛構作品建立在對歷史名人的模因(memes)之上,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和形象成為使讀者即刻對作品產生閱讀興趣的認知因素(?zyurtkilic,2014:4-5)。
布萊克摩爾的模因很容易讓批評家們想到哈琴(Linda Hutcheon)和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的傳記因子(biographeme)這一概念。“傳記因子”這一概念為羅蘭·巴特首創,定義為“由超然友好(沒有偏見)的傳記作家編撰的關于傳主生命故事的細節”(Barthes,1981:30)。哈琴繼而將其定義為“傳記和歷史文獻的小單位”(Hutcheon,1988:85)。我們發現,兩位理論家的概念主要與傳記和傳記虛構文類相對應。然而,在《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中,這些模因不只是源于學術型傳記,也來源于伍爾芙的書信、日記以及她所創作的虛構作品片段,更重要的是,在這部作品中,不是虛構的成分穿插在歷史名人——伍爾芙的模因之中,而是在整體虛構的文本之中穿插伍爾芙的模因。
為了區分作品里關于伍爾芙的傳記因子與虛構因子,我們將作品里與伍爾芙的傳記、自傳(書信、日記)以及虛構作品等可以找到文本和現實參照的敘事元素稱作生命因子(bio-meme),將作品里找不到參照依據的,或虛構或杜撰的各類文本和敘事元素稱為非生命因子(a-bio-meme)。出于進一步探討《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與傳統的伍爾芙傳記虛構的區別的需要,我們在“非生命因子”的基礎上,進一步劃分“可能性非生命因子”和“不可能性非生命因子”。
傳統的傳記虛構主要是對傳記主體進行可能性的虛構,創作者的自由被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McHale,1987:87),主要做的是對沒被納入官方紀錄范圍的文學家的非檔案性生命因子(undocumented bio-meme)進行補充和假想創作,在它們留下的朦朧模糊的空白處填入清晰連貫的信息(Latham,2012:356)。然而,《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則展示出更強的虛構傾向,非生命因子在伍爾芙生命進程中的作用加大,甚至偏離伍爾芙的生命進程。根據伍爾芙的生命因子記載,伍爾芙的生命結束于1941年3月28日,然而在這部作品中,伍爾芙的生命在21世紀得以延續,成為熙熙攘攘的紐約街頭的一位人物,成為出席關于自己在21世紀的文學地位的研討會的一位聽眾。亦即作品通過運用時空錯置錯層敘事,將伍爾芙置身于一個全然不同于她的生活世界的地方,突出后現代創作的時間錯置和非歷史性兩大趨勢,這遠遠超出了傳記虛構的自由范圍。
在傳記虛構中伍爾芙仍然是傳記主體,而在生命虛構中,伍爾芙則成為生命虛構主體,她在作品中所獲得的虛構身份大于她的傳主身份。作品通過伍爾芙的生命因子闡明生命虛構主體的“歷史性”和“確定性”,再通過非生命因子所凸顯的生命虛構主體的“非歷史性”和“不確定性”抵消了她的歷史人物身份和傳主身份。這是傳記虛構所不具有的特點。因而,我們認為《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不是一部傳記虛構作品,而是一部“伍爾芙生命虛構敘事”作品。
許多世界頂級作家在創作巔峰之際都會對文學先輩的傳記或自傳進行虛構化重寫,如,庫切的《福》(Foe,1986)和《彼得堡的大師》(TheMasterofPeterburg,1994)、溫森特(Jenette Winterson)的《藝術與謊言》(ArtandLies,1995)、坤(Dinah Lee Küng)的《伏爾泰來訪》(AVisitfromVoltaire,2004)以及懷特(Edmund White)的《芬妮:一部虛構作品》(Fanny:AFiction,2003)和《夢之旅館》(HoteldeDream,2007)等。這類作品大量使用平行敘事、錯層敘事、非自然敘事(不可能世界敘事)等敘事策略(Yang,2015:457)。它們大多將被虛構的文學家的虛構作品融入創作之中,因而它們在敘事層次上也呈現出比傳統傳記虛構更為復雜的特點,這類作品可稱作“生命虛構”(楊曉霖,2014:27),或者更精確地說,可稱為“文學家生命虛構敘事作品”。
文學家生命虛構寫作本身是一種“對話交流”形式,通過一種被敘述的作家和正在敘述的作家間的“主體間運作”實現(Regard,2000:408),他們的目的很可能在于“征服大師”(mastering the master)(Priest,2007:304),征服他們對自己影響的焦慮,正如洛奇所言,對先輩作家的人生故事進行虛構是“對付‘影響的焦慮’的一種積極和絕妙的方式”(Lodge,2006:10)*原文為“a positive and ingenious way of coping with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2.2 伍爾芙生命虛構作品的敘事特點
近年來,多部關于伍爾芙的生命虛構作品陸續出版,分別為弗里曼(Gillian Freeman)的《但是無人住在布魯姆伯里》(ButNobodyLivesinBloomsbury,2006)、拜蓉(Stephanie Barron)的《白色花園:一部關于伍爾芙的小說》(TheWhiteGarden:ANovelofVirginiaWoolf,2009)、帕瑪(Priya Parmar)的《文妮莎和她的妹妹:一部小說》(VanessaandHerSister: ANovel,2014)、文森特(Norah Vincent)的《艾德琳:一部關于伍爾芙的小說》(Adeline:ANovelofVirginiaWoolf,2015)等。其中麥琪的《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構思最為大膽和巧妙,屬于生命延展型文學家生命虛構敘事。然而,與延展濟慈生命的作品《凱克博士的杜撰》(TheInventionofDrCake,2004)不同的是,《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不僅涉及伍爾芙的生命延續,而且麥琪是讓伍爾芙的生命在另一個非連續的時空里得以延續。作品一方面采用非自然時空敘事框架,讓伍爾芙在21世紀獲得新生,跟隨當代英國小說家一起游歷紐約和伊斯坦布爾,讓麥琪游刃有余地對20世紀文化與21世紀的英美文化進行了充分的深度對比;另一方面大量地插入伍爾芙的傳記因子和虛構文本因子,并且融入學術圈元素(學術會議和文學評論等),讓讀者聯想到洛奇的《小世界》(SmallWorld,1995)和埃斯伯雷(Matthew Asprey)的《非洲紅山:一部中篇小說》(RedHillsofAfrica:ANovella, 2009)等作品。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充滿非自然敘事元素。“在不可能世界中構筑某種可能”是后現代生命虛構的新思維模式。在不可能生命敘事中,一切不可能都成為可能:時空可以穿越,生命可以改寫,現實可以轉變。就像《伏爾泰來訪》(AVisitfromVoltaire,2004)里從18世紀的法國穿越到現代美國的伏爾泰一樣,伍爾芙直接從1941年英國的歐塞河穿越到21世紀的紐約!這不具有可能世界的經驗性(experientiality),在現實中是不可實現的(non-actualizable)(Ronen,1994:51)。
伍爾芙不僅實現了穿越,還成為作品里的兩個主要敘事者之一。歷史現實中的伍爾芙是位極富貴族氣質的美學家,她敏感憂郁,不諳男女性愛,一生彌漫著強烈自殺傾向,而在小說里,她搖身變成了一位活力四射的生活和愛情的探索者,盡管時而也會情緒短暫低落,但總體來說,是一個與伍爾芙的傳記形象形成互補、讓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新舊文明的沖撞和新舊伍爾芙形象的鮮明對比給這部作品帶來喜劇氛圍。小說的另一個敘事聲音發自安吉拉(Angela Lamb),她也是一位小說家,與伍爾芙不同的是,她是一位麥琪·吉在其他已經出版的虛構作品里出現的虛構小說家。虛實世界中的小說家分別充當新的故事的述說者,故事層次的交錯邀請讀者進入奇幻的閱讀之旅。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交替使用安琪拉和伍爾芙的個性化話語。安琪拉的語言是一種潛意識里已受伍爾芙影響,但又保持著她作為獨立的當代作家語言特色的話語。由于作品選取伍爾芙的日記、信件和虛構作品等文本因子進行重新語境化虛構,因而,為保持話語風格的一致性,麥琪在以伍爾芙為敘事者的片段里必須盡量模仿伍爾芙的行文風格,同時為使伍爾芙的新形象不至于落入前人傳記的窠臼,作家麥琪也必然對作為生命虛構人物的伍爾芙話語進行微調,形成麥琪-伍爾芙式的話語特色,甚至讓伍爾芙時不時冒出三兩個時興詞匯。麥琪游刃有余地在故事進程中插入伍爾芙虛構文本因子,讓整部小說看似麥琪布設的一個顯示其作為伍爾芙研究者的高深造詣的游戲,如為使紐約和伊斯坦布爾兩條故事線聯系得更加緊密,麥琪模仿伍爾芙《去燈塔》里的《時間飛逝》(Time Passes)的寫法將兩部分自然地橋接起來。許多對話情節也與《海浪》等作品中的對話不無相似之處,互文拼貼感無處不在。
由于大量地采用伍爾芙的各級生命因子,熟悉伍爾芙的傳記信息和全套作品的讀者能更充分地欣賞這部生命虛構作品如何將事實和虛構精妙地糅合起來,判斷出哪些來自伍爾芙一級生命因子如自傳、信件、日記,哪些來自二級生命因子如傳記和文學研究著作,哪些屬于虛構文本因子中的引語和改述,它們如何恰如其分地植入一個個虛構片段的縱橫結構當中。這類讀者往往像文學偵探一樣,從作品的字里行間可以讀出元傳記評論(metabiographic comments)和文學學術元素(literary scholarship)來。而對于不熟悉伍爾芙的讀者來說,《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也可以視為了解伍爾芙的初始文本,它足以激起新讀者對伍爾芙傳記、日記和其他虛構文本的閱讀興趣,進而制造新一代的伍爾芙書迷。
3 結語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與伍爾芙各級生命因子之間存在創造性寄生關系(creative parasitism),它以伍爾芙的生命因子為參照,通過虛構化策略,將伍爾芙轉化成生命虛構主體,將作品轉化為生命虛構敘事。因而,更準確地說,《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是麥琪順應21世紀以作家為中心的文化迷戀和作家生命虛構創作熱潮的巔峰之作,是麥琪對伍爾芙傳記和伍爾芙創作的忠實性反叛(fidelity-in-betrayal)(Connor,1996:167)。
雖然屬于虛構作品,但麥琪·吉為創作《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曼哈頓》做了大量細致的文獻研究工作,通過虛擬話語、混搭敘事和錯層敘事等多種虛構化策略,將文學家的生命因子與可能性非生命因子和不可能性非生命因子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這部與伍爾芙相關的生命虛構不僅以另類的方式讓讀者加深了對伍爾芙生平以及作品的了解,也激起了讀者重讀經典的熱情。
參考文獻:
Barthes, Roland. 1981.CameraLucida.ReflectionsonPhotography[M].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 Wang.
Bennett, Andrew. 2005.TheAutho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onnor, Steven. 1996.TheEnglishNovelinHistory. 1950—1995 [M]. London: Routledge.
Fokkema, Aleid. 1999. The Author: Postmodernism’s Stock Character[G]∥Paul Franssen and Ton Hoenselaars.TheAuthorasCharacter.RepresentingHistoricalWritersinWesternLiterature. Cranbury, London and Mississauga: Associated UPs.
Gee, Maggie. 2014.VirginiaWoolfinManhattan[M]. London: Telegram Books.
Gee, Maggie. 2014. Review: Ghostwriter Maggie Gee in the footsteps of Virginia Woolf[N].TheGuardian, 20 (Sept.): 21.
Hutcheon, Linda. 1988.APoeticsof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M]. Routledge, New York.
Kr?mer, Lucia. 2003.OscarWildeinRoman,DramaundFilm:EinemedienkomparatistischeAnalyseFiktionalerBiographien[M].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Latham, Monica. 2012.Serv[ing] under Two Masters’: Virginia Woolf’s Afterlives in Contemporary Biofictions [J].A/B:Auto/BiographyStudies(27): 356.
Lodge, David. 2006.TheYearofHenryJames:TheStoryofaNovel[M]. London: Harvill Secker.
McHale, Brian. 1987.PostmodernistFiction[M]. New York: Methuen.
?zyurtkilic, Mine. 2014. A Sense of Completeness, of Understanding, Enfolding All Difference: An Interview with Maggie Gee [J].ContemporaryWomen’sWriting, (16): 1-15.
Priest, Anne-Marie. 2007. The Author is Dead, Long Live the Author [J].LifeWriting4(2): 303-305.
Regard, Frédéric. 2000. The Ethics of Biographical Reading: A Pragmatic Approach [J].CambridgeQuarterly, 29(4): 394-408.
Ronen, Ruth. 1994.PossibleWorldsinLiterary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ang, Xiaolin. 2015. Application of P & RBL Model to English Literature Course[J].TheoryandPracticeinLanguageStudies, 5(3): 457-462.
楊曉霖. 2014. 2013:菲茨杰拉爾德年——評四部作家生命虛構小說[J]. 外國文學動態 (3): 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