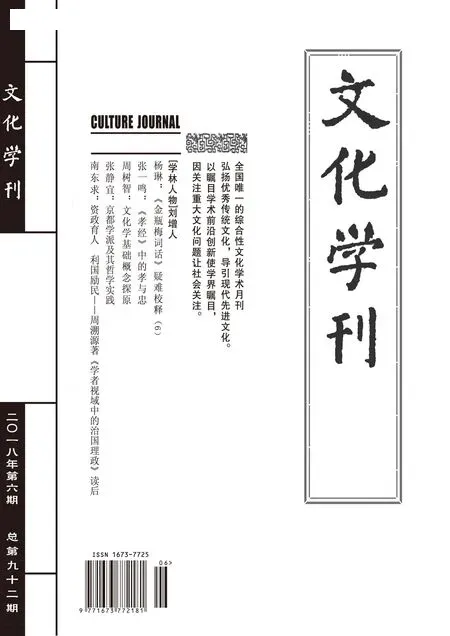藏族“一妻多夫”婚姻形態(tài)變遷實證調研
——以西藏自治區(qū)、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調查為例
曾彬彬 陳文聰(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1)
一、研究背景
“一妻多夫”是指一名女性和多名男性結為夫妻,共同組成家庭的婚姻形態(tài)。在我國,“一妻多夫”婚姻主要存在于藏族等少數民族中,分布于西藏、云南等地,其中以農耕地區(qū)尤甚。[1]筆者于2017年7月前往西藏自治區(qū)白朗縣的洛江村和迪慶自治州德欽縣的書松村進行調研,從調研情況看,經濟因素是當地居民選擇“一妻多夫”的首要因素,不過也不能忽視文化和倫理上存在認同這一婚姻形態(tài)存續(xù)的因素。在《婚姻法》有關規(guī)定的語境下,“一妻多夫”是一種違法的婚姻形態(tài),即便《婚姻法》50條賦予了民族自治地方進行變通規(guī)定的權利,這種變通也以不超過法定婚姻制度范圍為限。被調研的兩地都視“一妻多夫”婚姻為違法的封建陋習,雖然兩地可以通過頒布宣誓性條款或下發(fā)通知的形式宣告“一妻多夫”婚姻的違法性,但各地基層政府不得不面對“一妻多夫”家庭所存在的問題。基層政府試圖從“一妻多夫”婚姻產生的原因入手,逐漸動搖這一婚姻形態(tài)的存在根基。
二、“一妻多夫”婚姻的變遷與成因
據調查,洛江村共有196戶村民,其中48戶為“一妻多夫”家庭,占比約24.5%;書松村共有233戶村民,其中8戶為“一妻多夫”家庭,占比約3.4%。由此可見,這一違反國家法律婚姻形態(tài)依舊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不過從存在數量和比例看,“一妻多夫”婚姻已經不是當地藏民的主流選擇。這不僅反映在現(xiàn)存數量上,更體現(xiàn)在其增長速度上,西藏自治區(qū)的洛江村新締結的“一妻多夫”婚姻頻率已經出現(xiàn)較為明顯的下滑,每年不超過3戶,甚至會有連續(xù)2~3年沒有新“一妻多夫”家庭的情況;而迪慶自治州的書松村則已經徹底不再出現(xiàn)新的“一妻多夫”家庭,當地年輕的婚姻適齡者已然放棄了“一妻多夫”婚姻。可以預見到,這一婚姻形態(tài)終將走向消亡。值得注意的是,當地的國家機關并未刻意運用強制性手段廢除“一妻多夫”婚姻,而是通過發(fā)展經濟、提高教育水平、普及法律知識等方法,通過提升當地整體經濟文化水平的方式引導人們逐漸放棄“一妻多夫”婚姻。而前人通過構建“社會—經濟理論”為主、“文化心理”理論為輔的理論體系來解釋其成因[2],結合調研情況,筆者認為本組所調研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兩個理論的合理性。
第一,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使得“一妻多夫”婚姻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西藏和迪慶,農村基層政府一方面承接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創(chuàng)造了一定數量的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不斷招商引資,轉換土地的用途。以西藏的洛江村為例,當地將三分之一的農業(yè)用地轉變?yōu)樯虡I(yè)用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農業(yè)用地雖然減少,但機械化程度的提升保證了農作物的產量;創(chuàng)收方式的多樣化使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土地中得以解放,并從事商業(yè)、交通運輸等工作。迪慶的書松村則發(fā)展了具有合伙性質的民辦企業(yè),由村民出資購買機械,在原先的農田上組建工廠,加工農產品,提升產品附加值。“一妻多夫”婚姻的產生,是藏民基于迫切的生存需要所采取的生存手段,在一定時期內確實起到了增加家庭勞動力、保護家庭土地和財產的功效。[3]但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世紀經濟水平的發(fā)展,生存問題已經不再是最為迫切的問題,“一妻多夫”婚姻不再是保持生產、維持生存的唯一手段。隨著創(chuàng)收方式的增多,以及村民對土地依附性的降低,耕地上的作物早已不是當地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勞動力數量已經不完全是衡量一個家庭收入能力的唯一因素;隨著新技術和新生活思路不斷涌入這些地區(qū),人們的生產效率得到提升,對勞動力數量的依賴程度已經明顯降低,很多一夫一妻的家庭也可以獲得他們滿意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見,對“一妻多夫”存續(xù)影響最大的土地和經濟因素正在被沖淡,“一妻多夫”婚姻正在失去其存續(xù)的土壤。
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極大地改變了藏民的婚姻家庭觀。無論西藏還是迪慶都十分重視教育的普及工作,都實行集中辦學的政策,構建了村—鄉(xiāng)/鎮(zhèn)/縣—市的教育體系。在九年義務教育、十四年免費教育、教育“三包”政策和學業(yè)補助政策的扶持下,大部分適齡兒童都能獲得初中以上的學歷,基本不會因為經濟上的原因放棄學業(yè)。并且越是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藏族青年,他們在離開自己的家鄉(xiāng)去外地求學之后,其婚姻觀念改變得越徹底。幾乎所有受到過高等教育的藏族人都傾向于“一夫一妻”婚姻,可以說,“教育”在藏族同胞重新認識“一妻多夫”方面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從而并沒有與當地的傳統(tǒng)觀念直接發(fā)生沖突。
第三,人口流動的增多,帶動了思想的開放和生活觀念的轉變。很多村民選擇走出村莊,進入城市,這一過程帶來了兩個方面的變化。對于農村女性而言,進入城鎮(zhèn)務工,使她們的視野更為開闊,婚姻觀念更為開放,更加追求一份排他的戀愛和婚姻關系。隨著越來越多農村女性涌向城市,農村男性尋找伴侶的難度在逐漸增加,在農村的女性也隨之有了更大的發(fā)言權,可以更加遵從于自己的意志進行選擇。對于男性而言,由于“一妻多夫”婚姻中,眾兄弟之間的年齡差距,特別是年齡最長與最幼者之間的差距往往較大,一些不滿足于“一妻多夫”婚姻的丈夫也在尋求脫離原來家庭的可能,去城市尋找工作,組建“一夫一妻”家庭。隨著進城務工的農村藏民越來越多,他們的婚姻觀念也在逐漸走向開放。因此,人口的流動帶來了觀念的更新,觀念的更新又在推動著人口的不斷流動,從而使新組建的“一妻多夫”家庭的數量逐漸減少。
第四,依法治國的不斷深化推進促使權利意識覺醒。以洛江村為例,大部分當地居民都知曉《婚姻法》的存在,并對我國“一夫一妻”的法定婚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雖然“知法”和“守法”之間尚有一定的距離,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法律的不斷普及,當地民眾的權利意識已然覺醒,這主要表現(xiàn)在婚姻家庭糾紛數量的增多,特別是婦女起訴丈夫的案件增多。雖然大部分糾紛都可以通過調解的方式化解,但女性主張權利的行為已經證明她們知曉自己應當享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權利、人格尊嚴及婚姻戀愛自由等權利,并渴望這些權利得到實現(xiàn)。另外,婚姻登記制度的推行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的作用。婚姻與戶口登記對未來孩子是否能接受教育(學籍)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隨著政府的不斷宣傳,藏族家庭也都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為了方便孩子教育入學,藏族家庭都會到民政局進行婚姻登記。婚姻登記本身無法阻止“一妻多夫”婚姻的產生,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導和教育的作用:在婚姻登記的過程中,當地居民必然了解到,一位妻子在法律上只能有一位丈夫。
三、結語
如何在發(fā)展民族地區(qū)經濟的同時,尊重當地風俗習慣,提升當地居民對國家和國家法律的認同,是每一個基層地區(qū)國家機關都需要面對的課題。民族習慣有其特定的產生背景,在面對這些習慣時,不能單純地結合某一價值進行道德評判,而應客觀分析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并抓住其本質加以引導。民族團結是當前中國的基本國策,而民族團結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調和民族習慣和國家法律之間的關系。西藏和云南基層國家機關間接治理“一妻多夫”婚姻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可取性,即通過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方式引導人們逐步放棄同國家法律和政策不符的風俗習慣,讓群眾自發(fā)地對于“一妻多夫”婚姻進行反思和取舍,既達到了發(fā)展的目的,又避免了國家意志強制落實時引發(fā)的矛盾。“一妻多夫”婚姻形態(tài)的逐漸消亡,從某一種角度而言體現(xiàn)了我國治理水平的提升,也揭示了國家法律與民族習慣之間協(xié)調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