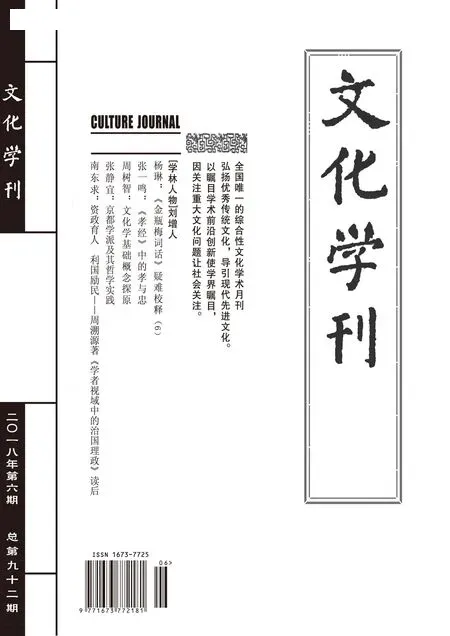昆劇《浣紗記》以《泛湖》作結的意義探尋
王宇菲(山西師范大學,山西 臨汾 041000)
梁辰魚作為魏良輔改革派系中的一位推動者,在明朝嘉靖末年的昆腔革新運動中,經過不斷的鉆研積累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一大流派,編著了第一部昆劇劇本《浣紗記》。劇本以描寫范蠡與西施的愛情為故事線索,揭示了吳越兩國興亡衰敗的原因,全劇以《泛湖》為尾聲作為情節發展的終結,其中蘊含著劇作家文學藝術的匠心精神,即在平衡觀眾審美心理之余還潛藏著多重可待挖掘的深意。
一、文人的自省意識
在《浣紗記》中,梁辰魚在傳統歷史故事的基礎上,增添了了范蠡、西施的愛情線索,那么作者的重點是想要表現吳越興亡的歷史教訓呢,還是體現范蠡、西施堅貞不渝的愛情故事呢?顯然,這其中飽含了梁辰魚“以曲為史”的歷史自覺性和省人的創作意圖。明清中葉以后,“以史作劇,以劇為史,成為傳奇作家自覺的審美追求”[1],文人傳奇作家們都自覺且有意識地把史論興嘆融會到劇本創作當中,在敘述中加入自身的感悟與探討。梁辰魚在首出《家門》中便道出他的創作動機:
【紅林檎近】何暇談名說利,漫自倚翠偎紅。請看換羽移宮,興廢酒杯中。驥足悲伏櫪,鴻翼困樊籠。試尋往古,傷心全寄詞鋒。[2]
本出以“暗說”的形式點明創作動機,作者自稱“驥足悲伏櫪,鴻翼困樊籠”“傷心全寄詞鋒”,頗有懷才不遇、壯志未酬之志。曲中所表現的淡泊名利、不追求“倚翠偎紅”豪華享受的思想傾向,以及寄情于“換羽移宮”的戲曲創作、思考歷史與人生的追求,無不顯示著對功名失意的感慨和歷史興亡的感傷。而后的【漢宮春】一曲中敘述劇情梗概,此曲盛贊范蠡、西施的愛情故事,也為他們在紛亂興亡的歷史環境中鋪墊了理想的結局。這在最后一出《泛湖》中對于吳越兩國的興衰喟嘆及飽含人生哲理的頌歌反思得到對應:
【北收江南】(生)呀!看滿目興亡真慘凄,笑吳是何人越是誰?
【北清江引】(生)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論興和廢。富貴似浮云,世事如兒戲。[3]
范蠡、西施二人遠離朝廷,擺脫紛雜的世俗,以《泛湖》作為結束,余韻裊裊,引人深思。功成身退、歸隱湖山,是古代文人實現人生價值的一條途徑。首出“平生慷慨,負薪吳市梁伯龍”與本出“盡道梁郎識見無,反編勾踐破姑蘇”首尾呼應,作者深意可見一斑。梁辰魚創作《浣紗記》時正當壯年,卻苦于報國無門,奈何最高統治者沉湎酒色、奸臣當道、殺戮良將。現實中的明世宗不就是《浣紗記》中的吳王、越王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對國家興廢置之不理。于是,梁辰魚借《浣紗記》來映射現實環境,袒露對歷史興亡的感慨,充分表現出梁辰魚“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創作宗旨。由此可見,《浣紗記》以《泛湖》為結縱觀悲歡離合的始末,既符合劇本的客觀內容和結構要求,也展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憤慨與無奈,同時在《浣紗記》中加強了濃烈的時代色彩,結合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使其達到思想上的高度融合。
二、正旦的家國情懷
能構成“離合之情”與“興亡之感”的必要角色非正旦莫屬,而此角色首先要具有政治觀念,進而才能促發其參與政治斗爭的事實。此外,劇中正旦必然是國家動蕩不安中的關鍵性人物。受封建社會的束縛,女子必須遵從“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教,女子以“無才便是德”的卑微社會地位立世,“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大家小姐成為行為典范。因而,她們極少接觸社會生活,更別提與政治興亡的聯系。在封建父系社會中,女性極少有家國情懷的政治參與意識,而《浣紗記》中的西施在有限的條件下展現著自己的政治才華。
關于歷史中的西施流傳著多種說法,《越絕書》與《吳越春秋》中,西施在吳越爭霸的故事中都十分被動,僅僅像妹喜、妲己、褒姒那樣,被冠以“美人計”的稱號,是用來惑亂帝王的工具。梁辰魚《浣紗記》中塑造的西施是一位美貌與智慧并存的美人,政治使命的賦予使西施擁有了勇敢正直的歷史形象,西施的這種以國家事為重的大家意識在《迎施》一出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別離三年后,杳無音信的范蠡再次與西施見面后解釋無音信的原因是“為君父有難,拘留異邦”,此時一個深明大義、不計較個人得失的西施在這時得到盡顯,“但國家事極大,姻親事極小,豈為一女之微,有負萬姓之望?”[4],可見西施的思想境界。后得知范蠡為了國家大義欲將自己進獻于吳王,迷惑吳王,致吳敗則越興,西施哀哉:“不過是田姑村婦,裙布釵荊……恐難移彼易此”[5],但是范蠡一句“稷廢興,全賴此舉”。雖無奈,西施“勉強應承”[6],接受了范蠡為國移情之議。至此,西施正式成為吳越爭霸的關鍵性人物,同時西施的人物地位達到了如同范蠡、文種等將臣一般的地位。文已至此,觀眾不禁感嘆范蠡到底更看重江山還是美人呢?在最后一出《泛湖》中梁辰魚給出了答案,范蠡通過【北雁兒落】【北得勝令】【北沽美酒】三首曲向西施傾訴衷腸,吐露當年薦西施入吳宮的矛盾與痛苦。可見范蠡既心系大國之憂樂,具有胸懷韜略的豪邁,又有傳統文人對自由美好的期許,無奈在政治背景下將愛情線索含蓄隱忍。故而,吳亡后,倆人終得眷屬便攜手相伴一同泛湖登舟遠遁,這樣的結局彰顯了范蠡與西施進退自如的人生態度,折射出不一樣的人性光輝。
三、明朝思學的影響
作為明朝理學的代表形態,陽明心學有著極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并發展形成一陣聲勢浩大的社會思潮。“明中葉以后出現的帶有近代化色彩的文學新思潮,特別是戲曲、小說的大發展,實際上正是左派王學及反理學思潮的直接成果。”[7]陽明心學盛行于嘉靖年間,而梁辰魚的《浣紗記》正是創作于此時期。
宋人強調程朱理學,重禮教,于是在北宋地理志《太平寰宇記》中,將魅惑吳王而失去貞潔的西施沉入太湖。梁辰魚的《浣紗記》中通過范蠡、西施的愛情對于男女愛情婚姻、貞節道德提出新見解。范蠡與失身的西施喜結連理,是對范蠡與西施超脫世俗觀念愛情的充分肯定,更是對窠臼貞節觀念的突破,體現了在古老歷史題材里熔鑄新內容、新思想的覺悟,這樣的結局展示了梁辰魚創新的思想理念,并且符合大眾的審美情感期待。文人的藝術創作在陽明心學的指引下開闊了視野,引發了嶄新的道德評判標準的思考。此外,在《被擒》一出中,越軍入吳,吳太子血戰被擒,痛心疾首,悲嘆吳國淪喪。越國將軍正準備火燒姑蘇臺,這時西施立于城樓中,在戰火紛飛的映射下她不再是集嬌寵于一身的妃子,而更像是一尊守護一方和平的神靈,她喊道:
“越國眾兵聽著,我就是越國西施,近作吳國夫人。傳示范文二位大夫,吳國大王又不在此,不得驚嚇我,你暫且收兵回去。”[8]
如此巾幗不讓須眉、大氣凜然的將士形象躍然眼前,加強了女性在歷史車輪中的使命感,女性角色獲得了與男性角色平等的地位。王陽明時就已經從人性良知上肯定人的平等性,陽明心學主張人的主體性和時代的個性解放,同時喚醒女性自覺的獨立人格意識。劇中,苧羅山下、若耶溪畔,范蠡游春,巧遇西施一見鐘情便留一縷溪紗私定終生,此情此景雖為古典戲曲中男女鐘情的固有模式,但范蠡以越國上大夫身份鐘情于農家浣紗女西施,其情超脫社會地位而表現為真誠的人性。這種人性的自然情感不再受等級觀念的束縛,與全劇結尾處范蠡、西施雙雙泛湖歸隱在思想上達成高度的一致性。
四、結語
明傳奇的成就使中國文學史又出現了一個高峰,不論是其文學性、音樂性還是審美表達都自成一體。梁辰魚的《浣紗記》則是昆劇最早的完整顯示,無論是創作者本身的現實體現,還是哲學支撐下的美學價值體現,在最后一出《泛湖》中都可以得到答案,這既是現實的必然走向,也是藝術的理想歸宿,是情景交融、情理結合的完美典范,也是對昆劇藝術的有效傳播,極富文學藝術魅力的《浣紗記》對于后世的一切影響都值得深究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