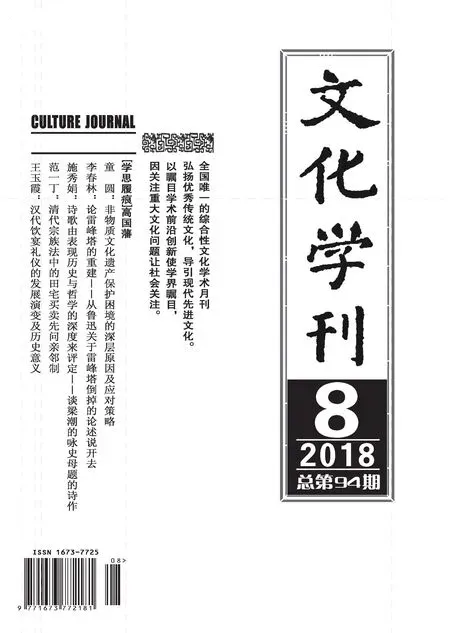論《山月記》的敘述者
曹 愫
(陽(yáng)光學(xué)院外語(yǔ)系,福建 福州 350011)
一、《山月記》敘述者兩種觀點(diǎn)
《山月記》小說(shuō)全文基本是由主人公的自白和嵌入話外敘述中的袁慘這一角色的心理描寫(xiě)所構(gòu)成的。無(wú)需贅言,主人公自白的部分是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如前所述,對(duì)于《山月記》敘述者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觀點(diǎn),這兩種觀點(diǎn)的差異便緣于對(duì)袁慘心理描寫(xiě)部分中的敘述者的獨(dú)立性程度之理解有所不同。
田中實(shí)氏認(rèn)為,袁慘并沒(méi)有與主人公進(jìn)行行為上的直接對(duì)話,因此,袁慘心理描寫(xiě)部分的敘述者也被主人公強(qiáng)烈的第一人稱告白所吸收。此外,他還指出,對(duì)于主人公詩(shī)作“何処か(非常に微妙な點(diǎn)において)欠ける所がある”這種評(píng)價(jià)也僅僅作為一種沒(méi)有外部化的心理被描寫(xiě),并沒(méi)有真正生成現(xiàn)實(shí)批評(píng)。在分析了“付加へて言ふことに”等一類話外敘述也只是主人公自白的延長(zhǎng)線上之物、與主人公第一人稱的自白明顯呈一體化之后,田中實(shí)氏進(jìn)行了總結(jié):“《山月記》的敘述者并不具有凌駕于所有人物角色的超越性視角,非但如此,還反被李征這一強(qiáng)烈的人物形象所吞并了。也即是,在《山月記》中,敘述者已被作品主人公這一人物形象所同化。”[1]
與田中實(shí)氏的理解形成對(duì)照的是松本修氏的分析。松本修氏分析認(rèn)為,《山月記》的敘述者在除主人公自白之外的篇幅中都出發(fā)于袁慘這一人物形象所在的立場(chǎng),能夠窺視主人公抑或袁慘一行人的心理,正如“(非常に微妙な點(diǎn)において)”和“(袁傪は昔の青年李徴の自嘲癖を思い出しながら、哀しく聞いていた)”中,“()”這一補(bǔ)充說(shuō)明性符號(hào)的運(yùn)用就充分顯示出了小說(shuō)敘述者的獨(dú)立性。[2]
關(guān)于《山月記》的敘述者,以上列舉了兩種形成對(duì)照且具代表性的理解。毫無(wú)疑問(wèn),對(duì)于《山月記》敘述者的論述除以上二者之外還有很多,但也基本都可以納入以上兩種觀點(diǎn)之一,所以在此不再贅述。
本文的立足點(diǎn)是《山月記》的敘述者是獨(dú)立的存在這一觀點(diǎn)。以下將著眼于小說(shuō)中重復(fù)出現(xiàn)的“聲音”這一表述,具體分析此表述背后所隱藏的敘述者這一獨(dú)立存在。
二、以“聲音”指代主人公之?dāng)⑹稣?/h2>
在《山月記》開(kāi)篇第一段中,小說(shuō)以極具張力的漢文調(diào)表述介紹了主人公李征虎變之前的整個(gè)人生。在描述虎變之前的主人公時(shí),敘述者不僅了解他的經(jīng)歷,還能洞察他的內(nèi)心。毫無(wú)疑問(wèn),這時(shí)的敘述者是全知全能型的第三人稱視角。
小說(shuō)從第二段到結(jié)束,依托于話外敘述的袁慘心理描寫(xiě)部分與主人公的第一人稱自白基本按照段落劃分間隔出現(xiàn)。特別是在小說(shuō)的后半部分,主人公的第一人稱自白以長(zhǎng)段落占據(jù)了絕大部分篇幅。在這一部分中,敘述者隱藏起來(lái),似乎徹底演變成了主人公本人,成功營(yíng)造出強(qiáng)烈的代入感,讓讀者感主人公所感,甚至產(chǎn)生自己就是主人公本人的錯(cuò)覺(jué)。換言之,敘述者正是通過(guò)這樣的第一人稱視角,使讀者忘記其存在,把讀者封印在第一人稱直白而強(qiáng)烈的感情中。也正因如此,田中實(shí)氏認(rèn)為小說(shuō)敘述者已被主人公第一人稱視角所吸收。但是,從小說(shuō)中對(duì)人物形象袁慘的心理描寫(xiě)部分來(lái)看,很難斷定小說(shuō)敘述者缺乏獨(dú)立性。
“叢の中からは、しばらく返辭が無(wú)かった。しのび泣きかと思われる微かな聲が時(shí)々洩れるばかりである。ややあって、低い聲が答えた。
(中略)
李徴の聲が答えて言う。
(中略)
草中の聲が次のように語(yǔ)った。”[3]
以上的引用部分是內(nèi)嵌有袁慘心理描寫(xiě)的話外敘述部分,“(中略)”的部分是主人公的第一人稱自白。不難發(fā)現(xiàn),諸如“微かな聲”“低い聲”等“……聲音”的表述都充當(dāng)所在句子的主語(yǔ)。如前所述,小說(shuō)從第二段開(kāi)始,話外敘述和主人公自白在小說(shuō)中交替出現(xiàn)。因此,穿插于主人公自白之間的這些話外敘述的作用之一就是為讀者提示出“主人公即將繼續(xù)自白”這一信息。而縱觀小說(shuō),此類提示的句子主語(yǔ)全部為“……聲音”,無(wú)一例外。毫無(wú)疑問(wèn),“微かな聲”“低い聲”等都是主人公的聲音,從小說(shuō)情節(jié)上看所指代的也都是主人公李征。所以,即便把“……聲音”這類表述全部置換成主人公名字“李征”,也不會(huì)產(chǎn)生任何意思上的誤解或歧義,對(duì)小說(shuō)情節(jié)的發(fā)展也同樣不會(huì)有任何影響。既然如此,便不得不去推斷,用“……聲音”指代虎變后的主人公的意義何在。
不妨假設(shè),當(dāng)這些句子的主語(yǔ)為主人公人名“李征”,那就表示敘述者對(duì)于情節(jié)的發(fā)展是“知道”的。但小說(shuō)中類似句子的主語(yǔ)全部為“……聲音”,這就說(shuō)明,對(duì)于敘述者“知不知道”這個(gè)問(wèn)題可以暫且不討論,但可以肯定敘述者確切地“聽(tīng)到”了。而正是這樣的“聽(tīng)到”,恰恰說(shuō)明了敘述者獨(dú)立地存在于主人公之外的某個(gè)立場(chǎng),這個(gè)立場(chǎng)與人物袁慘及其隨從類似,能夠聽(tīng)到主人公的聲音。嚴(yán)格來(lái)說(shuō),這樣的敘述者雖然也同樣是第三人稱視角,但是“聽(tīng)到”就表示是通過(guò)具體的感官感知到,這既讓讀者獲得了信息本身,同時(shí)又加強(qiáng)了臨場(chǎng)感,使讀者似乎身臨其境,成為小說(shuō)情節(jié)發(fā)展的見(jiàn)證者。帶來(lái)這樣的閱讀體驗(yàn),是因?yàn)閿⑹稣叽藭r(shí)通過(guò)“……聲音”這一表述與讀者共享了感官,甚至讓讀者演變成了敘述者,強(qiáng)化了讀者對(duì)小說(shuō)情節(jié)的感官體驗(yàn)強(qiáng)度。換言之,將虎變后的主人公用“……聲音”而非姓名來(lái)指代,這說(shuō)明了敘述者視角與主人公自白的第一人稱視角的區(qū)別,強(qiáng)調(diào)了其外在于主人公視角的獨(dú)立性。
如前所述,話外敘述中也包含了人物形象袁慘的心理描寫(xiě)。所以,關(guān)于“微かな聲”“低い聲”等表述,也存在將其僅僅看作為袁慘本人心理描寫(xiě)的讀解方法。但是,人物袁慘在聽(tīng)到主人公李征的喃喃自語(yǔ)“危ないところだった”,突然發(fā)現(xiàn)這聲音是自己的舊友時(shí),旋即問(wèn)道:“その聲は、我が友、李徴子ではないか?”這是小說(shuō)通篇唯一一處袁慘發(fā)出聲音直接與主人公進(jìn)行的對(duì)話。這唯一一處急切的甚至來(lái)不及進(jìn)行第三人稱轉(zhuǎn)述的直接引語(yǔ)與小說(shuō)其他話外敘述部分形成強(qiáng)烈對(duì)比,同時(shí),從小說(shuō)情節(jié)發(fā)展上說(shuō),也由此可以看出,此時(shí)的袁慘已經(jīng)認(rèn)出這個(gè)聲音就是自己的好友李征,且已經(jīng)無(wú)暇顧及也無(wú)所謂聲音的發(fā)出者是人、是虎,抑或是其他任何事物。那么,袁慘即使是在心中暗自稱呼自己的好友,較于用“……聲音”進(jìn)行指代,直接稱呼好友名字“李征”,無(wú)論從袁慘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還是從小說(shuō)情節(jié)發(fā)展來(lái)看都更加自然、流暢,完全沒(méi)有必要特意稱主人公為“……聲音”。所以,將虎變之后的主人公用“……聲音”進(jìn)行指代是特意為之,且是小說(shuō)敘述者之作為,而非袁慘所為。同時(shí),這也反過(guò)來(lái)證明了小說(shuō)敘述者獨(dú)立于主人公或人物形象袁慘而存在。
三、以“()”現(xiàn)身的敘述者
小說(shuō)中,主人公李征是“峻峭的李征”、是“淺ましい身となり果てた”的李征,而袁慘是“溫和的袁慘”、“監(jiān)察御史”袁慘。袁慘是與主人公李征呈現(xiàn)對(duì)照關(guān)系的人物形象設(shè)定。對(duì)于舊友李征想以詩(shī)人的身份借以留名千古的詩(shī)作,袁慘認(rèn)為“何処か(非常に微妙な點(diǎn)において)欠ける所がある”。無(wú)論這一“哪兒”具體是什么,甚至無(wú)論這種評(píng)價(jià)是否構(gòu)成批評(píng),在這一表達(dá)評(píng)價(jià)的句子中,值得關(guān)注的是“()”的使用。毋庸置疑,此表達(dá)中的“()”的作用是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解釋或說(shuō)明,即注釋。那么,是誰(shuí)在用“()”進(jìn)行注釋,進(jìn)行注釋的用意何在,這兩個(gè)問(wèn)題急需解決。
從小說(shuō)情節(jié)來(lái)看,袁慘對(duì)好友詩(shī)作的評(píng)價(jià)并未外釋成為話語(yǔ),僅僅停留在感想這一層面。不妨假設(shè)“非常に微妙な點(diǎn)において”這一注釋是袁慘自己進(jìn)行的,那么“()”的使用毫無(wú)意義。因?yàn)槿サ簟?)”不會(huì)對(duì)這一表達(dá)造成任何影響,閱讀體驗(yàn)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會(huì)變得更加順暢。畢竟,作中人物沒(méi)有必要在同一個(gè)句子中以“()”的形式為自身的想法進(jìn)行進(jìn)一步解釋和說(shuō)明,甚至小說(shuō)這一敘述文本本身也不同于科學(xué)性敘述,完全不必加入注釋。所以,此處的“(非常に微妙な點(diǎn)において)”這一注釋只能是敘述者對(duì)敘述的一種指點(diǎn)干預(yù)。[4]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敘述者的干預(yù)中,不僅包含了對(duì)敘述形式的指點(diǎn)干預(yù),也包含了對(duì)敘述內(nèi)容的評(píng)價(jià)干預(yù)。
“(非常に微妙な點(diǎn)において)”這一注釋從內(nèi)容上來(lái)說(shuō),解釋了小說(shuō)主人公李征的詩(shī)作的不足之處存在于很微妙的點(diǎn)上。這一評(píng)論干預(yù)首先使讀者獲得了他們可能并不清楚的情況,即主人公詩(shī)作在微妙之點(diǎn)有缺憾,同時(shí)也讓敘述者與袁慘這一人物視角“何処か”產(chǎn)生了呼應(yīng),甚至還促使讀者將主人公詩(shī)作的缺憾與其虎變聯(lián)系起來(lái),使讀者更容易接受主人公虎變這一不合常理的現(xiàn)象,達(dá)到了整合敘述主體的作用。正是此評(píng)論干預(yù)所體現(xiàn)的與袁慘這一人物、與受述者的強(qiáng)烈呼應(yīng)和整合關(guān)系使得敘述者的析出工作更加困難。
所以,“()”的使用從形式上說(shuō)是敘述者的指點(diǎn)干預(yù),從內(nèi)容上說(shuō)是對(duì)袁慘評(píng)價(jià)的補(bǔ)充和解釋,是來(lái)自于敘述者對(duì)敘述內(nèi)容的評(píng)價(jià)干預(yù)。反過(guò)來(lái),這種對(duì)敘述的雙重干預(yù)也就恰恰體現(xiàn)出了《山月記》敘述者并未被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敘述所吸收,而是具有獨(dú)立性的。
四、結(jié)語(yǔ)
就小說(shuō)情節(jié)來(lái)看,主人公李征從鄉(xiāng)鄰眼中“博學(xué)才穎”的“儁才”變成了殘暴的人人懼怕的“食人虎”;從敘述語(yǔ)言來(lái)看,虎變之前用姓名“李征”指代主人公,虎變之后用“……聲音”指代主人公。小說(shuō)情節(jié)與敘述語(yǔ)言形成了呼應(yīng)關(guān)系。在此基礎(chǔ)之上,敘述者又利用“()”進(jìn)一步在作中人物的觀點(diǎn)中強(qiáng)行插入了自己的干預(yù)。作為第三人稱小說(shuō)的《山月記》,敘述者非但沒(méi)有徹底隱身,甚至在全視角與小說(shuō)的各個(gè)人物視角之間自由地切換,使小說(shuō)獲得了時(shí)間和空間上的立體感,其獨(dú)立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