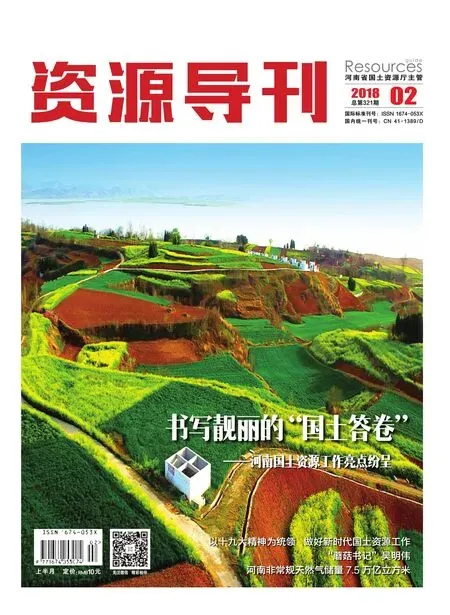雪 趣
文l張延偉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冬天里大雪封門的事經常發生,老天爺哪像現在這么吝嗇,只是“點眼藥”般丟下一點兒雪花,人們便都興奮地歡呼雀躍起來了。
小時候,我跟奶奶住在臨著土崖挖建的窯洞里。土崖坐東朝西,有四五丈高,夜里下雪,風夾著雪花打著旋兒從崖頂上撲下來,由下往上呈斜坡狀累積堆聚、瓷瓷實實。記得有年臘月二十三,母親早起做飯,推門看到外面的場景,嚇得趕緊喊父親,原來崖邊的積雪挨著距窯洞一丈多遠的南屋山墻堆得老高,把窯洞門全封住了!奶奶和我在里頭也只能干著急,好在窯洞高大寬敞,再加上積雪也有一定透氣性,才不至于窒息。由于積雪實在太多,從底下一時也清理不出頭緒,父親確定了洞門的大致位置,踩著梯子從最上面挖起,先把洞門上的天窗部分清理出來,頓時一股沁人心脾的涼氣撲進窯洞,舒服極了。
下雪天閑來無事,我就跟父親一起帶著家里那只叫作“阿黃”的狗去野地里逮野兔。曠野里白茫茫的,麥苗都被積雪覆蓋著,逼得那些原本在夜間出來覓食的野兔冒險出來活動,地堰邊留下它們跳躍的痕跡。父親循著這些蹄印一路搜尋,阿黃也靠鼻子嗅著朝四處張望,它往往先于我們發現雪地里那一抹灰黃,便箭一般地沖上去。等那野兔察覺危險時已經晚了,地里積雪太厚,它每跳躍一下都費力氣,最終被阿黃叼到我們跟前。
逢著下雪天,我還常按課本里魯迅先生教的,在院子當中掃出一小片雪地來,用拴著繩子的短棍兒支起一只竹編的籮筐,籮筐下撒一些小麥或高粱,人坐在屋子里遠遠盯著。不知是那些鳥雀太過聰明還是我手腳太過笨拙,它們探頭探腦地啄到一粒糧食就迅速地跳出圈外,根本不給我留機會。有次院里落下一只鴿子,它或許是餓極了,先是試探性地把頭伸進籮筐底下啄食,反復幾次后覺得沒什么兇險,就放心大膽地走進籮筐底下,我猛地一拉繩子,便聽見籮筐底下撲棱翅膀的掙扎聲了。

這只鴿子渾身雪白,“咕咕”叫著,一副可憐又可愛的樣子,誰還忍心吃它。我讓母親用剪刀剪去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用心養了起來,其間怕它飛走,新長出的羽毛又被剪掉一次。兩個月時間過去,這只鴿子慢慢和我們熟悉起來,等它再次能飛起來的時候,就直接棲息在屋檐下父親用碎木板為它做的那個鴿子籠里了,后來居然又從外面帶回一只伙伴兒繁衍起后代來,父親就又在土崖上挖出許多大小不一的洞穴供鴿子們棲息。傍晚時分,炊煙裊裊,窯洞上方的土壁落滿白色、灰色的鴿子,成為一道別樣的風景。
逢著下雪天,平時常玩的游戲派不上用場,我們就在雪地里“做文章”。于是學校的小操場成了“戰場”,擲雪球、打雪仗、滾雪球成了我們的最愛;還有的一人蹲著,另外兩人各自扯著他一只胳膊“拉雪橇”,跑著跑著一不小心撒開手,蹲著的人不是摔個“仰八叉”就是“嘴啃地”,爬起來拍拍身上的雪,相互換下角色繼續玩……玩累了,便以班級為單位各自占據操場一角堆“雪人”,破草帽,碎布條、黑炭渣、高粱笤帚等全都派上了用場,當一個個形態各異、惟妙惟肖的“雪人”笑容可掬地站立在耀眼的陽光下時,大家這才記起把凍得通紅的小手放在嘴邊哈上兩口熱氣。
孩子們更喜歡新年里下雪。家里大人早早地從集市上買來鞭炮,一部分收藏起來大年初一燃放,一部分則留給孩子。我們小心翼翼地把整掛鞭拆散成一個個小炮,裝一把在口袋里,再拿一根點燃的麻稈就高高興興地出門了。小伙伴們聚在一起,紛紛從口袋里掏出鞭炮,在麻稈火上點燃,飛快地扔進雪堆里,隨著“嘭嘭嘭”的聲音接二連三地響起,小伙伴們會賭斗,看誰的炮炸開的雪坑最大、濺起的雪花最多。有膽大的孩子還把從家里偷拿出來的“大雷子”或“二腳踢”埋在雪堆里,露出引線,遠遠地把手中的麻稈火湊上去點著,隨著“嗵”的一聲巨響,雪花飛濺,孩子們高興得跳起老高。
我們還常跟在人群后面看他們拿雪“訛女婿”。新女婿一般大年初二走親戚,抬“食盒”,過大禮,村里輩分低的大人小孩分班兒在村口守著,一“抓”一個準兒。新女婿當中有機靈的,早早地就把煙卷兒拿出來了;而那些生性木訥、提前沒有準備東西的,被人摁著胳膊,另外有人先把“雪球”填他脖子或褲檔里先“暖暖”再說,末了還得掏錢打發人到村頭的“代銷店”買來香煙或糖塊分了了事。也有僥幸逃脫的新女婿,順著河道在前面跑,大伙兒像捉賊似地在后面喊著攆,最后將其捉住,摁在雪地里好一頓收拾。來年再走親戚時,他們早早地就把整條香煙準備好了。
現在下大雪的機會越來越少,捉野兔、網鳥雀、打雪仗、堆雪人成為一種奢望。隨著農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各類文體活動豐富多彩,雪地里“訛女婿”等陋習也不復存在了。只是一想起小時候雪地里發生的這些趣事,仍令人忍俊不禁、留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