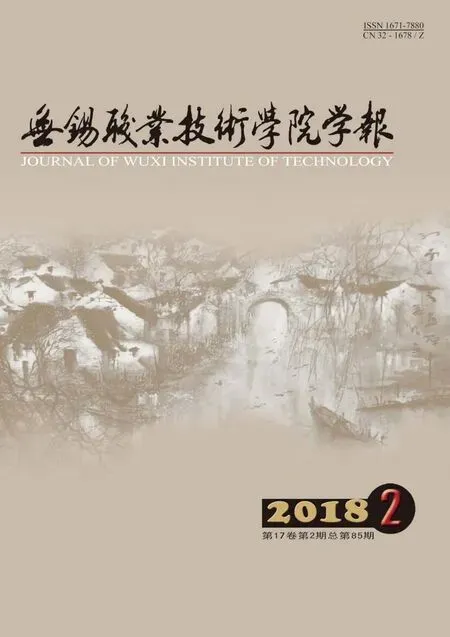余秀華詩歌中想象空間的建構
黃懷鳳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余秀華迄今出版了三本詩集,她在她的詩歌中建構了自己的想象空間,鄒建軍等人認為“文學與地理的關系與生俱來,地理是文學的土壤,是文學的生命依托”[1]114。顏紅菲認為“在文學地理學意義上所謂文學作品里的想象空間,是指文學作品中所存在的事物往往是作家審美認識與藝術想象的產物,并且多半是世界上不存在的東西,從性質上來說是作家自己的藝術創(chuàng)造”[2]39。
余秀華建構的地理空間中有一些是現(xiàn)實世界不存在的東西,這些她自己創(chuàng)造的地理空間同樣也能反映出她內心深處的一些想法,對她詩歌中的想象空間進行探究對我們更深入了解她的詩歌有很大的幫助。
1 人文想象空間
在余秀華天馬行空的想象空間中,人文想象空間占據(jù)半壁江山。詩人喜歡把自己隱匿于自己的房間里,以獲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感。在想象空間的建構中,這一點被發(fā)揮到了極致,不僅要把自己藏于屋中,更說:“你說如果不是把心放在保險柜里,你如今都缺了一部分。”[3]10余秀華構建了一個保險柜去存放自己的心,這反映的是她對自己交付癡心的不確定以及對愛的膽怯。詩人會“坐在房門口,看云,看書/看他的后腦勺”,“看到堂吉訶德進入荒山/寫下信件,讓橋桑帶走,帶給杜爾西內亞/然后他脫光衣服/撞擊一塊大石頭”[3]14。每每讀到這里,我們或許會吃驚,或許也不會吃驚,吃驚于只念到初中的余秀華文學素養(yǎng)很高,若不是仔細讀過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是寫不出這樣的詩句的;不吃驚在于,如果余秀華沒有飽讀詩書,她就成不了現(xiàn)在的詩人余秀華,而永遠只能是橫店村里的一名腦癱村婦。在想象空間中也要有一個院子,在《碎瓷》一詩中,詩人就構建了“曾經一個有柿子樹的庭院”[4]181。房前有院子,房后還需要一個園子,余秀華希望“找一個性感的男人共度余生”,在她的想象空間里,“清晨,他是要去屋后的園子走走的……他去菜園里摘兩個西紅柿”[4]209。這一切,放在別人那里或許就是現(xiàn)實空間的建構了,但是在余秀華這里,這樣的空間就只能是想象空間中才能有的事物。
走出院子,余秀華的想象空間里有許多巷子。其中有一條狹窄的巷子:“只有一種風吹著我。從這條狹窄的巷子/從沒有了花序的槐樹,枯萎的美人蕉/從青苔愈厚的石板路,一只不再熱衷于捕鼠的貓/從落不到地面的陽光/只有一種風吹著我……人間慢慢退到巷子的那頭,門關半扇。”[4]115在這里,余秀華構建了一系列消極的事物,反映了她當時消極的心態(tài)。她順便給鳥雀們也構建了一條巷子得以棲身:“而夜晚,他必然會在民國的一個巷子里,沽滿酒/循著未眠的鳥鳴找一塊濕潤的地方安身。”[5]14時間是民國,地點是在巷子里,主角是鳥雀,它們喝酒,而且夜晚降臨也不停歇地喝酒,還要找到同伴一起喝酒。還有一條巷子是有名字的巷子,巷子的名稱叫“情人巷54號”,在《一張廢紙》一詩中,“她”不關心一切,只要不妨礙她找到情人巷54號就可以了,但其實她最終并沒有找到這條巷子,這樣的情人巷只能存在于想象空間當中,而卻還是“54”號,諧音來看愛情與死似乎是緊密相連的。
余秀華在她的詩歌想象空間里還構建了“礦場”,礦場的寂寥與零詩意,使得這一空間展現(xiàn)的是一種被遺忘與落寞的心境。在《夢見雪》中,詩人寫道:“一個廢棄的礦場掩埋得更深,深入遺忘的暗河/一具荒草間的馬骨被揚起來/天空是深不見底的窟窿。”[3]96這無限的深與無限的高的地與天之間是寂寞孤獨的詩人,在這樣的礦場里,詩人就像那草間的馬骨一樣被風揚起來,卻只能面對深埋的礦場和深不見底的天,渺小與孤獨在這天與地的對比下更加強烈。在《下午》一詩中,詩人便直接以“我”來描寫:“我被埋得越來越深/如一座礦場回到地深處,黃金的憂傷斂起來/時光的旋轉中,捂緊內心的火焰。”[3]97
除了讓人壓抑的礦場,還有另一個讓人更壓抑的空間——墳墓。她自己說過,“我愛過白露,白露下寂靜的墓園”[5]71“我唯一能做到的/是把一個名字帶進墓園”[5]108。余秀華在《子夜的村莊》中描寫了一個留守婦女因為沒有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孩子溺水死亡的事件:“女人在孩子的墳墓前沉默,整夜流不出一滴淚/村莊荒蕪了多少地,男人不知道/女人的心怎么涼的/男人更不知道。”[3]30這很明顯是詩人想象的一個事件,卻真實地反映了余秀華內心的想法,余秀華的詩歌中常常會有一個長期在外打工且尋花問柳的丈夫,這也是她對于自己丈夫的認識,余秀華很明顯在借助女人在孩子墳墓前悲痛得流干了眼淚的這一場景,目的是譴責那些長期在外,不管家里糟糠之妻生死的男人們。余秀華稱“他們與我隔土相望。站在時間前列的人/先替我沉眠,替我把半截人世含進土里/所以我磕磕絆絆,在這墓園外剃去肉,流去血”[3]86。這就是余秀華,消極起來覺得自己本該是躺在墓地里的那個人,活在世界上也是醒著地死去。她在《寫給海子》中說,“我會從墳墓里捧出土,掩埋詩句里的水/胸口上的火”,[4]203其實我們都知道土可以滅火可以擋水,但是如果這土是從墳墓里捧出來的,水是詩句里的水,火是胸口上的火,那意義就完全不同了。墳墓就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力量,如果用在詩歌當中,就會產生陌生化的效果,帶來意想不到的詩意效果,因此,在詩歌中構建出墳墓這一想象空間,那么詩歌中的地理空間就會產生一種間離效果,讓人對詩人的用意一目了然。
與墳墓相關,與死亡相關,《繭》一詩中還構建了“黃泉路”意象空間,“埋你,也埋你手上的繭/這繭你要留著,黃泉路又長又冷,你可以撥弄來玩/如果你想回頭,我也好認得”[3]26。余秀華對父母的愛與愧疚是充斥在她的詩歌中的,她特殊的身體原因,給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帶來的壓力,這體現(xiàn)在她詩歌的許多地方。這首《繭》就表現(xiàn)了詩人對父親的不舍與愧疚,她甚至說:“不會再見了,爸爸,再見/一路,你不要留下任何標志/不要讓今生一路跟來。”[3]26她愛自己的父親,舍不得自己的爸爸,可是為了自己來世不再拖累自己的爸爸,寧愿來世不要相見。
家庭中,余秀華愛自己的父母,愛自己的兒子,唯獨對自己的丈夫不滿。不管是她的丈夫,還是她心儀的男人,似乎都遠在他鄉(xiāng),在那些燈紅酒綠之下常常將她忘記,“他還在那個燈火不熄的城市愛不同的人/受同樣的溫暖和傷害……我還是每天打掃院子,想想他在人間/我打掃得很仔細”[3]136。這首詩是寫自己心儀的人的,只要他活著,和自己在同一片天空下,她就已經覺得很幸福了。她對一個叫“阿樂”的人說:“阿樂,我們都在犯罪/我在村莊里被植物照耀/你在城市里被霓虹驅趕。”[5]86經歷同樣的事情,接受同樣的風,流淌同一條河流,“吹過我村莊的風吹過你的城市/流過我村莊的河流流過你的城市”[5]8。余秀華在想象空間里構建的“你的城市”仿佛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到了你的城市,也不過短暫停留/而我堅持認為我坐的每一趟火車/都是在通向你的路上”[4]107。
與火車相比,余秀華的詩歌中構建的交通工具以馬車和飛機為想象空間的事物。余秀華的詩歌中出現(xiàn)的交通工具以火車最多,極少出現(xiàn)飛機,她的三本詩集中出現(xiàn)飛機的詩是在第三本詩集《我們愛過又忘記》之中,且乘坐的人還不是余秀華本人,這首詩就叫《你坐的飛機經過我村莊的天空》。飛機比火車高級,因為機票通常比火車票昂貴,速度也比火車快。余秀華安排飛機的出現(xiàn),但并不安排自己坐上了飛機,這樣的對比表現(xiàn)出的是她一貫的“稗子式”的卑微。馬車竟然在余秀華的詩歌里也比火車顯得高級,“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到這里的,一場雨水還掛在/馬車上。如果是坐火車/卻看不到經過隧道時他臉上的夜色”[4]230。在余秀華心中,雖然火車是通向自由與理想的途徑,但過程并不輕松。
余秀華在現(xiàn)實生活中愛情道路很曲折,在她的想象空間里她構建了兩個見自己心儀的人的地方——茶館和旅館。這兩個地方擁有共同的特點:魚龍混雜。這是公共場合,許多人來來去去。在《給你》一詩中,詩人寫道:“一家樸素的茶館,面前目光樸素的你皆為我喜歡/你的胡子,昨夜輾轉的面色讓我憂傷/我想帶給你的,一路已經丟失得差不多/除了窗外凋謝的春色。”[5]9在《在一個小旅館的黃昏里》,最后一節(jié)是:“后來,星子一顆顆探出來/我想起曾經在詩句里寫過的一個旅館,旅館里的一個男子/便拉上了窗簾。”[5]76詩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感情不順,在詩中也是渴望愛而不得。前一首詩中,想要給“他”帶點什么,卻在來時的路上丟失得差不多了,只有一個春色,還是凋零的春色;后一首詩描寫得更是決絕,一寫到那個男子,那個男子就拉上了窗簾。余秀華想象空間構建過程中對愛的追求深受現(xiàn)實生活的影響,以至于最后形成她典型的“稗子式”的愛。
2 自然想象空間
在余秀華的詩歌世界里,她總是在強調自己和大自然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她說:“我是背著雨水上山的人,過去是,未來也是/我是懷里息著烏云的人,過去是,現(xiàn)在也是//你看我時,我是一堆土/你看我時,風把落葉散,我是一堆潮濕的土。”[3]214在她的自然想象空間中,余秀華構建了許多事物,每一個其實都是她內心的反映。
她在她的詩歌里構建了一艘船,似乎有靈魂的船,這條船不甘于自己的破敗,“只有它承認它還是一條船/在荒蕪的岸/有著前世的木性,今生的水性”[4]46。更多的時候余秀華構建的事物是在田野里,這和現(xiàn)實空間建構一樣,是余秀華地理空間建構中重要的一個地方。歸根結底余秀華在農村呆了四十年,這里的田野,這里的山水是她最熟悉的地方,哪怕是在想象的世界里,這些地方也是重要的想象地。例如,余秀華想象在田野上和一個相愛的人共同散步:“其實我想說的是,黃昏里,我們一起去微風里的田野/看蒲公英才黃起來的樣子/和那些草,用云朵搽過身體的樣子。”[3]32田野似乎常常是幸福的,“風從田野里捎來清晨,捎來蘋果的味道”[5]65。
地與天分不開,在田野里摔了一跤,割的草散了一地,這時詩人構建的是一個“云白得浩浩蕩蕩/散落一地的草綠得浩浩蕩蕩”[3]8的天與地,在余秀華的想象空間中,大自然是在一片開闊的天與地之間構建起來的。由于余秀華行動不便,她常常在做農活的時候摔倒,除了割草摔倒,背棉花也摔倒過,而兩次摔倒都建構了她想象空間中的天與地:“背一袋棉花往回走的時候,她摔了一跤/她爬起來/天上沒有一朵云/地上倒有很多。”[3]206她不光構建了天與地,也構建了海與天:“那么多的水匯集起來,仿佛永世不會枯竭/只有倒過來的天空,沒有倒過去的海。”[4]118就算現(xiàn)實中的橫店村深處內陸,離海很遠,但是她會在想象的空間里構建一個能夠聽見海洋聲音的橫店村:“一次意外,在荒村里聽到海。”[4]149之所以喜歡海,大概是因為水面下的世界和陸地上的世界不一樣,“有時候我躺在水面之下,聽不到任何聲音/有時候深夜打開/我的身體全是聲音,而雨沒有到來”[4]18。水、雨、海,在余秀華的詩歌里不僅是自然界的事物,更是她內心最真實想法的載體。
江漢平原上除了水,還有廣闊的平原,余秀華不僅在現(xiàn)實空間構造了平原,在想象空間也構建了一個江漢平原,心情不好的時候把它稱作荒原,“當我從屋后經過一個樹林,陷入遼闊的荒原”[5]45“大地寬容一個人的時候,那力量讓人懼怕/這荒原八百里,也許更大”[5]79。這樣的荒原遼闊而寂寞,就像《呼嘯山莊》里讓人悲傷的荒原一樣。甚至,她說:“江漢平原薄如一層裹尸布。”[4]179余秀華對江漢平原的情感十分復雜,她偶爾說:“江漢平原上/陽光把傷口照出果實的模樣。”[4]173偶爾又說:“我在江漢平原上尋找能做裙子的樹葉/把越來越不敢張揚的年輕裝進瓷翁。”[4]149平原很平凡,偶爾平淡無奇:“風從南而來。這里的小平原,即將升騰的熱空氣/忍冬花將再一次落上小小的灰麻雀/信件在路上,馬在河邊啃草。”[3]44她在《平原上》這樣寫江漢平原:“不是一棵樹沒有。不是一棟房子沒有/如果一列火車經過,許多房子就跑了出來/許多能活動的部分,螞蟻,豬,誤入歧途的烏鴉/人家稠密的地方是人間。人家洗漱的地方也是人間/在這個倒春寒里,雨落在平原上,那些彎曲的炊煙,一忽兒就飄散。”[3]116
對更遙遠的地方建構,余秀華這樣寫著,“一說到遠方,就有遼闊之心: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水城”[3]148“從湘西到北京,到西藏,到沙漠,你在路上/你熱愛的地方是我的祖國/你正在的地方是我的故鄉(xiāng)”[4]67。余秀華的詩歌中有一種單戀者的味道,她的詩歌也就成了一種單戀書寫,她對遠方世界的構建多摻雜了單戀的因素。在余秀華的想象空間中,構建得最遠的就是對宇宙的構建,既然是現(xiàn)象,就可以到達現(xiàn)實里到達不了的地方:“唯有這一種渺小能把我摧毀,唯有這樣的疼/不能叫喊/抱膝于午夜,聽窗外的凋零之聲:不僅僅是薔薇的/還有夜本身,還有整個銀河系/一個宇宙。”[3]68
總的來說,余秀華的想象空間所構建的空間比較大,其中的事物也比較龐雜,許多事物都被構建在想象的空間里。余秀華在自己的想象空間里構建了比實際生活空間更廣闊的空間,在這些現(xiàn)實空間中沒有的空間上,我們看見了余秀華想要突破現(xiàn)實對自己的圍困,看見了她對愛情的渴求,對外界、對自由與理想的向往。
參考文獻:
[1] 鄒建軍,周亞芬.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35-43.
[2] 顏紅菲. 開辟文學理論研究的新空間: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述評[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4,67(6):112-117.
[3] 余秀華.月光落在左手上[M].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14:10,14,96,97,30,86,26,136,214,46,32,8,206,18,44,116,148,68.
[4] 余秀華.我們愛過又忘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181,209,115,203,107,230,149,179,173,67.
[5] 余秀華.搖搖晃晃的人間[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14,71,108,86,8,9,76,4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