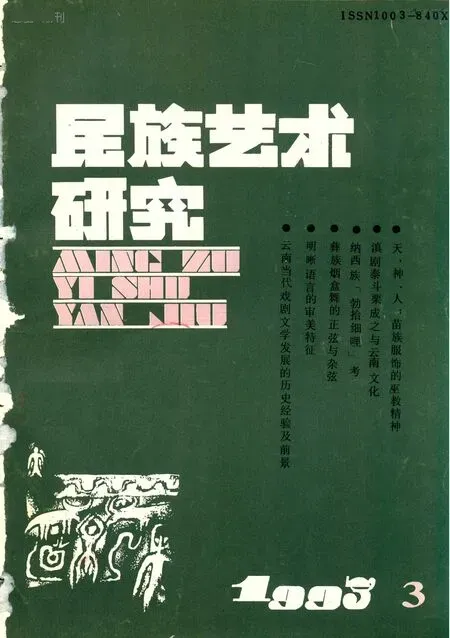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民族紀錄片”的歷史演進、“國家傳統”與美學創新
森茂芳
英國學者休·希頓——沃森在其著作《民族與國家》中說:“民族,民族國家”已成為如今“撼動我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力量。”*[英]休·希頓·沃森:《民族與國家——對民族起源與民族主義政治的探討》,吳洪英、黃群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1頁。著名的挪威人類學學者弗雷德里克· 邁特更不無感慨地說:人類學、民族學及人類學民族學影視創作,是當今世界“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事業。*[挪威]弗雷德里克·邁特:《人類學的四大傳統——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的人類學,前言》,高丙中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3頁。這是就世界范圍來說的。而對于自古以來民族問題就命系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多民族的中國來說,民族學研究、包括影視在類內的民族文化藝術創作在我國雖不敢說“悠悠萬事,唯此為大”,那也是在所有人文學科、文化藝術中位列“重中之重”的大事要題。就是基于這一原因,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在黨和國家偉大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在中華文化復興工程的感召下,在民族文化大省強省建設工程的推動下,憑借多民族大國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民族學、民族題材的文藝作品大量涌現,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時代主題話語之一。其中借助電視這一被歷史“提升到權威地位”*王逢振主編:《西方學術大師講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頁。的最具大眾傳播優勢的媒體而創作的“民族題材紀錄片”或稱“民族紀錄片”,在我國更是以數以萬計的巨大的創作量、以其社會意義的重大、文化內涵的深刻、人文風致的醇美、藝術樣式的豐富、民族特色的鮮亮而成為當代中國最為重要而獨特的影視片種。
一、民族志寫作的兩大歷史背景
美國民族志詩學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說:“民族志從來都是在國家體系形成和世界政治經濟進展這一歷史變遷之背景下寫出來的”。*[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高丙中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209頁。他認為“人類學電影”“民族志電影”直至如今的“民族紀錄片”,誕生于這樣兩個“歷史變遷”的時候:(一)“國家體系形成”的時刻;(二)“世界政治經濟進展”的節點。當然,這兩者之間又是互為表里關系的,因為歷史的事實是:“世界政治經濟進展”往往引發一系列甚至成批的新興“國家體系”的誕生。
影視史學界一致公認美國弗拉哈迪于1922年攝制的《北方的納努克》為世界“人類學電影”的開山之作,弗拉哈迪因此被譽稱為“世界人類學電影之父”。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到爆發前夕,用恩格斯的話說,這是一個“民族被買進和賣出,被分割和合作”*[德]恩格斯:《德國狀況》,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卷第641頁。又見楊生茂等主編:《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上冊第187頁。的時代。為配合這一“民族被買進和賣出”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目的,或國家派遣,或應殖民者的驅使,許多武裝有各種學科知識與技術設備的殖民官員、商人、探險者、記者、旅行家、冒險家、傳教士、科學家,走向美洲、非洲、亞洲、澳大利亞等殖民地,對所謂“原始民族”進行社會、文化、歷史的田野調查與研究。英國學者奈杰爾·拉波特等在其《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一書中將之定義為“殖民上升時期的學科活動”。*[英]奈杰爾·拉波特等:《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鮑雯妍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當時又正值電影技術誕生并趨向成熟的時刻,所以他們配合人類學的文字記錄拍攝了大量的影像資料與作品,學界稱之為“人類學電影”。同樣弗拉哈迪也難逃“殖民上升時期的學科活動”的宿命。他是美國的采礦工程師,受雇于一家在加拿大修建鐵路的美國公司,遠征找礦,他來到了愛斯基摩人(意為“吃生肉的人”)的部落。出于對域外“異文化”的關注,他們拍攝的第一部人類學電影《北方的納努克》誕生了。步其后塵,大批的后繼者們,也應各自帝國殖民探險、拓張的需要,走向亞洲、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亞各地,攝制了大量的作品,于是構成世界紀錄電影史上的:“人類學電影”奇觀。
二戰后,一大批新興民族國家誕生,史學界將之概括為“去殖民化的民族解放運動”。自此“民族主義”“民族解放”“民族獨立”“民族國家”成為二戰后“世界政治經濟進展歷史變遷”的最熾熱的關鍵詞與歷史主題。應運而生,“民族志電影”被大批的新興的民族國家呼喚而出。為回避當時“人類學”“民族學”的學科之爭,與“人類學民族學”這個二合一的概念相對稱,稱之為“人類學民族學電影”,后來又厭其概念疊加之弊而以“文化”置換“民族”,改稱“文化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電影”。也許是出于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強烈的文化情懷吧,中國學者剛開始只接受了“民族學”的概念,就稱其為“民族志電影”;后來接受了“人類學”的概念,因而就有了“影視人類學”和“影視人類學電影”。這給人的印象是在有意或無意淡化與忽略“民族志電影”的獨立價值。但從“人類學電影”到“民族志電影”,再到“民族紀錄片”的“創作運動的延續過程”來看,我以為作為民族志寫作內容之一的“民族志電影”是一種上承“人類學電影”,下啟“民族紀錄片”的重要片種。尤其是“民族志電影”作為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產物,更是不宜回避與忽視的。關于這一點,國外學者也有人注意到。如有一種意見認為,“民族志”是“人類學”的應用,其具體表現形態就是“田野民族志”,并對其進行區別:“田野民族志是關于民族的寫作實踐”,而“人類學家通常更多地研究異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文化。”*[英]阿蘭·巴納德:《人類學歷史與理論》,王建民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這里雖給予“民族志電影”以地位,但是卻只局限在所謂的“田野寫作”上。另一種意見是“把民族志,而不是理論推崇為人類學的真正基礎”。*[挪威]弗雷德里克·邁特:《人類學的四大傳統——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的人類學,前言》,高丙中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84頁。“民族志”在人類學上“應用”也好,是人類學的“基礎”也罷,從這其中我們已看到“民族志電影”已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存在意義。不僅如此,學界還將“人類學電影”到“民族志電影”的變遷稱作“范式轉換”或“程式跳轉”,即:“一個現實的研究程式達到一個臨界點”時,“很多從業者可能會轉而投向另一個程式——一種作品的新方向”。*[英]阿蘭·巴納德:《人類學歷史與理論》,王建民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這一“程式跳轉”最重要的意義是使原來的人類學電影找到“一種作品的新方向”,被人們用一個意味深長的“志”字加以定義,名曰“民族志電影”。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哈佛大學電影研究中心的創作。如他們拍攝的《獵人》《恩魯姆·特柴》《一場婚姻的爭論》等20多部作品記錄下了非洲卡拉哈里大沙漠的布須曼人的狩獵生活、降神儀式、婚姻習俗等等,后來的研究者雖將其定義為“人類學片”*張江華等:《影視人類學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頁。。但原創者在其與之同時出版的配套著作《未受損害的民族》一書中卻將布須曼人當作“未受損害的民族”即“原始民族”來觀察、記錄、研究,是一批有別于以往“人類學電影”的“民族志”片。這給人的印象是,學人們在理論上不愿放棄宏大的“人類學”概念,而作品創作用的卻是“田野民族志”的方法。面對這種人類學理論與“田野民族志”創作實踐的脫節,怎么辦呢?這就面臨尋找“作品新方向”的又一次“程式跳轉”。其間為“人類學電影”“田野民族志電影”尋找“作品新方向”,其中創新了“民族紀錄片”成就最為巨大的是中國。
中國“民族紀錄片”如今之所以如此繁榮眾多,我以為原因是其遇到兩大“國家體系形成”的“歷史變遷”的關鍵時刻:其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二是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改革開放與民族復興。1949年,這是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體系形成”的偉大時刻。經百年的歷史苦難與革命斗爭,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中走出,從東亞病夫的民族委屈中站起,一種油然而生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的精神促成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覺醒。作為新興“國家體系形成”的一項重要工程,剛成立的中央政府為促進民族團結、民族平等、民族發展,先后派出了多個“中央民族訪問團”“民族調查組”奔向全國各少數民族地區,跟團隨組同時拍攝了相當多數量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片”。僅1957年到1967年間,共拍了15部,它們是《佤族》《黎族》《涼山彝族》《額爾古納河畔的鄂溫克人》《獨龍族》《景頗族》《西藏農奴制》《新疆夏合勒克鄉農奴制》《苦聰人》《西雙版納傣族農奴社會》《大瑤山瑤族》《鄂倫春族》《赫哲族的漁獵生活》《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麗江納西族的文化藝術》。從其涉獵的民族之多、地域之廣,可以看到在新興“國家體系形成”之時,人類學、民族學及人類學電影、民族志電影的興盛。其強烈的“民族志”敘事意識,是“人類學”三個字難以精準概括的,甚至可以說這些作品“人類學”的意義,只是其次生價值,其直接而現實的意義是民族文獻、民族志記錄。
歷史來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來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又一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興“國家體系形成”的更為偉大的歷史時刻,這是“民族紀錄片”再次得到巨大發展的歷史節點。事實也正是這樣,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話說長江》《黃河》《舌尖上的中國》《鄉愁》《走遍中國》以及大量的中國各少數民族紀錄片引發的巨大反響,在某種程度上遠超同期播出的電視連續劇。人們對生于斯、長于斯的中華大地、民族風情的記錄,已不只限于過去“民族志紀錄片”“人類學電影”中的奇風異俗、花花草草、唱唱跳跳、古寺古廟,而深化為對民族文化、人文情感的深層叩問,詩意情懷細膩到“舌尖”的體悟、“走遍”中華大地,充分表達出一種悠悠“鄉愁”。這些作品有如“風信子”一樣,昭示我們可以遠瞻預設的未來,伴隨“中國夢”的偉大征程,“民族紀錄片”大有希望、天地廣闊。
二、“民族紀錄片”的“國家傳統”
《人類學歷史與理論》的作者阿蘭·巴納德說人類學或民族志電影寫作一般沿著這樣兩條線路發展:“按照截然不同的國家傳統間發散的和匯聚的影響線索發展”“基于國家的傳統的因素”發展。*[英]阿蘭·巴納德:《人類學歷史與理論》,王建民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我國繁榮如此的“民族紀錄片”之所以取得今天如此巨大的成就,并有如此極具民族特色的面貌,正是它不但廣泛吸納了“國家傳統間發展的和匯聚的影響”,更是對我國4000年古國、古老的民族書寫的“國家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明古老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自170萬年前的云南元謀人到陜西的藍田田人、周口店的北京人、廣東的馬壩人、湖北的長陽人、山西的丁村人、北京的山頂洞人、廣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資陽人等等的發掘,這是考古學描繪下的中華民族相沿170萬年的發展圖譜。中原的炎帝族、黃帝族,北方的狄人,東方的夷人,南方的九黎、三苗等等,這是中華民族神話記憶中的民族世界。族群聚居的地區稱為“方”,甲骨文中留下了上百個“方”字,這是遠古族群聚居的地緣態勢。商周以擁護“天下共主”的聯盟的形式,舉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面“民族團結”“民族統一”的旗幟。巨大的歷史慣性、文化認同,使中華民族超穩定性地始終保持“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就是基于這樣的歷史傳統,釀成中國特有的、數千年一脈相承的、代代修史的“歷史書寫”傳統。其中“民族書寫”始終是最為重要的部分。《二十四史》的《四裔傳》《魏書》《北史》《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元史》直至《清史稿》等,都記述了眾多少數民族建立王朝的歷史。《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蠻書》《契丹國志》《大金國志》等地方史志,以及數量大得驚人的歷朝歷代文人的筆記、文集、詩詞、戲劇中都記載了少數民族的歷史、民俗、文化、宗教、藝術等等。周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史官中更設有專事“民族書寫”的所謂“掌邦國之志”的“小史”(《周禮·春官·小史》)。這部小史書寫的“邦國之志”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志”……這一切做法不但保留了珍貴的中華各民族的歷史文獻資料,更結晶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書寫”的“國家傳統”——“史志”。
甲午戰爭,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使中國陷入落后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為救中華,針對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問題,借助西方以研究歐洲民族為對象所產生的民族學思想,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五族共和”的主張。1926年,時任國民政府高官的蔡元培發表《說民族學》一文,第一次將“民族學”這一學術概念、人文思想寫入中國的辭典。1928年調任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長的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專設民族學組,組織人員對廣西的瑤族、臺灣的高山族、黑龍江的赫哲族、湘西的苗族等民族的歷史、社會、文化、語言進行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推動其他省區以及燕京、清華、云南、四川等地的大學也開展了民族研究。其間,配合民族學田野調查,同時攝制了不少影像資料,編成了中國影視民族學片史上的第一批作品,中國本土的第一批裝備有電影攝影設備的民族紀錄片藝術學家也應運誕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兩個:其一是人類學博士凌純聲。1933年他與同事芮逸夫、勇士衡等受中央研究院派遣,前往湘西,后又到云南進行苗族、瑤族等民族的田野調查與民族學電影拍攝。他說:“科學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的真相,非借標本影片不足以表顯,多方采購標本,及攝制影片,正所以求真而保存其特質也。”*單萬里:《中國紀錄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其中給出這樣一種重要的創作思想:科學求真,應攝制標本電影。很明顯這是科學家的眼光。與此同時的另一條創作路線是由以鄭君里為代表的電影藝術家開創的。1939年4月,為抗日救亡,鄭君里作為國民政府派遣的“西北抗日救亡宣傳隊”的成員,來到西北,沿途拍攝了意在報道西北和西南地區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彝族的風土人情、宗教活動、支援抗戰為內容的大型紀錄片《民族萬歲》。其在《我們怎樣制作“民族萬歲”》一文中闡釋自己的創作思想是在“保存被攝對象的真實神韻”的前提下,“對實際事物加以創造的戲劇化”。*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頁。又見單萬里:《中國紀錄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頁。就這樣,凌純聲以“科學求真”為目的的“標本電影”的品相,鄭君里的“對事物加以創造的戲劇化”處理,構成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繼二十四史“史志寫作”后的又一影響巨大的民族志電影的“國家傳統”。這是我國后來的“民族紀錄片”最早的母本。
1955年配合大規模的民族調查,攝制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影片”,云南就有《佤族》《獨龍族》《景頗族》《苦聰族》《納西族》《永寧納西族阿注婚姻》《怒江——一條迷失的峽谷》。很明顯,這些作品雖也強調“科學目的”,但是更偏于民族“社會歷史”的宏觀透析,所以大多數作品的視野落在對整個“族”的社會性質、歷史發展、人文特征、信仰傾向等的實證性發現與記錄。就是由于這一原因,使這些作品至今仍為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多種學科所珍重;而且作為一大“國家傳統”來說,這批作品有如一座橋——一頭血脈相連的是從《二十四史》時代的“史志實錄”,凌純聲的“標本電影”的“傳記式民族片”,鄭君里的“創造的戲劇化處理”的時政紀錄報道;一頭是今天的“民族紀錄片”。從中我們看到要真正過渡到今天的“民族紀錄片”,光靠上述的“史志實錄”的“紀實”、“標本電影”的“求真”、“戲劇化處理”的“求藝”還不夠,還欠一大后來才真正完善強化起來的“大眾傳播”的“新聞性”元素。
有人統計說,僅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以來“共攝制長紀錄片239部、1506本,短紀錄片2007部、共3632本,新聞期刊片3528本。”*單萬里:《中國紀錄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頁。盡管其特點被不無片面性地概括為“形象化的黨報”,但是我們還是要說,這些作品在歌頌新中國、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推動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事業中起到了極為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為我們認識一個“新國家體系的形成”留下了不朽的“時代的日記”“民族的相冊”。是的,到了電視技術在中國大地大普及的20世紀80年代,電視紀錄片成為影視世界“天下第一”的片種。其作品題材遍及大千世界、萬事萬物,其作品類型多得只能用“風起云涌”來加以泛化表達。其核心品質與文化力量來自作為“時代日記”的新聞性,源自“民族相冊”的莊嚴性。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兩點——國家日記的新聞性,民族相冊的莊嚴性,構成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族紀錄片”新的“國家傳統”。如云南紀錄片導演范志平在拍攝《甲次卓瑪和她的母系大家庭》時跟蹤多年,記錄下被人譽為女兒國的云南麗江瀘沽湖摩梭人的一個家庭的生活變化與村寨變遷。郝躍進的《最后的馬幫》、孫曾田的《最后的山神》將記錄視點切在一南一北兩個民族進入現代社會這一“歷史節點”時刻的變化,生活方式的、心理的、文化的、信仰的變革上。其具有人類學、民族學“標本電影”的品質,更具有強烈的新聞紀錄片的沖擊力與時政意義,其“兩棲性”,使這些作品既為“影視人類學”點贊,又為新聞紀錄片世界所推崇。
三、“民族志詩學”的建立與我國“民族紀錄片”的藝術創新
1984年10位世界著名的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志電影的學者、藝術家會聚美國新墨西哥州召開題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的研討會,最后匯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其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民族志詩學”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
何謂“民族志詩學”?西方學者將其定義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高丙中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代譯序第6頁。面對我們在大國崛起、民族復興中壯勢發展的民族紀錄片,我以為對國外的“民族志詩學”進行積極的梳理與研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志詩學”,或說是“民族紀錄片詩學”,這對推動我國民族紀錄片的發展應有著積極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其一,“寫文化”意識的確立。《寫文化——民族志詩學與政治學》一書,將“寫文化”置于主標題位置,而“民族志詩學”倒只作為副標題出現,這一“詞位”排列,給出這樣一個信息:“寫文化”是“民族志詩學”的首要精魂。持這一觀點的不只是這10位提交論文的學者,而是當時學界的一大“歷史共識”。英國學者奈杰爾·拉波特等在其《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一書中提出人類學的本質就是“寫文化”。*[英]奈杰爾·拉波特等:《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鮑雯妍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頁。如何寫文化?“殖民主義上升時期”的人類學或民族志基本上將西方殖民者的“他者”眼光,在他們的學術眼光里,或“電影眼睛”里,看到的是殖民地的原始、落后、愚昧。1974年,美國學者斯坦利·戴蒙德出版了《尋找原始人》一書,提出要拯救“西方世界的危機”,只有“向原始人學習”。*葉舒憲等著:《人類學關鍵詞》,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頁。《原始人的挑戰》的作者羅賓·克拉克等更把“高貴的原始人”看作照見西方文明危機的一面“高尚的鏡子”。*葉舒憲等著:《人類學關鍵詞》,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頁。但不管怎么說,上述這些還是“他者”眼光。相比之下,真正以平等科學的眼光,很好地建構“寫文化”的是中國。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影視人類學研究室,自組隊伍,自主創作,如赴貴州攝制了苗族文化系列片《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藝美術》《苗族的節日》《苗族的舞蹈》。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1983年拍攝的《白褲瑤》以及17個民族的近40集民族紀錄片,其“文化志”特征異常鮮明。云南民族電影制片廠八九十年代攝制的《白族》《迪慶藏族》《瀘沽湖的母系親族》《阿佤山紀行》《獨龍掠影》,廣西電影制片廠攝制的瑤族壯族紀錄片,云南電視臺攝制的《走進獨龍江——獨龍族及其生存環境》《甲次卓瑪和她的母系大家庭》《山洞里的村莊》《最后的馬幫》《瀾滄江》等明顯以“寫文化”的哲學意識、“文化志”的歷史情懷來把握題材。有意思的是,盡管科研所與民族大學的“學人們”習慣于將自己的作品冠以“學術”的名謂:人類學電影、民族志電影,但電影廠、電視臺、音像公司的編導們卻把原先的“民族志”片的“志”字換了個新聞體裁命名,稱作“民族紀錄片”。兩股力量都在“寫文化”,都或多或少共用影院與電視臺這一平臺播映。“寫文化”的傳統源起20世紀80年代,至今30余年,已鑄成中國“民族紀錄片”的一大“國家傳統”,已釀為中國“民族紀錄片”的一大文化奇觀。
其二,“文學轉向”的美學選擇。英國學者拉波特說 :“文學轉向”成為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寫作的“一項當務之急”。他觀察到通過“文學轉向”,人類學、民族志寫作出現了這樣一些新變化:“人類學逐步擺脫了埋頭于對‘他者’進行天真的不偏不倚的分析的企圖”,從而表現出一種大別于以往作品的“創造性和美感”,為此,他甚至把這種作品稱作“文學人類學作品”“鄉村的牧歌”。*[英]奈杰爾·拉波特等:《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鮑雯妍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頁。
這一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寫作的“文學轉向”在中國引發的反響,如下:一是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文化人類學小說”。如賈平凹的鄉土小說《晚雨》,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高行健的《靈山》,姜戎的《狼圖騰》,趙宇共的《走婚》《炎黃》等等。另一“文學轉向”即影視紀錄片中明顯的文學意趣的強化。且不說《話說長江》《黃河》《話說運河》等的文學散文式的解說詞的引入,就是“民族紀錄片”也常以散文、散文詩或戲劇化、故事化的方式構筑作品。例如紀錄片導演喬丹,為拍好藏族題材錄片,這位藝術家長期深入西藏,自學藏語,她創作的《貢布的幸福生活》(1999年)和《老人們》(2002年)的濃郁的“文學性”,被評說家譽之為有一種西藏圣地賦予的“贊美詩氣質。”*朱靖江、梅冰:《中國獨立制片檔案》,陜西: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頁。再如云南電視臺導演魏星編導的《學生村》,記錄的是一個云南民族山村小學的生活,作品以兄弟兩個小學生為主要記錄對象,以極為平常的校園讀書生活記錄,讓人看到云南少數民族孩子的求學之路的艱辛。該作品幾如一部“紀實性電視劇一樣”,有人物、有故事、有戲劇矛盾,有如一部“人間悲喜劇”。
其三,新聞化走向。人類學,民族志是拒絕“新聞性”的。但是一方面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所給出的內容的神奇、情景的神秘、人文的驚艷,其本身就具有某種程度的 “新聞性”。另外再加上一位美國評論家所觀察到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作家“要保住地位就得寫出新奇的小說——不但要‘新’,而且要成為‘新聞’。”*[英]貢布里希:《理想與偶像——價值在歷史和藝術中的地位》譯序,范景中等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頁。事實也正是這樣,人類學、民族志只有走出大學的講堂,走出科學院的大門,走向大眾,才可能真正獲得新生。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學理指引的方向在西方未真正得到廣泛采納,倒是在我們中國找到了另一種集“寫文化”“文學化轉向”為一爐的“新聞化走向”。最為典型的例子如西藏的“民族紀錄片”,其“新聞化走向”已然構成一大傳統:1942年出品的大型紀錄片《西藏巡禮》,以國民黨蒙藏委員會委員吳忠信1939年12月赴藏參加班禪坐床大典的事件為記錄對象,展現了西藏的地理風光、風土人情、宗教文化,以及作為抗戰后方的西藏人民的活動,其“新聞紀錄”的“當時性”十分撼人。《光明照耀著西藏》出品于10年后的1952年,這是隨軍進藏記者,以積累了幾年的鏡頭素材,最后編輯成功的作品。該作品以巨大的政治熱情為西藏的解放、農奴的翻身留下了不朽的影像文獻,是人類學、民族學中的“史記”,更是“新聞紀錄”在歷史第一時間留下的偉大場景。1959年出品的《百萬農奴站起來》,記錄了平息西藏叛亂和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情況。其片名就有如一個“歷史性定義”一樣,標明這一作品展現的“歷史節點”:西藏農奴制滅亡的時刻。1976年的《西藏高原大寨花》,其中雖多有時政記錄的歷史局限,但其可貴的新聞記錄,同樣值得珍視。1985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的《西藏——西藏》《五十年代西藏社會紀實》《西藏今昔》,組合為半個世紀西藏解放、社會變革的“新聞記錄”史。20世紀90年代推出的《西藏的誘惑》《雪域明珠》,到新世紀獨立制片人攝制的《喇嘛藏戲團》《青撲——苦修者的圣地》《天主在西藏》《八角街》《拉薩雪居民》等,盡管其間多有獨立制片人特有的“作者人類學”的敘事品格,但是其“新聞記錄”的報道功能仍溢于畫面。是的,盡管西方學者對中國如此的新聞紀錄片走向不一定贊賞,但人們不能不承認,這在中國紀錄電影史上,甚或世界人類學電影、民族志電影史上,都是不可忽視的創新。
其四,敘事模式的創新。學人們將人類學,民族學寫作分為四種模式:“經驗的、解釋性的、對話性的、復調的”。說雖然“經驗的和現實的,解釋性的模式”是長期以來人們公認的“權威模式”,但是隨著民族志寫作藝術的發展,其“逐漸讓位于話語的,對話的和復調的范式”。“對話”是“一個體現了兩個主題間的話語交流的文本”,“復調”“是一個不僅給予合作者以獨立的陳述者地位,還給予寫作者地位的多重作者的烏托邦”。*[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高丙中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296、298頁。更有學者說“未來人類學將是各種方法的混合”,是一個“再本土化”即“對本土知識的維護,再發現或創造”*[英]阿蘭·巴納德:《人類學歷史與理論》,王建民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0頁。的創新過程。美國紀錄電影史家尼柯爾斯認為世界紀錄片敘事模式經歷并積累了這樣四大模式:“格里爾遜傳統的直接表達”;“無須添加含蓄的或直率的解說”的“真實電影,又叫直接電影”;“常以采訪的形式進行直接表達”的“以訪問為主流的影片”;“把評述和采訪、導演的畫外音與畫面上的插入字幕混雜在一起”的“自省式”,即“個人追述式”或叫“自我追述式”,并說這是“當代紀錄片的標準模式”,其特點是“把直接談話(人物或解說員直接向觀眾講話)結合于訪問會見中”。*單萬里主編:《紀錄電影文獻》,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第537頁。又見任遠編譯:《海外名家談電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頁。第四種是我們今天常見的以“主持人”或“嘉賓主持”,甚或以記者的談話為敘事主體的作品,也即是實施上述“對話”“復調”“混合”“文本策略”的作品。美國的埃里克·巴爾諾沒有專門為紀錄片定義敘事模式的發展軌跡,但從他為定義紀錄片創作者的創作動因與歷史貢獻而給出的一系列關鍵詞中,可以窺見其對“紀錄片義敘事模式”、“結構策略”與“文化戰略”的描述,他點贊紀錄片作者是“預言家、探險家、報道、記者、畫家、擁護者、喇叭手、揭發者、詩人、編年史作者、觀察者、觸媒者”*[美]巴爾諾:《世界紀錄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版,目錄。等。
從上述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民族紀錄片”其結構模式與敘事策略既堅守了人類學電影、民族志電影所特有的長期的田野觀察記錄、歷史文獻的運用,更集“預言家、探險家、報道記者、畫家、擁護者、喇叭手、揭發者、詩人、編年史作者、觀察者、觸媒者”等的功能于一身,再加上少數民族的“人文秘境”的神氣,更使這些作品有著別樣的文化色彩與美學情調。如對獨龍族的記錄,早自20世紀50年代的“少數民族科學文化紀錄片”《獨龍族》,到80年代的《走進獨龍江》《最后的馬幫》,2016年的《一步登天》等等,是對獨龍族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第一時間的觀察與記錄。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的《獨龍族》用的是解說加畫面的“格里爾遜式”,那么《走進獨龍江》則是有解說、有訪談的直接電影式;《最后的馬幫》幾為“以訪問為主的影片”;《一步登天》可視為運用“混合方式”的。
“民族紀錄片”的發展于新中國“國家體系形成”之時,定基調于在我中華文化的“國家傳統”之中,汲取世界人類學電影、民族志電影的“民族志詩學”的美學沃潤,以開放的胸懷、創新的理念,擁抱這一全面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中國“民族紀錄片”天地更為寬廣,作為將更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