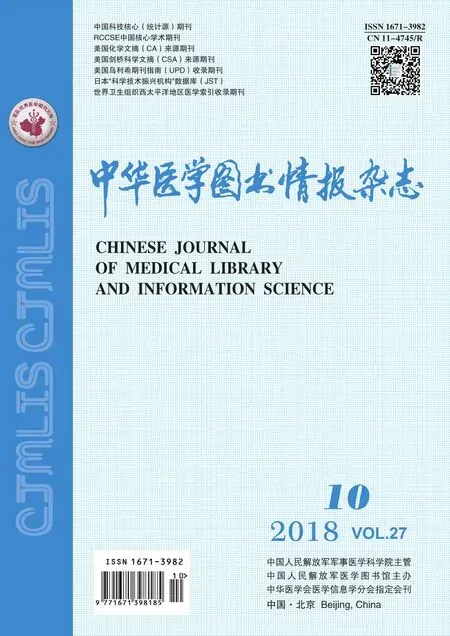“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教材基礎理論研究與展望
,
自1984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在高等學校開設<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距今已有44年[1]。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文獻載體的變化,文獻檢索已發展到信息檢索和知識檢索階段。課程基礎理論是學科根基與發展的重心,現選擇1959年以后出版發行的“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 課程教材(含中醫和藥學)作為調研樣本,總結分析“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教材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發展歷程,期望對“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教材(以下簡稱“課程教材”)的基礎理論和整個教材的建設有所啟迪。
1 課程教材基礎理論的文獻調研
1.1 文獻調研方法
調研工具選擇中文最大的圖書學術搜索工具——“讀秀”學術搜索和中文圖書專業檢索方式。
采用檢索式(T=文獻|T=信息|T=情報|T=知識)*T=檢索*(T=醫學|T=醫藥|T=藥學|T=中醫),檢索得到相關圖書405本。另外,對于從信息素養角度出版的教材,采用檢索式(T=素養|T=素質)*T=信息*(T=醫學|T=醫藥|T=藥學|T=中醫),檢索得到相關圖書5本。考慮到早期文獻檢索教材的表達形式,采用檢索式T=文獻工作*(T=科學|T=科技),檢索得到相關圖書31本。
搜索1959-2018年國內出版的文獻檢索教材,在線瀏覽各教材的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同時補充瀏覽南京圖書館藏書和近一年出版教材書店的圖書。
1.2 文獻調研結果
對檢索到的圖書逐一瀏覽其基礎理論部分,按照圖書館開展“文獻檢索與利用”用戶教育的發展過程,發現主要有檢索工具使用法、文獻學理論和情報學理論3個方面的文獻檢索基礎理論。這3個方面的基礎理論在時間上交叉并存,反映了編者還沒有達到學科上的共識(表1)。

表1 醫學文獻檢索課教材基礎理論文獻調研結果
2 課程教材基礎理論文獻調研結果分析
根據文獻調研,分析3種基礎理論的來源、基本概念和范疇。
2.1 檢索工具使用法
文獻的積累和社會對文獻利用的需要是書目(bibiliography)產生的根源,書目工具結構與使用構成其基本知識。書目工作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對書目工作的概括與總結,形成目錄學[2]。書目是系統獲取文獻線索的必備工具,學習使用書目是獲取文獻線索的必備知識。教育部《意見》印發前,醫學圖書館在20世紀50-60年代文獻檢索書目工具介紹的基礎上,編寫了檢索工具指導用書,其主要內容為檢索工具的概念、種類、檢索方法、途徑和步驟,如葉銘主編的《醫學情報檢索》、劉元江主編的《藥學信息檢索技術》等。20世紀50-80年代是中國科技檢索體系創建時期,為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相關單位普及檢索工具使用知識,讓用戶了解常用的檢索工具,學會使用檢索工具獲取文獻線索,促進了用戶更好地利用文獻。隨著21世紀網絡檢索的興起和網絡檢索工具的普及,一些專業性的檢索教材,從課時和實用出發僅介紹檢索工具與信息源,難以適應當今的社會需要。
2.2 文獻學理論
S·C·布拉德福在《文獻學(文獻工作)》一書中認為文獻學(文獻工作)是搜集、分類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動記錄的技藝;J.H.謝拉在《行動中的文獻學》一書中則認為文獻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發展新的分析、組織與檢索方法,以充分利用各種記錄下來的知識。目前文獻學(documentation)的一般定義是研究文獻的獲取、組織、存儲、檢索和傳播等規律的學科[3]。針對醫學文獻數量龐大、知識更新快、醫學院校師生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需求量大的特點,1963年中山醫學院病理生理教研室侯燦老師編寫了《醫學科技文獻工作》。該書是此次文獻調研中發現最早的“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教科書,它從文獻學角度闡述了科學文獻的尋找、選擇、閱讀、積累、創新和利用[4]。1984年在教育部《意見》推動下,吳觀國的《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李健康的《醫學文獻檢索》、范家永和吉文輝的《中醫文獻檢索與利用》與葉銘的《醫學文獻檢索》等“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教材的框架都采用《意見》的課程內容,主要為文獻、文獻檢索的知識,主要檢索工具的內容、結構及查找方法,主要參考工具書的內容、作用及使用方法。在上述內容基礎上,適當增加閱讀方法與技巧、文獻整理與綜述、情報分析研究以及論文寫作方法等內容[1],從而推動了當時的用戶教育從檢索工具擴大到文獻。文獻是記錄一切知識的載體,檢索工具也屬于文獻范疇,文獻中的知識才是獲取文獻、知識創新的源泉,文獻、知識構成課程教材基礎理論中的基本概念。
2.3 信息、知識和情報相互轉化的情報學理論
20世紀40年代后期,美國科學家V.布什發表的《誠如所思》提出機械化檢索的設想和S.C.布拉德福發表的《文獻工作內容的改進與開展》強調文獻工作必須變革的倡議,推動了文獻工作向情報學的歷史轉移[3]。C·E·香農將信息的傳遞作為一種統計現象,開啟了現代信息論(information theory)的研究。1981年肖自立從信息視角闡述人類經過信息的接受、存儲、加工、組合、輸出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信息是描述物質存在的方式和運動的規律與特點,知識是人類通過信息對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方式與運動規律特點的認識和掌握,是人的大腦重新組合的信息系統,情報則是思考和行動所需的知識。信息、知識、情報三者是包含關系,三者均可記錄、存儲、編碼、傳遞,并在特定條件下相互轉化[5]。為了闡明信息、知識與情報之間的轉化關系,有些教材還吸納了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知識結構的方程,即K(S)+ΔI=K[S+ΔS][6]。1992年高教司《文獻檢索課教學基本要求》(以下簡稱《基本要求》)頒發的課程內容與1984年的《意見》相比,增加了情報、知識、信息的概念以及情報與情報意識對科學活動及個人知識增殖的作用作為課程的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要求[7]。知識是對信息加工、吸收、提取、評價的結果,即系統化的信息成為知識,知識記錄下來成為文獻,文獻經傳遞并加以應用成為情報,情報(information)體現了人運用知識的能力。“信息-知識-情報信息鏈”成為文獻檢索教材基礎理論的基本概念,并為國內多數課程教材采用。但此理論的信息和情報對應的英文單詞都是information,違背了同一術語不能代表不同概念的科學研究的原則。2009年以后,許多課程教材開始將情報對應英文單詞“intelligence”[8](通常被翻譯為“智能”)。雖然此階段的基礎理論在信息論的推動下,從認識論角度形成“信息-知識-情報鏈”的基本理論,但在如何將知識激活為情報,或者說缺乏情報如何轉化為行動能力方面的論述,基礎理論與應用結合不夠緊密。
2.4 近10年教材基礎理論的探索
由于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在情報概念對應方面的不一致性[9-12],一些課程教材在基礎理論闡述中避開了“情報”一詞。如黃燕的《醫學文獻檢索》,羅愛靜、于雙成的《醫學文獻信息檢索》,黃晴珊的《全媒體時代的醫學信息素養與信息檢索》等均采用信息、知識和文獻的基本概念框架[13-16]。以哲學的視角認識信息從獲取到利用過程的思維活動,強調信息思維,即借助于已有的認識論信息、已知的條件推測未知事物的重要性[14-16]。《全媒體時代的醫學信息素養與信息檢索》強調信息是知識的原材料,知識是信息加工后的精華部分,新知識融會為接受者的知識體系,知識又必須轉化為智慧[15];《醫學信息檢索與利用》在基礎理論部分用較多篇幅介紹了波蘭尼等專家的知識理論[17]。筆者在《醫藥信息檢索與利用》一書的基礎理論部分介紹了信息及其相關概念,即消息、信號、數據、知識、情報、智能、智慧和文獻等,從信息科學的視野闡述了信息轉換為解決問題所需智能的過程,應用“知識理論”作為方法論統領全書脈絡[18]。郭繼軍的《醫學文獻檢索與論文寫作(第5版)》提出信息科學的科學觀是信息觀、系統觀和機制觀,其機制觀也是方法論,即“信息-知識-智能”轉換原理。檢索獲取知識的根本效用在于被激活為智能,并描述了信息轉換過程的4個步驟[19]。此階段探索將知識理論作為課程教材的基礎理論,即知識是如何從信息加工的過程中產生的(知識與信息的關系), 知識又如何被激活成為智能的(知識與智能的關系),轉換的機制是“知識理論”的核心[20]。從認識論角度看,知識是信息轉化為解決問題行動(智能)的中間環節,信息、知識、智能和智慧就構成了基礎理論中的基本概念。
3 課程教材基礎理論研究的展望
通過對1959年迄今課程教材基礎理論的文獻梳理與分析,筆者提出兩點展望。
3.1 從課程教材基礎理論的發展過程展望
T·庫恩的科學發展模式認為任何一門科學知識的發展都是一個演化與革命、積累與創新、連續與間斷交替發生的歷史過程,典型的形態是受某個既定的哲學范式支配的,是積累性常規研究同創新性非常規研究交替出現的歷史進程。T·庫恩將學科歷史進程劃分為“前科學階段”“常規科學”“科學革命”。前科學階段的特征是諸學蜂起、百家爭鳴,研究者從不同視角觀察和研究事物,因此對同一社會現象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21]。從課程教材基礎理論的回溯可以看出,掌握書目或者數據庫使用是為了獲取文獻線索,研究和觀察的對象是書目或者數據庫。如果僅僅學會了書目或者數據庫使用,不了解在文獻交流中的各學科文獻特點、種類、選擇等,在利用文獻方面仍然有欠缺。因此,研究和觀察的對象不僅上升為文獻,而且書目也屬于文獻范疇。獲取文獻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文獻中的知識,獲取知識是為了利用知識、再生知識。信息是知識的原材料,知識是信息加工的產物,信息的核心價值在于被提煉為知識。知識是智能生成的基礎,智能是在一定條件下知識激活的結果,知識的根本效用在于被激活為智能[22]。由此可見,信息如何轉化為知識和智能成為最關鍵的問題。從情報學智能取向的維度看,抽象的信息、知識、智能(情報)概念變成研究和觀察的對象,屬于認知范疇[23]。為此,課程教材基礎理論研究從關注書目工具、文獻表象描述的經驗基礎理論,逐步向探索表象背后信息發展規律的理性基礎理論轉變。研究范疇得到不斷的更新和拓展,基礎理論研究由簡單走向復雜、由表層走向核心。馬費成在2017年10月29日召開的“情報學與情報工作發展論壇”認為,從信息鏈上理解和定位情報學,是情報學突破以文獻為基礎的學科范式的一條學科發展基本范式,并達成“南京共識”[24]。近10年課程教材信息鏈基礎理論的探討和建設方向代表了專家的共識,“信息-知識-智能策略-行動”基礎理框架為每個轉換環節提供了理論指引。如何在“信息-知識-智能策略-行動”基礎理論上,結合圖書館、社會信息資源和信息工具構建信息獲取、信息處理和信息利用的新體系,是課程教材今后需要下大力氣研究的問題。
3.2 從課程的性質、任務和目標展望
1992年高教司《基本要求》中基礎理論是“信息-知識-情報”的信息鏈,C·L·博格曼定義情報學是研究情報信息的獲取、加工、存儲、檢索和傳遞的學科。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情報”這一術語顯示出“剪不斷,理還亂”的現實特點[25]。結合課程的性質是方法課即學習是獲取信息、利用信息的方法,課程的任務是增強自學能力和研究能力,課程的目標是學習信息的獲得、處理與利用而不是傳遞情報信息。筆者認為“信息-知識-智能”的信息鏈是課程教材基礎理論,所以教材編寫的目的是讓用戶學習如何獲得信息,并促進信息向知識的轉化。知識(認識論信息)的獲取是手段,知識的運用和知識發展是最終目標。利用知識解決問題涉及到“智能”的概念。智能,即人們在給定問題、問題約束(領域知識)、問題求解目標的前提下,獲得“問題—環境—目標”的信息。根據這些信息獲得相關知識(實現認知),在目標引導下生成策略,把策略轉化成行為去求解問題,并通過學習優化策略最終達到預定的目標[26-27]。就文獻檢索與利用而言,所謂“給定”,是對一組已經明確問題條件的描述,即問題的初始狀態。所謂問題的“目標”,是指關于構成問題結論的明確描述,問題要求的答案或目標狀態。在問題的初始狀態,借助于經過鑒別、篩選、存貯、整序的信息系統迅速獲得相關認識論全信息,經過知識組織(形態性知識、效用性知識、內容性知識的集約化)、知識建構(布魯克斯知識方程的實現)、知識關聯(內容性知識關聯化、效用性知識的匹配化)和在知識網絡環境下通過智力共融、眾創協作,促進知識激活為行動策略[28],并通過學習優化策略最終達到預定的目標狀態。
2015年,美國保羅·澤考斯基指出,目前的信息素養教育由于在信息搜索中缺少稱為“行動素養”的環節,培養用戶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為此,他認為要將信息轉化成知識、知識轉化成理解、理解轉化成智慧[29]。筆者認為,信息、知識、智能、智慧和理解等概念今后將會成為課程教材基礎理論中的基本概念,課程教材的基礎理論、信息資源、智能工具和資源利用等章節知識將會在“信息-知識-智能策略-行動”的認知鏈條中有機融合,更好地體現該課程科學方法課的特點。
4 結語
“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教材基礎理論從關注書目工具使用法、文獻到信息資源,再到知識、情報和智能,這種演變推動了自身學科邏輯的起點向更高層次發展。課程及其教材必須加大轉型與變革的力度,回歸“醫學文獻檢索與利用”是輔助人類提升信息加工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本源。深入到信息、知識、智能與智慧的內容和過程之中,構建以培養醫學專業學生自學能力和研究能力為核心、以信息技術開發應用為手段、以大數據獲取知識為核心能力的教材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