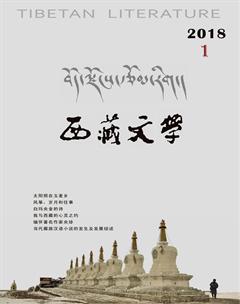當代藏族漢語小說的發(fā)生及發(fā)展綜述
鄭靖茹,女,漢族,四川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結緣當代藏文學研究15年,默默關注漢文版《西藏文學》和當代藏文學的發(fā)展。曾主持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西部項目《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研究》。主要論文有《現代文學體制建立的個案考察:漢文版〈西藏文學〉與西藏文學》、《讀屏時代的西藏文學》、《現代傳媒與西藏當代文學》、《“西藏當代文學的縮影”——漢文版<西藏文學>》、《一個語言原鄉(xiāng)者的艱難跋涉——從〈血脈〉看阿來小說中的族際邊緣人》、《跨越文化禁忌的艱難——〈魚〉的一種文化解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漢文版〈西藏文學〉的譯介情況分析》、《試論西藏當代文學生成發(fā)展的歷史語境》、《“西藏新小說”的興起與終結》、《現代進程中的西藏當代文學六十年》、《再談“理解色波”——色波小說述評》、《從西藏作家群的代際轉換看西藏當代文學》等。
一九九二年深秋,中國作協(xié)黨組常務副書記、著名蒙族作家瑪拉沁夫在西藏一個座談會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西藏的現代小說創(chuàng)作起步很晚,但為什么新時期之初那幾年,西藏高原上一下子就冒出了一個很強的作家群體,特別是其中的藏族作家,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出就是一群,起點之高,勢頭之猛,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很罕見的,一下子就走在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前列,并且至今還后勁不衰。什么原因?值得好好總結。”1若是回到歷史的場景中,可以發(fā)現:正是西藏漢語小說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驚人成績,使西藏作家擺脫了一種潛在的文學自卑感,獲得了空前的文學自信,并且這種文學自信還從西藏影響到其他藏區(qū),召喚更多的當代藏族作家投身到漢語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來。2000年,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進一步增強了年輕一代藏族作家運用漢語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的自信心和積極性。不僅當代西藏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而且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的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也同樣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就目前已有資料來看,如果從1963年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瑪在《兒童文學》第2期發(fā)表《清晨》2的一個片段算起,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已經走過了50余年的歷程,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和小小說都出現了不少優(yōu)秀的作品,作家間的代際特征也逐漸顯現出來:不僅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藏族作家還在繼續(xù)創(chuàng)作(如西藏作家扎西達娃和色波、四川作家阿來、青海作家多杰才旦和才旦),六十年代出生的藏族作家已然呈現出不俗的創(chuàng)作成績(如青海作家萬瑪才旦、龍仁青、梅卓,西藏作家次仁羅布、吉米平階,四川尹向東和澤仁達娃等),而且七十年代出生的藏族作家也開始展現出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實力(如西藏作家尼瑪潘多、青海作家江洋才讓、四川作家洼西彭措和仁真旺杰等),更可喜的是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藏族作家也開始了漢語小說的寫作(如四川作家洛桑卓瑪、甘肅女作家何延華和王小忠等)。
當代藏族作家漢語小說的發(fā)展五十多年來,就其出版和發(fā)表狀況來看,已經積累了相當的量,下面就出版概況做如下方面簡要分析:
第一,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是當代藏族作家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要體裁。由于文學雜志的版面需求以及對小說這種藝術形式的自我訓練,大多數當代藏族作家都以中短篇小說的形式走上文壇:如德吉措姆1977年發(fā)表處女作《駿馬飛奔》,扎西達娃處女作《沉默》發(fā)表在《西藏文藝》1979年1期。在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中,中短篇小說的數量最多,甚至他們最主要的代表作都是中短篇漢語小說,如:扎西達娃、色波、才旦、萬瑪才旦、龍仁青、吉米平階、次仁羅布、何延華……而這些中短篇小說如《自由人契米》、《世紀之邀》、《圓形日子》、《星期三的故事》、《旃檀》、《塔洛》、《瑪尼石,靜靜地敲》、《光榮的草原》、《綠波帶》、《曲郭山上的雪》、《立春》等小說無論是放在藏族小說的背景下,還是放在全國少數民族小說的背景下,甚或是放在整個中國的當代小說發(fā)展背景下來審視,都是當代小說中的優(yōu)秀作品。
第二,當代藏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說結集出版標志著作家個人風格的逐漸形成。藏族作家漢語小說集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如意西澤仁《大雁落腳的地方》和《松耳石項鏈》、扎西達娃《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尕藏才旦《半陰半陽回旋曲》。90年代之后,更多的藏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說結集出版,如扎西達娃《西藏,隱秘歲月》、色波《圓形日子》、多杰才旦《達賴六世逃亡》、益希單增《金塔》、意西澤仁《意西澤仁小說精選》、查拉獨幾《雪域風景線》、扎西東珠《山梁上的白馬或愛的折磨》。進入21世紀之后,出版小說集的作家更多更普遍了,幾乎每個作家都出版了自己小說集:如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3和《扎西達娃小說集》4, 丹增的《小沙彌》,索朗仁稱的《索朗仁稱小說選》,才旦的《菩提》和《香巴拉的誘惑》,萬瑪才旦的《流浪歌手的夢》、《嘛呢石,靜靜地敲》和《塔洛》,龍仁青的《光榮的草原》和《咖啡與酸奶》,次仁羅布的《放生羊》,尹向東《魚的聲音》,洼西彭錯的《鄉(xiāng)城》和《失落的記憶》,永基卓瑪的《雪線》,何延華的《嘉禾的夏天》等;還有的小說集通過再版方式重新出版,如色波的《圓形日子》和吉米平階的《北京藏人》。這些小說集的出版,說明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在中短篇小說領域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個人風格。
第三,當代藏族作家長篇漢語小說的大量出版在展現創(chuàng)作實績的同時,也給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創(chuàng)作提出一些新的難題。當代藏族的長篇漢語小說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于21世紀走向繁盛。1980年,降邊嘉措的《格桑梅朵》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成為當代藏族文學史上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隨后益希單增、益西卓瑪、多杰才旦、丹珠昂奔相繼出版長篇小說。這些小說中,除了丹珠昂奔的《吐蕃史演義》是歷史小說外,其他長篇小說主要運用現實主義方法再現藏族各階層民眾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的所思所想所見,力圖客觀真實地再現各地的藏族同胞的現實生活。進入21世紀,當代藏族作家的長篇漢語小說出現了較為繁榮的局面:在阿來的《塵埃落定》獲獎之后,阿來相繼出版了《空山》和《格薩爾王》,江洋才讓的《灰飛》、《然后在狼印奔走》、《康巴方式》、《馬背上的經幡》、《牦牛漫步》相繼出版,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索朗仁稱的《藏·甘寨》、多杰才旦《倉央嘉措》和《菩提夢》、才旦《安多秘史》、澤仁達娃《雪山的話語》和《走在前面的愛》、仁真旺杰《雪夜殘夢》、達真《命定》和《康巴》、尹向東的《風馬》、阿瓊《渡口魂》。但是,長篇小說不是中篇小說的簡單拉長,因此也對藏族作家對于小說敘述節(jié)奏的控制能力、小說結構的把握能力以及思想闡釋的深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藏族女作家群的崛起是當代藏族文學的重要收獲。較早的藏族女作家主要有益西卓瑪、德吉措姆、西繞拉姆、梅卓、央珍、格央、白瑪娜珍等,她們是藏族文學史上較早出現的女作家,因此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益西卓瑪的《清晨》、德吉措姆的《漫漫轉經路》、梅卓的《太陽部落》、《薩姆佳朵黛》、《月亮部落》、央珍的《無性別的神》、格央的《小鎮(zhèn)故事》、《一個老尼的自述》等小說中細膩的女性敘述,為藏族女性書寫奠定了一定的經驗。如梅卓的小說中時時流露出濃濃的女性細膩和溫情,形成了一種特有的詩化語言風格。藏族女作家群體的出現,使得藏族文學史上第一次有了女性群體的歌唱,成為藏族女性文學歷史中的寶貴開端。新世紀以來,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藏族女作家逐漸登上文壇,如西藏的尼瑪潘多、云南的永基卓瑪和央金拉姆、甘肅的何延華,她們的小說視野更加寬廣,小說技法更多樣,小說涉及的社會生活也更加廣泛,因此,表現為對小說藝術有著更加明確的追求。
第五,“康巴作家群”書系的連續(xù)出版計劃為“康巴作家群”的橫空出世提供出版保障的同時,也給康巴作家們帶來了新的問題:如何以小說的方式來敘述康巴大地以及康巴歷史。對此,不同的作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尹向東集中在對當代歷史的書寫,洼西彭措則集中在近代史的書寫,達真則關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現代歷史;尹向東寫出了邊城小鎮(zhèn)人在當代歷史中的凄惶和掙扎,洼西彭措則在傳說與史實的縫隙寫出了歷史的偶然與必然,達真在對史詩般的宏大敘述中講述了個人的命運史。總之,個體心靈史與家國史、部落史和民族史匯集在一起,畢竟所有的歷史大敘述最終必將以個體的心靈承擔為基礎,康巴作家們在他們的小說中講述了康巴人的群體承擔和個體承擔,并從中書寫出了康巴人令人敬佩的血性。這種血性,在康巴作家的小說中更多地體現為對康巴人的各種仇殺及戰(zhàn)爭的書寫中,也體現在他們與自然環(huán)境的搏斗中。
綜上所述,上世紀80年代毫無疑問是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無論是長篇小說還是中短篇小說,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很多作家在這段時間里呈現出爆發(fā)式的創(chuàng)作高峰,為當代藏族漢語小說的發(fā)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增強了文學自信。綜觀上世紀80年代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可以這樣說,其創(chuàng)作成就是輝煌的,甚至是空前的。他們以開闊的視野和胸懷,在積極吸納藏族文化資源、漢文化資源和西方文化資源的同時,做出了寶貴的探索,不僅使西藏小說空前地擁有了豐厚的文化背景資源,也帶動了其他文學樣式共創(chuàng)藏族文學的繁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正是80年代的藏族小說家在小說藝術的探索過程中,打破了過去形成的許多不適當的條條框框,沖破了不少禁區(qū),為爭取藏族作家的自由創(chuàng)作空間做出了努力。進入21世紀,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經過90年代的短暫沉寂后又呈現出復蘇趨勢,萬瑪才旦、龍仁青、次仁羅布、江洋才讓、尹向東、洼西彭措逐漸成為值得期待的新一代藏族小說家。
回首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所走過的歷程,我們可以發(fā)現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從題材到形式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不僅從無到有地發(fā)生發(fā)展并繁榮從而開啟了藏族文學史的新篇章,不僅走在了全國其他少數民族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的前列,還為我國漢語小說的豐富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而且其中部分藏族漢語小說具有相當的先鋒性和探索性。顯然,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寫作傳統(tǒng)和寫作姿態(tài),以群體的力量匯入了中國當代漢語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成為一個值得討論并研究的寫作群體。就當代藏族漢語小說發(fā)生發(fā)展的主要原因來看,有以下因素:
一、各藏區(qū)相繼實行藏漢雙語教學及內地西藏班教育制度的推行,為藏族作家漢語小說的發(fā)生發(fā)展準備了讀者和作者。在藏區(qū)基礎教育中實行藏漢雙語教學是我國基礎教育的一項重要舉措;1978年針對藏區(qū)基礎教育較為薄弱的現狀,我國又采取了內地為西藏辦學的模式,這成為培養(yǎng)西藏人才的又一條重要途徑;同時,邊疆地區(qū)少數民族高考錄取政策的完善以及現代民族高等教育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客觀上促進了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作者群體和讀者群體的誕生。
目前,當代藏族文學創(chuàng)作主要有藏語、漢語、藏漢雙語及其他語言。其中,藏語小說和漢語小說是最常見的。由于漢語讀者群數量龐大,事實上,藏族漢語小說的讀者要比其它語言類別的藏族小說讀者要多得多,這也符合傳播學的規(guī)律。當代藏族漢語小說的產生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藏族作家對小說這一現代文類的理解,二是作者對漢語的操控能力到達一定程度才能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就漢語的操控能力來看,當藏區(qū)實行藏漢雙語教學和內地藏族班的教育模式以后,逐漸培養(yǎng)了小說這一文類的作者和讀者。藏族作家漢語小說大量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在時間上與藏區(qū)社會的現代進程并未同步,這也說明當代藏族作家掌握作為現代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需要一定時間的探索和積累。
二、當代藏族作家漢語小說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中國大陸出版界的繁榮狀況也是一個重要的催生因素。
就對西方文學作品的介紹和出版來看,粉碎“四人幫”后,我國出版界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出版了各種系列的西方文學書籍,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外國文藝叢書”、“拉丁美洲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漓江出版社)、“世界著名文學獎獲得者文庫”、“詩苑譯林”、“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法國20世紀叢書”、“現代西方文學譯叢”、“作家參考叢書”、“當代外國文學叢書”、“外國現代驚險小說選集”中的好多小說都是作家們的案頭必備。此外《世界文學》、《譯林》、《外國文學》這樣能及時刊載世界各國文學漢譯作品的最新前沿動態(tài)的文學雜志更是當代藏族作家經常訂閱的。
此外,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也在出版文學書籍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比如,青海人民出版社就曾經出版了一批高質量圖書,如1982年10月出版的美國詹姆斯·皮克林編的《世界小說100篇》,該書每篇小說后都有解讀;1998年出版一套《凡爾納科幻探險小說全集》(共35冊);此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很多重量級的藏文化類圖書。這些出版物打開了當時藏族作家們了解世界現代小說的窗口,擴大了藏族作家的視野并使他們從中獲得有益的營養(yǎng)。
同時,對于文藝理論著作的譯介也在一定程度上給藏族作家以啟示,如“外國文藝理論叢書”,“文藝探索書系”,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名著叢書”,三聯(lián)書店的“當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讀書文叢”、“文化生活譯叢”、“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等也相繼出版面世。在學習、借鑒和實踐中,當代藏族作家們的視野逐漸開闊,有的藏族作家的小說觀念也逐漸發(fā)生變化,逐漸開始思考小說的現代性問題并付之實踐,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出版界的盛況不僅開闊了藏族小說作者的閱讀視野和思考范圍,也讓小說讀者積累了更多的閱讀審美經驗,使得這些小說讀者在接受具有西方現代主義小說創(chuàng)作技法的作品時更加從容。
小說創(chuàng)作出來后,還得有可發(fā)表的園地。上世紀80年代正值中國大陸的文學雜志熱潮,各地文學雜志風起云涌。青海、四川、甘肅、云南的各級文聯(lián)也相應創(chuàng)辦了一些刊物作為藏族作家的發(fā)表園地:《西藏文學》、《拉薩河》、《民族文學》、《青海湖》、《貢嘎山》、《飛天》、《草地》、《格桑花》、《海南文學》,近年來又有《康巴文學》、《倒淌河》等文學雜志相繼創(chuàng)刊。
可見,上世紀80年代純文學期刊的大量創(chuàng)辦為當代藏族漢語小說作家準備了發(fā)表園地,而出版社又為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藏族漢語小說家出版小說集和長篇小說提供了更多的市場;文藝理論期刊的大量創(chuàng)刊并發(fā)行對小說的分析和批評為當代藏族作家提供了理論視野,而我國八十年代各級文聯(lián)的文學雜志的大量創(chuàng)刊發(fā)行、出版界對西方現代小說的譯介出版熱潮又為當代藏族作家提供了西方現代小說的國際視野。
三、援藏大學生和內地知識分子的支邊不僅促進了民族融合,還起到了加強文化交流的作用。民族融合帶來文化融合,客觀上也成為藏族當代漢語小說的一個重要催生條件。20世紀80年代,大批援藏大學生進入西藏,為西藏建設注入了新的力量;此外,青海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內地先后有幾次支邊到青海,分布在各大墾荒農場以及一些重要的工作崗位。此外,青海還有一些勞教基地,在這些勞教人員中,不乏各行業(yè)的能人,客觀上也會影響到當地的文化發(fā)展。就目前的資料來看,關于青海墾荒農場的敘述還缺少一些口述史的史料支撐,在互聯(lián)網上也僅能查到一些博客的書寫,一是東方竹子的《神秘的青海文人回遷大潮》5、《我在勞改農場二十年》6、《青海農場的發(fā)展》7。由此可見,援藏大學生、支邊知識青年、內遷的三線企業(yè)、墾荒農場的勞教人員,都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四、藏族作家直接到內地上大學,接受現代的大學教育,更會直接對一個作家的世界觀發(fā)生重要影響。在當代藏族作家的履歷表中,可以發(fā)現,這些作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都是大學畢業(yè)。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作家的產生有著較為直接的聯(lián)系,大學教育對作家世界觀的最終形成有著積極而直接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發(fā)表并出版小說集的作家中,無論是益希單增、降邊嘉措、益希卓瑪、多杰才旦、才旦,還是扎西達娃、色波,都在漢族地區(qū)有著較長時間的受教育經歷。60年代以后出生的藏族作家更是絕大部分接受了現代大學教育,而大學期間正是一個作家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重要形成時期。
綜上所述,由于諸多歷史和社會因素的客觀存在,為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提供了最適宜的土壤。作為中國當代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不僅躍出了藏族讀者群擴大到了漢語讀者群中,還走向了英語讀者:一批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經由漢語而譯成英語,受到英語讀者的關注。當代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創(chuàng)作雖然只有五十多年,但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中國當代漢語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釋:
1.范向東,《往事漫憶》,載《西藏文學》1994年第1期,第104頁。
2.《清晨》益希卓瑪在1980年出版的藏族作家第一部長篇兒童小說。
3.扎西達娃《西藏,隱秘歲月》,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4.扎西達娃《扎西達娃小說集》,中國出版集團、中華書局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465
350102vfkq.html。
6.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09523
-1.shtml。
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4457
130100ypqd.html。
責任編輯:次仁羅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