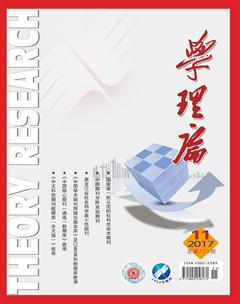斯賓諾莎實(shí)體論對(duì)生態(tài)文明理論構(gòu)建的啟示
王香凝 楊志華
摘 要:在本體論上,斯賓諾莎堅(jiān)持“實(shí)體一元論”,即以“實(shí)體”“神”“自然”三個(gè)概念來(lái)表述絕對(duì)存在,并用“實(shí)體”與“樣式”的關(guān)系分析了終極實(shí)在與萬(wàn)物的整體與分殊的關(guān)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笛卡爾開(kāi)創(chuàng)的心物二元論的二分,彌合了終極實(shí)在與萬(wàn)物的分裂。在中國(guó)推進(jìn)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過(guò)程中,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一元論”思想對(duì)于克服人類中心主義的人與自然的二分,以及非人類中心主義中的人的主體性的喪失的情況具有一定的啟示,可為中國(guó)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理論構(gòu)建提供參考借鑒。
關(guān)鍵詞:實(shí)體一元論;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tài)文明
中圖分類號(hào):B563.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589(2017)10-0084-03
改革開(kāi)放之后,隨著中國(guó)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加快,環(huán)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問(wèn)題也隨之凸顯。在這樣的事實(shí)背景下,我國(guó)提出了建設(shè)生態(tài)文明的戰(zhàn)略任務(wù)。然而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推進(jìn)過(guò)程中,面臨著種種困難。首先在理論界至今仍然存在很多爭(zhēng)論,這也就意味著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在理論層面仍需完善。在哲學(xué)史的長(zhǎng)河中,近代哲學(xué)家斯賓諾莎以其獨(dú)特的實(shí)體一元論,在當(dāng)時(shí)受到眾多爭(zhēng)議,但是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今天,其整體論的視角表述了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關(guān)系,不失為今天中國(guó)生態(tài)文明理論構(gòu)建值得參考的對(duì)象。
一、生態(tài)文明理論構(gòu)建亟須克服二元對(duì)立思維
環(huán)境問(wèn)題是當(dāng)今全球性的問(wèn)題,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話題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并從基督教對(duì)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批判性反思和生態(tài)神學(xué)改造開(kāi)始,開(kāi)啟了環(huán)境哲學(xué)的構(gòu)建,并發(fā)展出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兩種環(huán)境哲學(xué)綱領(lǐng)。
在1971年舉行的關(guān)于環(huán)境問(wèn)題的第一次哲學(xué)會(huì)議上,會(huì)議組織者布萊克斯通發(fā)表了“倫理學(xué)與生態(tài)學(xué)”一文,人類中心主義這一概念首次提出。他認(rèn)為,在迄今為止人類擁有的人權(quán)當(dāng)中,應(yīng)該包括擁有適宜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環(huán)境的權(quán)利。這種宜居的權(quán)利只是與人類切身相關(guān)的,對(duì)于其他非人類物種及周圍環(huán)境的保護(hù),僅僅出于人類自身的需求,因此這一提法被視為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諾頓繼承并發(fā)展了這一類型的理論,諾頓認(rèn)為在改造自然和制定環(huán)境保護(hù)政策時(shí),應(yīng)該以人的理性與價(jià)值為基礎(chǔ)和衡量標(biāo)準(zhǔn)。哈格洛夫則在人類理性的基礎(chǔ)上,加入了審美的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自然的審美價(jià)值是一種除了自然的工具價(jià)值之外的另一種內(nèi)在價(jià)值。當(dāng)然審美價(jià)值也是由人的審美需求而產(chǎn)生,但是由于人類具有審美的需求,故而對(duì)于保持自然環(huán)境的美也是人類的一種義務(wù)。到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擁護(hù)以人類價(jià)值為衡量自然的尺度的相關(guān)理論逐漸增多。
與人類中心主義截然相反的理論流派稱為非人類中心主義。相比于人類中心主義來(lái)說(shuō),非人類中心主義流派比較繁雜,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大類:感覺(jué)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以及生態(tài)中心主義。感覺(jué)中心主義包括動(dòng)物解放論和動(dòng)物權(quán)利論,其理論強(qiáng)調(diào)動(dòng)物不是作為人類可以隨意利用的工具而存在的,動(dòng)物自身?yè)碛衅浯嬖诘膬r(jià)值。用雷根的話說(shuō):“就像黑人不是為白人、婦女不是為男人而存在的一樣,動(dòng)物也不是為我們而存在的。它們擁有屬于它們自己的生命和價(jià)值。一種不能體現(xiàn)這種真理的倫理學(xué)將是蒼白無(wú)力的。”[1]173除雷根之外,這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還有:范伯格、斯坦利、古德洛維奇、辛格等。到了20世紀(jì)70-80年代,動(dòng)物的道德地位問(wèn)題曾經(jīng)成為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爭(zhēng)論的一個(gè)熱點(diǎn)問(wèn)題。生物中心主義認(rèn)為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所有生物都擁有內(nèi)在的善,因而所有有生命的物種都應(yīng)該獲得相應(yīng)的道德關(guān)懷。相比于感覺(jué)中心主義者來(lái)說(shuō),生物中心主義者把人類的道德關(guān)懷范圍由動(dòng)物擴(kuò)展到了所有有生命的物種之上。而生態(tài)中心主義,則再次擴(kuò)大了人類的道德關(guān)懷對(duì)象,從有生命的存在物擴(kuò)展到有生命的存在物及其生存環(huán)境,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這種觀點(diǎn)把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作為理論建構(gòu)的基礎(chǔ),認(rèn)為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具有內(nèi)在價(jià)值,并強(qiáng)調(diào)從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出發(fā),來(lái)看待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認(rèn)為對(duì)于環(huán)境危機(jī)的解除僅僅依靠人類的理性和法治是不夠的,還需要人類情感的延伸。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利奧波德和羅爾斯頓等。
西方這些關(guān)于環(huán)境的思想,除了生態(tài)神學(xué)之外,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兩種派別都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有所體現(xiàn),并在中國(guó)二十多年環(huán)境哲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中不斷對(duì)話交鋒,雙方的研究也得到進(jìn)一步深化。無(wú)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其思想都具有各自優(yōu)點(diǎn),但也存在某些缺陷。簡(jiǎn)單來(lái)說(shuō),人類中心主義從人的主體性、人的利益出發(fā),認(rèn)為保護(hù)環(huán)境是為了保護(hù)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這種同心圓主義有利于激發(fā)人們的行動(dòng)熱情,但最終無(wú)法限制人類對(duì)環(huán)境的無(wú)休止的剝削;非人類中心主義擴(kuò)大了道德主體范圍,通過(guò)論證其他道德主體的內(nèi)在價(jià)值和天賦權(quán)利而賦予了人類保護(hù)環(huán)境的道德義務(wù),這是一種帶有平等主義色彩的強(qiáng)勢(shì)限制,可能會(huì)導(dǎo)致人類對(duì)自然資源合理利用的不恰當(dāng)限制。在大力推進(jìn)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當(dāng)今中國(guó),無(wú)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感覺(jué)都不能滿足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在哲學(xué)層面的理論構(gòu)建,難以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實(shí)踐工作做出方向指導(dǎo)和理論論證,有必要對(duì)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提供新的探索。在這個(gè)新理論的探索過(guò)程中,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一元論思想可以作為一種借鑒的理論資源。
二、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一元論思想
雖然“實(shí)體”這一概念早在古希臘時(shí)期就已經(jīng)提出,并且經(jīng)過(guò)了長(zhǎng)時(shí)間的演化,具有不同的意義。而在斯賓諾莎的思想中,“實(shí)體”意味著作為存在的最高統(tǒng)一體,并且在《倫理學(xué)》這一著作中,斯賓諾莎把“神”“自然”與“實(shí)體”三個(gè)概念一同使用,這三個(gè)概念可以說(shuō)是斯賓諾莎對(duì)于這一最高統(tǒng)一體的不同表述。
在《倫理學(xué)》的開(kāi)篇的界說(shuō)(三)中,對(duì)實(shí)體做了界定,“實(shí)體(Substantia),我理解為在自身內(nèi)并通過(guò)自身而被認(rèn)識(shí)的東西。換言之,形成實(shí)體的概念,可以無(wú)須借助于他物的概念。”[2]并且在之后的表述中又對(duì)實(shí)體做了進(jìn)一步的表述:“神是唯一的,這就是說(shuō)(據(jù)界說(shuō)六),宇宙間只有一個(gè)實(shí)體,而且這個(gè)實(shí)體是絕對(duì)無(wú)限的……”[2]“一切存在的東西,都存在于神之內(nèi),沒(méi)有神就不能有任何東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東西被認(rèn)識(shí)。”[2]從這樣的表述可以看出,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不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個(gè)體”,也不是柏拉圖所說(shuō)的屬或種,而是唯一的包含萬(wàn)事萬(wàn)物的絕對(duì)統(tǒng)一體。“通過(guò)自身而被認(rèn)識(shí)”也就意味著實(shí)體是獨(dú)立自存的,唯一的,無(wú)限的,不變的,自因的,獨(dú)立的,并且只與自身保持同一性的整體。因?yàn)槿绻皇仟?dú)立自存的,就意味著它與其他事物有所聯(lián)系,而這種聯(lián)系使得實(shí)體不是通過(guò)自身被認(rèn)識(shí),而是通過(guò)他物而被認(rèn)識(shí)的。如果不是自因的,那么也就不符合通過(guò)自身被認(rèn)識(shí),而是通過(guò)他者被認(rèn)識(shí)。在這些特征中,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的獨(dú)立自存的唯一性是其區(qū)別于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的重要特點(diǎn)之一,并且斯賓諾莎就是用實(shí)體的一元論解決了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中存在的主客二分的問(wèn)題。
斯賓諾莎所說(shuō)的“神”,是“實(shí)體”的另一種表述,這種“神”的思想產(chǎn)生,是受到其青年時(shí)期信奉猶太教的影響。雖然斯賓諾莎因?yàn)閷?duì)猶太教的質(zhì)疑和批判被逐出猶太教系統(tǒng),但是對(duì)于神的信仰可以說(shuō)是深深地影響了其理論的構(gòu)建。但斯賓諾莎所說(shuō)的神,并非宗教中的那種人格的神,因?yàn)樽诮讨械纳系凼浅饺酥獾模c人不同的一種存在,是萬(wàn)物形成的外因;而斯賓諾莎的神是寓于萬(wàn)物之中,是萬(wàn)物存在發(fā)展的最根本的基礎(chǔ),是萬(wàn)物形成的內(nèi)因。這種觀點(diǎn)被稱為“泛神論”,即神在萬(wàn)物之中,與萬(wàn)物相同一,神就是自然本身。
而斯賓諾莎所說(shuō)的自然,也并非只是物質(zhì)世界的萬(wàn)事萬(wàn)物,而是“實(shí)體”的另一種表述方式。受到布魯諾的影響,斯賓諾莎把自然分為“能生的自然”和“被生的自然”,即斯賓諾莎的“自然”這一概念是統(tǒng)一的整體的實(shí)體以及由實(shí)體而產(chǎn)生的自然的統(tǒng)一。也就是說(shuō),斯賓諾莎所認(rèn)為的自然,從個(gè)體角度來(lái)看,是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變化的個(gè)體,同時(shí)從整體的角度看,是一個(gè)永恒的整體當(dāng)中的統(tǒng)一體的存在,即自然是系統(tǒng)的聯(lián)系的統(tǒng)一體的存在。
在實(shí)體一元論的本體論基礎(chǔ)上,斯賓諾莎從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提出了“屬性”與“樣式”兩個(gè)范疇。斯賓諾莎對(duì)于屬性的定義是:“屬性(attributus),我理解為由知性看來(lái)是構(gòu)成實(shí)體的本質(zhì)的東西,”[2]也就是說(shuō),屬性是實(shí)體所固有的,是實(shí)體的表現(xiàn)形式,而這種表現(xiàn)形式是從人類的認(rèn)知出發(fā)的對(duì)實(shí)體的認(rèn)識(shí)。斯賓諾莎認(rèn)為,實(shí)體具有無(wú)數(shù)個(gè)屬性,但是由于人類的認(rèn)知方式有限,從而在實(shí)體對(duì)人類的表現(xiàn)方式來(lái)看,只有思維和廣延兩種屬性。而屬性又作為實(shí)體的本質(zhì)規(guī)定,故而與實(shí)體一樣是永恒的,思維與廣延的關(guān)系則是平行而統(tǒng)一的,即二者在互不干擾的同時(shí)又統(tǒng)一于實(shí)體。在這里,斯賓諾莎是把笛卡爾的思維與廣延的兩種實(shí)體,降格為同一實(shí)體的兩種屬性,從而化解了由笛卡爾引起的主客二分的問(wèn)題。
接下來(lái),斯賓諾莎對(duì)樣式的界定是:“樣式(modus),我理解為實(shí)體的分殊,亦即在他物內(nèi)通過(guò)他物而被認(rèn)識(shí)的東西”[2]。也就是說(shuō),相對(duì)于實(shí)體的永恒、唯一來(lái)說(shuō),樣式則是變化的、多樣的,是通過(guò)屬性對(duì)于實(shí)體的分殊,即具有廣延的具體存在物以及被思維出來(lái)的各種主觀思想、客觀規(guī)律。由于樣式是實(shí)體的分殊,并且樣式是通過(guò)他物而被認(rèn)識(shí)的,這也就說(shuō)明,樣式每一個(gè)是與其他樣式相互支持相互限制的,是有限的,而與樣式相比的實(shí)體則是無(wú)限的。并且由于樣式是實(shí)體的分殊,所以樣式同樣也是實(shí)體的一部分。換句話說(shuō),對(duì)于每一種樣式的認(rèn)識(shí)可以有兩個(gè)角度,一種是通過(guò)與其他樣式的區(qū)分而對(duì)某一樣式產(chǎn)生認(rèn)識(shí),另一種則是站在實(shí)體的高度,即整體的普遍聯(lián)系的高度,對(duì)于某一樣式進(jìn)行認(rèn)識(shí)。在斯賓諾莎看來(lái),后一種才是對(duì)于樣式的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如果沒(méi)有實(shí)體,樣式就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認(rèn)識(shí)。所以樣式只能存在于神之內(nèi),只能借神而被理解”[2]。也就是說(shuō),樣式還是要依靠實(shí)體,沒(méi)有實(shí)體,樣式也就不復(fù)存在,更不能被認(rèn)識(shí)。
三、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一元論對(duì)中國(guó)生態(tài)文明理論構(gòu)建的啟示
雖然斯賓諾莎以實(shí)體為核心的本體論思想帶有“泛神論”的神秘主義色彩,但是,其“實(shí)體一元論”是對(duì)笛卡爾心物二元論存在問(wèn)題的一種解決方式,對(duì)于我們克服人與自然的對(duì)立也不無(wú)啟發(fā)。
如果把斯賓諾莎的“自然”本體論思想與現(xiàn)代生態(tài)學(xué)這一科學(xué)理論相聯(lián)系,去除其“泛神論”的神秘主義色彩的話,那么,就可以把整個(gè)作為生態(tài)系統(tǒng)而存在的自然,與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意義上的“自然”相類比,從而用生態(tài)系統(tǒng)這個(gè)統(tǒng)一的整體來(lái)克服人與自然的二分的問(wèn)題。
具體來(lái)說(shuō),從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看,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即是“自然”“實(shí)體”的樣態(tài),在本質(zhì)上,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實(shí)體的分殊和表現(xiàn),是與實(shí)體一致的。也就是說(shuō),如果脫離超驗(yàn)意義上的自然實(shí)體,從可言說(shuō)的有限層面來(lái)看,生態(tài)系統(tǒng)才是唯一自因的,無(wú)論人類如何發(fā)展,即使某一天人類滅絕,生態(tài)系統(tǒng)依然存在,并且正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時(shí)間的演化,才產(chǎn)生了萬(wàn)物,產(chǎn)生了人類這一物種。這樣人類就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而成了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一員,是與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融為一體的。人不在作為生態(tài)系統(tǒng)而存在自然之外,自然也不在人之外,人類在其自身中就擁有自然的因素,人作為理性的人的同時(shí)也是自然的人,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包括人類自身均離不開(kāi)自然,人類與作為生態(tài)系統(tǒng)而存在的自然相互交融。
從斯賓諾莎的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來(lái)看,斯賓諾莎認(rèn)為人對(duì)于世界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要源于“實(shí)體”,也就是說(shuō)要從世界是一個(gè)整體的統(tǒng)一體的角度,來(lái)對(duì)世界的萬(wàn)事萬(wàn)物進(jìn)行認(rèn)識(shí)。而把斯賓諾莎的這種認(rèn)識(shí)論的思想與生態(tài)學(xué)思想相結(jié)合,也就意味著,人類要從生態(tài)系統(tǒng)整體的角度去認(rèn)識(shí)自然。這種思維的方式與利奧波德所提出的“像山那樣思考”的思維相契合,即把整個(gè)人類與生態(tài)系統(tǒng)看作是一種整體的、聯(lián)系的共同體。而人類的實(shí)踐活動(dòng)最終也是要按照是否是維持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和諧、穩(wěn)定、美麗為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所以人類對(duì)于世界的認(rèn)識(shí)應(yīng)該是源于從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角度出發(fā),來(lái)認(rèn)識(shí)世界萬(wàn)物。
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gè)層面,則還是停留在利奧波德式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范疇內(nèi)。斯賓諾莎對(duì)于今天生態(tài)文明理論構(gòu)建,具有更深層的啟示。
首先,在斯賓諾莎談?wù)摗白匀弧钡臅r(shí)候,已經(jīng)把自然分成了“能生的自然”和“被生的自然”。按照這個(gè)思路,則可以把自然分為在實(shí)體層面的“能生的自然”,即生態(tài)系統(tǒng),和在具體的物質(zhì)層面的“被生的自然”,即自然資源和自然環(huán)境。“能生的自然”與“被生的自然”的區(qū)分,生態(tài)系統(tǒng)與資源和環(huán)境的區(qū)分,對(duì)于我們?cè)谏鷳B(tài)倫理上處理人與自然的道德關(guān)系,具有特別的意義。也就是說(shuō),對(duì)于“能生的自然”即生態(tài)系統(tǒng),人類不是中心,人類應(yīng)該對(duì)之心存敬畏,這是生態(tài)中心主義所強(qiáng)調(diào)的。而對(duì)于“被生的自然”,即生態(tài)系統(tǒng)孕育而成的自然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完全可以為人類合理利用,則是人類中心主義所強(qiáng)調(diào)的。
其次,在斯賓諾莎的認(rèn)識(shí)論中,只是認(rèn)為實(shí)體是高于個(gè)人的,并不意味著物質(zhì)化的自然要高于人類。因?yàn)槿祟愐矒碛袑?shí)體所擁有的思維和廣延的屬性。而物質(zhì)自然是通過(guò)人類的思維和廣延的屬性作用下對(duì)于實(shí)體的分有。所以人類也可以通過(guò)其思維和廣延的屬性,對(duì)于物質(zhì)的自然進(jìn)行利用。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維持人類生存發(fā)展的資源、能源以及人類所生存的環(huán)境,都是在以人類所具有的本質(zhì)屬性——思維和廣延——下從實(shí)體中產(chǎn)生的,并且這些具體物質(zhì)性的資源、環(huán)境作為樣式的一種,是借助于他者來(lái)界定自身。也就是說(shuō),有了人類才有與人類相對(duì)應(yīng)的資源、環(huán)境。資源的產(chǎn)生是根據(jù)人類的科學(xué)技術(shù)水平的變化而變化的,例如石油這種物質(zhì)成為人類發(fā)展的一種資源,是在19世紀(jì)中期石油蒸餾工藝的發(fā)明之后開(kāi)始的,而石油的存在則有上億年的歷史。如果沒(méi)有人類的產(chǎn)生以及人類技術(shù)的發(fā)展,石油就不會(huì)作為一種資源而只是一種物質(zhì)而存在于地表之下,就像其他人類目前還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的物質(zhì)一樣。正是因?yàn)闃邮降倪@種相對(duì)性,使得資源本身就具有了與人類聯(lián)系,維持人類發(fā)展的一種屬性。環(huán)境也是同樣。所以從這一角度來(lái)看,人類對(duì)于資源的開(kāi)發(fā)是合理的。但是與此同時(shí),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論認(rèn)為,樣式是實(shí)體的分有,沒(méi)有實(shí)體,樣式也就不會(huì)存在。同樣,無(wú)論是相對(duì)于人類來(lái)說(shuō)的資源或是環(huán)境,其本質(zhì)都是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變得不適合于人類這個(gè)物種繼續(xù)存在,那么與人類相對(duì)而言的資源與環(huán)境也就不復(fù)存在,但這并不是說(shuō)這種物質(zhì)不存在,而是說(shuō)作為這種相對(duì)于人類來(lái)說(shuō)的資源不復(fù)存在。所以對(duì)于環(huán)境以及資源的利用也要從本質(zhì)出發(fā),即從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這一整體的角度出發(fā)。只有對(duì)于環(huán)境和資源的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才能更好地利用資源和環(huán)境,得以保證人類更好的發(fā)展。
總之,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一元論,從本體論和認(rèn)識(shí)論的角度,使我們可以從雙重的角度來(lái)審視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即把生態(tài)系統(tǒng)看作是“實(shí)體”,而把具體的物質(zhì)化的資源和環(huán)境看作是通過(guò)人類的屬性分有“實(shí)體”的“樣式”。根據(jù)斯賓諾莎關(guān)于實(shí)體的理論,不但能夠解決人類中心主義中存在的人與自然的二分,也能很好解決在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中人面對(duì)自然的主體地位的喪失。在這種理論指導(dǎo)下,人類既可以合理利用自然,也要求在對(duì)自然的利用程度上較好地做到適度。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一元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guó)生態(tài)文明理論構(gòu)建的理論源泉之一。
參考文獻(xiàn):
[1]納什.大自然的權(quán)利[M].楊通進(jìn),譯.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
[2]斯賓諾莎.倫理學(xué)[M].賀麟,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