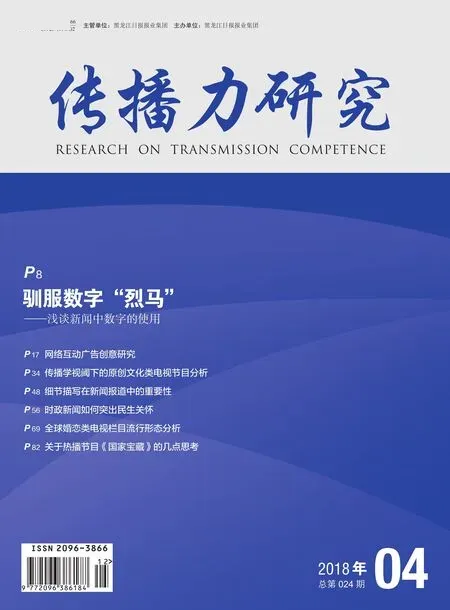微信朋友圈用戶認知與行為的特征分析
近年來,隨著微信的普及,有關微信與微信朋友圈的研究很多,但是從媒介場景的視角對微信朋友圈的研究卻寥寥無幾。微信朋友圈作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生事物,擁有不同于以往媒介產品的信息系統,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一個新場景。在這個新場景中,微信朋友圈的用戶會產生不同于其他場景的新認知與新行為。
一、微信朋友圈的場景特征
(一)混合人群集聚
微信朋友圈最初是在熟人網絡的基礎上創建的,但隨著學習、工作與生活等場景的逐漸融合,用戶的“圈內人”便包含了家人、朋友、同學、同事等群體。這些群體具有不同的人口統計學特征,擁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經濟水平與社會地位。微信朋友圈將這些本該分隔在不同地方的人群帶到了相同的地方,打破了物質地點與社會場景的聯系。
(二)私人性與公開性交替
微信朋友圈是一個公開的私人日記。微信朋友圈中的“曬客”(微信朋友圈的信息發布者)在微信朋友圈這個新場景中,基于分享信息、宣泄情緒、展示自我等動機,“曬”出自己的日常瑣事與情感獨白,將自己的個人私生活公開化。“曬客”所“曬”內容雖然源于個人私生活,但在微信朋友圈這個新場景中,還存在著“曬客”的觀眾,即“看客”(這里所指的“看客”并非魯迅先生筆下麻木的圍觀者,而是與微信朋友圈信息發布者相對的信息接受者),因此“曬客”“曬”出的信息內容并不完全具有私人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能公之于眾的性質。
二、微信朋友圈“看客”新認知的特征
(一)以偏概全
微信朋友圈中的“看客”基于特定動機,如窺探“圈內人”的日常生活,維系與“圈內人”的人際關系,舒緩自身的壓力與負擔,滿足自我的信息需求,不知疲倦地利用碎片化時間瀏覽微信朋友圈。“看客”在瀏覽微信朋友圈時,會根據微信朋友圈的特定信息內容去認知“曬客”或客觀世界。比如,“看客”會根據“曬客”轉發的文章類型去判斷他/她是什么素質及階層,根據“曬客”發自拍的頻率去判斷他/她的自戀程度,根據微信朋友圈內容去揣測“圈內人”的性格與喜好。由于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內容是有限的,所反映的只是“曬客”或者客觀世界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看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曬客”或者客觀世界的認知是片面的。
(二)補充客觀現實卻不同于客觀現實
微信朋友圈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親身參與”對于經歷人物和社會事件的重要程度,用戶能夠在微信朋友圈中了解到以往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密切接觸的人或事。微信朋友圈的用戶可能不會主動聯系微信通訊錄上的大部分好友,但是卻會主動或被動地觀看其在微信朋友圈發布的信息內容,并在此基礎上與之建立長期關系。由于“看客”的存在,“曬客”會對“看客”有所顧忌,會根據預期效果對其所“曬”內容進行修飾,因此,“曬客”在微信朋友圈“曬”出的內容并不一定是其生活最真實的反映。
三、微信朋友圈“曬客”與“看客”新行為的特征
(一)“曬客”的“線上”新行為的特征——前臺與后臺行為的模糊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書中提出,人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表演。我們每一個人就像演員一樣,在某一特定場景下,根據特定的角色要求在舞臺上表演給觀眾看。當表演結束,演員回到后臺以后才展現出真實面目。“曬客”在微信朋友圈的傳播行為即是一種前臺表演行為,“曬”出的信息內容看似是有關后臺行為的,但是由于“看客”的存在,“曬客”便會出于維系人際關系、提升個人形象等目的進行表演,從而具備了前臺行為的特征。
(二)“看客”“線下”新行為的特征——擬態環境的環境化
“曬客”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信息時,根據預期“看客”對自己形成的印象,對其所“曬”內容進行修飾。“看客”在瀏覽微信朋友圈時,會根據“曬客”在微信朋友圈構造的虛擬世界去認知客觀世界,并根據認知結果在客觀世界中采取行動,在微信朋友圈場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看客”將會難以區分客觀世界與微信朋友圈構造出的虛擬世界的區別。這是日本學者指出的“擬態環境的環境化”。
四、結語
微信朋友圈是一個由“曬客”與“看客”共同組成的場景。微信朋友圈的用戶可以同是“曬客”與“看客”,單一承擔“曬客”或“看客”角色的用戶很少。作為客觀現實的補充,微信朋友圈使用戶的“線下”關系得到“線上”延伸,反過來,用戶在微信朋友圈中形成的“線上”認知又會影響用戶的“線下”行為。用戶需要警惕微信朋友圈的虛擬性,做到趨利避害,并時刻牢記,微信朋友圈在本質上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表演舞臺,其中的信息內容可看但不可全信,不能單純依照片面的內容去評價“曬客”和認知客觀世界,應在“親身參與”的基礎上辯證地對待“圈內人”或者客觀世界。
[1]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2]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第2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張海燕.電子媒介、場景與社會行為[D].蘭州大學,2007.
[5]董晨宇,丁依然.當戈夫曼遇到互聯網——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與表演[J].新聞與寫作,2018(1):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