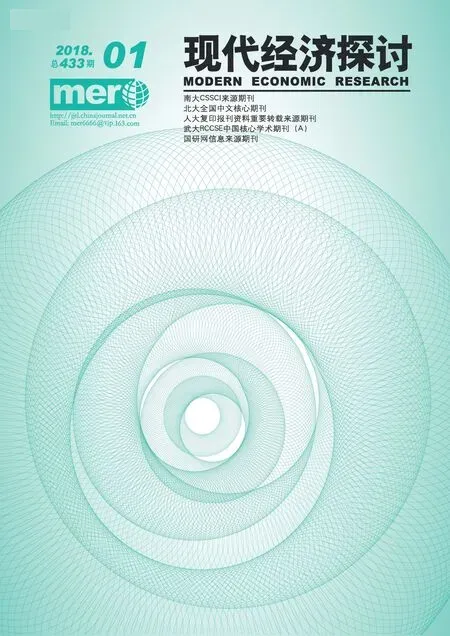跨國并購是否有助于提高企業動態生產效率:“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證據*
彭 薇
一、 引 言
“經濟帶”是經濟要素在一定地理區域內不斷聚集和擴散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空間形態。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2015年3月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標志著具有戰略意義的“一帶一路”構想進入了全面推進實施的階段。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帶一路”經濟帶將是一個從貿易投資便利化到產業產能合作區,從產業產能合作區到區域基礎設施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態演進過程。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到要深入實施《中國制造2025》,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和基礎能力為重點,推進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深度融合,促進制造業朝高端、智能、綠色、服務方向發展,培育制造業競爭新優勢。“中國制造2025”與“一帶一路”戰略的疊加,是我國淘汰能耗大和效率低的產業,提高增長質量效益,擴展發展空間,形成產業新動能的有益契機。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推進,我國企業全球發展意識不斷加強,主動走出國門配置資源和拓展市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快速發展。圖1顯示了我國近15年來對外投資的發展態勢。截至201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456.7億美元,同比增長近20%。同期,有2.02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共設立境外企業3.08萬家。這些境外投資企業廣泛分布在全球188個國家及地區。2015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了4萬億美元。整個“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全球占比保持逐年遞增的態勢,2011-2015年全球整體占比分別為4.8%、6.7%、8.2%、9.3%和9.9%。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同期吸引外資水平,較同年吸引外資高出100.7億美元,實現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中國開始步入資本凈輸出國行列。

圖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
數據來源:《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劃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分為跨境并購投資和綠地投資。《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5年全球跨境并購流向最大的行業是制造業,中國對外并購投資流向最大的行業也是制造業。2015年中國跨境并購在發達經濟體的并購額占比67%,同比上升了近8%。2015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并購項目101起,并購金額92.3億美元,占并購總額的17%。從圖2可以看到,從投資方式上來看,綠地投資一直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2009年,綠地投資額達到了1091億美元,而跨國并購僅為234億美元。到了2015年,綠地投資下降為594億美元,而跨國并購上升到436億美元。雖然綠地投資仍大于跨國并購數額,但兩者差距大幅減小。跨國并購近年來保持了穩中有升的態勢。

圖2 2009-2015年中國跨國并購與綠地投資情況
數據來源:《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
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競爭環境,越來越多的制造業企業積極迎合“中國制造2025”戰略部署,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平臺,選擇采用跨國并購方式“走出去”,通過“走出去”促進企業的效率升級與提質增量。那么,我們不免想要探尋,為什么國內企業越來越偏好于跨國并購?進一步地,跨國并購這種方式是否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促進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在實施對外并購的企業當中,對投資區位的選擇是否會有差異?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差異是否會影響企業的并購選擇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程度?這些正是本文想要嘗試解決的問題。
二、 文獻回顧
本文嘗試厘清企業跨國并購選擇與企業生產效率之間的動態關系。相關研究大致包含新興市場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企業進行東道國方式選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的影響研究等三個主要方面。Wells(1977)在《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新興市場正是因為具備了小市場需要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生產技術,具有服務于國外同一種族團體需要的優勢以及較低的成本優勢均促進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Wells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強調了發展中國家使用“降級技術”生產發達國家成熟產品的行為,但對當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日趨增長以及發展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缺乏解釋力。隨后有大量文獻從新興國家國際化擴張的“第一浪潮”(Lall,1983;Lecraw,1977)、“第二浪潮”(Lecraw,1993;Tolentino,1993)、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Dunnin, kim & Parkc,2010;Sauvant et al.,2009),政府促進(Luo et al.,2010)、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投資行為比較(Bonaglia et al.,2007;Buckley et al.,2008)等不同視角來分析新興市場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從而進一步豐富充實了對新興市場國家海外投資的研究。
第二類相關文獻是關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選擇的研究。大量文獻討論了綠地投資與跨國并購的優劣與特點。與綠地投資相比,跨國并購涉及東道國企業現有資產產權的轉移,從長期看對于目標企業的追加投資可以增加東道國的資產總量(武銳和黃方亮,2010)。對跨國企業來說,可以很快適應當地的管理習慣、文化習俗,加速業務發展(皮建才等,2016;林莎等,2014)。實證研究方面,胡麥秀和薛求知(2007)從技術與環境差異而形成的創新性壁壘和差異性壁壘的視角,利用一個雙寡頭模型分析了企業跨越上述兩種差異的跨國投資選擇。李善民和李昶(2013)通過構建一個三階段實物期權模型,分析投資項目建設時間、需求增長漂移率以及需求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對企業跨國并購進入的影響。
第三類文獻是關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效率的研究。國內目前有關跨國公司績效的研究,主要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楊平麗和曹子瑛(2017)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相關數據檢驗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資產利潤率的影響,發現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上顯著降低了企業利潤率,無論企業投資于單個或多個國家(或地區)。薛安偉(2017)關注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報酬率和投入資本回報等三大財務指標,發現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產生了異質性影響。毛其淋和許家云(2016)利用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數據,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加成率的影響及作用機理,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顯著提高了企業加成率,其中投資高收入國家對企業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要明顯大于投資中低收入國家。
本文嘗試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研究對象設計上強調“跨國并購”。如前所述,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方式主要有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近年來,跨國并購無論是數量還是并購金額都快速增長。因此,本文主要以企業跨國并購行為作為研究對象。二是在研究內容設計上強調“生產效率”。本文重點關注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生產率增長是經濟長期增長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對企業而言,生產率增長是企業保持長期競爭力的源泉。企業選擇是否進行跨國并購除了考慮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外,同時會關注是否提升企業生產效率。這對于追求學習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企業而言尤其重要。三是對效率檢驗的方法設計上強調“動態與異質”。利用滯后數據從靜態到動態時間變化的視角考察跨國并購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同時,考慮到處于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出于不同投資目的的企業進行跨國投資活動可能會對企業產生異質性影響,研究中我們將考察行業效應、地區效應以及企業屬性效應的差異化影響。
三、 研究思路、方法設計與數據描述
1.研究思路與方法
計量經濟學中的“處理效應”,指的是評估某一項目或政策實施后對研究主體產生的影響,此類研究亦被稱為“項目效應評估”。Heckman & Ichimura(1997)提出用基于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來處理類似工作培訓的這種“項目效應評估”。這種績效評估采用了一個兩階段評估方法:首先估計一個主體參與項目的可能性,接著將經典的匹配方法運用于預估的可能值中。本研究將根據Heckman & Ichimura(1997)的方法,將PSM-DID法運用于企業跨國并購對企業動態績效的影響評估中。具體思路如下。
(1) 對樣本企業進行分組,以確定“實驗組”與“對照組”。考慮企業跨國并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一個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直接對比實驗組與對照組未來績效狀況。值得注意的是,是否選擇進行跨國并購是企業的一種自我選擇的結果,由于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初始條件不相同而不可避免地存在“選擇偏差”。因此,本文真正感興趣的問題是,實驗組企業的未來績效是否會比這些企業在進行并購之前的績效更高。參照Rubin(1974)的研究提出“反事實框架”,即設立一個是否參與跨國并購的虛擬變量,表示為M&A。如果M&A=1,表示企業參與了跨國并購,而M&A=0則表示沒有參與。同時,設立一個參與時間點的時間虛擬變量time。如果time=1,表示并購之后的期間,而time=0則表示并購之前的時期。
(2) 傾向得分匹配。假設企業未來績效以EFF表示,則可以得到:
EFFi=(1-M&Ai)EFF0i+M&Ai*EFF1i=EFF0i+(EFF0i-EFF1i)M&Ai
(1)
進一步,由于處理效應EFF0i-EFF1i是一個隨機變量,我們關心其期望值,得到全體樣本的ATE“平均處理效應”以及僅考慮進行跨國并購企業的ATT“參與者平均處理效應”,得到:
(2)
其中,E(EFF1i|M&A=1)為實驗組企業i的績效,E(EFF0i|M&A=1)代表假如實驗組企業i不進行跨國并購投資時這一“反事實”情況下的企業績效。
由于“反事實”情況下的期望值不可觀測,于是利用傾向評分匹配的方法在對照組中尋找企業與實驗組企業i最為相似,但是沒有進行過跨國并購的企業j,并用該企業同期效率E(EFF0j|M&A=0)近似代替企業i沒有進行跨國投資的效率E(EFF0i|M&A=1)。得到:
ATT=E(EFF1i|M&A=1)-E(EFF0i|M&A=1)
=E(EFF1i|M&A=1)-E(EFF0j|M&A=0)
(3)
這種做法也體現了匹配估計的基本思想,即假設企業i屬于實驗組,找到對照組的企業j,使得企業i和企業j的可測變量值盡可能匹配。傾向得分匹配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選擇協變量xi。企業是否進行跨國并購以及企業的生產績效還會受到一些可觀測特征值的影響,比如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本密集度等指標。借鑒楊亞平和吳祝紅(2015)、喬晶和胡兵(2015)等做法設定變量。
第二步:擬合傾向得分。以LOGIT回歸方法估計傾向得分。該得分表示在控制了匹配變量之后企業進行跨國并購的概率。
第三步:進行傾向得分匹配與平衡檢驗。進行傾向得分匹配有多種匹配方法,本研究采用目前使用較為廣泛的鄰近匹配法進行匹配,并進行匹配的平衡性檢驗。如果標準差不超過10%,即診斷為匹配平衡;否則通過重新計算傾向得分、選擇其他匹配方法的方式進行調整,直到檢驗平衡。
(3) 倍差法檢驗。如前所述,由于企業i不進行跨國并購投資時這一“反事實”情況下企業績效的期望值不可觀測,我們在倍差法中可以采用對照組企業的動態績效來代替“反事實”動態績效,即用E(EFF0j|M&A=0)代替。
依照二階差分模型的基本框架,我們的擬自然實驗可以用如下模型表示:
EFFit=β0+β1·OFDIi+β2·timet+β3·M&Ai·timet+φi+γi+εit
(4)
其中,φi和γi分別代表地區固定效應和行業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EFFit、M&Ai、timet與前文解釋相同。
根據式(3)及式(4),實驗組企業在跨國并購前后的績效為β0+β1和β0+β1+β2+β3。因此,實驗組企業并購前后績效的變化為E(EFF1i|M&A=1)=β2+β3。同樣地,對照組企業在跨國并購前后的績效分別為β0和β0+β2。因此,對照組企業績效的變化為E(EFF0j|M&A=0)=β2。由此可知,式(4)中M&Ai·timet的交乘項系數β3的值即為我們關注的ATT值。如果β3>0,表示跨國并購前后實驗組企業的績效增加大于對照組企業。
進一步地,企業績效不僅與企業是否進行跨國并購有關,同時還與企業的特征變量以及其他影響企業并購行為的控制變量有關。因此,式(4)可以寫為:
EFFit=β0+β1·M&Ai+β2·timet+β3·M&Ai·timet+∑θi·Xi+φi+γi+εit
(5)
其中,Xi表示影響企業跨國并購的控制變量,θi表示變量系數。雙重差分估計的一個顯著優點就在于它可以對諸如實驗組與對照組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或者是具有不同企業屬性等不可觀測的組間差異進行控制。
2.數據來源及統計性描述
(1) 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10-2015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跨國并購事件為研究對象。上市公司一般規模較大,屬于行業中比較領先的企業。在資金、技術、管理等多方面都有優勢,具備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跨國并購的比例也比較高。2010-2015年這一時期不僅是我國實施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戰略期間,也是我國“一帶一路”戰略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以這一期間為研究時間對象,可以較好地檢驗“一帶一路”戰略在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從而達到擴大市場、提高競爭力、提質增效的實施效果。上市公司跨國并購的信息來自Thomson One數據庫,并將相關數據資料與BVD-Zephyr并購數據庫、WIND、同花順數據庫進行核對整理,以確保數據的有效性和完整性。我們在篩選跨國并購實驗組企業樣本時,參照以下四個方面的標準:一是并購方是在中國大陸的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二是被并購企業是中國大陸以外的企業,包括港澳臺企業在內;三是跨國并購交易已經完成,并能夠對交易結果進行界定,即交易成功或失敗;四是在2010年沒有進行跨國,而在2011-2015年進行了跨國并購的企業。之后,我們再對相關樣本進行第二次篩選,剔除了目標國家為開曼群島和英屬維京群島的并購案例;去除重復的跨國并購案例;還剔除并購交易金額低于100萬美元的交易數據。根據以上條件,最終本文獲得113個跨國并購事件。從并購完成的時間來看,2011-2015年分別有12家、23家、24家、22家以及32家企業。2015年從事海外并購的企業數量有大幅增加。從并購企業的所有權分布來看,有33家企業是國有企業,有5家外資企業,其余均為民營企業。從并購企業所屬區域來看,62%屬于東部,19%屬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及東北部地區共占19%。
對照組企業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所有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我們在篩選對照組企業樣本時,有兩個方面的標準:一是在2010-2015年均未進行并購活動;二是企業各年度各項數據沒有缺失。根據以上條件,最終獲得1321個對照組企業。
以上所有并購公司以及對照組企業的相關財務指標和特征數據均從WIND數據庫中獲得。本文的數據處理和分析運用Stata13、DEAP2.1及Excel軟件。
(2) 變量的設定。本文以代表生產績效的全要素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分為企業特征變量與其他控制變量兩大類,其中企業特征變量包括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本密集度、企業利潤、企業屬性等;其他控制變量包括地區虛擬變量以及兩倍數的行業虛擬變量來控制企業因所處地區以及所處行業不同而可能存在的差異。變量含義及度量方法見表1。
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全要素生產率(TFP),是“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的體現。它主要衡量的是總產出與總投入量之間的比值關系,是產出增加中除去勞動和資本后剩下的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部分,因此也通常被認為是衡量生產技術進步的指標。Tinberger(1942)基于Cobb-Douglas生產函數確立了一個用來表示生產率發展水平的時間趨勢變量,索洛在1952年首次提出利用索洛余值法度量全要素生產率。之后,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廣泛開展起來。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利用動態面板數據進行估計,OP模型、LP模型、隨機前沿、數據包絡分析以及近似全要素生產率法等一系列方法。本文借鑒陳一博和宛晶(2012)、李姝(2016)等的研究方法,根據表2所示投入產出關系,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法對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計。

表2 全要素生產率計算的投入產出指標體系
(3) 統計性描述。表3提供了一個全部企業、實驗組企業以及對照組企業相關變量的簡要統計。總體來看,三組分類中各變量的統計指標值相差不大。細化各具體指標的均值來看,實驗組的TFP、roe、profit、scale等指標值略高于其他兩種,而capiden以及age則稍低。從地區分布來看,三類企業沒有差異;從企業屬性來看,實驗組中屬于地方國有企業的數量相對較少,而行業分布來看均值明顯高于其他兩類。

表3 各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四、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1.匹配及匹配質量檢驗
根據PSM方法的基本思路,本研究選擇鄰近匹配法進行匹配,表4報告了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匹配結果。平均處理效應分別為0.069,對應的t值為3.11,通過顯著性檢驗。匹配結果中,在總共8604個觀察值中,對照組共有56個觀察值不在共同取值范圍內,而實驗組則全部處于共同取值范圍內。兩組中符合匹配結果的共有8548個觀察值。接下來對以上結果進行匹配平衡檢驗,發現匹配后大多數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小于10%,且對比匹配前大多數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均有不同程度的縮小,通過了匹配平衡檢驗。同時,為保證匹配方法選擇的可靠性,實踐中還嘗試了用卡尺匹配與核匹配進行檢驗。這兩種方法的匹配結果與鄰近匹配結果接近,進一步印證匹配方法的選擇是合適的。
2.基于倍差法的雙重穩健分析
(1) 全部樣本的初始檢驗。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企業跨國并購對企業的生產效率的影響如表5所示。方程(1)為基準檢驗,只對M&A、time以及兩者的交乘項進行估計,未添加任何控制變量。方程(2)

表4 平均處理效應檢驗

表5 全部樣本的初始檢驗
注:(1) 括號內為t值;(2) *、**和***分別表示10%、5%和1%顯著性水平。
在方程(1)基礎上,增加了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本密集度、企業利潤水平等控制變量,而方程(3)-(5)繼續在方程(2)基礎上增加了行業效應、地區效應、年份效應。回歸結果中,M&A·time是M&A和time的交互項,代表了跨國并購的全要素生產率效應,5個方程中,除了方程(2)以外,其他都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確實能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估計結果中,凈資產收益率、企業盈利水平、是否為民營企業、資本密集度以及企業規模均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正向影響。依次控制行業效應、年份效應和地區效應,對結果影響不大。只有在方程(4)和方程(5)中,企業年齡的系數為負,產生了負向影響,但是t值并不顯著。從估計系數來看,以企業就業人數表示的企業規模相對于企業的資本密集度影響程度比較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資本的跨區域流動會比勞動力流動更具靈活性,受到的地域、行業以及技術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因此,資本密集度對于企業全要素生產效率的提高影響更顯著。
(2) 滯后效應檢驗。正如前面所論證的,企業跨國并購對生產效率的提升會產生正面影響。然而這種影響的成效并不一定會馬上顯現,跨國并購對生產效率的提升往往會存在滯后效應。基于這樣的考慮,本研究做了時間滯后效應檢驗以觀測時間變化的動態影響。為實現這一目的,將式(5)擴展為:

(6)
其中,Mdum_tYear為企業跨國并購的年份虛擬變量,當企業處于跨國并購對外直接投資的第t期時,取值為1,否則為0。由于本研究中實驗組企業均從2011年開始進行識別,因此動態效應檢驗的滯后期為4期,估計結果見表6。其中,變量Mdum_tYear(t=0,1,2,3,4)分別代表在t不同取值情況下M&Ai·timet·dum_tYear的交乘項。
從包括了當期的共5期時間效應來看,分別控制行業、控制地區并加入相關控制變量,方程(1)至方程(4)各時間效應均顯著,說明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對外并購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應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區間內顯現出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近年來我國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走出去。從不同年度的回歸系數來看,滯后2期回歸系數相對于當期與滯后1期有顯著提高,是全部5個時期中最高的,說明跨國并購對生產效率的提高效應在并購后的第三年效果最明顯,第四年及第五年雖略有下降,但基本保持穩定。對此可能的解釋是,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后需要一定的時間融入東道國,適應東道國風俗習慣、法律環境以及政治環境。同時,那些出于追求學習效應的企業同樣會經歷一個“技術學習—消化理解—技術內化”的過程。因此,企業創新能力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效果需要一個時間周期。

表6 跨國并購的動態效應檢驗
注:(1) 括號內為t值;(2) *、**和***分別表示10%、5%和1%顯著性水平。
(3) 企業異質性效應的檢驗。我們還認為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是否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還受到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東道國發達程度、企業所處行業以及企業所處地區的影響。基于研究篇幅限制的考慮,本文通過控制行業和地區對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東道國發達程度等差異進行企業異質性效應的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回歸中Mdum_1att-Mdum_5att分別代表是否屬于地方國有企業、中央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集體企業的虛擬變量。Mdum_develop代表是否投資于發達國家的虛擬變量。

表7 跨國并購的企業異質性效應檢驗
注:(1)括號內為t值;(2)*、**和***分別表示10%、5%和1%顯著性水平。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呈現出企業所有制性質上的差異。當未對行業和地區進行控制以及未增加其他控制變量時,只有地方國有企業和中央國有企業顯著。當加入各類控制變量后,前四類企業顯著,并呈現正向影響,而集體企業卻呈現反向影響。從影響程度上看,民營企業的影響會明顯高于其他類型的企業。實驗組樣本中有近70%的企業為民營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民營企業正積極地參與到全球的第五次并購浪潮中,并成為其中一個重要主體。回歸結果還顯示,民營企業參與跨國并購確實可以實現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也與民營企業機制體制更加靈活、創新意識較高、追求技術溢出以及注重企業經營的交易費用等特質有關。而集體企業參與跨國并購的意愿并不強。從東道國發達程度上看,上市公司更加偏好于投資發達國家。這一回歸結果也佐證了為什么實驗組企業中計算機、通信和電子設備制造業企業所占企業總體比重較高。這些類型企業比傳統制造業企業更重視新產品開發與技術創新,具有較強的技術尋求特征。因此這些企業也會更多地選擇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盡可能地利用東道國的技術資源與研發環境,通過逆向溢出效應反饋于母公司。
五、 結論與政策啟示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是中國由經濟大國發展為經濟強國的核心環節之一。在以建設自由貿易區和“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為標志的新一輪開放背景下,中國企業通過對外投資積極尋求國外市場、自然資源與技術環境,以期實現企業競爭力的提升。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評估跨國并購對企業動態生產效率的影響。一般地,一個自然的做法是直接對比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生產效率的高低或者考察實驗組的生產效率是否比未進行跨國并購時更高。然而兩組企業可能存在初始條件的差異,同時也不可能觀察到實驗組的“反事實”。鑒于此,本文利用傾向評分匹配與倍差法相結合的估計方法,實證檢驗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走出去”進行跨國并購的動態生產率效應。
本文得到的主要結論及政策啟示有:第一,企業以跨國并購的方式“走出去”會顯著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中國企業以產業國際轉移的方式“走出去”會在一定程度上消化和緩解國內日益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同時,以研發平臺為目標的“走出去”在當前成為常態,這將有助于進一步構筑中國的全球生產網絡和全球供應鏈。借助于“一帶一路”戰略平臺,需要有更細化的“政策紅利”的釋放。這種“政策紅利”需要進一步覆蓋包括發展定位、產業選擇、區位抉擇、合作方式等方面。第二,從企業異質性角度觀察,民營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效應會相對高于其他類型企業,集體企業對外投資意愿則不強。然而民營上市公司同時也會更多地面臨審批程序較繁瑣、境外并購貸款安排困難、對外投資的法律障礙等現實難題。從企業層面上看,由于跨國并購往往涉及龐大的資金投入,為了順利完成并購活動,并購企業一定要制定嚴密的并購交易方案,立足于企業自身狀況,選擇對自身最為有利的融資方式,充分考慮并購行為對未來生產經營的影響,防范可能發生的資金鏈斷裂。政府層面上除了減化程序,提供一攬子稅收優惠外,還應當給予“走出去”企業在境外法律咨詢、人員培訓、融資等方面的服務,促進服務平臺建設從供應鏈角度延伸到服務業。第三,上市公司投資目的地更多地選擇發達國家,體現了國內企業對于提升技術水平與創新能力的渴求。為此,也需要加快制定和出臺對重點行業和重點領域的支持政策,對不同類型東道國采取不同投資策略與方向。包括對高新技術產業鼓勵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利用全球智力資源,加強新一代技術研發;在市場需求大、資源條件好的國家,加強資源開發和產業投資;在勞動力資源豐富、生產成本低、靠近目標市場的國家投資建設勞動密集型項目,帶動相關行業出口等。
1. Bonaglia, F., A. Goldstein,and J. A. Mathews.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Emerging Markets Multinationals:The Case of the White Goods Sector.JournalofWorldBusiness, 2007,42(4):369-383.
2. Buckley, P. J., L. Clegg, A. R. Cross, X. Liu, H. Voss, and P. Zheng.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 2007, 38(4):499-518.
3. Heckman,J.J., H. Ichimura, and P. E. Todd.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 1997, 64(3): 605-654.
4. Heckman, J.J., H. Ichimura, and P. Todd.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98,65(24): 261-294.
5. John, H., K. Changsu, and P. Donghyun. Old Wine in New Bottles:A Comparison of Emerging Market TNCs Today and Developed Country TNCs Thirty Years Ago.SLPTMDWorkingPaperSeries,2010, No. 011.
6. Lecraw, D. Direct Investment by Firms from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OxfordEconomicPapers, New Series, 1977,29(3): 442-457.
7. Lecraw, D. J.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by Indonesian Firms:Motivation and Effects.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 1993,24(3):589-600.
8. Li, J., and F. K. Yao. The Role of Reference Group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ecisions by Firm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Management, 2010,16(2): 143-153.
9. Sauvant, K., W. A. Maschek, and G. McAllist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Recession, and Challenges Ahead.OECDGlobalForumonInternationalInvestmentOECDInvestmentDivision, 2009.
10.Wells, L. T.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ITPress, 1983.
11. Luo, Yadong, Qiuzhi Xue, and Binjie Han.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Experience from China.Journalofworldbusiness, 2010,23(2):219-232.
12. 陳一博、宛晶:《創業板上市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數法的實證研究》,《當代經濟科學》2012年第4期。
13. 胡麥秀、薛求知:《技術-環境壁壘與企業的最佳投資模式選擇——綠地投資還是跨國并購》,《經濟管理》2007年第23期。
14. 李善民、李昶:《跨國并購還是綠地投資?——FDI 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經濟研究》2013年第12期。
15. 李姝:《基于Malmquist 指數法的火電上市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來源分析》,《宏觀經濟研究》2016年第4期。
16. 林莎、雷井生、楊航:《中國企業綠地投資與跨國并購的差異性研究——來自223家國內企業的經驗分析》,《管理評論》2014年第9期。
17. 毛其淋、許家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如何影響了企業加成率:事實與機制》,《世界經濟》2016年第6期。
18. 皮建才、李童、陳旭陽:《中國民營企業如何“走出去”:逆向并購還是綠地投資》,《國際貿易問題》2016年第5期。
19. 喬晶、胡兵:《對外直接投資如何影響出口——基于制造業企業的匹配倍差檢驗》,《國際貿易問題》2015年第4期。
20. 武銳、黃方亮:《跨境進入的模式選擇:跨國并購、綠地投資還是合資公司》,《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21. 薛安偉:《跨國并購提高企業績效了嗎——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經濟學家》2017年第6期。
22. 楊平麗、曹子瑛:《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利潤率的影響——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23. 楊亞平、吳祝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溢出效應——基于企業異質性與微觀面板數據的考察》,《產經評論》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