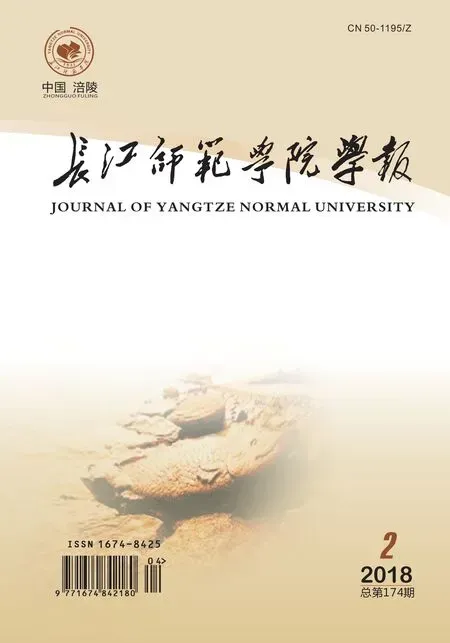孤獨的映襯與共謀的反諷
——論不可靠敘述的反諷效果
陳志華
(江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引言
作為20世紀一種特有的文學觀念,不可靠敘述已經廣泛滲透到整個文學活動當中。不獨作家的創作觀念、文本表征展示出不可靠敘述蔚為大觀的局面,讀者閱讀也深受不可靠敘述觀念的影響。人們之所以會對不可靠敘述產生濃厚的情趣,鐘情于天真敘述、白癡敘述等不可靠敘述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不可靠敘述所引發的獨特的藝術效果,而反諷效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種。
作為西方文論中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反諷(irony)在我國有“諷刺”“滑稽”“譏諷”“暗諷”等多種譯法,可見這一概念內涵之豐富,時下似乎已基本統譯為“反諷”。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修辭方法,反諷自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在很長一段時期作為微觀修辭的技巧被人們運用于文本修辭的狹義研究中,比如,新批評派就在修辭層面討論反諷。隨著對反諷理論探討的深入,人們意識到,反諷能形成復雜的審美意味和豐富的主題意蘊,決非簡單的修辭技巧。反諷已經超越出了微觀修辭技巧的層面,日益被當作一種評價作品的標準和美學尺度,人們正傾向于將它視為一種超技巧的范疇來看。米克在分析了F.施萊格爾、海涅等人的觀點以后,指出:反諷“也許在于獲得全面而和諧的見解,即在于標明人們對生活的復雜性或價值觀的相對性有所認識,在于傳達比直接陳述更廣博、更豐富的意蘊,在于避免過分的簡單化、過強的說教性,在于說明人們學會了以展示其潛在破壞性的對立面的方式,而獲致某種見解的正確方法”[1]。這顯然是在效果層面談論反諷。
由于反諷構成要素的復雜性、反諷形式的多樣性、反諷發展的未定性,對反諷這一概念的界定,就成為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一般將它理解為表里不一,尤指字面意思與深層真意的不一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因而,反諷效果一般就表現為,作者將自己的態度或實施的真相暗含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述中,我們只能透過表象,領會其深在的含義,其情形有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確實比直接宣白更有力量、更具意味。我們將從不可靠敘述的角度切入,分析此種文學觀念所導引的敘述策略會引發怎樣的反諷效果。
二、審美與倫理:不可靠敘述反諷效果的雙重審視
“當敘述者的講述或行動與作品的思想規范(也即隱含作者的思想規范)相一致時,我將這類敘述者稱為可靠的敘述者,反之則稱為不可靠的敘述者。”[2]158布斯這一經典界定對不可靠敘述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不可靠敘述進入人們的理論視野,對于其效果的探討也便成為備受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那么不可靠敘述會生成何種獨特的效果?作為“不可靠敘述”概念的提出者,布斯對其效果進行過較為充分的探討,主要從審美效果和倫理效果兩方面進行闡述。
審美效果,是指具體文本因其潛在的藝術價值、美學質素在閱讀中所生成的效果。因而,探討藝術效果,有別于對文本的道德、認知、教育等效果的分析,而是基于藝術本性,從審美的角度去考察效果。藝術的效果或效應,是實用批評最為關注的問題。在實用批評看來,作品的目的就在于對讀者產生影響,無論這種影響是審美的、道德的、情感的還是認知的。實用批評傾向于以是否成功地達到上述目的來判斷作品的價值。我們暫不評述其整體理論構架的得失,就其強調藝術作品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和效果之間的血肉聯系來看,無疑是正確的。布斯接著以《喧嘩與騷動》中“杰生的敘述”為例,指出,“盡管根據小說中敘述的事件,我們理解杰生邪惡的道德世界的思路,在許多方面已經清晰,但實質上,它的形成還在于我們自己與作者之間達成的隱蔽而帶有嘲諷性質的默契”。這種默契的形成并不需要作者任何直接介入性的提示、指引。不可靠敘述者富于幽默的、或不光彩的、或滑稽可笑的、或不正當的沖動等行為舉止,將會使文本整體呈現作者寄寓其中的反諷意味。“當我們與錯誤從未被直接指出、很少令人同情的主人公進行交流時,也發現我們的反諷快感增強了。”[2]306正是在這種秘密的交流中,讀者與作者所共享的價值規范與敘述者所秉持的價值規范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形成對于敘述者的反諷。相反,任何對于敘述者的評論將會大大降低文本的反諷意味。布斯也意識到,有缺陷的敘述者并非都是文本的反諷指向所在。布斯以《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為樣本,展示了不可靠敘述反諷效果的另一類型:通過有缺陷的敘述者的不可靠敘述,將諷刺的筆觸伸向站在敘述者對立面的其他人物及相應的社會情境。對于“聲稱要自然而然地變邪惡”的敘述者哈克,作者“沉默地”表示著對他的美德的贊揚。哈克的不可靠敘述成為一面鏡子,折射出其所處社會的罪惡,正是因為受了當時種族歧視思想的毒害,哈克才會把自己幫助黑奴吉姆的行為視為不可饒恕的罪過,文本強烈的反諷意味由此生成。
作為不可靠敘述的命名者,布斯充分肯定了它在生發獨特的藝術效果方面的出色表現,但不可靠敘述所可能帶來的一系列道德問題,讓布斯憂心忡忡。不可靠敘述不僅造成敘事文本情節上的含混,蓄意混淆讀者對小說基本真實的認識,而且使讀者在閱讀、接受文本時產生極大的困惑。相對可靠敘述清晰而確定的倫理表達,不可靠敘述文本中的倫理關系顯得復雜而多樣,含混而朦朧。不可靠敘述使得從作者、文本到讀者的整個文學活動呈現出豐富的倫理交流場域。這種復雜而生動的倫理交流關系,豐富了文本的藝術效果和讀者的審美感受,也對讀者的倫理判斷構成極大的挑戰。因而,對于不可靠敘述倫理效果的考察就成為布斯的一個重要的理論興奮點。即便在對藝術效果的分析中,布斯也時常隱約提到,不可靠敘述者可能對讀者產生的倫理觀念上的誤導。在“非人格化敘述的道德與技巧”一章中,布斯干脆把全部的重心都轉向他極為關注的道德問題。“非人格化敘述已經引發了許多道德困難,以至于我們無法將道德問題視為與技巧無關的東西而束之高閣”,原因在于,“內心觀察甚至可以為最邪惡的人物贏得同情”[2]378。而不可靠敘述恰是最能展現內心觀察生動性的一種敘述方式,試想,當一位不可靠敘述者占據著話語權,不斷向讀者展示他內心世界的沖突、困惑時,讀者如何能不受其影響?當這位不可靠敘述者又是一位懂得修辭藝術的自覺敘述者時,其感染力豈不更為強烈?盡管我們不能要求文學為生活提供道德指引,然而,當某些作品確實以不可靠敘述等出色的技巧,挑戰了社會的道德底線,甚至可能引發類似的道德實踐行為,我們還能無視敘事的道德安全問題嗎?對于不可靠敘述反諷效果的探討可以從多個角度進入,我們主要依據上述對不可靠敘述審美與倫理這雙重觀照,以文本的反諷指向為劃分標準,區分了指向文本中人物和社會情境的反諷和指向敘述者的反諷這兩種反諷效果類型。
三、孤獨的映襯者:人性探索與社會批判
指向文本中人物和社會情境的反諷,即隱含作者通過不可靠敘述者的敘述,對虛構世界中的人物和社會情境進行反諷。換句話說,敘述者的不可靠成為隱含作者對文本中人物和社會情境進行反諷的方式。如此,不可靠敘述者往往秉持著與所處社會環境中大多數人不同的價值觀,成為文本世界中一個孤獨的個體或孤獨小群體中的一員,以不可靠敘述者坎坷的生活歷程折射出其所處社會環境中存在的諸種問題,實現對于人性的深度探索和社會問題的嚴肅批判。從存在認知缺陷的人物視角進行敘述,是達成此類反諷效果最常用的手段。在具體文本實踐中常常分為兩種表現方式:一種是直接采用兒童、白癡等有缺陷的人物進行敘述,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狂人的敘述)、莫言的《檀香刑》(趙小甲的敘述)、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海明威的《我的老爸》等等。這類敘述者往往能對事件的表象作出較為客觀的描述,卻無法形成正確的判斷,他們敘述的不可靠構成對成人、常人所處世界的強烈反諷。由于兒童單純天真的本性,依靠他們的生命直覺認識世界,更能接近世界的原初形態,也就是說,不夠世故的孩子承擔敘述者的角色,反而能因童心未染塵俗從而對事件的報道更加可靠。隱含作者正是通過這些兒童或者白癡的敘述,見出處于對立面的虛構世界的丑惡、荒誕,從而生發出強烈的反諷意味。
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第一部分以白癡班吉為敘述者。之所以通過白癡講述家族歷史,那是因為“覺得這個故事由一個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人說出來,可以更加動人”[3]。福克納這一解釋很好地表達了白癡敘述者班吉可靠性與不可靠性的膠著狀態。“只知其然”表明班吉的敘述盡管由于意識流的手法,特別是多層次的閃回而顯得極為混亂,但從他的只言片語中卻能傳遞出可靠的敘事信息。“不能知其所以然”則見出了班吉在感知、評價軸上的不可靠性,無法對自己所經歷的事情作出可靠而穩妥的反應。這樣,白癡班吉就成為一面鏡子,周圍的人在他面前展現出或善或惡的人性本相,白癡眼中毫無意義的所見事物經過白癡眼光的聚焦與客觀呈現,形成了別具特色的空間畫面與意義組合。凱蒂在《喧嘩與騷動》中反復被提到,在杰生、昆丁的敘述中,凱蒂是一位充滿欲望、自甘墮落的女性。那么,班吉眼中的凱蒂呢?班吉的智力缺陷使他不會產生任何修辭性的敘述行為,他只是憑著自身的感受,仔細地記錄了凱蒂對他的關愛,也記錄了以下場景:接吻之后用香皂洗嘴、查理面前她的興奮、從婚禮上跑開,等等。杰生和昆丁的敘述,由于各自的原因,有意識地放大了凱蒂的缺點,忽略其性格中美好的一面。班吉的敘述無疑有效地顛覆了杰生、昆丁對凱蒂形象的過度歪曲,但同時又傳達出凱蒂的墮落。盡管他無法對周圍的事件形成正確的判斷,然而,隱含作者正是借班吉的眼光,表達對以杰生、昆丁為代表的沒落的康普生家族的反諷。更深一步看,康普生家族的敗落實際上是美國南方歷史性變化的一個側面,這樣,隱含作者的反諷指向就擴大到了當時整個社會情境,既諷刺了南方舊制度的破敗,也包含有對杰生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價值標準的批判。
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兒童視角運用的典型文本。敘述者少年哈克講述了幫助黑奴吉姆逃亡的故事。在第三章中,我們已經分析過哈克敘述的不可靠性。哈克正是因為受了種族歧視的傳統思想的毒害,才會覺得自己幫助一個黑奴逃脫他的主人,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死后要下地獄的。哈克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混亂反映了美國當時種族歧視的深重影響,因而,文本的反諷意味指向國王和公爵等人物及文本所呈現的當時美國的社會情境。作者對哈克美德的贊揚,就是對哈克所處的社會情境的反諷,尤其是對于美國種族歧視制度的反諷和憎惡。
另一種是兒童、白癡等有缺陷的人物并不作為敘述者,而只是從他們的視角進行敘述,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等等。這類文本從兒童、白癡的眼光進行限知敘事,好比一面“鏡子”,能客觀反射事物的原貌和人物的外在行為,即能對事件作出較為可靠的報道。借助于有缺陷的認知視角,作家實現的是對這些有缺陷人物所處的虛構世界的客觀冷峻的呈示,批判和反諷的意味也就隱匿在敘事之中。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中敘述者少年霍爾頓的敘述帶著明顯的孩子氣,鮮明呈現出青春期少年成熟與幼稚混雜的心理特征,如:“我那時十六歲,現在十七歲,可有時候我的行為舉止卻像十三歲。說來確實很可笑,因為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頭上還有白頭發。我真有白頭發。在頭上的一邊——右邊,有千百萬根白頭發,從小就有。可我有時候一舉一動,卻像還只有十二歲。誰都這樣說,尤其是我父親。這么說有點兒不對,可并不完全對。我壓根兒就不理這個碴兒,除非有時候人們說我,要我老成些,我才冒火來。有時候我的一舉一動要比我的年齡老得多——確是這樣——可人們卻視而不見。他們是什么也看不見的。”這段不可靠敘述突出的表現為他對自己成長的矛盾看法:他一會兒覺得自己的行為舉止還像十二三歲,對于別人讓他老成些的說法頗為惱火;一會兒,他又認為自己的舉動顯得成熟得多,進而埋怨人們對此視而不見。在小說的其他段落,當別人認為他的年齡小時,他居然一次一次扒拉出自己的白頭發以證明自己的成熟,而此時卻又說白頭發從小就有,言下之意,白發與年齡的成長毫無關系。敘述的不可靠性就在少年霍爾頓頗顯幼稚的敘述聲音中清晰的呈現出來。整個文本充滿著這種青春期少年所特有的敘述聲音,真實地展現了處于人生轉折點的少年成長的迷茫和彷徨,也體現出他對于社會上那些中產階級之間種種無趣規矩的討厭以及人與人之間虛偽的厭惡。
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描繪的是多層通奸的故事,敘述這一切的任務完全是通過孩子“梅西”的所見所聞來完成的。梅西既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同時對這一切又毫不理解。“如今她看得出媽媽這次婚姻很美滿,她也總算有望開開心了——這個不諳世事的小女孩惟一的心愿是巴望好事,有朝一日能盡情地玩耍嬉戲。”梅西觀察得很準確,可靠地展現出她周圍發生的事件。然而,以孩子的認知力,梅西顯然無法對事件作出可靠的判斷。實際上,梅西的母親伊達只是在趕赴社交聚會途中順便進來看看她。盡管大人們只顧尋歡作樂,把她禁閉在枯燥無味的學堂里,梅西對媽媽依然深信不疑,滿懷希望期待著“有朝一日盡情玩耍嬉戲”。然而,讀者對此并不抱幻想,深知孩子這小小的心愿是無法實現的。孩子的信賴與大人們的自私、虛偽形成鮮明對比,敘述的不可靠性恰恰表現出隱含作者對于伊達為代表的成人世界的強烈反諷。
四、遭諷的敘述者:作者與讀者的共謀
指向敘述者的反諷是指文本的不可靠敘述體現出隱含作者對于敘述者的反諷。將敘述者作為反諷的對象是不可靠敘述中最為常見的反諷表現方式。從文學發展史看,反諷在可靠敘述文本中早已出現,比如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記》、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等都是極富反諷意味的文本。可靠敘述文本中的反諷從來都是指向虛構世界中的人物或者社會情境,并不構成對敘述者的反諷。換言之,敘述者與作者(隱含作者)一樣,只是反諷意味的發出者,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菲爾丁的《湯姆·瓊斯》等。在傳統的可靠敘述中,敘述者幾乎都是作者理想化人格的具現,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基本是同一的,占據著美德、智慧或學識的制高點。這種敘述權威性的樹立,使讀者對于敘述者深信不疑,總是依據敘述者的認知、判斷去感受、理解故事,閱讀的結果往往是達成與敘述者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敘述者不可能成為反諷的對象,也就是說,只有故事中的人物才會成為反諷的對象。
在不可靠敘述文本中,敘述者不再擁有這種特權。相反,不可靠敘述者往往都是文本的反諷指向所在,比如福克納《喧嘩與騷動》中杰生的偏執和殘忍、亨利·詹姆斯《說謊者》中萊昂的虛偽等等。布斯從交流形式出發分析反諷效果。“反諷部分地總是一種既包容而又排斥的技巧,那些被包容在內的,又剛好具有理解反諷的必備知識的人,只能從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感受中獲得小部分的快感。在我們參與其中的反諷中,敘述者自己就是嘲諷的對象。作者與讀者背著敘述者秘密地達成共謀,商定標準。正是根據這個標準,發現敘述者是有缺陷的。”[2]300也就是說,不可靠敘述者的缺陷使得讀者與作者在共享與敘述者相異的價值規范時,形成文本的反諷效果。在此,盡管布斯沒有進一步闡發,但他還是意識到了不可靠敘述反諷效果的獨特之處:敘述者已無力承擔反諷效果的發出者。敘述者的缺陷既可能是自身成為反諷指向的原因,也可能是讀者藉此讀解出對其他人物或社會情境反諷意味的路徑。在可靠敘述中,敘述者所處的優越位置使其只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成為反諷的發出者,從來不會陷入如此尷尬的境地。盡管不可靠敘述者未必都成為被反諷的對象(比如天真敘述中,反諷多是指向與兒童處于對立面的人物或社會情境),然而,不可靠敘述者顯然已不再成為反諷的發出者。20世紀以來,許多作家不滿于敘述者的權威性,不斷消解其敘述的可靠性。作為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全知敘述”遭到了作家普遍的厭棄,作家放棄了說教者的角色,消失在作品中,也即昆德拉所說的作家放棄了“公共人”的角色。第一人稱敘述、第三人稱“意識中心”敘述等各種限知敘述形式紛紛涌現。限知敘述往往是敘述者作為旁觀者或者親歷者對于故事的講述,里蒙·凱南曾將敘述者親身卷入事件列為不可靠敘述的主要根源[4],敘述者的可靠性很容易引起讀者的質疑。而且,根據布斯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那些最緘默的敘述者,一旦把自己以‘我’來提及時……他也就被戲劇化了……在此類作品中,敘述者與創造他的隱含作者常常根本不同”[2]152。一般而言,限知敘述多為同故事敘述,往往加深了敘述者的戲劇化程度。戲劇化的敘述者往往和他所講述的其他人物一樣活靈活現,讀者可以根據對其品質的判斷來判定他所講述的事是否可信。因此,無論采用何種敘述人稱,敘述者的可靠性都越來越容易受到質疑。這些敘述者往往秉持與隱含作者截然相反的價值規范,從而被置于反諷的境地。既然是不可靠敘述文本,敘述話語的不一致必然會造成敘事信息的含混不清,文本或多或少都會呈現含混特質;由于敘述的不可靠,也必然會出現敘述者與作者(隱含作者)之間在事實/事件、知識/感知、價值/判斷等軸線上的不一致,作者(隱含作者)對于敘述者的否定也經常帶有善意的或惡意的、強的或弱的反諷意味。
敘述者的不可靠性加劇了文本的反諷意味。可靠敘述文本中的敘述者接近于作者(隱含作者)的趣味、判斷、倫理觀念,其敘述總能產生一種強烈的導向性,讀者往往只要緊隨敘述者就能獲得對虛構世界的認知和判斷。由于有敘述者的引導,盡管這種引導總是以間接方式表現出來,這些文本的反諷效果比較容易被讀者所識別和領會。而在不可靠敘述文本中,作者(隱含作者)只能在敘述者身后與讀者交流,敘述者的不可靠性經常會干擾讀者對事件的認識和判斷,這種無聲的交流顯然對讀者更具挑戰性。也就是說,不可靠敘述者對于讀者推斷力的要求,顯然比可靠敘述者所要求的更為強烈。可見,這種基于不可靠敘述所產生的反諷效果顯然更為復雜。不可靠敘述的反諷效果,有助于作者含蓄有力地體現自己的修辭目的。當敘述者的不可靠性越隱蔽,讀者最終對于整個文本反諷意味的體會也會越強烈。
指向敘述者的反諷是指文本的不可靠敘述體現出隱含作者對于敘述者的反諷。將敘述者作為反諷的對象是不可靠敘述中最為常見的反諷表現方式。根據敘述者不可靠性的展露程度,我們可以區分兩種指向敘述者的反諷類型:顯在型反諷和隱在型反諷。
顯在型反諷,一般指隱含作者直接傳達出對于不可靠敘述者的反諷意味。這一反諷類型有著清晰的文本標識,讀者很容易與隱含作者產生“共謀”關系,從而讀解出對于敘述者的反諷意味。這類敘述者一般有以下特征:敘述者被賦予“偏執狂”“惡棍”“罪犯”等非常態型人格特征;敘述語調或激烈、偏執,或無知、愚昧;敘述內容清晰地展現出迥異于隱含作者和讀者的價值取向。由此,讀者一進入文本,就會自覺對其敘述可靠性產生警惕,體會出隱含作者對這類敘述者的反諷指向。《喧嘩與騷動》中杰生的敘述就是個極為典型的例子。福克納說過,“對我來說,杰生純粹是惡的代表。依我看,從我的想象里產生出來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惡的一個”[5]3。小昆丁是杰生的妹妹凱蒂寄養在母親家中的私生女,康普生太太的冷漠和杰生的殘酷讓小昆丁得不到任何溫情,由于小昆丁不服從杰生的命令,杰生居然拿出皮帶抽她,老仆人迪爾西不畏懼杰生的仇視與世俗觀念的影響,勇敢地保護小昆丁,杰生敘述如下:“她抱住了我的胳膊。這時,皮帶讓我抽出來了,我一使勁把她甩了開去。她跌跌撞撞地倒在了桌子上。她太老了,除了還能艱難地走動走動,別的什么也干不了。不過這倒也沒什么,反正廚房里需要有個人把年輕人吃剩的東西消滅掉”[5]201。對于為康普生家族忠心耿耿服務了一生的迪爾西,杰生居然“一使勁把她甩了開去”。年邁的迪爾西成天為康普生家族勞作,他卻說“除了還能艱難地走動走動,別的什么也干不了”。杰生自私、殘酷和陰冷的本性在這段敘述語流中鮮明地表現出來。隱含作者在杰生的自我表白與辯解寄寓了強烈的反諷意味。顯在型反諷多為不可靠的同故事敘述者。敘述者常常由于價值體系的混亂和錯誤而成為反諷對象。托爾斯泰的《克萊采奏鳴曲》、伊恩·麥克尤萬的《他們到了死了》、馬丁·埃米斯的《金錢》、朱利安·巴恩斯德《好好商量》等文本都屬于這一類型。
隱在型反諷,則是指隱含作者隱蔽地展示出對于不可靠敘述者的反諷意味。與顯在型反諷的清晰、直白不同,隱在型反諷的辨識對于讀者的文本理解能力要求更高,讀者需要在細致的文本閱讀中才能體會出來對這類敘述者的反諷意味。這類不可靠的同故事敘述者常具有以下共性:一般呈現出常態型人格特征,有的甚至從表面上表現出誠實、真摯、理性等優秀的個人品質;敘述語調通常比較理性、和緩;敘述內容體現出高超的修辭藝術,“超越了各種旁觀者與敘述代言人之間的區別,是意識到自己是作家的自覺敘述者”[2]155,敘述態度真誠,甚至表現出自我懺悔的傾向,讓讀者稍不留意就為其敘述所迷惑,而認同其所傳達的為隱含作者所否定的價值立場。亨利·詹姆斯的《阿斯彭文稿》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敘述者是故事的主人公,一位美國評論家,他講述了自己如何為獲得大詩人阿斯彭的文稿而費盡心機,最后卻功敗垂成的故事。與杰生不同,敘述者一直將自己裝扮成一位具有紳士風度、非常文雅,對詩人阿斯彭充滿敬意的追隨者。表面上看來,如他所敘述的,“我一直盡可能親切和藹”,這位敘述者確實盡可能地展現出他的紳士風度。他對于阿斯彭老情人的慷慨大方、對于蒂娜示好,甚至帶其出去游玩……然而,當我們意識到這一切都是因其不可告人的企圖而采取的手段:慷慨大方是為了接近文稿創造條件;對蒂娜示好是為了利用她的癡情得到文稿,甚至將自己不擇手段獲取文稿的行為美化為對于詩人阿斯彭的熱愛所致,敘述者對于其卑劣意圖的掩蓋都昭然若揭。盡管敘述者一直占據著話語中心,不斷為自己辯護,甚至,偶爾也會對自己利用蒂娜感情的行為進行反省,表現出一定的自審意識,“我有氣無力地想到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錯誤,無意之中,但終究是令人遺憾地愚弄了人家的情感。然而,我并沒給她任何理由——很明顯,我并沒有”[6],但獲取文稿的狂熱追求使敘述者的道德感發生偏差,從這段反省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中更多具有為自己的行為尋求辯護的色彩,這種自我辯解的敘述行為貫穿文本始終,讀解出作者對這位敘述者的反諷需要對整個文本敘述的不可靠性仔細加以甄別。
五、結語
隱在型反諷不僅包括難以辨識不可靠性的同故事敘述者,而且還包括全知敘述者。全知型敘述是一種非常傳統的敘述模式。全知敘述者如上帝般盤踞在文本上空,可以從任何角度、任何時空進行敘述,既對事件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將故事娓娓道來,又可任意透視人物的心理,傳達人物豐富的情感體驗。對于文本的這種全面掌控能力很容易樹立全知敘述者的權威性。全知敘述者在文本中有兩種表現方式:戲劇化和非戲劇化。非戲劇化是指全知敘述者不訴諸于任何人稱講述故事,而戲劇化則是指全知敘述者通過“我”或“我們”使自身在文本中顯形,直接對故事置評。一般而言,無論是否被戲劇化,全知型敘述者都是比較可靠的。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司湯達的《紅與黑》、雨果的《悲慘世界》等都屬于可靠敘述之列。而在有些文本中,無論是否被戲劇化,全知敘述者也會出現不可靠的情況,而且其不可靠性往往比較隱蔽。在全知敘述者將自己或多或少地“個性化”或人物化時,全知敘述者的可靠性就會削弱。也就是說,敘述者在諷刺、挖苦人物的時候,自己也成為了隱含作者的反諷對象,從而形成了雙重反諷:敘述者對于人物的反諷,隱含作者對敘述者的反諷。
不可靠敘述的反諷效果主要表現為指向敘述者的反諷和指向文本中人物和社會情境的反諷。這兩種反諷效果在文本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實際上,很多文本都呈現出反諷雙重指向性。不可靠敘述的反諷效果強化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交流,豐富了反諷的審美效果,極大地激發了讀者對于文本積極、主動的思考,呼喚讀者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建構中來。
參考文獻:
[1]D·C·米克.論反諷[M].周發祥,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2:35.
[2]BOOTH W C.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3]福克納.福克納評論集·福克納談創作[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262.
[4]SHLOMITH R K.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M].Florence,KY,USA:Routledge,1983:100.
[5]福克納.喧嘩與騷動·譯本序[M].李文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6]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M].主萬,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164.